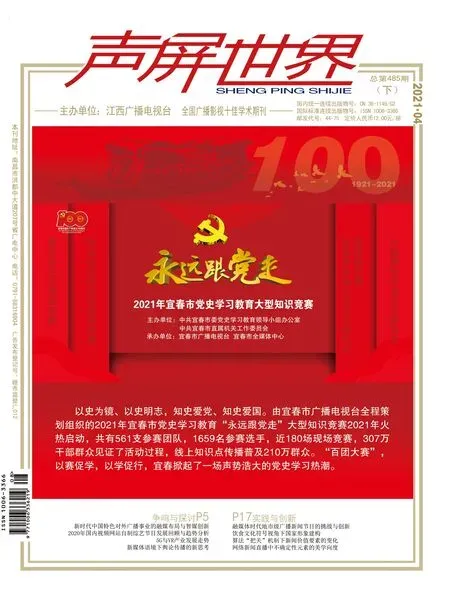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的叙事分析
2021-11-12陈银乔
□ 陈银乔
在应试教育模式下,一些分数低、成绩差的孩子往往被贴上“差”“懒”等标签,让孩子心灵受到创伤,也让家长痛苦不堪,实际上,有些孩子并非不努力,而是患上了阅读障碍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1年1月播出的系列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用《校校》《群晓》《若汐》三部纪录片的方式分别讲述了校校、群晓、若汐三个罹患“阅读障碍”孩子的学习困境及家长的努力、矛盾和调适,并在“爱”和“接纳”中让孩子获得成长。该片播出后,引发学生家长的热议。本文将从叙事学的三个要素——故事、叙述和话语对《我不是笨小孩》展开分析,探究其影像叙事艺术。
《我不是笨小孩》的“故事”分析
第一集的校校是一个活泼幽默又善于隐藏情绪的孩子:他在做作业时多次对镜头做鬼脸、上课打伞……而在面对妈妈严苛的“每日运动打卡”计划时,他一边默默承受一边说“妈,其实你做错了”;面对同学“垃圾”、竖中指的嘲笑,他选择独自隐忍,只有在姥姥家独自面对着摄像机时,他才敢大胆地说“我只有在你这才敢嘀咕”。与顽皮的校校不同,《我不是笨小孩》第二部的主人公群晓展现出了一个要强自律的形象:为了突破阅读障碍,群晓多次在高铁、吉他课等嘈杂的环境中专注地看书,用18-30遍默写来记生词,还把学霸同桌鲁丹阳视作“假想敌”。《我不是笨小孩》第三部的主人公是一个女孩——若汐,在纪录片中她表现得文静、敏感而要强:面对老师公开的批评和威胁“开除”,一年级的若汐流泪难过了好几天;每晚的家庭作业也在消磨她和父母的耐心,但历经指责的若汐并未放弃,最后若汐期末考成绩取得了进步,不擅长的芭蕾舞也能做出完整的高难度动作。
在纪录片中,不同孩子的父母展现出了不同的教育方式,但价值内核——爱和接纳是不变的:校校的父亲表现得随和、乐观,对镜头进行独白时说“还不如让他去痛痛快快地玩一玩”;校校妈妈的性格则雷厉风行,为校校的教育问题曾险些与丈夫离婚。这样一个家庭在孩子阅读障碍的诱因下,必然会充满矛盾和冲突,而这也正是《我不是笨小孩》第一部的感染力之所在。群晓的父母表现出了十分耐心、宽容的品质,爸爸说“不在孩子的位置理解不了他的痛苦”,妈妈甚至放弃工作只身从北京到山西为儿子陪读;若汐的父母对女儿的病情表现出了积极、勇敢直面的态度,他们并未因成绩优异的姐姐而忽略了妹妹,妈妈生病住院爸爸就辞职在家一直陪伴着若汐的功课。
事件分析。事件也就是叙述的客体,它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会导致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我不是笨小孩》通过众多的事件构建讲述了校校、群晓、若汐三个阅读障碍孩子的故事。
《校校》讲述了男孩校校的故事:他课堂纪律差、考试分数低,妈妈和姥姥轮流辅导他功课时却一一受阻;校校成绩差的原因从最初的懒惰到多动症,最后才被确诊为阅读障碍;为了治疗校校的病情,妈妈为他制定了严格的健身打卡计划,却收效甚微;每天耗到深夜的功课在一点一滴消磨妈妈的耐心,但妈妈仍经常组织集体活动来帮助校校融入社会群体;面对其他家长对校校第一次听写全对的鼓励,坚强的妈妈在镜头前也不禁哽咽;由于阅读障碍所带来的长期的挫败感,校校开始出现了厌学情绪,在军事训练营释放压力;教授建议妈妈要“温柔而坚定”,但妈妈很快在辅导校校作业时又一次发飙。孩子与父母同阅读障碍的斗争漫长而艰苦,但在结尾妈妈也相信校校的这种“抗争精神”能让他在将来免于成为生活的奴隶。
《群晓》讲述了另一个男孩群晓的故事:一年级时的群晓由于阅读障碍饱受周围同学的欺凌,父母不得不带他转学,并且妈妈辞职陪读;在新的环境中,老师不以成绩为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多方面地培养孩子阅读、国画、吉他等能力;更难得的是,老师们还专门为群晓召开了教学研讨会,调研针对孩子的教学思路;群晓因为写作业的时间问题与同学发生了争吵,后在武老师的沟通下顺利解决;在放假回家的日子,爸爸还带群晓去滑雪;当他的阅读能力和书写水平越来越好之时,学校的投资方突然宣布撤资,学校不得不就地解散,这最终导致11岁的群晓独自一人远赴开封游学。纪录片的最后,努力的群晓已经掌握了不逊于同龄人的阅读能力,没有父母参加的期末汇演也昭示着他的求学路正独立地走上正轨。
《若汐》讲述的是关于女孩若汐的故事:她的叙事始于“一年级时被老师恐吓开除”,在老师和同学们另类的眼光下,父母也不得不带若汐转学;接着引入成绩十分优异的若汐姐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氛围;即使学习芭蕾舞,她也因为大脑的缺陷难以掌握精细的动作;与校校的情况相同,每晚若汐也因功课和父母“对峙”到深夜;后来妈妈被确诊为需要住院治疗的“皮肌炎”,爸爸于是不得不辞职在家照顾若汐的学习;在日复一日地努力下,若汐的成绩终于从不及格进步导及格再到70多分,还获得了妈妈颁发的奖状。《我不是笨小孩》第三部中若汐的从分数从低到高,性格从缺乏自信到乐观阳光,展现的就是一个女孩及其家庭同阅读障碍作斗争并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历程。
场景分析。事件的发生离不开时间、地点、和状态,即事件都是在一定的场景中发生的。时间序列或时间的先后顺序是事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是安排事件顺序的依据;地点是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是强调素材的意义或者是确定其意义的主要方式。在《我不是笨小孩》中,最突出的场景要素即为地点。
《我不是笨小孩》主要在学校与家庭两个地点间来回切换进行叙事,并辅以少部分户外的场景。在学校场景中,三集纪录片都强调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与人相处过程中遇到的隔阂。在家庭场景中,校校家庭和若汐家庭较多地渲染了父母辅导孩子功课时的艰辛和崩溃,群晓的家庭氛围则比较舒缓,他可以和妹妹交流、玩耍,爸爸还会带他去滑雪。但不论是学校场景还是社会场景,其体现出的焦虑都是“唯分数论”这个社会大场景下的映射。因为阅读障碍,孩子的分数低成绩差,自然导致孩子、家长和老师三方的烦恼不断。
《我不是笨小孩》的叙述分析
叙事学中的“叙述”可以特指讲故事的行为本身。在“叙述”方面,本文主要对其进行叙述者、叙述角度和叙述结构的分析。
多元的叙述者。叙述者指叙事作品中进行陈述行为的主体。纪录片或新闻报道的叙述者往往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缺席叙述者,用摄像机“客观”记录发生的事物,视听语言呈现中性色彩,受众难以察觉叙述者的存在;第二种是隐蔽叙述者,即事件由旁白或记者来讲述,但叙述者隐藏于幕后;第三种是公开叙述者,指旁白或记者作为事件的旁观者或参与者,公开地叙述故事。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的叙述者采用隐蔽叙述者为主、公开叙述者为辅的手法:占纪录片大部分篇幅的隐蔽叙述者,主要采用记录三个孩子与其家长的对话,以及他们对镜头进行独白,运用多个第三人称叙述者来进行叙事,但呈现哪些对话、引导他们说出哪些独白,实质上都是制作者叙述安排的结果,是“隐蔽”的叙述者。另一种公开叙述者则采用了传统的旁白方式,公开、清楚地用解说词来进行叙事,在纪录片中主要发挥承接故事和背景说明的作用。
不定内焦点视角叙事角度。根据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的分类,叙事学中的叙事视角被分为零度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和外焦点叙事。零度焦点叙事也就是所谓的全知视角,这是一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或人物可以从任何视角进行叙事的类型。外焦点叙事也称纯客观视角,主张完全客观地用镜头记录事件的外表,拒绝任何解说词。内视角叙事也称限制性视角,是一种以见证或亲历事件中的人物作为叙述者的一种角度,叙事者只能在其立场、视野上叙述和记录所感所想。《我不是笨小孩》的叙事角度属于典型的内视角叙事,但其特殊性在于采用了多个人物的视角来呈现不同的事件。这种不定内视角与零度视角不同,其在某一进程必须局限于某一人物,即纪录片运用多个人的内视角组合而成。
《我不是笨小孩》第一集《校校》的前半段以妈妈、爸爸、姥姥和老师等多个人的视角讲述了校校在学校、家庭、姥姥家等场景下学习所遇到的障碍,后半段则集中于以妈妈和校校的视角展示做功课时的凝重和崩溃。第二集《群晓》的开头先以武老师的视角说明群晓在阅读上存在一些困难但十分上进,接着转入妈妈的视角讲述她为了群晓放弃工作来陪读,然后以群晓的视角,用言语和刻字、背诵、默写等事例来讲述他在阅读上具体的困难,最后又回到了武老师的视角,以信的形式鼓励群晓继续怀有希望,并开启了群晓独自异地游学的历程。第三集《若汐》先以妈妈的视角叙述若汐在读写上遇到的障碍,并从爸爸的视角进行情况补充,在妈妈生病住院后,纪录片就单独以爸爸和若汐视角进行叙事,待妈妈的病情好转后,妈妈、爸爸和若汐的三人视角就成为了叙述的主要方式。
逻辑渐进与时间渐进叙事结构。电视纪录片叙事结构的任务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将材料、观点、体验等内在要素,有步骤、有主次地加以安排,形成聚合和支撑电视纪录片各个部件的框架。在渐进结构的纪录片中,其叙事内容以时间、空间、逻辑等顺序组成层层递进且不可逆。《我不是笨小孩》采用的就是比较常见的按逻辑顺序渐进和时间顺序渐进的叙事结构。
《校校》中,父母对校校成绩差的原因认知就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架构的:从不努力到多动症,接着被确诊为阅读障碍,再据此展开一系列全家与病情作斗争的故事。《群晓》则是按时间渐进的叙事结构,群晓在一年级时因成绩差而饱受欺凌,他的父母于是决定为他换一个更宽容的学习环境,而后来学校却因变故不得不就地解散,11岁的群晓就此踏上了独自异地游学的道路。《若汐》中,若汐从成绩倒数到及格再到70分,从初学芭蕾舞到做出翻跟斗动作,妈妈从生病住院到康复回归家庭,也体现了典型的时间顺序。
《我不是笨小孩》的话语分析
“话语”,主要指的是叙述故事的口头或者笔头的语言本身。纪录片的话语又可以分为视觉语言与听觉语言,本文就对这两种话语展开分析。
视觉语言。纪录片的视觉效果不仅是为了艺术美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话语”来隐晦地表达制作者的思想。《我不是笨小孩》中的构图、长镜头、视觉修辞、动画和的表意效果就十分突出。
在构图方面,创作者通过筛选画面中各个元素来表达纪录片背后的意图。《我不是笨小孩》在展示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大量的中心构图法,即将拍摄对象置于画面的中心,这对凸显纪录片的严谨、庄严感尤为有效。在构图的拍摄角度上,《我不是笨小孩》以平拍为主,这种拍摄角度相较于俯拍或仰拍更具有客观、中立的色彩。同时也不乏一些特色的构图,如在《校校》末段的一个画面中,妈妈与校校分别行走于走道和旁边的土地,形成了对称构图,两人一左一右互不理睬,而这也就是全片母子隔阂的一个缩影。
在长镜头方面,创作者还通过长时间纪实拍摄中表现出审美的意蕴,真实地还原时间和空间的完整性。比如在《校校》的中段,衔接一条从夜晚到白天延时长镜头的是两段同样的校校写作业画面,这从侧面烘托出了校校课业压力的繁重。
在视觉修辞方面,《我不是笨小孩》多次使用该手法来进行“言外之意”的讲述。比如校校在经历妈妈高强度的体育打卡后,趴在窗台上落寞地望着黑夜,此时无声胜有声;当妈妈在姥姥家辅导校校作业发飙时,出现了妈妈年轻时青春靓丽的照片,与当下她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直观地看到妈妈为校校付出了多大的心血。
在动画方面,其运用弥补了阅读障碍这一疾病本身难以直接展示的不足,同时也提升了纪录片观赏性。动画集中运用于第一集描绘校校阅读时产生的文字混乱,十分形象地向普通观众展示了阅读障碍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会难以克服。
听觉语言。除了视觉语言外,由人物对话、独白、解说词、背景音乐等组成的听觉语言也为纪录片思想的表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就占篇幅最大的人物对话和最易被忽视的背景音乐进行分析。
《我不是笨小孩》中的人物对话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解说词来进行叙事,但其最主要的特色在于与画面搭配成蒙太奇来形成纷繁的表意效果。比如在《群晓》的后半段,伴随着武老师读信声音的画面是群晓在收拾行李,这样一封满怀期待与鼓励的信与他即将独自面对异地游学的挑战不谋而合。又如在《若汐》的中段,播放着钢琴老师夸奖其他同学的声音,画面展现的却是若汐从期待到落寞的神情,可见她对于获得一张奖状的发自内心的渴望。
纪录片的背景音乐除了能够渲染一定的艺术效果之外,也能与画面搭配形成烘托气氛的效果。比如在《群晓》的末尾,群晓上台进行期末汇演,背景音乐的节奏变得舒缓、欢快,这昭示了他在新的环境中不论是学习还是与人相处,都在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发展。
结语
《我不是笨小孩》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向社会揭示了阅读障碍这一常见却鲜为人知的先天疾病,呼吁家长、老师和孩子们以科学的方法来探究孩子的成绩问题,以爱、包容和耐心接纳孩子的不足,发掘孩子的潜力,而不是一味地歧视和指责。不过,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也反映出当下国内“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仍十分严重,三个阅读障碍孩子的父母的行为仍表现出对教育模式的顺从,从另一方面说明我国教育体系的还有待完善。
注释:[1]蔡之国.新闻叙事学研究框架的构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130-136.
[2]申丹.叙述[J].外国文学,2003(03):66-71.
[3]蔡之国.电视纪录片的结构分析[J].当代传播,2009,(02):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