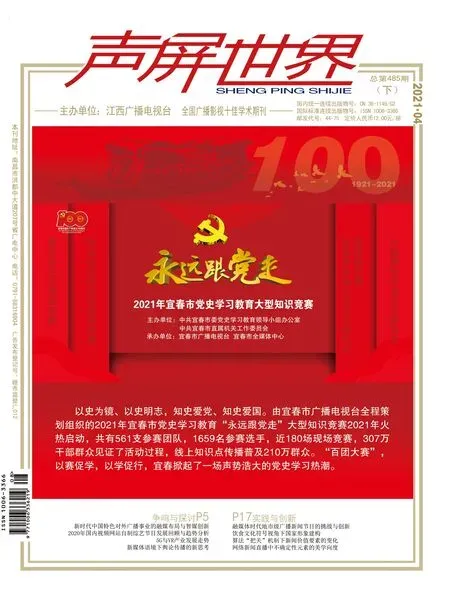“她综艺”的女性价值传达与现实困境——评《乘风破浪的姐姐》
2021-11-12艾芳怡
□ 艾芳怡
新世纪以来,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互联网娱乐的蓬勃发展驱动女性注意力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女性为综艺主角,围绕女性的生活、工作、情感、社交等话题展开讨论,以折射当下社会女性价值观的“她综艺”应势而生。2020年芒果TV自制“她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下简称《姐姐》)是在女性意识崛起的社会背景下,汲取“她综艺”的实践经验创作的成果。节目聚焦30位1990年之前出生的“姐姐辈”女艺人的女团追梦历程,以“三十而骊”为口号,以“破龄成团”为宣言对抗着传统的男性话语和固化的市场思维。本文将梳理潜藏在节目中的女性话语内涵和价值传达机制以及女性叙事的阻力,为“她综艺”的创作带来更深入的思考。
女性主体的自我认知与成长
重构女性主体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观点,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主体性是女性走向解放的关键,展现女性主体性对于“她综艺”的价值建构具有结构性意义。如果说以《创造101》为代表的女团养成综艺的本质是资本方借力娱乐工业体系以谋求粉丝经济的红利,潜在地表达了女性的成长价值,那么《姐姐》则是理念先行,是以女团选秀模式为依托对女性意识的自觉集中展示。
“镜中我”深化自我认知。库利认为,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节目中的“30+”女艺人虽然都是在演艺圈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但由于演员、歌手、舞者、主持人等职业的分化而鲜有交集。节目以女团的形式将她们聚合在同一环境,为她们设立共同的任务,在团队训练、集体生活和舞台竞争中展示个性之间的碰撞,在相互学习和经验交流中看到自身的闪光点和不足,从而在更加深刻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基础上促使个人能力得到恰当发挥。作为女性,她们对于同性的评价无疑倾向于以女性视角为基础,此种带有女性共情色彩的评价往往更加中肯,也更有利于被评价的女性主体获得清晰的自我认知。自我认知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过程,姐姐们在与社会、她人的联系上,在“乘风破浪”中持续挖掘自身潜力,重新认识自我,形成新的意志和行为主体,凸显了女性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主体性价值。
“蝶变”彰显女性价值。成长不受年龄限制,“30+”的女性同样能够在突破自我中抵达成长。节目召集的30位“30+”女艺人,绝大多数并非女团出身,对于一些唱跳表演零基础的姐姐,在短时间内配合队友展现出一个完美的舞台,并满足观众对“女团”的审美绝非易事。然而,没有什么比挑战自我更能凸显女性的成长。节目通过介入式采访和直接电影式的镜头,记录了她们的生理、心理体验,展现了她们“自为存在”式地追求在舞台上乃至人格上的成长的独立姿态。早在第二次公演就被淘汰,而在第五次公演的复活赛中重返舞台的阿朵,从不争不抢到主动竞争队长表露自己的野心,“教科书级”的拉票,阿朵以行动表明自己不再只充当参与者而是要当胜利者。多年以来背负着《快乐大本营》“小透明”标签的吴昕,也在这个节目里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姐姐们所表现出的勤奋、进取的精神,彰显了中年女性的自信与魅力,同时也激励着观众确立自我的主体价值。
推动女性媒介话语体系的构建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指出,女性银幕形象是男性审视下的呈现,而非女性自我阐释的产物。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在男性话语体系的支配下,女性的本质特征及生存经验是由男性言说的,性别差异与偏见的存在,势必造成对女性本质特征和生存经验的歪曲。因此,实现女性的全面发展和真正解放,构建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尤为重要。
解除枷锁,走出边缘。女性的年龄,似乎一直是整个社会无时无刻不在“介意”的要素和“审视”女性个体价值的尺度。演艺界的“潜规则”是社会意识的投影。潜在的年龄标尺下,女艺人主动选择的余地愈发有限。因此,只有打破年龄的束缚,给予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平等的选择权和话语权,才能广泛地构建属于整个女性群体的话语体系。“三十而励”,《姐姐》设定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年龄。从构成群体的年龄层次上看,30位女艺人介于30岁至52岁的年龄跨度之间,被边缘化的中年女艺人重新获得了多元个性展示及自我表达的平台,有助于解构以往传统媒体塑造的刻板的中年女性形象。“成团之夜”对中国女排精神以及来自各行各业和不同年龄段的榜样姐姐的致敬,更是超越了节目原有框架下的价值表达,对女性年龄及价值的肯定从特定的女艺人上升到了普遍意义上的女性群体。因此在形式上,节目直观地构建了一个提升女性话语权利的媒介环境。
撕掉标签,真诚表达。《姐姐》在节目形式上呈现的女性媒介话语权在年龄层次上的拓展,最终指向节目叙事中女性话语内涵的丰富表达。
其一,女性价值与年龄无关,姐姐也要乘风破浪。在男性中心文化影响下,“年龄”不仅束缚着女性话语的自由表达,而且成为诱发中年女性人生焦虑的重要因素。《姐姐》则直面女性年龄议题,赋予年龄积极意义。50岁的钟丽缇在节目中谈到:“只要梦想没有停止,不管你是10岁、30岁还是60岁,都要一直往前走。年龄只是一个数字。”52岁的伊能静为了展现更加完美的舞台,在长期患有低血糖的状态下凌晨四点还在坚持训练,直呼“不要因为我的年纪放过我”。她们用话语和行动以诚恳的态度为女性群体发声,鼓励女性敢于撕掉男性中心文化规制的年龄标签,以“无惧年龄”的精神追求价值目标的实现。
其二,拒绝“被定义”的人生,每位女性都有无限可能。女性特征往往在男性中心文化的塑造中被“标签化”,比如性格不够温柔或者不爱穿裙子的女性被认为没有“女人味”,不行使生育权的女性则过着“不完整的人生”等。这些带有强制意味的设定,往往成为女性自由发展的桎梏。实际上,女性特征是由女性自己来言说和界定的,恰如杨澜在第四次公演中表示“每个女人都应该由自己来定义女人味”。主题曲《无价之姐》正呼应了节目对女性“自信归位”的呼唤,体现出作词人对女性意识的自觉掌握和宣扬。“保持独有锋芒”“什么人生,什么梦想,我自己造”“我是我的无价之宝”,《无价之姐》旨在说明女性无论外表还是内在都要勇于坚持自我、认同自我、释放真我,女性价值无需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宇春作为传统审美标准的抵抗者和个人审美的坚守者,由她为节目主题曲作词并演唱,本身就是一种女性意识的潜在表达。同时,节目要求演员、主持人、制片人像女团成员一样在舞台上表演唱跳,也正是在看见女性价值的多样性中挖掘她们的无限潜能。
反思:女性叙事在博弈与妥协中的弱化
“她综艺”在本质上是一类文化产品,在“泛娱乐化”时代和资本主导的娱乐市场环境中,既承载着观众在屏幕上寻求审美愉悦和娱乐的愿望,又先天携带着商品属性,企求获得更广阔的利润空间。因此,《姐姐》虽努力承担着社会议题、追求着艺术价值,但受众的审美偏好、娱乐市场的商业逻辑也在影响着节目的女性价值传达。
窠臼:“文化工业”表征复现。《姐姐》作为一档立意深远的竞争性节目,其赛制应与节目理念一脉相通,然而决定选手去留的却是“观众喜爱度”,其中潜藏的娱乐工业法则值得细究。“观众喜爱度”即现场观众根据个人喜好为姐姐们投票,只有占据喜爱度排行前排的姐姐才能暂时避免被淘汰。观众喜爱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她们的名气相匹配的,在名气的加持下现场的观众评审在投票时就很难无视她们之前获得的成绩,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排名结果带有浓重的“论资排辈”的意味。像宁静、张雨绮、伊能静这些“咖位”大、话题度高的姐姐,有节目组和观众“撑腰”,几乎未曾面临淘汰的边缘。而最“优先”被淘汰的选手基本上都有两个特点:不够红,话题少。抛开舞台专业素养,不谈女性人格差异,仅仅以人气热度高低来决定姐姐们是否有资格继续留在舞台上“乘风破浪”,甚至可以说,留下热度高的选手以赚取更高可以变现的流量,节目赛制使得自身已经陷入普通女团选秀节目的市场规律。
除了名气,舞台感染力也是影响“观众喜爱度”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的是,对于现场观众来说,唱跳结合的快节奏歌曲要比纯声乐的慢歌更具有感染力,这也是在前两次公演的比赛结果中得到印证的事实。因此,创造更“燃”的兼具视听刺激的舞台,成了姐姐们获得观众喜爱的“安全牌”。在缺乏视听刺激的歌曲每每遭受组队“轮空”的尴尬后,在第四次公演中纯声乐慢歌已经无迹可寻了。一边是音乐总监赵兆坚持自己的艺术品味,一边是“孟佳组”想要迎合观众口味。节目在个性与大众之间摇摆不定,姐姐们在自我矛盾中与“观众喜爱度”这一指标不断地做出妥协,反映出商业逻辑与节目女性叙事的冲突。
展望:“她综艺”女性叙事的改进。“定义不一样的女团”,节目的初心是对女团传统形象的反叛和对女性所承载的社会成见的反抗。然而,对固化思维和现存规则的颠覆并非一蹴而就。观众已然形成的审美偏好、商业模式对女性叙事的征用、资本逐利的本性,都在阻碍着“她综艺”新锐的女性价值观的传达。《姐姐》在与资本博弈中妥协,造成的女性叙事弱化的局面,也为“她综艺”的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她综艺”在促进女性媒介形象改观的过程中,应该对男性中心话语降噪,减少商业利益干扰,在传达当代女性价值、塑造更多立体鲜活的女性形象中推动观众审美偏好的改变,不断在自我的“否定之否定”中实现女性叙事的逻辑自洽。
结语
现象级“她综艺”《姐姐》以其独到的性别叙事为“她综艺”创作树立了理念标杆、开拓了广阔道路,为社会议题与娱乐文化的初步结合打下的良好基础。虽然在资本竞相逐利的娱乐市场中,节目还未逃离积聚女性叙事力量的同时又被商业逻辑弱化的命运,但节目仍将继续激励更多富有多元价值的女性形象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