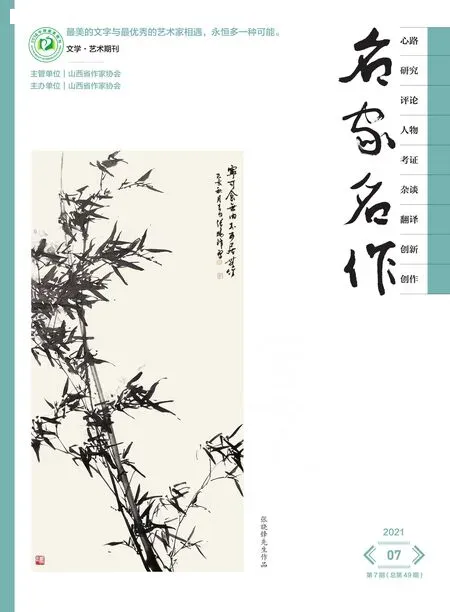浅析安德列耶夫作品中的疾病书写
2021-11-12郭雅婧
郭雅婧
“疾病”本是指人类机体出现异常的一种状态,属病理学范畴,但随着人类对疾病认知的不断加深,它逐渐走出原有范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疾病”也给文学带来了新的启发,成为人们了解社会风貌、感知社会文化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疾病”母题始终受到各国作家的青睐,它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机体经验过渡为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包含着众多意味深长的文学隐喻。
一、引言
不同时期,疾病在文学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差异。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认知水平有限,疾病被看作是一种不可侵犯的神的惩罚,此时的疾病多为生理疾病。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随着科学思想的萌芽和发展,人们开始把视线从神身上转移到人本身,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此时,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优秀作家开始关注人的心理健康与精神状况,蔓延几个世纪的忧郁者形象便滥觞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18世纪末,浪漫主义迅速崛起,原本丑陋的疾病被赋予了一种奇异的美感,例如,结核病成为这一时期的宠儿,《茶花女》中身患肺病的玛格丽特成为人人追捧的对象。人们甚至把作家的创造力归功于疾病,认为是疾病将作家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激发了出来。19世纪,现实主义占据了文学主流,疾病仍是各国作家的重要书写对象,如狄更斯的《小杜丽》、契诃夫的《第六病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多数作品也都充满了疾病叙事,这时疾病也获得了更多的隐喻意义,成为作家揭露社会黑暗的重要途径。进入20世纪后,哲学非理性思潮的出现及其带来的信仰真空加快了疾病向内转变的进程,文学作品中开始遍布由迷茫、焦虑、压抑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与痛苦。例如,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通过各种心理疾病与变形来反映世界的扭曲与社会的不真实。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各种前所未见和难以治愈的癌症以及艾滋病走进文学作品。例如,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身患绝症,包括骨癌、舌癌、心肌癌、乳腺癌等,这些癌症不仅是个人机体上的疾病,更是社会中存在的毒瘤;阎连科的《丁庄梦》将笔触伸向恶疾艾滋病,剖析了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人性的贪婪;俄罗斯当代女作家安娜·科兹洛娃荣获民族畅销书奖的作品《F20》则描绘了精神分裂患者的境遇。这些作品警示人们必须思考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以及新时代下人类新的生存困境。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疾病一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作家通过疾病传递出不便言说的隐喻意义,读者通过疾病叙事便可更为深刻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同样,读者结合具体的社会现实又可加深对文学作品中疾病叙事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整体思想。因此,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书写是十分必要的。
二、安德列耶夫作品中的疾病书写
安德列耶夫(1871—1919)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坛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他不从外部塑造人,省略了对人物外貌的刻画,而是执着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寻,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尤为喜欢发掘人物内心深处的阴暗面。因此,他的作品始终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悲观主义基调,这一点也颇受争议。在这种带有悲观主义的创作风格下,疾病便成为其表达理想的重要叙事策略之一。浪漫派作家大多只是痴迷疾病那种独特而忧郁的美感,而非疾病本身,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患病后也总是带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贵族忧郁气质。而安德列耶夫作品中的疾病颠覆了这种传统的美感,疾病重回丑陋面目,有的甚至阴森可怖,令人只想对其避而远之。
生活的苦难为作家积累了丰富的疾病体验,安德列耶夫出生于俄国的一个低级官吏家庭,从小生活艰苦。中学起,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但创作初期寄往报社的习作多被退回,生活十分拮据,时常陷入困境。晚年更是为了躲避迫害而离开祖国逃往芬兰、瑞典和法国。1919年冬天,安德列耶夫在芬兰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因心肌梗死发作而与世长辞,结束了他这艰难而又短暂的一生。
除不幸的个人境遇外,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也极其深刻。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虽已进行了农奴制改革,但实质上并未发生改变,人民仍然生活在贫苦之中,俄国社会依然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在此情况下开始向20世纪迈进,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接下来将走向何处也无从知晓,迷茫、绝望、孤独、颓废的乌云笼罩在俄国社会上空。1904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将俄国的腐朽暴露无遗,社会上响起了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革命瞬时风起云涌。但是,1905年革命的失败摧毁了人们的希望,白色恐怖日益加强,整个社会愈加悲观失望,涌现出了种种对社会的病态感受。另外,工业革命加速发展带来的物质进步扭曲了人的精神,同时也刺激了在新的社会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的艺术家在失落与苦闷中对反常生命状态的美学兴趣,而“疾病”正处于这种新的美学范式的中心。
因此,安德列耶夫将对生活与社会的感受寄托于作品之中,塑造了许多“病人”形象,例如《墙》中的主人公即为麻风病人;《沉默》中女儿卧轨自杀后母亲中风瘫痪,父亲也神智失常;《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中瓦西里神父自幼便在疾病和苦难中度过,儿子瓦夏意外溺死后,妻子酗酒度日,精神痴癫,第二个儿子更是一出生就患有痴疾,头大腿细、呆滞迟钝,女儿娜思佳也染上疱疹,就连家里的雇工也很快就染上古怪的忧郁症;《红笑》中主人公从战场归来虽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阴影成为心疾,始终能看到“红笑”,等等。安德列耶夫的作品中既有生理疾病,又包含众多心理疾病,他利用这些“疾病”意象来构建新的美学理念与精神主题。本文将选取《墙》和《红笑》分别作为生理疾病书写与心理疾病书写的范例进行分析,以此管窥作家独特的艺术特色与深刻的思想关怀。
(一)生理疾病书写——《墙》
短篇小说《墙》开篇即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没有名字,仅仅是“我和另外一个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美的化身,而是丑陋恶心,他“身上已经溃烂”“说话时带难听的鼻音”,而且还“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主人公总是政治高尚,外貌姣好或英俊,再不济也与普通人无异,而此时安德列耶夫颠覆了传统的审美范式,将目光投向偏离常规的、反常的生命状态上。尽管麻风病人丑陋,但他们还是抱着热切期望,希望能翻过墙,到墙后那个不存在疯狂与相互残杀的世界中去。由于墙太高,一个麻风病人主动让同伴站到自己的背上,可还是无法触及墙的顶部,他们又提议推倒这堵墙。而其他人对墙仅是声讨,没有实际行动,声讨后发现墙始终完好,其他人翻过墙去的愿望也逐渐消失。只有两个麻风病人对大家发出请求,哪怕尸体上堆尸体,哪怕只剩一个人看到新世界,也要攀爬到底。但是周围只有冷漠与倦怠,没人在意他。
“墙”在这里既是指生活中的阻碍,又是指人性中不完善的地方。两个麻风病人拼尽全力去冲破墙的束缚,为真理、幸福和自由不懈奋斗,而周围所谓的“健康的”人们却无动于衷,在墙内浑浑噩噩,看到麻风病人只是“带着嫌恶的神情转过身去”。“疾病”增添了文章的讽刺意味,到底谁是健康的而谁又是病人?“疾病”成为具有独立个性、善于思考、努力向恶势力发起攻击的标识,而“健康”则代表了群体、混沌、无意识。尼采认为,疾病是生命的催化剂,“对我所有的疾病和痛苦,我打从心底感激它们,因为这些疾病与苦痛给我许多可以逃避固定习性的后门”,“固定习性”即思想的僵化与逆来顺受、接受一切的奴性。作为尼采的追随者,安德列耶夫将这种“生命的兴奋剂”赋予两个麻风病人,他们打破了停滞的思维,积极地向恶势力发起挑战,成为生命力旺盛的强者,而健康的庸众已经习惯了“固定的习性”,反而变得脆弱不堪。疾病作为一种表征符号,隐喻着个体基于自身的严肃反思,以及对规范化整体性价值的质疑与超越。在充满灾难与不和谐的时代向往美好世界的人竟沦为异端成为“病人”,找不到出路,可见整个社会荒诞至极。此时,疾患已经失去了原本病理学上的意义,它成了作者反讽社会的一种手段,以此来昭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疾病在这里还隐喻了个体无可奈何的悲惨命运。
(二)心理疾病书写——《红笑》
小说《红笑》讲述的是日俄战争时期的故事,与其他战争小说不同,《红笑》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战斗场面,没有刻画战场上的血雨腥风,而是致力于表现战争对人心理与精神的异化,即使离开战场这种心理阴影也久久无法消散。《红笑》中的主人公“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疯狂的,即使身旁遍地都是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但别的士兵还是自顾自地做事,甚至聊天嬉笑。这些士兵虽然活着,却像“梦游病患者”,毫无感情,麻木不仁,自己的同伴倒下也无人去扶,都继续向前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但经历过战争之后却犹如冰冷的机器一般,没有感情,没有爱与温暖,这是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毁灭。在恐怖的战争的影响下,主人公的精神出现问题,时常能看到“红笑”。“红笑”并不是真实存在的物体,而是主人公在经历过战争之后心灵和精神遭受创伤臆想出来的物象。无论是日军还是俄军都出现了许多精神病患者,这种疯病疯狂蔓延,很难有人能够幸免。
“我”在一次战争中失去了双腿,非但没有感到痛苦反而开心起来,因为好歹保住了性命,可以被遣送回家了,剩下的时光都可以平平稳稳地活下去。但是,战争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即使离开战场也无法逃离战争带来的恐惧,永远不能回归正常生活。战前“我”是一个评论家,为报社撰写文章,写作令“我”感到欢欣愉悦,回家后“我”本想继续这项工作,但一提笔却什么都写不出,只能想到战场上的火光与鲜血、呻吟与呼号,只能画出一些不成形的、歪斜而毫无意义的线。心理与精神上的压力摧残着主人公,“我”最终彻底走向疯狂。“我”忘记了很多事情,甚至包括挚爱妻子的名字,但却一次也没有忘记战争,每天昼夜不分地进行创作,但纸上始终只是一些不成形的线,最终在写作时死去。战争不仅给亲历战斗的人带来痛苦,也使参与者的亲属备受折磨,“我”的弟弟直言自己已经传染上了精神疾病,一半的思想都不属于自己、不听使唤了,这种精神疾病比可怕的瘟疫还要坏。直到最后,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大家都走向疯狂,“红笑”笼罩了世界,战争带来的危害可见一斑。
“疾病”使人获得了认识自身唯一性、独特价值的机会,由于成为病人,和世界拉开距离,成为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个体化存在,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自己的孤独,开始思考善与恶、美与丑、个体与世界,成为个体意识反思的契机。丑陋的疾病赋予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呈现出积极的价值与意义。疾病给予人思考的空间,强化了敏感,开启了反思,丰富完善了人生历程。《红笑》中的主人公包括他的弟弟都是在患上精神恶疾后开始与世界对话,思考战争的本质与世界的存在。表面上,作家是在对主人公的精神分裂病症加以描摹,实际上是对一种灵魂声音的隐喻表达,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强烈批判,把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心情、对理智的极致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安德列耶夫是典型的“外冷内热”型作家,他的笔触虽阴郁寒冷,内在却蕴含着对人类生存的深刻思考。作家描写了战争过后出现的心理疾病与精神疾病,首先是“我”,随后扩展到“我”的家人,最终蔓延到所有人身上。战争给每个人都带来极大的创伤,不仅是生理上的残缺,更是心理和精神上几乎不可痊愈的重疾。作者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的残酷与荒诞及其对人性的无情泯灭,他认为战争使人永远失去了幸福生活的机会。“疾病”在此成为作者巧妙的叙事策略,进一步凸显了创作主题,加强了对战争的批判意味,反映出作家的战争观念与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三、结语
疾病作为小说的一种叙事手法,负载了众多隐喻功能,诠释着政治、文化、宗教、道德等多重语义指向,既是表达愤怒焦虑的手段,也是对政治失序的指控。苏珊·桑塔格指出:“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全部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借疾病之名,这种恐惧被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安德列耶夫作为“白银时代”艺术花园里的一朵奇葩,汲取了各种文学流派的艺术养分,在作品中加入了自己的哲学思考与人生感悟,思想深刻,文笔精致,在众多作品中都通过疾病书写表露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观念。无论是生理疾病还是心理疾病,折射出的都是当时那个病态的社会,承载了作家对世界的客观思考与深切关怀,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安德列耶夫在作品中广泛加入疾病元素,也彰显出对传统的大胆挑战,由审美转向审丑,丰富延展了传统的审美范围,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规束走向自由,为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