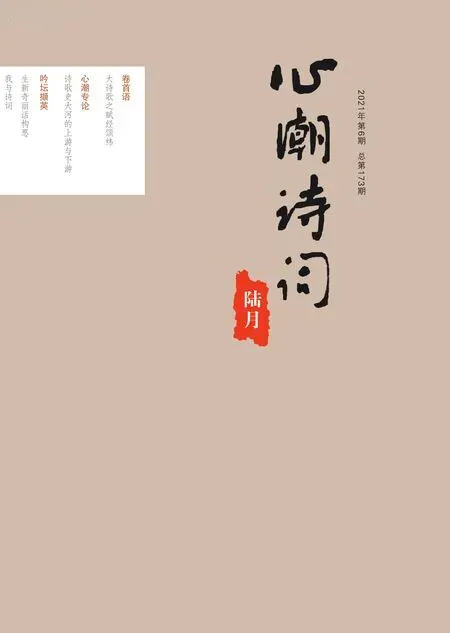诗歌史大河的上游与下游——古典诗歌传统与20世纪新诗
2021-11-12杨景龙
杨景龙
20世纪的中国新诗,借鉴西方、横向移植较多本是客观事实。从白话取代文言、自由取代格律的大趋势看,新诗无疑是对古典诗歌传统的背离和反叛。但是,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仍然纵向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横向移植”只是事实的一半,“纵向继承”则是事实的另一半。文学史是一条水流不断的大河,上游之水总要往下游流淌。居于大河上游的那些蕴含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情感内容的“母题”和“原型”,作为“背景或大的观念”,总要对后世文学进行笼罩性的渗透,致使一些题材形成“一个特殊形式或模型,这个形式或模型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一直保存下来”。或显性或隐性地,出现“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或引用已有的言辞”的结果。因此说,后来的诗歌接受前代的影响就是必然的。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尝试集》作品的说理言志性质、伦理品格和新旧体兼收的编排,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过渡状态。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之外。小到一个意象,一句诗,一篇作品,大到一个诗人,一个流派,一种诗体,一种诗学主题,一种表现手法,古今之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皆可寻绎出彼此施受传承的脉络和痕迹。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存在着直用、活用、化用几种关系。戴望舒《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一样结着惆怅的姑娘”,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席慕蓉《长城谣》中有句:“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直用北朝乐府《敕勒歌》开头成句。闻一多《口供》中有句:“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活用了温庭筠《春日野行》中的“鸦背夕阳多”和周邦彦《玉楼春》词句“雁背夕阳红欲暮”。余光中《碧潭》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了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卞之琳那首脍炙人口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原是一首长诗删改后留下的几句,诗中意象之间的主客关联转换,一如南宋杨万里《登多稼亭》诗句“偶见行人回头望,亦看老子立亭间”和清代厉鹗《归舟江行望燕子矶》诗句“俯江亭上何人坐,看我扁舟望翠微”。而李瑛的《谒托马斯·曼墓》:“细雨刚停,细雨刚停/雨水打湿了墓地的钟声”,也很容易让人想起杜甫《船下夔州郭》诗句“晨钟云外湿”。舒婷《春夜》中的名句:“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与宋代张先《江南柳》词句“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可说是活脱相似。这几例都属化用。还有洛夫的诗句“清晨,我在森林中/听到树中年轮旋转的声音”,与杜甫的“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具有同样的超现实艺术效果,也是新诗化用古典诗歌句意的典型例子。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的传承,如何其芳的名篇《罗衫》,语言、意象、情思有着浓重的唯美色彩,含蕴着晚唐五代温李爱情诗词的遗韵。它的整体构思和比兴手法,则有意无意间模仿了汉代班婕妤咏纨扇的《怨歌行》诗句:“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将二诗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何其芳的《罗衫》是对班婕妤《怨歌行》的改造重组。郑愁予的名篇《错误》,主题仍是传统游子思妇的闺怨情感,“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的误会与巧合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笑声无意,行人有情;马蹄无意,思妇有情。苏词里的墙外行人错解墙内佳人的笑声,郑诗里的江南小城思妇错把过客当作归人,从情节因素来看,二者均构置了带有无焦点冲突性质的戏剧化情境。郑诗对苏词的借鉴还有更深的比兴象征层面,诗中那古典的游子思妇的浓重怨情里,掺入的是现代社会迫于政治分裂而去国怀乡者的浓重乡愁。可见郑诗不仅借鉴了苏词单相思的生活喜剧情节,郑诗更像苏词那样,寄托了社会政治意义和身世悲凉之感。席慕蓉的名篇《悲喜剧》,写“白苹洲”上的等待与相逢,是对温庭筠《望江南》词意的翻新与掘进。舒婷的名篇《船》,表现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一机杼。还有陈江帆的《穷巷》与王维的《渭川田家》、高准的《香槟季》与《诗经·关雎》、洛夫的《长恨歌》与白居易的《长恨歌》、苏青的《最好回苏州去》与周邦彦的《少年游》等,措辞、构句、立意皆有直接的联系。在古今比较的“溯本求源里”,就会看到“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的有趣现象。
古今诗人之间的传承,像郭沫若、贺敬之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的大气包举、豪放飘逸,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臧克家诗歌的乡土写实与杜甫诗歌的关心民瘼、沉郁顿挫,李金发象征诗的生涩凄美与李贺、卢仝诗歌的险怪冷艳,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词的艳情绮思,余光中诗歌的骚雅、才气、琢炼与屈赋李诗姜词,席慕蓉、舒婷诗歌的浪漫忧伤气质与温庭筠、柳永、晏几道、秦观、李清照等为代表的唐宋婉约词的浪漫感伤气息等。以舒婷诗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为例,舒婷诗歌的美感风格,即酷肖以浪漫感伤为抒情基调的唐宋婉约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崛起于中国诗坛的朦胧诗,曾因所谓“难懂”等原因引发争论,招致诘难。作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舒婷也曾一度受到攻讦,但其作品很快又被持有不同诗观的人们广泛接受认可。这和迄今仍在评价上存在较大分歧的北岛等人的遭遇大为不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舒婷诗作的美感风格酷肖唐宋婉约词以浓重的感伤为抒情基调的浪漫主义气质风韵,与闪射着冷峻阴郁的现代晦涩色彩的北岛诗作大相径庭。与北岛等同派诗人相比,舒婷诗歌的观念和手法都是相当传统的,她的诗作选取的爱情离别题材的人性内涵,流露的忧伤执着的悲美情调,语言的柔婉清新,结构的曲折层递,意境的隐约朦胧,均深得唐宋婉约词之神髓。唐宋婉约词是古代文学优美风格的代表,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切,古代文学诸文体无出其右,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寻绎舒婷诗的艺术魅力,离不开对其与唐宋婉约词之间承传关系的探讨。
古今诗体之间的传承,像胡适之体诗歌的语言节奏,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闻一多等人倡导的新格律诗与古典格律诗的影响,郭小川诗歌的铺排夸饰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与古代绝句小令的形式、内容异同等。中国新诗虽以彻底破坏旧诗的诗体(语言形式)开始,但在自己的诗体(语言形式)建设方面,还是和传统诗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新诗在用韵上基本遵从的逢双押韵的原则,大致还是古代诗歌几种押韵方式的借用或变通。新诗的章节安排惯例,多以四行为一节,有律绝的形式痕迹;白话小诗一体,有很多四句一首,更像是古代绝句的现代白话版。30年代中期,林庚发表了《小春吟》《落花》等许多四行诗,戴望舒就认为林庚是在用“旧瓶装新酒”,为了证实这些白话四行诗的“旧”,戴望舒不惮烦劳地把它们一首首还原为绝句,而意思和韵味基本不变。除了四行体,还有诗人尝试五行体、十行体和三句体。而那些两节一首、句子参差的新诗,总让人感觉出双调词的形式遗留。任钧在《谈谈胡适之的诗》中曾指出:《尝试集》里的诗“跟旧词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许多诗“都带着词调”。公刘50年代的“八行体”诗,全诗句数与律诗相等,结构方式又与双调词的上下片分工十分吻合,应是受双调词的结构和表现方法启发影响的产物。新诗在字句节奏上对传统诗词的借取更多,古典诗词曲和民歌以三、四、五、七言为主,节奏分明,流畅顺口,凝练简洁。初期新诗如刘大白、刘半农的作品,即是三、五、七言句子居多。稍后如俞平伯的新诗,朱自清认为他运用词曲的腔调去短取长,闻一多也说他的诗“音节是从旧诗和词曲里蜕化出来的”。从4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强调新诗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所以在音韵节奏行句方面仿效古典词曲和民歌的情况更为普遍,成就突出者如郭小川、严阵、流沙河等,他们的新诗的语言句式节奏甚至意境韵味都逼肖古典词曲,是古典词曲体式在白话新诗领域里变通演化的结果。
古今诗歌流派之间的传承,像新生代诗的口语谐趣与元散曲本色派浅俗的“蛤蜊风味”,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等。以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的关系为例,“新边塞诗派”的流派命名,即显示其与古代边塞诗之间的渊源有自。从时代的角度看,新边塞诗创作繁荣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与唐代尤其是盛唐时代同样都是变革、开放的时代,民族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大都具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浪漫精神气质,表现出气势宏大地吸收外来、融汇古今的襟怀与魄力。这一切由时代决定的创作主体的心理、情感,正是构成盛唐边塞诗和80年代新边塞诗的共同审美特质的基本内涵。从地域的角度看,古今边塞诗产生的地方主要是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等西北边地。从诗人的角度看,古今边塞诗人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从内地到边塞观光的“行吟诗人”,世代生活在边塞的“土著诗人”,较长时期生活在边塞的“羁旅诗人”。古今边塞诗的代表诗人、诗作都是“羁旅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从诗风的角度看,古今边塞诗豪放、粗犷、刚健、悲壮的流派风格大同,但古今两大边塞诗派成员的个人风格各异,如盛唐边塞诗人高适悲壮而厚,岑参奇逸峭丽,王昌龄雄豪深沉;新边塞诗人昌耀悲慨奇崛,周涛机智犷放,杨牧高远旷达。从新边塞诗对盛唐边塞诗的继承与超越方面看,二者在语言形式上的不似之中显示出深刻的相似性,盛唐边塞诗多用七言和古体这种“长句”“大篇”,新边塞诗的行句和篇幅一般也较长较大;在题材内容上,新边塞诗的劳动建设基本上取代了盛唐边塞诗的战争生活;在情感指向上,新边塞诗抒写的建设开拓的劳动热情,取代了盛唐边塞诗抒写的追求功名功业的豪情;在情景关系上,盛唐边塞诗的写景更纯粹,更富异域色彩,更富地域性,新边塞诗的写景已与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因素糅合在一起,更为繁复,更富人文色彩,更富社会性。
古今诗歌主题之间的传承,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以社会政治主题为例。在《诗》《骚》传统和孔子说诗、《诗大序》等儒家诗论的影响下,中国诗歌、诗论始终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沿着“修齐治平”道路前行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难解的“入世情结”,士大夫文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对社会政治、对社稷苍生有着特别的关怀。他们创作了大量的社会政治性的抒情诗,在诗歌和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但同时也应看到,属于社会政治、政教伦理范畴的“志”“道”“礼”“理”,对诗歌中的个人化的“情”的抒发,构成了巨大的压抑和损害,个人的、情感的、唯美的带有与政教伦理疏离倾向的诗人、诗作,一再受到批评、指责和贬低、攻击。一些诗人、诗论家急功近利,为了政教目的,忽视诗歌艺术,审美视野单一狭隘,使诗歌沦为政教目的的附属物,甚至牺牲品,取消了文学、诗歌的独立性和审美、娱乐价值。这种不良影响一直延伸到现当代白话新诗的创作、批评领域。20世纪的白话新诗革命,作为新文学革命的首要部分,既是为社会政治思想革命而发起,又是为社会政治思想革命服务的,革新诗歌与革新政治、革新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启蒙到救亡,从普罗诗歌、国防诗歌、抗战诗歌、根据地诗歌到五、六十年代“政治标准第一”“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颂歌”与“战歌”,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和归来者诗歌,以及与这些诗歌创作紧密联系、引导呼应的诗歌理论批评,在本质上都是社会政治性的。新诗这种与中国古代诗歌一脉相承的与时代人群、社会政治的胶着状态,其正面价值与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其负面作用也导致了政治压倒艺术,政治学取代诗学,群体伦理道德对个人化、个性化的自由抒情构成压抑排斥,从而降低了诗歌的艺术品位,出现了大量粗糙、假大空甚至滥施语言暴力的诗歌文本,其经验教训无疑是沉痛的。
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的传承,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的借鉴,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与戏剧化,互文性与用典,主情、主智与主趣等。以意象化为例,中国诗歌文本的基本构成单位是“意象”,中国诗歌是典型的意象诗,诗人表情达意时,一般不采用直抒的方式,而是借助意象来间接传示。这与中国诗人的生存环境有关,又与诗人接受《易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哲学思维表达方式有关。传统中国社会是早熟的农业社会,人与大自然关系密切,对自然物象了解、稔熟、亲和,即目兴感、见景生情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创作心理发生机制,借景抒情、托物寓情即意象化的方法,也就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表现方法。诗歌中的意象是主客契合的,所以意象既具客观的形象性,又涵容了诗人主观的情感状态和审美趣味,因此,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呈示一首诗或一个诗人的风格特色。一首内涵丰富的诗或一个风格鲜明的诗人,都拥有自己的意象群落和中心意象。意象往往成为一首诗或一个诗人的标志性代码。古代诗歌史上那些最有个性风格的诗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中心意象,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意象群落。如屈原的“灵修美人、善鸟香草”,陶潜的“园田、松菊、南山、桃源、归鸟、孤云”,李白的“月亮、大鹏、黄河、蜀道、剑侠、酒仙”,岑参的“大雪、沙碛、热海、火山”,李贺的“酸风、铅泪、黑云、冷雨”,李商隐的“锦瑟、梦雨、蓬山、青鸟、金烬、红楼”等;形成个人风格的现当代新诗人亦是如此,如郭沫若的“凤凰、天狗”,闻一多的“死水、红烛”,戴望舒的“雨巷、断指、暗水、残阳”,艾青的“大堰河、火把、太阳、土地”,纪弦的“狼、铜像、6与7”,余光中的“莲、白玉苦瓜、五陵少年、李白”,昌耀的“高原、古堡、牦牛、吐蕃特女人”,舒婷的“橡树、双桅船、神女峰、鸢尾花”,海子的“麦地、亚洲铜”等。可以这样说,古典诗歌的意象化手法被现当代新诗人较为自觉地加以继承,这对新诗人形成个人风格大有助益。而一些古代诗人诗歌经常写到的通用意象,如“莲荷、月亮、黄昏”等,在现当代新诗中被继续反复抒写,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新诗对古典诗歌艺术手法的承传。
如果说初期白话诗中的古典诗词因子,是那一代诗人深厚的旧诗功底的不自觉(或不情愿)流露;那么,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新诗人和诗论家,则明确地意识到,要想提高新诗艺术,必须向辉煌灿烂的古典诗歌艺术学习,在继承借鉴中创新发展,实现古典诗歌艺术在现当代新诗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在新诗发展史上,新诗人、诗论家认同古典诗歌传统的表述很多,20年代,可以朱自清、梁实秋、朱湘为例。朱自清说:“我们现在要建设新诗的音律,固然应该参考外国诗歌,却更不能丢了旧诗词曲”,因为“旧诗词曲的音律的美妙处,易为我们领解、采用”。梁实秋在《新诗与传统》一文中反思新诗得失之后表示:“新诗之大患在于和传统脱节”,“新诗应该是就原有的传统而探询新的表现方法与形式”。朱湘在《诗的产生》一文中具体分析了传统诗词曲的艺术特色,从而说明了新诗必须向旧体诗词学习的道理。30年代以后,可以何其芳、叶公超、冯文炳(废名)为例。何其芳说自己童年时就喜欢古典诗词“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他“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叶公超30年代主张新诗人应多读文言诗文,从而扩大意识,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现阶段的知觉,他强调“以往的伟大的作家的心灵都应当在新诗人的心灵中存留着。旧诗的情境,咏物寄托,甚至于唱和赠答,都可以变态的重现于新诗里”,他指出新诗“要在以往整个中国诗之外加上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使以往的一切又重新配合”。叶氏的观点,与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表述的诗人与历史传统的联系看法大致相近。可见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关系,是东西方诗人、诗论家所共同关注思考的一个问题。冯文炳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新诗时,认为温庭筠、李商隐一派诗表现出的感觉的联串、自由的想象和视觉的盛宴,“倒似乎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新诗将是温李一派的发展,因为这里无形式,意象必能自己完全”。
50年代以后,可以卞之琳、余光中为例。卞之琳总结自己的创作特点时说:“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我也常吸取文言词汇,文言句法”,他自评前期诗作“冒出过李商隐、姜白石以至《花间》词风味的形迹”。西语系出身、终生讲授西方诗歌的蓝星诗人余光中,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最深,他追求受过现代意识洗礼的“古典”,和有着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指出了新诗与以屈原为代表的古代诗歌传统一脉相承的联系。从余光中与古典诗歌传承关系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永不释然的祖国情结主要来自屈原赋,他那天马行空般的纵逸才气主要来自李白诗,而他的雅致琢炼的语言风格则主要来自姜夔词。80年代以来,可以洛夫、郑敏为代表。创世纪诗人洛夫指出:“现代诗人在成熟之前,必然要经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和学习阶段,古典诗则是探索和学习的主要对象之一。”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诗的意象化”“诗的超现实性”三点,是现代诗人向古典诗歌学习的主要内容。而早在40年代西南联大即已成名的九叶诗人郑敏,90年代以来屡屡撰文,立足西方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的相通性,呼吁新诗应向古典诗歌学习,借鉴古典诗歌的表现艺术经验。她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创作要想跳出困境,就需要重新发现认识“自己的诗歌传统(从古典到今天),使古典与现代接轨,以使今后的新诗创作不再引颈眺望西方诗歌的发展,以获得关于明天中国新诗发展的指南”。这就从诗歌史发展的高度,指明了沟通古今诗歌的现实和未来意义。除了诗人个体化的表述,还有一些诗歌流派呈现出共同的回归趋势,表达了他们孺慕古典诗词传统的群体愿望。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如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废名、林庚等,就不约而同地表达过对晚唐五代诗词和姜吴雅词的爱好与醉心。70年代台湾的笠诗社、龙族诗社、大地诗社、草根诗社诗人群,也表现出共同的反拨西化、回归传统的倾向。
依照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古今诗歌之间的传承关系研究,应属于诗学领域的影响史和接受史研究范畴。这是一个涉及古今、十分复杂的诗学课题,研究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开展相关研究的意义则更为重大。它不但有利于古典和现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重建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以使自己有能力透视古典诗歌对20世纪新诗所施与的影响,理出20世纪新诗人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公正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歌艺术为参照,剖析现当代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肩负起诗歌史家指导当代诗歌创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它更有助于打通当前新诗与旧体诗词创作、欣赏上仍然存在的互相对立的森严壁垒,纠正热爱旧体诗词的人认为新诗语言芜杂、意味寡淡,而喜欢新诗的人又认为旧体诗词观念陈旧、形式过时的偏颇之见,加强当代新诗和旧体诗词之间的互相学习交流,让旧体诗人和新诗人携起手来,优势互补,共同促进民族诗歌的再度繁荣;它还有望打破古典诗歌研究领域的僵化保守局面,避免大量的重复无效研究,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培育出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构建起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古典诗歌研究者和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