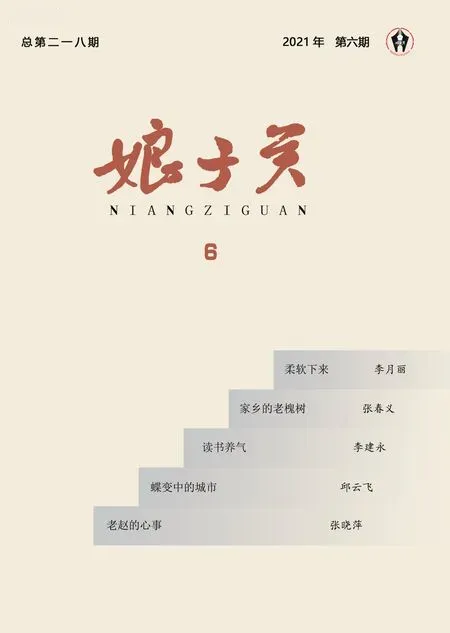悠悠夏日长
2021-11-12王今
◇王今
春虽妩媚,却短暂;秋虽绚烂,却凄凉;而冬的冰冷、荒凉,让人郁闷、沉重。唯有夏,如人生的青春期般,由内而外焕发着勃勃生机。置身夏日,体轻盈,心舒展,神飞扬。
黄 昏
长久以来,我一直迷恋夏日黄昏。
黄昏时分,太阳已不再那么嚣张霸气,开始缓缓向西天沉落。然而,即使太阳已坠于天际,但天光还在,天地间仍然光明一片。这时,劳作一日的人们已经陆陆续续走出单位,走在了回家的路上。他们离开的不仅仅是工作的地方,还离开了烦琐、忙乱、焦虑和重压,奔向的是温暖、自由、舒适和轻松的家,心情可想而知。我和千万个“工作者”一样,怀着这样的心情,长长呼出一口气后,融入夏日的黄昏。
不可一世的暑气已经弱下来,运气好的话,会偶遇习习凉风。端坐了一天的身体,在四肢的牵动下逐渐活络起来,酸困的不适感也随着步伐渐渐消失。
散散漫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满眼是景,满心是美,满身的细胞都活蹦乱跳,思绪更是如脱缰的马。生命真是神奇。冬日里,那棵不知名的灌木干枯消瘦,像个干瘪的“朽老头”,如今,浑身披绿,枝条张扬,成了个英姿勃发的“壮小伙”;那棵落叶松似乎又高了一截,胖了一圈,树干挺立,枝叶浓密,俯视苍生,稳如泰山。春日里,那些粉的、白的、黄的花,使人们一眼便知,这是桃,那是李。而今,粉黛褪去,绿叶纷披,绿洼洼一片,谁又能分清谁是谁。小草从严丝合缝的人行道地砖间倔强地钻出来,即使承载每日成千上万次蹂躏踩踏,它们依旧鲜绿挺拔,让人不由心生怜爱。入眼最多的是麻雀,忽地飞上枝头,忽地落到地面,叽叽喳喳,焦虑不安。很少见它们安静,总是躁动,总是忙碌。时逢夏日,有树有草有虫,可食可栖,何必慌乱?人们走过,鲜有人注意它们,更不必说伤害了。如我般多看几眼的人,都是心里有喜、有爱、有暖,又哪里会去伤它们?小小麻雀,认知进化速度实在太慢,如何能理解人类的行为?有时会看到雨燕上下翻飞。暴雨来临之前,大自然的这些“绅士们”也沉不住气了,是担心觅食未归的伴侣?还是牵挂巢中嗷嗷待哺的幼雏?或是害怕自己的“礼服”被打湿?抑或在给人类报告讯息?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让天地多了些灵动,多了些生机。
穿过一个街心公园,休闲的人们吸引了许多过往的目光。在家闷了一天,傍晚时分,迫不及待地想出来透透气。于是,呼朋引伴,来到公园,或是吹拉弹唱,或是促膝交谈,或是跳舞跑步,或是遛狗带娃。多数是老年人。虽已步入人生的黄昏,却不失激情和梦想。只要心中有梦,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快乐和美好。弹一首曲子,跳一个舞,唱一首歌,画一幅写意。童年的理想,老年时去追求,一样的感觉,一样的味道。享受的不是实现理想的结果,而是追求理想的过程。
一排单车闯入我的视线。小小一座山城,共享单车要入驻,确实有些风险。到处是坡,怎么骑?然而,就在某些大都市共享单车遭遇“寒潮”时,这里的单车却高调登场,且运行的风生水起。先是哈罗小蓝车亮相街头。更多山城人关心的不是效益,而是小小山城多了一道风景,自己的城终于也有大都市的待遇了。面对大都市,小城的人们总有些自惭形秽。小蓝车的出现,既提升了城市品位,又增加了人们的自信,还方便了大家的出行。小蓝车属助力车,很好地克服了山城坡多的特点。近来,又有了青桔小绿车、松果小黄车。哈哈,好不热闹!有朋友问:你说这个行当能挣了钱吗?我说看看种类不断更新和数量不断增加的势头,应该能。少年时代,我也是下了大力气才学会骑车,但技术平平。多年没骑,心里胆怯。每每走过一排排停放的单车,总是跃跃欲试。可想想自己的腿脚,还是算了。摇摇晃晃骑上去,自己摔倒不说,万一剐蹭了“豪车”,如何赔得起?不过,等夜深人稀时,还是想骑上一试。这种随停随走、点对点的自由,还是充满诱惑的。
走到公园尽头,突然想起那片荷。拐个弯走过去,池塘里已是荷叶田田,荷花亭亭。
有荷,就有一夏清凉。
荷
虽有“夏花绚烂”之说,但用它形容荷,似觉不妥。
荷是有灵魂的。每次见到荷,总有“空灵、高洁、静谧”之类的词从脑海里蹦出来。那叶,或两边卷在一处,像紧闭的唇,像三三两两的舴艋舟;或被柄高高擎起,随风摇曳,像华盖,像绿伞;或匍匐于水面,像河中的搭石,像茵茵的碧玉。最妙的是一颗豆大的雨滴不经意落在张开的荷叶上,随着荷叶摆动摇来晃去,如一个荡秋千的顽皮小儿。晴日里,雨滴晶莹剔透,熠熠生辉,真如一粒琼珠。若是一只蜻蜓或麻雀恰好过来歇歇脚,就成一幅妙趣横生的写意了。
在这蓬勃的绿意中,一团粉红或浮于之上,或藏于其间,由中通外直的柄托着,亭亭玉立,不蔓不枝。花朵如新生的婴儿,纤尘不染;花瓣如少女的皮肤,吹弹可破。花虽硕大,虽透亮,虽挺拔,却不骄纵,不蛮横,不招摇,不喧闹。只是立在碧波之上,脱俗、淡泊、宁静,一片冰心。有时,因雨打风吹,花会失去几个瓣,或飘零于叶间,或不知所踪。其余花瓣仍坚守着自己的位置。花虽残缺了,却并不失其美,倒如美人腮边之痣,或是断臂的维纳斯,那美、那贵,更是摄人心魄。还有那娇羞的花蕾,是恰到好处的点缀,避免千篇一律。这片荷塘因她而有起伏,有错落,有主次。“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景致也是常有的,只是我未遇到过。
关于荷的香一直不知。茉莉、米兰、桂花之流的香,远远就能闻到,真可谓香飘十里。月季的香需把鼻子凑上去才能闻到,那香也是沁人心脾的。或许荷只可远观吧,从未嗅到过它的香。“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众多文人如是说,荷定是有香气的。只是,从未划桨入荷间。仅远观,故不得其香,也是可能的。想来,荷的香是纯净的,如婴儿的眸,如少女的心;荷的香是清爽的,如夏日晨的风,如山涧淌的泉;荷的香是温婉的,如江南的刺绣,如美人的罗衣。
立于荷前,似面对一位君子、一位仙人,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多余,所有的欲望都显得无聊,所有的杂念都显得浮躁。仅仅是片刻,虽处于闹市,却像置身事外。所有的所有,都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颗敬畏、平静、超然的心。灵魂终于挣脱绳索,偷得一时自由,重又见到那个初生的自己。
据说,莲与荷是一回事,就像母亲和妈咪一样,只是叫法不同。若真如此,我更喜欢荷的叫法。荷听起来有诗意、有文化、有内涵。莲却拙朴,无法引起联想。但睡莲却另当别论。睡莲之名让我联想到“睡美人”,不仅有诗意、有文化,而且梦幻、空灵,使人产生无限遐想。睡莲与荷是不同的。睡莲的叶呈近似圆的椭圆,叶面有一个豁口,如一把将合未合的圆形扇子,那个豁口恰似扇柄。它们静静地平铺在水面上,像一张张绿色的床。花朵躺在片片绿叶间,紧贴水面,与叶相依相偎。睡莲的颜色五彩斑斓,嫩嫩的黄、浓浓的紫、烈烈的红、淡淡的粉。她们真似一个个睡美人,着一袭罗裙,仰面躺于绿叶丛中、碧波之上。面容姣好,神色安详,长长的睫毛微微上卷,轻轻颤动,宛如蝶翼般撩人。清风徐来,睡美人随波荡漾,那份恬静令人心如止水。
由睡莲,想到江南的院子。在江南古镇大户人家的院子里,在沉入历史长河前,该是家家都有楼台亭榭的。那后花园的池塘,花厅前的流水,都会有一些睡莲飘浮其中。调皮的鱼儿在花叶间游来游去,不时打破睡美人的酣梦。于是,人们便创作出一幅幅鱼闹莲的工笔写意。北方的富户院子也不小,只是少了水,便拿一个个粗笨的缸,盛满水,养睡莲、鱼于缸中,也很有趣味。若下点小雨,雨滴落入池塘或水缸中,水面泛起圈圈涟漪。如空中恰好飞过几只雨燕,真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意境。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愿做一个采莲女,划一叶扁舟,穿行于田田荷叶间,在荷香的氤氲中,与荷共舞。
裙
夏,是女子最美的季节,因了一条裙子。每位女主人的衣橱里,不可或缺的便是裙子。女性的妖娆妩媚,娇艳娉婷,也离不开裙子。
夏季的美好对女性而言,就是可以穿裙子。
我人生的第一朵裙花,是在农家院子里开放的。那是条白底上印有桃红色小花的裙子,泡泡袖,齐膝,棉质,穿在身上既漂亮又舒适。那时我还生活在村里。那时的村庄很封闭,觉得裙子是城里人的专利,村里的女人们不仅自己不穿,也会笑话穿裙子的村里人,而且小孩也不穿。我也算是吃螃蟹的人。父亲是工人,母亲有亲戚在城里。来来去去,城市的风就吹进了母亲的心里。于是,家里的吃穿用度,也会时不时透出一些城市气息。我的裙子便是“气息”之一。那时我只有五六岁,但已知道炫耀。穿着裙子走在街上,同伴的眼神,大人的夸赞,都让我心里美滋滋的,也有一点点得意。穿着这条裙子,我还与城里的小姨合了个影。有晚,突然想起这张照片,翻箱倒柜,终未找到。时隔几十年,照片或许早已遗失,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清晰如昨。
该是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就不再穿裙子了,无论天气多么炎热。母亲为此常常数落我。现在想来,那是进入青春期的缘故。不仅我,同学们也如此。而且我的学生,今天的女孩子们,也大都如此。原本正值花季,却把自己深深裹藏起来。以为遮住的是丑陋,实际却是把美丽掩藏。青春就是这样矛盾和复杂。那时的我,总认为自己胖,身段不窈窕。现在翻出少女时代的照片,哪里胖了,不胖不瘦刚刚好。可那时就是不满意自己,于是就不穿裙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高考结束。
进入大学,似乎天地豁然开朗了,心也打开了,美丽的裙子也回归了。
年轻的我,偏爱白色。大学里的第一条裙子就是纯白色。连衣裙,泡泡纱面料,无袖,配一条黑色腰带,自认为很美。我曾穿着它在天安门广场留影,头上斜戴一顶淡蓝色草编遮阳帽,双臂交叉胸前,笑容灿烂,裙袂飘飘,有韵味,很艺术。在北京大观园潇湘馆的竹林边的一张照片,也是穿着这条连衣裙。微微侧身,露出脑后扎头发的手绢,笑容不大不小恰恰好,背景是浓绿茂盛的竹林,素净淡雅,很有意境。我洗了十几张,送于至亲好友。那时的我们,喜欢相互赠送照片。恋人如此,同学朋友亦如此。
除了喜欢白裙子,我还喜欢长裙。其实长裙并不太适宜身材矮小的人,可我只顾喜欢,不管效果。那是一条半身裙,长及脚踝。雪青色,像一汪浅淡的湖水。面料光滑柔软,如丝如缎,流光溢彩。每每穿上它,我就觉得自己是窈窕淑女,脚步款款移动,裙子翩翩起舞,飘逸灵动,像一片紫云,像一团青雾,像一朵烟霞。不知别人看着美不美,我心里是美极了。
婚纱的兴起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对于内地小城,这股“流行风”到达的更迟些。还好,正巧让我赶上了,便在结婚时时髦地穿了回婚纱。当时,整个小城也只有零星几家婚纱店。拍个婚纱照也就算了,真正在大婚之日穿婚纱者寥寥无几。我们家乡的传统是在婚庆典礼时不兴穿裙子,因裙与穷谐音,不吉利。西方的婚纱都是白色,意为纯洁无瑕。中国人以红色为喜庆的主打色,忌讳白色。因此,婚纱店的婚纱大多为红色、粉色、蓝色、黄色,少有白色。白色太前卫,家里绝对不允许,我也无底气冲破传统,于是便选了淡粉色。婚纱很漂亮,淡淡的粉,嫩嫩的,如春之桃花,夏之青荷,艳而不俗。整个裙身都是薄如蝉翼的纱,如烟如雾。裙摆长及地面,颀长却不拖沓。最妙的是下摆的边缘有一圈波状蕾丝,约半尺宽,如花托般把人整个托起,人像立于一朵粉努努的荷花中,亦仙亦幻。只是,婚纱是租来的,婚礼一结束,便匆匆归还了。
说到旗袍,就想到民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旗袍,是那个烽鼓不息时代的一点温柔。说来也有趣,据说旗袍的兴起既不优雅婉约,也不美丽浪漫,只是为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男女平等。民国是个纷繁复杂的年代,也是个魅力无限的年代。它如一坛老酒,入口浓郁,细品醇厚,回味绵长;似一曲长歌,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澎湃激荡;若一幅画卷,山险水急有,清风明月有,残荷败柳有。而旗袍便是那醇厚、那婉转、那清风明月。着旗袍的女人,自是高雅、曼妙、妩媚的。只要提到旗袍,民国就会从时间深处跳出来。随之跃于眼前的,必是一位头绾发髻、手执香包的娉婷女子。似乎,旗袍不只是衣服的名称,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能唤起人们无限怀恋的字眼。
20世纪90年代,旗袍又回归生活,但我也就是在近几年才感到它扑面而来的气息。而我,由最初的观望、羡慕,也终于成为亲力亲为者。我的衣橱里竟然也有两件旗袍了。每次见到店铺里的旗袍,总是不由驻足,仔细品味,用手抚摸,忍不住试穿,只是下不了购买的决心。除了价格原因,就是不够自信,缺少勇气。当我真正穿着旗袍走出家门时,还好,既无生人侧目,也无熟人嗤鼻。偶尔,还能听到朋友们的一半声赞许。这,也算是一次小小的超越自我吧。不管怎样,穿过旗袍,就不枉做一回女人。
早年有部电影,片名是《街上流行红裙子》。至今,我还从未穿过红裙子。“美人”已迟暮,能否着一袭红裙,擎一把油纸伞,飘逸于夏日街头?
呵呵!
伞
夏日里的主角还有伞。
伞花不只在夏季盛开,但夏季却是伞花绽放最多的时候。
儿时的村里,有伞的人家并不多。家家户户最常用的是草帽,既遮阳又挡雨还不占手。农人们下地干活全凭两只手,如果一只手里举着伞,又如何锄地割草?
城里人就很少戴草帽了。似乎草帽是农人的标志。刚到城里那会儿,大多数人家用的是塑料伞。我用的也是把塑料伞,淡绿色。阴天下雨,撑开它,就像春天里刚刚萌生的嫩绿,是阴沉沉的城市街道上的一点星。随着脚步移动,一闪一闪,给沉闷的天地送上一束光。
大约是十几岁的一个暑假,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知识竞赛的消息,出于兴趣,我答了题并寄出了答题卡。后来,竟然获了奖,奖品是一把自动伞。那是我第一次拥有了一把自动伞。当时,这算是个稀罕物,少有人有,我自然有几分沾沾自喜。这是把布伞,淡红色底上密布着白色小圆点,不甚好看。心里十分好奇,衣服见雨就湿,这布伞不会湿吗?这把伞我用了好些年,质量还是蛮好的。之后,伞也就更新换代了。塑料伞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自动伞因其身量小携带方便,备受青睐。起初,黑色伞居多,像我的奖品那样“带色儿”的也算凤毛麟角了。渐渐的,花色伞多起来。一到雨天,各色伞张开,一眼望去,真如一朵朵色彩斑斓的伞花。
不知何时起,街头兴起了遮阳伞。最初,爱美的女士们只是为了防晒,夏日有毒日头的时候,随便拿把雨伞遮挡一下。后来知道,大太阳下打伞,除了防晒黑,还防紫外线,也就是既美又健。于是,晴朗的白天打伞的人越来越多。有心的商家不失商机地开发出了新产品——防紫外线的名副其实的遮阳伞。仅从外观看,遮阳伞就与雨伞不同。用来制作遮阳伞的布料明显厚于雨伞的布料,有的遮阳伞面料呈黑色,据说是特殊材质。无论如何,作为一款新产品,很快走入寻常百姓家。盛夏的街头,伞花绽放,或清新如雏菊,或妖娆如桃花,或高洁如玉兰……千娇百媚,缤纷着夏日,美丽着城市。
伞作为装饰品,也是很能营造浪漫气氛的。在一些餐馆里,天花板上会吊许多漂亮的油纸伞,让走进餐馆的客人会觉得温婉柔美,如身穿桶裙的傣族少女正微笑着迎接一般,心情立刻舒缓开来,心底柔软的弦被拨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与亲密的人共度良宵,自是神仙般的享受。很流行的一句话,“人生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有油纸伞装饰的茶馆,自有诗意和品位。置身其中,暂时抛开眼前的苟且,尽情体味诗意与禅意,清茶一杯,知己一个,仙乐一曲,偷得浮生半日闲,便是神仙境界。
最温馨的伞花开在校园门口。无论是幼儿园,还是中小学校门口,下雨天,还没到放学时间,已挤满了人。个个都是一只手里举着一把伞,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伞,或伸长脖子向校园里张望,或时不时抬腕看看时间,或与旁边和自己一样等待的人拉几句家常。虽互不相识,心情却一样。漫长地、心焦地、无奈地、烦躁地等待,只为了心里牵挂的那个“宝”。时间一到,伞花齐刷刷开放,如果此时用无人机拍摄一下,那气势,一定十分壮观。
最浪漫的伞花开在公园里或林荫路上。两个身影紧紧拥在一起,一把小小雨伞,怎能遮挡住两个身体?没关系,火热的心,沸腾的血,澎湃的情,几滴雨又算得了什么?即使大雨倾盆,浑身落汤,也只会使两人相拥得更紧。那把伞花的花心,甜蜜、羞涩、缠绵,芬芳四溢,令人心醉。
最贴心的伞花开在商场、宾馆或银行的大厅门口。它们身体合拢,表情严肃,如门迎般静静立于伞架上,等待某个匆匆出门忘记带伞的人,等待某个突遇大雨手中无伞的人,等待某个身处异乡没有备伞的人。这是公共场所的细微关怀,贴心服务,是急他人所急的一点小用心,也是提升形象的一个小举措。但就是这些严阵以待的伞,如雪中炭旱时雨,为那些被雨止步的人带来了方便,送上了温暖,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最美丽的伞花开在那条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它美丽,因了它开在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手里。烟雨蒙蒙中,两边粉墙黛瓦,石板路湿润光滑,小巷幽静凄清。姑娘撑着油纸伞缓缓而行。她身着丁香一样颜色的长裙,周身散发着丁香一样的芳香,眉间结着丁香一样的惆怅,在细雨霏霏中像梦一般飘过,留下无尽的凄婉与迷茫。那把油纸伞,如玉石雕塑般,永久地美丽着、芬芳着、静默着……
冰 棍
小时候,冰棍是城市孩子的专属,村里的孩子只能在电影里看到。比如《黑三角》里的那个老太婆,推着一个带着轮子的木箱子,箱子顶端盖着厚厚的白色棉被,棉被下面就是一根根冰棍。既然冰棍是冰,大热天,又盖着厚厚的棉被,不会化了吗?我的小脑瓜是想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当然,长大以后,课本知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冰箱、冰柜在大多数人头脑里是没有概念的。事实上,连电影里都是推着木箱子卖冰棍,估计全国上下也没几个人知道冰箱、冰柜为何物。
有幸,在童年的尽头,我来到了城市。于是,像其他城市孩子一样,我深深迷恋上了冰棍。
那时的冰棍呈梯柱形,上窄下宽,约四寸长。用纸包裹。纸上印着浅浅的粉色或蓝色图案。冰棍有两种,一种含奶,一种无奶。含奶冰棍五分钱一根,无奶冰棍三分钱一根。无奶冰棍估计就是水加糖,能明显感到水的清淡与寡味。若无糖的话,根本就是冰块。含奶冰棍的口感就好多了,不仅甜,且有些黏稠,不甚爽口,却有味道。父母给的零用钱是有限的,含奶冰棍只能偶尔食之,大多时候吃的还是无奶冰棍。
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对冰棍很贪婪,把大部分零用钱都花在了买冰棍上。校门口的小商小贩会向学生们兜售各种零嘴,有酸枣、爆米花、糖瓜、瓜子等,比起现在孩子们的小吃食,这些东西要环保绿色得多。每次,父母只给几分钱,最多时候也就一毛钱。我也会买酸枣之类的零食,但更多时候还是买冰棍。
我吃冰棍的速度很慢。同样长短的一根冰棍,别人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我却还有半根。长大以后仍是如此。我常常会惊讶别人怎么会吃得那么快,至今不解。质量好的冰棍,吃到最后还是硬硬的,不会像蜡烛一样“泪流满面”。质量差一些的冰棍,融化的速度比我吃的速度快。刚吃到一半,就“身子”发软,浓稠的液体直往下滴。常常不是滴到衣服上,就是弄得满手都是,粘哇哇的,令人心烦。更糟糕的是,冰棍在制作过程中,用来作“把儿”的小木棍有时没放周正,不是偏“头”就是向“尾”。随着冰棍“身体”的缩短和融化,剩余的部分偏离了“主心骨”(冰棍把儿),让人猝不及防地掉到地上,捡又捡不起来,急得人直跺脚。
小学高年级开始,我便下决心不再买零食(包括冰棍),把父母给的零用钱攒起来。至于攒起来做什么,似乎心里也不是很清楚。我很惊讶自己的自控力,竟然真的做到了不买零食。因此我攒了许多钢镚儿。父亲把这些钢镚儿按币值分了类,摞成一摞,用报纸卷好,这样既容易清点,也容易保存。父亲曾拿着钢镚儿到银行里兑换过。婚丧嫁娶用过一些,现在还剩一些,放在一个铁盒子里。这些钢镚儿已不能流通,只是作为一种记忆存于某个角落。
后来,属于我们童年时代的冰棍永远地被淘汰于历史的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满目的雪糕、冰糕、冰激凌。这些冰品的包装纸风格各异,有简约的田园风,有可爱的小清新,有时尚的咖啡派,还有传统的豆沙绿。形态也别出心裁,或是“一把火炬”,或是“一只小熊”,或是“一根玉米棒”,或是“一根香蕉”,都惟妙惟肖。最最诱人的,还是味道。自从冰棍升级为冰糕、雪糕以来,其味道也随之丰富起来,巧克力味、柠檬味、香草味、奶油味……不胜枚举。不论哪种味道,都十分地道。黏黏的,滑滑的,甜甜的,香香的,绵绵的。尤其在炽烈的夏日,一股凉爽由口入心,自是十分惬意。
这个老少皆欢的小小食品,为缤纷夏日增加了一个美丽的注脚,使得其更浪漫,更欢快,更舒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