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果子
2021-12-16春晨
◇春晨
爸妈的工厂因原料断顿,停产了。上级领导研究决定,全体干部职工及家属倾巢出动去支援生产原料的兄弟单位,厂子里除了看大门的俩老头再无一人。
那一年,我读小学四年级,随爸妈去了一个叫武家坡的山村,那里有一座硫铁矿,出产爸妈工厂需要的原材料。姐姐读初中寄住在亲戚家,我们在武家坡待了半年之久。
武家坡村子拥有百十户人家,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川”字形的山坡上,厂部和村里取得联系,凡带家属的职工分在各村民家里暂住。
我家的房东是两位上了些年纪的老人,他们热情地为我们腾出一间屋子,帮着搬东西并絮絮叨叨地说:“放心住吧,缺甚,吭一声。这间屋子当年住过红军……”
房东膝下有一双儿女,年龄尚幼,不知内情的人,乍一看,像是祖孙辈分。
房东老汉说:“新中国成立前,俺穷得连个刨地镢头都没有,土改时才分得一眼窑洞和你们住的这间平房,俺一块石头一撮土垒起了围墙,成了现在这个小院。”
爸妈在家的时候常和房东两口子拉家常叙旧事,“俺是修起这院子才敢张罗娶媳妇。俺们都是穷苦人没甚讲究,到一搭过日子就行。”房东老汉指着在一旁坐着纳鞋底的女人说,“没想到结婚两年才生了个妮,急得俺们跟甚似的。”
爸不解:“生下孩子是喜事,为啥急?”
老汉一本正经地说:“光有妮不行,没有小子咋传宗接代?会被人笑话看不起!当时她也岁数不小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生?”女主人像是做错了事,红着脸低头做活再也不敢抬起来。
爸笑着给他们解释:“如今新社会,闺女小子都一样,我就俩闺女没小子,觉得挺好嘛!”老汉固执地又摇头又摆手,连连说:“不行的,不行的!农村跟城市不一样。”
我在屋里写作业听见爸这样说心里很高兴,庆幸自己没生在农村。
房东老汉又很有经验地告诉爸:“头生要是个妮,给妮起名顶重要,俺给妮取名牵弟果然叫灵了,真的有了个小子!要是取名叫个花呀草呀的肯定生不下小子。”老汉自觉很有水平很有见识的样子,“光景过得有房有地,有儿有女,还不红火?还想咋!”
房东老人的女儿牵弟比我小一岁,个子却到我肩头,瘦瘦小小的像一株细细的玉米秆子。瓜子型脸上嵌着两只黑乎乎的大眼睛占去了近半张脸,鼻子和嘴都显得很小。两条一尺来长的辫子系着红头绳打着花结,干活时两条辫子甩来甩去像两只蝴蝶在飞舞,很好看。
牵弟的弟弟比她小四岁,是房东两口子费了老大劲才得的宝贝儿子,两人的重心都扑在儿子身上无意中忽视了闺女,牵弟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很多家务事,如今已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每当看到牵弟干练利索地干着家事,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不知是好奇羡慕还是怜悯同情。
那时候,全国一窝蜂地食堂化,武家坡也积极筹备吃大锅灶,各家各户的炊具都交到村委会,只留下领饭用的盆碗筷。
房东老汉极神秘地问爸:“我说兄弟,这敢情就是共产主义了?”
爸很拿不准:“是……嗯……反正是朝那道上走哩。”
房东老汉疑疑惑惑,不知是点头还是摇头,极留恋地和牵弟妈把那些东西也交出去了。
集体化大锅灶生活省去了女人们一日三顿饭的烦琐杂事,家庭主妇们欢喜雀跃,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为牵弟得到解脱而拍手欢呼,她终于能和我在一起玩玩了。可她很不贪玩,总在屋里打转转,偶尔和我在一起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很让我扫兴,这个小伙伴满身都是大人味。
集体食堂的饭菜太丰盛了。早饭:炸米、糕炸、油条、白面疙瘩汤;午饭:过油肉拉面、烙饼;晚饭:米汤、馒头、葱花卷、炒菜。村民们吃得满嘴流油,可惜的是剩饭剩菜到处都是。村干部们天天开会,会后总要在饭桌上讨论工作。
食堂大吃大喝了一阵子便奄奄一息,只能开出小米稀饭玉米面糊糊一类的东西。村民们不再浪费力气地聚一起评论饭菜的咸淡与口味的好赖,各自为填饱肚皮挖空心思地操劳奔波。
牵弟大和妈都是老实巴交的人,他们没有别的能耐只能依靠从大队食堂领回的食物度日。食堂的饭菜一天不如一天,从早饭是稠糊糊的玉米面撒,后来彻底成了一日三顿玉米面糊糊,午饭略稠一些。
牵弟大从食堂按规定的数量领回来饭再交给牵弟妈重新分配。牵弟妈非常慎重地握着一把勺子掂量来掂量去:男人是顶梁柱,是天,不能倒,多舀一勺;儿子是根说什么也得保住,又多舀一勺;妮子呢,虽说长大是外人可也是自家身上掉下的肉,家里大活小活离不了她,把孩子拖累得瘦肋巴筋光长岁数不长个。牵弟妈鼻子一酸,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手里的勺子不由地又多舀一勺。都打点好之后,锅里底朝天了,牵弟妈赶紧把锅端在一边对家人说:“趁热快吃吧”粗心的男人和不懂事的儿子急不可待地端起碗吸溜咕噜地吃了,唯有牵弟迟迟疑疑地走过去,端着自己的那一份递给母亲:“妈,你吃这吧,俺吃锅里的。”
“我吃锅里的!”牵弟妈一把将锅夺过来。
“妈……”
“妈!俺没吃饱,还要吃,还要吃!”不知足的儿子还不懂得心庝母亲和姐姐。
牵弟妈为难地看看儿子,又看看锅里。
“来,姐给你。”牵弟把碗里的饭拔了一半给弟弟。
“牵弟!你……”
牵弟一声不吭地端着碗走开了。
“唉……”牵弟大长叹一声,拿出烟锅子,耷拉着脑袋抽闷烟。
那时候,工厂的职工家属都干临时工,妈在厂食堂负责摘菜洗菜切菜,这工作是极令人羡慕的。妈的人缘好,爸和我的领饭盆里每天都有极深的奥妙。尽管如此却仍然满足不了我的食欲,肚子像个无底洞总也填不满。妈每晚会带回一个小窝头供我度过那漫长难熬的黑夜。
入春以来,干旱连月,老天爷幸灾乐祸似的不给一滴雨,好容易发了慈悲又很吝啬,只湿了湿地皮。土地爷很知足,很快长出了绿油油的苗苗来。
这可喜坏了以土地为根本的庄稼人。
人们疯狂地奔往各处角落,寻找挖掘这些绿苗苗填肚子充饥。可怜那些绿色生命刚一露头便莫名其妙地夭折了。
村干部着了急,慌忙派出人去看护庄稼、果树林,并贴出了告示,违者如何如何。说得很邪乎但很起效,庄稼地、果树林果然没人敢祸祸了。
人们只能漫山遍野地挖野菜,野菜越挖越少,土地爷再慷慨也不会接二连三地往外冒,人们渐渐地陷入了饥馑蔓延的危机。
牵弟妈病了,我奇怪她总是溜锅底,有一口没一口的怎么反而胖了呢?胖得无法无天样子很吓人。妈说这是浮肿,村子里很多人得了这种病。我很恐惧,爸妈不在的时候一个人缩在屋子里不敢出来,极无聊地翻看小人书。
乡村的学校本来就很松散,学生想去就去,不去也没人过问,如今,离放暑假还有好些日子,学校却莫名其妙地停课了。
晚饭后,村子里的大喇叭响了,呼唤人们去各大队分领杏子桃子,每人各二两。
喊声刚落,院子的大门“吱扭”一声开了,想必是牵弟大出去了。
一顿饭的工夫,牵弟大回来了,隔了一会儿,送过来一个杏子,给我的。“给妮尝个稀罕”爸客气一番收下了。牵弟大走后,妈递给我,我觉得这很像是牵弟的一只眼睛,黑青黑青地瞪着我,皮色一点也不诱人。我咬了一口,很酸、很涩又很苦,没有一点果香味,我不想吃,递给妈。妈看了看,叹口气:“这杏子本来就没熟”但还是咬了一口又递给爸,爸彻底把它吃了,末了说:“再酸再苦也得吃,人家当宝贝似的送给咱,好意思扔了?那不造孽!”
自从牵弟妈病了,妈三天两头过去看看。后来,牵弟妈越来越厉害了,妈反而去的次数少了。我明白,妈的问候只是一种虚伪的关心,一点实惠也没有,是不济事的。我有好几次发现,妈晚上回家从兜里给我掏出那个小窝头时,犹犹豫豫很不爽快。我能猜出妈的心思,妈很想周济给牵弟妈,但我却极自私极贪婪地紧紧握着不放,妈的动机被我一次次击败,败得那样可怜连一次成功的机会都没有。
一天晚上,牵弟到我们屋子送还小人书。她经常给弟弟借小人书,为了不消耗弟弟的体力,牵弟循环地把我的小人书拿给弟弟看。那个傻弟弟始终被姐姐这种善良的圈套蒙蔽着,总以为姐姐拿回来的书是新的,从没看过的,一天到晚坐在炕上津冿有味地翻看着。
牵弟放下上次借的又随意拿了几本,正要走,妈推门进来了,看见牵弟,忙从衣兜掏出小窝头很果断地掰了一半塞进牵弟手里,牵弟执意不要但妈决不松手,牵弟睁着两只晶莹晶莹的眼睛望着妈,不等眼泪掉下来猛地一转身快步走出去。
望着牵弟的背影,妈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懂事得总让人心酸”
我没有怪怨妈,觉得妈像救世主一样的高尚。我激情地想,如果明天或是后天,牵弟来还小人书时,希望她晚上来,我要像妈一样亲自掰一半窝头给她,做一次伟大的行动给妈看看。
第二天,第三天牵弟都没有来,不知怎的,我却暗暗庆幸,可是,这种庆幸很快成了一种懊悔,直到如今。
三天后的傍晚,院子“哗啦”闯进来几个人,气势汹汹地进了牵弟家把牵弟大连拉带推地带走了。爸妈和我都吃惊地跑出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听那些人甩下的一句半句,好像是牵弟偷摘了队里的果子被逮住了,把牵弟大叫去不知要怎样处罚。我们急忙进了牵弟家,见牵弟妈躺在炕上默默地流泪。妈询问了几句,可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们不好再问下去,安慰了几句,出来了。
爸妈睡不着,我也睡不着,我们在小屋焦急地等待。
很晚了,听见院门被推开的声音,我们一起奔出去,见牵弟大耷拉着脑袋疲倦地走进来,后面跟着牵弟,手里提着个篮子。爸忙走上去轻声问道:“老哥,咋样?不要紧吧?”牵弟大被爸这一问竟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两只手哆哆嗦嗦地搭在爸肩上,很悲哀地说:“兄弟,俺活了几十岁可是清清白白的呀!再穷再苦也没拿过别人一根线毛毛。没给祖宗丢过人……”他转回身指着牵弟恶狠狠地说:“今天让这死妮子丢尽人、败尽兴了!俺……”牵弟大呜呜地哭起来:“俺没脸到人跟前了……呜……呜……”爸很理解地点头道:“老哥,算了,孩子还小……哎,队里咋处理的?”一句话又勾起牵弟大的愤怒,他气得顶直了身子,声音也高了起来:“咋处理?当着大家伙的面把俺数落得里外不是人!说前几天刚分了杏子桃子咋又馋得管不住嘴了?再馋得慌就等不迭长熟了再吃?哪次分东西落了你们啦?”牵弟大委屈地说:“兄弟,上次分得果儿那哪熟了?熟的果儿轮不到俺,还不够他们分哩!俺知道,每次分的果儿不可能全是熟的,那也是熟的多,生的少,搭配着分不就行了?哪怕你们熟的多,也得给俺一两个熟的吧,不能给俺全是生蛋蛋,这不欺负老实人吗?”牵弟大抬起手抹了把泪:“欺负就欺负吧,不就几个果儿吗?俺不跟他们计较,念在共产党分给俺房子分给地,俺才活得像个人,娶了老婆有了儿。”
爸看到牵弟大心情缓了下来,说:“老哥这样想就好了,快回屋歇着吧,太晚了。”谁知牵弟大一屁股坐在院子的木墩上又气又急地抬头跟爸说:“兄弟,他们还要扣掉俺二十个工分……二十个呀!让那死妮子摘的这几个黑青圪蛋给顶了,一个果儿扣一分,你说坑人不坑人……呜……呜……”牵弟大伸出俩手指一个劲地摇晃。
爸也觉得太过分了,但这是村大队的事,自己不好说什么只能劝慰。
牵弟大哭着说着猛地脱下只鞋照牵弟头上狠劲地摔打,牵弟被惊吓得直了神,她没有躲闪。妈实在忍不住了,扑过去护住牵弟,牵弟大甩过来的鞋子落在妈身上,他只好住了手。
妈和我护着牵弟,爸劝着牵弟大,总算把他劝得回了屋。
半夜,我们又被牵弟一家子给折腾醒了。
原来我们走后,牵弟大像钻了牛角似的仍然怨气难消,非逼着牵弟把那二十个果儿吃下去才可罢休。
牵弟没等吃完,肚子就翻江倒海地难受起来,可怜牵弟虚弱的肠胃经不起这些生果儿的突然袭击,肚子疼得惊天动地,在炕上痛苦地滚来滚去,大颗大颗的汗珠往外冒,急促地喘着粗气。
我们都惊呆了,爸急得连连跺脚:“老哥!你好糊涂啊!咋忍心往孩子身上撒气!还不快去叫医生,耽搁了,会要命的!”
牵弟大一听急得两腿瘫软,反而蹲下来不会走了。爸见状,拔腿就往外走,边走边回头命令众人:“你们快收拾收拾,我去叫厂里的汽车,送牵弟到医院!”
说是众人其实就妈和我,牵弟妈根本指望不上。惊慌失措的妈和我得到指示,立刻手忙脚乱地摆弄牵弟。
但是,牵弟没有等来爸叫的汽车。
牵弟用尽所有的力气,绝望地看了看病重的母亲,微弱地叫了一声:“妈……”牵弟妈已哭成泪人。牵弟又望着蹲在地上捶打着脑袋后悔莫及的父亲,叫了一声:“大……”牵弟大抬起泪涕满面的脸,连连应着:“哎,哎……”牵弟望着被吓得缩在墙角的独根苗弟弟,弟弟正惊恐地瞪着她,嘴里喃喃着:“姐……俺再也不吃果果了,俺不要你去摘果果了……”牵弟想跟弟弟说什么,可肚子疼得她已张不开嘴。
牵弟可能还想挣扎着看看我,就在朝我扭头的一刹那,她失去了已剩不多的力气和意识,眼睛往上一翻,两只大大的黑眼珠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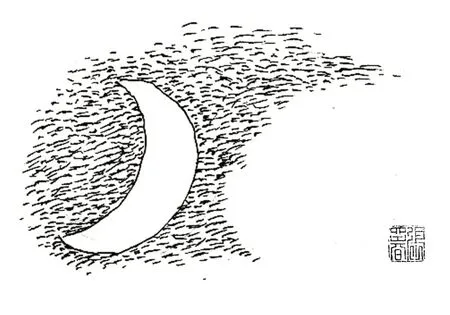
牵弟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慢慢地没有了痛苦扭曲的表情,安静了,一双没有黑眼珠的眼睛向上翻着,妈哭着用手把牵弟的眼皮抹下来,她死了。
屋里只静了几秒钟,无声的流泪变成了哭喊声……
牵弟死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村子里的喇叭又在呼叫人们去分领果儿瓜儿什么的,并一再声明果儿瓜儿都是熟的没有生的。
没有听见院门被推开的声音,爸妈同时停下手里的活儿对望了一下,他们明白,牵弟大没有出去,没他的份了。
这喇叭声激起我对牵弟受到不公的愤慨,她本不该这样小的年纪就死掉,可我又茫然地不知该怨谁,我又奇怪这地方分东西为什么总是在晚上,好像有什么见不得人似的。
我敢肯定,今天晚上分的果儿瓜儿熟的少生的多,因为天黑,谁能看清那些果儿到底熟没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