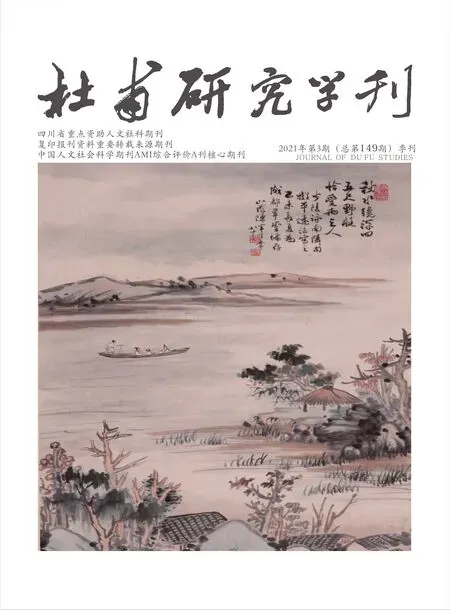草堂人日我归来
——写于《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年之际
2021-11-12周裕锴
周裕锴
作者: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610041。
因为疫情,今年“人日”我又没有去成都杜甫草堂朝圣,心中未免感到歉然。屈指一算,我跟草堂在学术上的结缘已经四十周年,至于首次参观杜甫草堂,更早在五十年前。记得那时从青羊宫向西走出一环路不远,就已到郊外,浣花溪畔是一片农田菜地。茂林修竹掩映着古朴的杜甫草堂,园中桢楠参天,幽兰芬郁。“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这真是一处值得流连的胜迹。那时的大雅堂还是草堂寺的旧址,堂中挂满楠木镌刻的名人书法,皆是抄录的杜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工部祠前清代四川学政何绍基撰写的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从那时起,草堂就向我展现出她那不同世俗的神圣和亲切。当时我在读初中,也见过不少古迹文物被毁,但草堂是个例外,因为她不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成都人引以为荣的胜地,甚至可以说是安顿灵魂的一处圣地。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再也不是杜甫草堂来去匆匆的游客,而几乎成为她终身的朋友和家人。1980年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读大三,因写学年论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古代文学专业。那时的大学本科生,要先后完成学年论文(大三)和毕业论文(大四),才能取得学士学位。辅导员干天全老师把我分配给张志烈老师指导,特意介绍说:“张老师年富力强,很有才华,写诗填词都很在行,跟着他做论文会很有收获。”初见张老师,我立即产生好感,他声音洪亮,为人热情爽朗,更重要的是,他对学生极好,这是某些大牌教授所不具备的。这次学年论文写作对我非常重要,从此以后,我跟张老师建立了长达四十年的师生情谊。
张志烈老师出的学年论文题目中有两个是关于杜诗的,一个是论杜甫的咏马诗,另一个是论杜甫的咏鹰诗。我当时省吃俭用买了一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先浏览一下目录,发现杜甫的咏马诗多于咏鹰诗,此外也因为自己属马,对马更有感情,所以就最终选择前者作为论题。张老师出的题目本身就很有诗意,直接用杜甫《丹青引》里的名句“一洗万古凡马空”为标题,副标题是“谈杜甫的咏马诗”。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把《杜诗详注》中所有的咏马诗(含题画马诗)按年代逐一找出来抄写阅读,发现杜诗中马的形象寄寓了诗人自己的身影,从骏马、瘦马到病马、老马,从青年时代的开朗豪迈到中晚年的沉重凄楚;同时杜甫的咏马诗也具有表现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象征意义。张老师读了我稚嫩的论文,感到很满意,用骈文写了一篇评语,文采斐然,这是我数十年来看到的最有特色的论文评语,可惜我只记得起“穆王八骏”“昭陵六图”以及“不难万里之选”等三句。最后这句是老师对我的殷切期望。
张老师把我的论文推荐给《杜甫研究学刊》的前身《草堂》杂志编辑部。此后的具体过程我不太清楚,听说是《草堂》的副主编刘开扬教授读了拙文,大为赞赏,与编辑部濮禾章等先生商量,最终将拙文安排在《草堂》1981年第2期发表。我当时不认识刘开扬教授,只读过几篇他在唐诗和杜甫研究方面的论文,非常崇敬,能得到他的青睐,实为我之幸事。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作为一个大学本科生,能与自己仰慕的老学者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文章,真有点不可思议。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中国学术环境最为干净的时代,即所谓“科学的春天”。不少老一辈学者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目睹学术界一片凋零的现象,急于培养人才,奖掖后进,以尽快振兴中华文化学术。我非骏马,却遇伯乐,实在是幸运之至,从此对《草堂》以及前辈学者充满感恩之心。
最难忘的是1981年4月,成都杜甫学会首届年会在杜甫草堂召开。暮春天气,景色宜人,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作为初出茅庐的学生,我荣幸地受邀参会,见到很多仰慕已久的知名的老学者,如缪钺、屈守元、杨明照、成善楷、王仲镛、钟树梁、白敦仁、王文才、刘开扬、金启华、叶嘉莹等先生,一时盛况空前。还记得叶嘉莹教授当年声情并茂地讲杜甫《秋兴八首》,讲到“每依北斗望京华”时,竟潸然泪下。这次年会上,我认识不少研究杜甫的学者,也结识了不少杜甫草堂以及《草堂》编辑部的朋友。可以说,跟杜甫草堂的结缘,使我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学术之路。
1982年初,我考取了成善楷先生的研究生,跟随先生读《诗经》和杜诗。成先生的研究和讲义集结成《杜诗笺记》,在巴蜀书社出版。更重要的是,成先生的诗词造诣很高,学杜而得其骨髓,对我影响很大。读研期间,我还在川大历史系旁听缪钺、叶嘉莹先生联袂主讲的唐宋词。这些读书求学的机会,多少都跟草堂的杜甫学会年会有某种机缘。
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参加过几次杜甫年会,陪同过韩国学者李炳畴教授、中国台湾学者张高评教授等参观杜甫草堂,还为一些学界朋友当过导游。在1990年的年会上我认识了日本学者浅见洋二教授,十一年后,他邀请我到日本大阪大学做客座研究员,这也是由草堂成就的一段学术友谊。遗憾的是,由于四川大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我先后参加《苏轼全集校注》和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科研项目,到杜甫草堂参加学术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对此深感惭愧。在《草堂》首次发表论文后,四十年间我只有寥寥四篇论文以杜甫为题,其中两篇在《草堂》改名后的《杜甫研究学刊》上发表,一篇是《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杜甫与江西诗派》(1990年第3期),另一篇是《杜甫诗中的儒家情怀及其思想渊源》(2017年第2期)。其余两篇分别是《试论杜甫诗中的时空观念》(《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和《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四川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新华文摘》2018年第3期)。
尽管我在关于杜甫研究方面乏善可陈,但必须要说明的是,在我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杜诗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我的学术和人生始终具有最重要的潜在影响。我的书斋里,除了仇兆鳌《杜诗详注》,还有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金圣叹《杜诗解》、洪业等编《杜诗引得》(含宋人《九家集注杜诗》)以及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我并不只是把杜诗当作单纯的古典文献,而是将其视为能引起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视为最重要的灵魂导师之一。
自从在川大留校任教以来,三十多年间,我开过与杜诗相关的课程,先后有硕士生周瑾、李贵、温煦的论文曾在《杜甫研究学刊》发表。在指导过的博士生当中,有三人以杜甫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即杨经华的《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刘欢的《杜诗赵次公注研究》以及陈婷的《经典与形塑:绘画中的杜甫研究》。博士生杨经华、马强才和刘欢等人也曾在《杜甫研究学刊》上发过文章。另外,我为研究生开设唐代诗歌研究课程,学生期末作业中以杜甫为题的优秀文章,有的接受我的建议给《杜甫研究学刊》投稿。我曾参加川大学生的杜甫读书会,师生共同研读杜诗。而草堂举办的硕博论坛,我忝为评点者也参加过一两次。我希望自己的学生,能从文本阅读中领略杜甫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海涵地负的艺术成就,培养自身的精神人格和审美能力,以及关注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
在我撰写的两部学术著作中,有不少关于杜诗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把杜甫放在中国诗歌史和阐释学史的视野下来讨论。在《宋代诗学通论》中,好几个章节涉及宋人对杜甫诗歌的讨论和继承。至于《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一书,更从历代杜诗注释本和评点本中提炼中国文学阐释学的观念和方法,成为该书立论的重要内容。而这些都得益于《杜甫研究学刊》多年来给予的刊物馈赠,以及当年成善楷和张志烈两位老师在杜诗研究方面给我打下的基础。
这几十年来,杜甫草堂一直以其广阔的胸怀给予我包容和爱护,这里有我的师长、朋友,也有我的学生,友谊令人铭感。《杜甫研究学刊》编辑换了几届,老编辑退休殆尽,但每次我到草堂,都像回到家里一样,感到特别亲切。当年令人景仰敬佩的老一辈学者大多已仙去,我的导师成先生也在三十二年前魂归道山,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还浮现在我的眼前。翻阅四十年前杜甫学会首届年会的照片,恍如隔世,不免唏嘘。令人欣慰的是,在杜甫草堂的支持下,杜甫学会日益欣欣向荣,成果丰硕,《杜甫研究学刊》也成为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刊物。另有不少比我当年还年轻、学历更高的年轻人加入了杜甫研究的队伍,这不仅是后继有人,而且定会后来居上。而《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诸君,也像当年老一辈学者和编辑一样,慧眼识珠,薪火相传,守住并拓展杜诗的“大雅”之境!
今年正月初七人日那天,我曾在杜甫研究学会一位朋友微信圈发的草堂照片下留言:“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难来。”想想实在愧对老杜。在此谨立誓言:草堂的人日,我定会归来朝圣,就在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