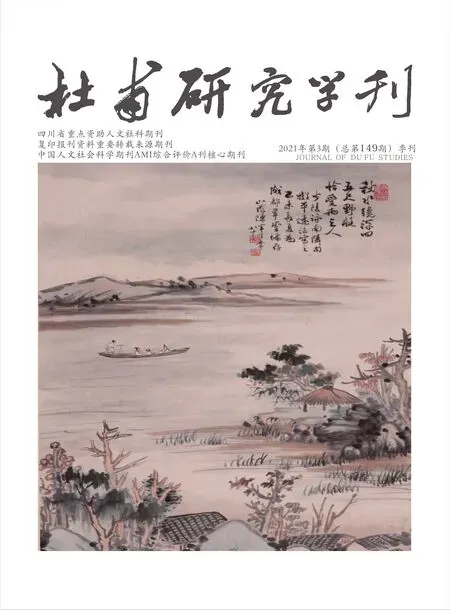文字与想象的交汇
——论王昌龄七绝中的影像叙事
2021-11-12徐韫琪
徐韫琪
一、“蒙太奇”与诗的碰撞
纵观王昌龄一生的诗歌创作,其七言绝句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盛赞:“七言绝句,贵言微旨远,语浅情深,如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开元之时,龙标、供奉,允称神品。”王昌龄对诗歌的立意构思极为讲求,正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言:“昌龄工诗,绪密而思清。”前辈学者多从诗歌批评的传统角度讨论王昌龄七绝的艺术成就,受莱辛《拉奥孔》的启发,笔者试图超越文与图的界限,从影像叙事角度剖析王昌龄七绝的独到之处,以期有所深入。本文讨论的“影像叙事”,其核心是以文字介入读者的审美想象,将声音、光线、构图、色彩、节奏等感官因素涵盖于若干个“诗歌镜头”中。马塞尔·马尔丹曾指出影像的两层内涵:第一种是直接的、可以鲜明地看到的;第二种则来自于画面中虚拟的象征意义。第二种虚拟内容所传递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也是诗歌的精髓所在。这与中国古代诗论中“兴象”概念有契合之处,它要求艺术家透过外在物象的描绘,展现出作品内部丰富的蕴含和深远的艺术境界,即“兴在象外”“含不尽之情于言外”。读者需要根据形象的细节去揣摩、玩味文本,并借助自身想象完成与诗人的互动,开拓出“象外”的世界。首先不妨以影像理论中的“蒙太奇”手法为切入点,一窥王昌龄七绝中的关于时空与感官的综合调度及鲜明的“镜头感”。
“蒙太奇”(montage)即镜头的剪接,是指将一系列在不同地点、距离、角度,以不同方法拍摄的镜头排列组合起来,用以叙述情节和刻画人物的艺术表现手法,细分为叙事蒙太奇、隐喻蒙太奇、心理蒙太奇等。它不仅是操纵时空的技术手段,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戴锦华指出,“这(注:蒙太奇)不仅是一个在连续的时间幻觉中‘复原’一个现实空间的过程,而且是创造、建构出一处迷人的幻觉时空的过程。”笔者试将七绝中的每一句视作一个由众多意象群构成的“诗歌镜头”,句与句之间既可以是镜头切换关系,也可以是景深延续关系,整首诗即由镜头转换、延伸构成,其美学含义正产生于镜头与镜头的组合和撞击之中。诗人须努力超越语词的局限性,通过采集意象、构图等“造境”方式将文字扩充成影像,并赋予凝固的诗歌意象以流动感,从而开拓含蕴更为深邃的诗境。
王昌龄擅长的边塞类七绝流露出盛唐的英雄主义思潮,他以慷慨的气度连接历史与当下、想象与现实,构筑了宏阔的时空维度,使情感内涵更加厚重凝练。这类作品中体现的时空调度意识已经相当成熟,如被后人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的《出塞二首》(其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诗人巧妙地从千年前切入,打破了连续的时空叙述,使前于被述时间发生的场景成为意义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过往时空与现实世界的对立隐喻着霸权的脆弱和短暂,明月与关塞默默见证了连绵不断的征战,月亮盈虚的周而复始与士卒一代代身死沙场的宿命形成同构,寄托着诗人深切的关怀和思索。黄叔灿《唐诗笺注》指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七字天造地设,诂训不得……秦筑长城,汉亦戍守,关山明月,同此悲凉;万里征人,迄无还日。”悲壮氛围的背后亦隐含着士卒们立志报国的慷慨与豪迈,正如诗评家顾璘所言,“音律虽柔,终是盛唐骨骼。”
感官的综合调度是王昌龄七绝中不可忽视的特色。在短短28个汉字中,诗人往往能够以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多重角度丰富诗歌涵义和读者想象力,突破文字表达的一维局限,吸引读者进入更加真实可触的影像化诗境。如被誉为“代为之思,其情更远”的送别诗《送魏二》: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诗人用文字延伸了读者感知的途径,并充分调动身体感官:首句嗅觉入境,恰合醉酒后其他感官暂时模糊,唯有嗅觉正常运转的情状,迷蒙之中,隐约飘来的橘香伴着舟外的雨声入梦,听觉又渐渐苏醒。微醒后诗人又念起送别友人的感伤,从“不知愁”到“愁”,酒醒后凄哀的猿啼渲染了悲凉的氛围,全诗围绕着“醉”写出了一番别样的复杂别愁。“忆君”句的心理蒙太奇赋予声画形象强烈的主观性,画面的跳跃揭示诗人内心的遐想与惋思。
在王昌龄众多脍炙人口的诗作中,几乎都有“以景结情”的表现手法,它将读者的想象定格在某一特定场景中,类似于影片结尾的特写镜头,试图唤醒读者的共鸣。与七绝萌芽时期西晋的七言歌谣相比,诗人在结尾处隐藏了个人情感与诗歌旨归,因而这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结尾方式在保留“能指”的基础上开放了文本的最终“所指”,提供读者介入的更多可能。如广为流传的《从军行七首》(其二):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尾句“高高秋月照长城”以一幅含蕴无限的夜景收束,如同影片结尾处意蕴深长的定格镜头,月下思归的戍人竟夕凝伫,愁思之深言不成句,眼前唯有明月高悬。诗中含蓄缠绵的情感在定格之景的烘托下进一步蔓延,黄叔灿评其尾句“‘高高秋月照长城’,妙在即景以托之,思入微茫,魂游惝恍,似脱实粘,诗之最上乘也。”又如描写失宠妃嫔的《西宫春怨》: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
朱之荆盛赞尾句语脉深曲:“只写到‘昭阳’二字便住,妙有可望不可即之思,彼之多少恩宠,在所不言。”这种“不言”之韵不妨视为镜头剪辑中过渡性的手段——渐隐。“渐隐”即一个镜头的画面渐渐隐没在黑暗之中的过程,它是一种介入到表意的视觉语言,意味着一段时间的流逝,在文本末尾亦传递着某种前途未卜的茫然,而“朦胧树色隐昭阳”所传递的审美感受正是一种“余音袅袅的心理或时间体验”。当深夜的层叠树色将远处的宫殿渐次隐没,似乎也意味着女子内心希望的慢慢湮灭,而视觉影像与心理感受的同构渲染了黯然神伤之情。
受到绝句篇幅的限制,诗人需在尾句启发读者产生更多联想,因此早期七绝产生出递进、因果、反问、否定等多种结句形式,然而这些结句方式带来的僵化与拘束限制了诗境的开拓。王昌龄则努力探索以景语结情的策略,营造开放空阔的意境,从而产生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以景结情”的表现手法在《诗格》中也得到了强调,这种“境生于象外”的含蓄蕴藉之美被诗人总结为“十七势”中的“含思落句势”:“含思落句势者,每至落句,常须含思,不得令语尽思穷。或深意堪愁,不可具说,即上句为意语,下句以一景物堪愁,与深意相惬便道。仍须意出成感人始好。”“以景结情”令诗中色彩、构图、内在的感情流动都和谐地统于一体,营造出空灵蕴藉的诗歌境界,“使深心人于言外领会,意境既超,婉而不露,此其七绝所以独冠三唐。”
二、诗歌叙事:组合段的视角
“蒙太奇”与叙事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张力,如巴赞认为使用蒙太奇会限制影片的多义性,故而主张用长镜头和场面调度保持剧情的完整性。诚然,各种意象符号的堆砌不足以构成优秀的作品,创作者需要对一系列符号进行合理组接,使所呈现的画面具有故事性,完成情节或内在情感的起承转合。那么诗歌创作者如何将碎片化的场景组合成叙事片段,从而形成流畅的叙事结构?换句话说,王昌龄七绝中绝伦逸群的“一唱三叹”“绪密思清”具体如何呈现?试看《从军行》(其一):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独登高楼的征人与闺中思妇在不同空间中同时产生的愁绪构成平行蒙太奇,诗中镜头的转换不着痕迹,边关戍兵细腻的情感世界尽得彰显。陆时雍评此诗曰:“言己之愁已不堪,而闺中之愁更将何奈,此昌龄诗法不与众同也。”如将诗评家的感性审美经验与影像组合段理论加以对照,可更直观地解读文本背后的叙事技巧。“组合段理论”由电影语言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提出,他将叙事的基本单位定义成“独立语义段”,并总结了影像文本中的八种形态:a.单镜头,b.平行组合段(两个以上场景交替呈现),c.括入性组合段(打破连续时空叙述而插入某个场景),d.描述性组合段(对某一时刻、场景的描述和呈现),e.交替叙事组合段(两个不同空间中、在同一时间发生的相关事件),f.场景(不同镜头连续呈现同一空间),g.插曲式段落,h.一般性段落。其中b,c为非时序组合段,镜头组接具有时空交错的特征;d,e,f,g,h为时序组合段,其中的镜头、场景依据连续的时空予以呈现。不妨参考上述划分进行文本细读: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d.描述性组合段)+(f.场景)+(e.交替叙事组合段)
首二句作为环境描写和背景交代,奠定了黄昏时分的晦暗色调。此际一曲幽怨的笛声随远风飘来,诗人从听觉角度呈现同一时空场景的苍茫寥廓,思乡之情接踵而至。尾句的平行蒙太奇更将相隔万里的空间交替呈现,愁绪亦如同笛声般绵长呜咽,全诗情节的起承转合灵动含蓄。再以《闺怨》一诗为例: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d.描述性组合段)+(f.场景)+(e.交替叙事组合段)+(c.括入性组合段)
全诗富于戏剧性地表现了“不知愁”的少妇登楼赏春,望见依依杨柳而心生悔恨的怅惘之情。先以旁观者的视角切入,后变为少妇的视角,转换巧妙自然,写出女子微妙复杂的情感变化。尾句运用“闪回”手法,将前于被述时间的场景插入到情节的顺时叙述之中,用以呈现主人公的记忆场景,起到补充情节、解释事件脉络的作用。全诗情节和人物情感的起承转合应诗评家周珽所言:“一句一折,波澜横生”。朱光潜曾盛赞王昌龄《闺怨》达到了“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又如《长信秋词五首》(其四):
真成薄命久寻思,梦见君王觉后疑。火照西宫知夜饮,分明复道奉恩时。
(d.描述性组合段)+(f.场景)+(c.括入性组合段)
开篇“真成薄命”四字将失宠宫嫔之于自身境遇的难以接受与无奈和盘托出,梦中的女子仿佛又回到承宠时夜宴欢饮的时光,后两句详细叙述梦中之事,以色调温馨的梦境反衬暗淡悲惨的现实。“分明”二字细腻地刻画了女子心中的痴念与失落,可谓深情幽怨,意旨微茫。诗中“闪回”手法的运用并置了想象与现实两个叙事空间,两个空间的转换与穿梭生发出恍惚迷离的“间离”效果,渲染出凄迷幽寂的氛围。诗评家周敬也敏锐地抓住此诗中诗人虚实互换的造境手法,激赏此诗“因思而梦,既梦而疑,描写宫人心事尽无馀”。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诗人能够充分运用诸多叙事技巧,将零散的意象群组合成富于美感的诗歌镜头,再通过视角转换,将分散的镜头串联成有情节起伏的叙事段落,而非意象的堆砌或一味的抒情。这种影像叙事为读者开拓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构筑起深邃的诗境,精准地传达了尚未被概念固化的审美原初体验,正如钟惺所评“龙标七言绝妙在全不说出,读未毕,而言在目前,可思可见矣,然终说不出。”王昌龄诗中一波三折的视角变换和情节转承更为七绝这一诗体增添了灵动之美,“起承转合之法,自此而定,是为唐体,后人无不宗之。”
三、影像叙事的成因与影响
王昌龄七绝中影像叙事形成的具体原因,既与七绝这一诗体在盛唐的成熟相关,也离不开作者本人对前代诗歌资源的吸取创变与独到的审美感受力。葛晓音先生曾在《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一文中从诗体演变角度详细论证了七言绝句律化的具体过程。与五言绝句相比,七言绝句的起源和格律化的时间较晚,中宗前七绝作品数量很少,“此后到中宗神龙、景龙年间,七绝才突然增多,并成为应制诗的重要体裁”。王昌龄正处于七绝这一诗体蓬勃发展尚未完全定型的时期,这无疑为诗人的艺术探索提供了更多创新的可能。相较于前人七绝中普遍采用的比兴、警策、对句等形式,王昌龄更重视意象的提炼和组合,强调“巧运言词,精炼意魄”(《论文意》),用尽可能精炼的语言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诗歌境界,从而达到“深情幽怨,音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的效果。
“诗歌镜头”中众多意象的巧妙安排离不开诗人良好的构图意识和画面感,更需要非凡的艺术想象力,王昌龄本人独到的审美领悟力也是影像叙事形成的重要因素。纵观王昌龄现存诗作,有大量关于绘画、音乐等不同门类艺术作品或表演的专门描写,体现了诗人深厚的美学修养和超常的审美感悟力,如《听弹风入松阕赠杨补阙》《观江淮名胜图》《江上闻笛》《素上人影塔》《听流人水调子》。值得赞叹的是,诗人能够以文字的形式传达出复杂的艺术境界和微妙的审美感受,尤其在《观江淮名胜图》一诗中,诗人以欣赏者的“飘移”视点为读者缓缓展开了一卷宏大繁密的画作:既有远景(山岭、海峤)的眺望,又有近景的特写(独往寻胜之僧),观赏者与画中僧人的视角交替变换,营造出似真似幻、庄生梦蝶般的飘渺氛围,流露归隐的志趣。尽管读者无缘亲自欣赏诗人所观之画,但通过王昌龄的精妙描述,仍令读者感受到强烈的视觉震撼,并在文字的指引下完成了对一幅绘画作品的“心摹手追”。在图像与文字之间,王昌龄以其卓越的才华构筑了对话和想象的桥梁,这正见于其诗中良好镜头意识和整体画面的流动感。
殷璠批判南朝“理则不足,言常有馀,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绮靡诗风,推崇以“神、气、情”为核心的“兴象”之说,他在《河岳英灵集》中辑王昌龄诗16首,所举例句42句,超过集中其他诗人,并推其为“中兴高作”。王昌龄七绝中所呈现的纵横古今的磅礴气势、心兼人寰的高远情思恰合“兴象”所要求的力量之美和深蕴情致,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言,“造成了一种明朗透彻、丰满阔大、能以深切或强烈的情绪激发读者的艺术世界。”“兴象”作为景象与情思的交融,它要求作品具体可感、鲜明生动,这既是殷璠作为批评家的审美理想,也发轫于诗人创作的理论自觉。王昌龄在《诗格》中将诗分为物境、情境、意境:“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出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于心,则得其真矣。”在王昌龄看来,意境是心与物契合的产物,其最终指向是将物色与人的生命状态真实生动地呈现,使读者“怳然有如目击”“惊耳骇目”(殷璠评王昌龄诗)。我们不妨将王昌龄七绝中的影像叙事视作“意境”理论的具体实践,诗人以主客视角转换和时空调度开拓“曲涧层峦”的深峻风格,使场景历历在目,又与诗歌主人公情感的起伏波动相交融,兼得“境”之真与“情”之真。
与王昌龄同时代的诗人岑参在七绝创作中也体现出鲜明的影像叙事特色。如《逢入京使》一诗暗含了三条叙事线索:远赴西域的诗人、返京述职的使者、留守长安的妻子。三条线索交织在短短28字中,“故园”与“边塞”的空间对峙以及渺小个体行走于广袤空间内的流动形成对比蒙太奇。征马之上相逢的场景涵盖了双方的对话、表情、心理活动,构成内涵深蕴的诗歌镜头,凸显出旅途的颠沛流离与思乡的肝肠寸断。《碛中作》则穿梭于现实与想象两个时空之中,收束方式依旧是以景结情:“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将荒凉大漠无涯的苍茫镜头呈现给读者,似答非答,气象壮阔。中唐诗人刘禹锡的咏怀名胜类七绝开拓了七言绝句的描写题材,在他笔下名胜古迹的作用不仅是诗人抒情的参照物,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无论是《石头城》中的空城、女墙,还是《乌衣巷》中的朱雀桥、堂前燕,都成为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意象符号,这些符号被诗人巧妙地安置于诗歌镜头中。诗人将这些镜头放在不同的时空之中,呈现为“闪回”“平行蒙太奇”等效果,尽抒怀古伤今之情。《乌衣巷》中“燕”的意象被诗人置于昔日王谢堂前和今日的寻常百姓家,两种空间、两个镜头在此发生奇妙的重叠,文字与想象的交汇流露出人事变幻、兴衰无常的感喟,显现出诗人安排意象和组织结构的纯熟技巧。
回顾唐代七言绝句发展脉络,以影像叙事营造时空交错画面的表现手法屡见不鲜,这一方法的演进同时意味着诗歌意境不断向纵深开拓。诗人的“造境”意识亦即突破二维文字局限性的自觉尝试,创作者渴望超越语言符码的规训,解放人性中自由的想象力,以多维呈现的方式恢复审美原初体验。影像叙事的更深含义是一场复归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文学实践,借用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的术语来说,诗人力求展现一个比真实还要真实的世界,从而深入到“前真实的自然”之中。其实质是将审美对象的本然状态以文字的形式作用于读者的想象,诗歌中所呈现的“象外之兴”正显现于读者阅读与想象交汇的刹那,这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照亮”和“唤醒”,更是文学试图突破自身局限的探索之路。
注释:
①㉒(清)沈德潜选注:《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第645页。
②(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80页。
③参见(法)马赛尔·马尔丹著,何振淦译:《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④⑫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第22页。
⑤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0页。本文凡引用王昌龄诗、文,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⑥⑩(清)黄书灿:《唐诗笺注》卷八,清乾隆刻本,第13a页、第16b页。
⑦(明)顾璘:《批点唐音》,(元)杨士弘编选,(明)张震辑注,(明)顾璘评点,陶文鹏、魏祖钦点校:《唐音评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1页。
⑧⑭(明)陆时雍撰:《唐诗镜》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a页、第7b页。
⑨《豫州耆老为祖逖歌》:“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思歌且舞。”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九,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79-780页。
⑪(清)朱之荆:《增订唐诗摘钞》,何庆善点校:《唐诗评三种》,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09页。
⑬(清)潘清:《挹翠楼诗话》卷四,张寅彭主编,吴忱,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册,第6040页。
⑮克里斯蒂安·麦茨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引入电影领域,提出“电影语言”的概念,他认为电影语言不同于自然语言,无法确认其最小单位,故从“句法”层面(包括镜头的选取、组接方式)提出叙事段组合理论。镜头构成场景,场景构成组合段,组合段根据不同作用分为八种基本类型。参见(法)克里斯蒂安·麦茨,刘森尧译:《电影的意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15页。
⑯⑱(明)周敬编,周珽补辑:《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6册,第590页、第589页。
⑰朱光潜:《谈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56页。
⑲(明)钟惺,谭元春辑:《唐诗归》卷十一,明刻本,第17a页。
⑳(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二,清借月山房汇抄本,第27b页。
㉑葛晓音:《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76-90页。
㉓《观江淮名胜图》:“刻意吟云山,尤知隐沦妙。远公何为者,再诣临海峤。而我高其风,披图得遗照。援毫无逃境,遂展千里眺。淡扫荆门烟,明标赤城烧。青葱林间岭,隐见淮海徼。但指香炉顶,无闻白猿啸。沙门既云灭,独往岂殊调。感对怀拂衣,胡宁事渔钓。安期始遗舄,千古谢荣耀。投迹庶可齐,沧浪有孤棹。”
㉔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6页。
㉕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204页。
㉖“书有利涩,诗有难易。难之奇,有曲涧层峦之致;易之妙,有舒云流水之情。王昌龄绝句,难中之难;李青莲歌行,易中之易。”(明)陆时雍著,丁福保校:《诗镜总论》,1916年铅印本,第12a页。
㉗(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06页。
㉘ Mikel Dufrenne,In
the Presence of the Sensuous:
Essays in
Aesthetics
,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Inc.1987,pp.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