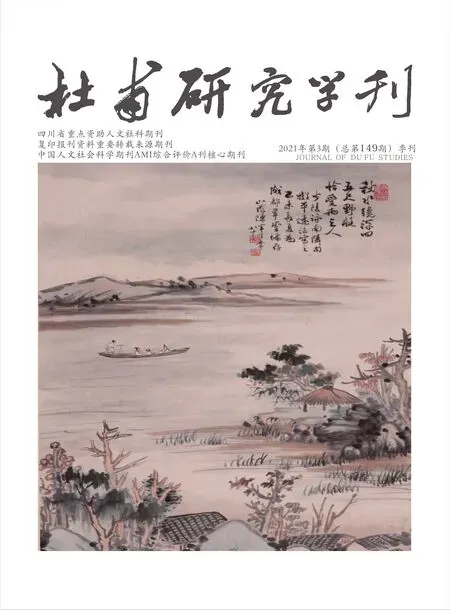云和露:明前期台阁诗人创作中的政治心态与山林趣味
2021-11-12李璨
李 璨
台阁诗人的创作与“台阁体”的产生与发展是明代诗坛的独特现象。严格来说,历朝历代都不乏以文字为能事,立足庙堂,服务于君主的文人,因为应制、制诰、赋颂、纪铭等本就是台阁文臣的日常职务,也是他们文字写作的基本功;但是却鲜有内臣群体的创作像明代的“台阁体”这样成为文学史上的代表符号。然而,明前期的台阁诗人并非仅提供了“台阁体”这一种面貌,台阁诗歌表现的是台阁诗人创作的整体风貌,不应被典型的“台阁体”所遮蔽。“台阁”在这里指的不是写作场域,也不是正统的文风,而是诗人的身份。针对台阁诗人的创作,以往的研究多从外部环境考量,重点讨论明前期台阁诗歌,特别是“台阁体”与政治生态的互动关系,而较少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考察台阁诗人的艺术语言,存在放大政治价值而轻视文学内涵、重视抽象意义而忽略形象分析的不足。
对于“台阁体”,明清以来存在大量尖锐批评,尤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著,馆臣指其“形模徒具,兴象不存”,将批判的重点放在意象语言的问题上,这一点关乎古典诗歌审美的要害。但实际上,包括台阁体在内的台阁诗歌,其兴象并非“不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兴象在诗歌中的表现形态。如果从意象语言的丰富程度和灵活性来看,台阁诗歌的兴象无疑是贫瘠的;但如果从意象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体系的意义稳定性和群体价值共性来衡量,兴象反而成为我们理解体量庞大的台阁诗歌的关键“入口”。
如何从大量的台阁诗作中找到具有典型价值的意象呢?首先要看该意象的使用频率是否足够高。我们知道,诗歌的意象语言多集中在山川景物、鸟兽虫鱼之类事物上,即《文心雕龙`·物色》所说的“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在台阁诗歌中,云和露作为节候表征,表现出不可忽视的高密集度。作为一种诗歌意象,“云”在杨士奇《东里诗集》和《东里续集》中出现516次,在杨荣《文敏集》中出现227次,在杨溥《杨文定公诗集》中出现144次,在黄淮《省愆集》中出现87次,在金幼孜《金文靖集》中出现274次;而“露”在杨士奇诗作中出现105次,在杨荣诗作中出现62次,在杨溥诗作中出现36次。此外,这一现象在胡广、胡俨、王洪等台阁诗人身上也都有显著表现。
其次要看该意象在台阁语境下是否具有独特的阐释价值和充足的意义空间。云和露绝非随手拈出的寻常事物,云有隐逸的风度,露有山水的野趣,二者显而易见的山林气质与潜藏的政治内涵,构成矛盾的张力。这就使云和露以一种“非台阁”的表象,实现与“台阁”话语的相互参看,共同构成了台阁诗歌意象语言中的暗明两条路线。
梳理云和露两个意象在古典诗歌中的使用史,均能发现这两条不同的路线。对于云意象来说,一条是作为山林志趣的隐逸符号,一条是作为政治话语的祥瑞代表。就起源而言,后者似乎更早,在上古时期已出现以云作瑞象讴歌明君的颂词;而前者则是以云的自然特征为基础,在历代诗人有意地进行抽象化、符号化后,使其拥有隐逸淡泊的意韵。前者兴盛在六朝,而成熟在唐宋。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玄学,而云带有缥缈特征,符合隐者的心态,南朝陶弘景就写道:“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将云当作山中隐趣的代表。自六朝以来,云的隐逸个性有不断被禅化的倾向,这主要归功于陶渊明和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葛兆光指出,“真正给‘云’赋予盎然禅意的是中晚唐诗人”,但“陶渊明《归去来辞》已开其端,而盛唐诗人也曾在诗中写有‘禅意的云’”。从“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云确已有禅味的理性淡然色彩,进而到皎然《白云歌寄陆中丞使君长源》中已写道:“逸民对云效高致,禅子逢云增道意。”无论是道家之“逸民”还是佛家之“禅子”,都把云提升到了清静高远的哲学思考之中。宋人延续了这种隐逸传统,且将其扩展到词的审美空间内,使云的山林内涵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在意象语言体系中,以隐为主流的山林之“云”到了明前期台阁诗人手中,却退居暗线;相反,政治空间内的“云”,逐渐占据意象体系的主导。由于云的瑞兆功能,其在庙堂的阐释自先秦以来就未曾断绝,但与台阁话语真正高密度的重合是在歌颂祥瑞蔚然成风的唐代之后。《旧唐书》记载:“(贞观)十四年,有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讌乐,奏之管弦。”再如于季子《咏云》:“瑞云千里映,祥辉四望新。”宋之问《驾出长安》:“淑气来黄道,祥云覆紫微。”王涯《献寿词》:“宫殿参差列九重,祥云瑞气捧阶浓。”岑参《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树降甘露诗》:“昆仑何时来,庆云相逐飞。”皆是从祥瑞出发,逐渐形成了台阁场景下的颂云传统。对于“露”来说,也存在这样的两条路线。相较于云,露没有那么超蹈出世的隐逸倾向,但也蕴含了文人清高的审美寄托。早在《离骚》中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露是高洁人格的象征。到了魏晋南北朝,其山林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展,但是在此间大量出现的风露、朝露、霜露、行露等意象,都含有某种凄清意韵,使露在山林情景中拥有更显性的野逸气质。然而在唐宋诗人的馆阁吟唱之中,露有时也包含富贵清气,例如西昆体诗人就喜欢用露来点缀升平:“金茎吹晓露,玉宇动轻尘”;“翠幄飘香映绮襦,钿盘清晓露成珠”。这种柔靡、雍容的华贵风气,被明前期的台阁诗人继承。同时,“露”的政治阐释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多作为恩泽的一种表述形式。这一传统从《诗经》中的“露”已有渊源,到了唐宋更是蔚为大观,例如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和思归乐》:“君恩若雨露,君威若雷霆。”李白《送窦司马贬宜春》:“圣朝多雨露,莫厌此行难。”黄庭坚《送曹黔南口号》:“归去天心承雨露,双鱼来报旧宾僚。”露成为君主恩情的一种象征。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云和露在台阁诗人笔下拥有相互关联的特性,理应得到并置的分析。一方面,当台阁诗人暂时摆脱台阁心态而表现出对自然逸趣的回归时,云和露能成为合适的寄托。另一方面,台阁诗人常有将云、露对举的习惯,用以渲染祥瑞气象,这也成为云和露能够关联庙堂、进入台阁话语,从而得到政治化阐释的逻辑基础。从这种基础出发,云和露构成了台阁诗歌意象语言中的明线,分别体现了台阁诗人的附从和感恩心理,并形成了空间与感官的两重阐释维度;而其源于自然本征的山林内涵则退居暗线,成为反映台阁诗人创作侧面的切入点。
一、明前期的政治生态与云和露的祥瑞象征
明前期有盛世的发展气象。在经历洪武永乐年间的文武建设之后,明代发展到仁宣两朝,政治和平,百姓安乐,虽仍存在一定的社会问题,但已流露出一种蒸蒸日上的太平气象——“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在这样的盛世背景下,为了适应国家新的文化发展需要,符合新王朝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台阁诗人自觉产生了一种颂世鸣盛的使命感,承担了作为馆阁重臣的文化责任。正所谓“国朝既定海宇,万邦协和,地平天成,……复发为文章,敷阐洪猷,藻饰治具,以鸣太平之盛”。明成祖确立了内阁制度,让台阁诸臣参与机务,为缓和逐渐僵化的君臣关系释放出友好讯号。到了洪宣两朝,仁宣二帝与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文人之间突破了此前谨慎的表面和谐,真正达到了君臣上下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友好局面。正如仁宗所说:“朕以菲德承大统……亦惟赖文武贤臣,相与协德,共图康济。”在稳定繁荣的政治生态之中,在高度作为的政治参与之下,台阁诗人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得到进一步加强,进而主动地推进了明前期鸣盛颂世的创作风气。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描绘祥瑞气象成为书写盛世的重要路径之一。不同于嘉靖时期世宗对于祥瑞之事乐此不疲,官员皆常以进奉贺词来谋取政治利益的风气,明前期的台阁诗人对于祥瑞的应制之作,当有许多是出于真心实意的。瑞兆的表现形式有很多,而在古人的观念里,天象气候是左右吉凶的关键象征,而云和露正是能预示祥瑞的自然符号。《列子·汤问》云:“景风翔,庆云浮,甘露降,澧泉涌。”张湛注曰:“至和之所致也。”祥云作为瑞兆,源远流长,很早就与帝王产生关联。例如,《大戴礼记·五帝德》描写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又如《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描述黄帝降生时:“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本用来表示天地祥和气象的云,成为黎民百姓的一种精神寄托,后转而用于歌颂天子德化。同时,“露”表现祥瑞也自有其传统,《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露”成为歌颂天地阴阳相合、民生和平昌顺的象征。《礼记·礼运》中形容嘉瑞集结:“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天降膏露,乃是天不吝惜神通的降福之举,露在其中得以与多种常见的祥瑞并列。
明前期台阁诗人对云和露这两个意象的选择与利用,首先在于将它们密集地用于歌颂祥瑞的诗作中,其次在于经常将二者并用,以形成云和露之间相互映照的关系。例如金幼孜诗曰:“庆云丽层霄,膏露时委积。”“九天宫阙风云会,一统山河雨露新。”杨荣诗曰:“景星庆云,煜煜氲氲。甘露醴泉,如酎如饧。”云与露作为一对相互对照的自然意象,接续了以排比吉兆来称颂祥瑞的传统,在台阁诗人的写作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云在天,露在野,两者都与农业生产密不可分,也就顺理成章地与整个天下的苍生福祉关联在一起。若将这种关联作政治化解读,那么云的状貌与天子德化有关,露的降临则体现君主的恩泽,云和露都可用以展现帝王功业,乃至启示国运盛况。
先说云。用云表示祥瑞,其深层次的心理基础是人们在土地农事上对天降恩泽的感念。杨士奇常有“出云作霖雨”的表达,例如《题宋知州瞻彼南山图诗》:“常时出云作霖雨,滋育万物乘阳春。”《吕主事泰山春云图》:“不闻泰山云,作霖雨八荒。”《萧启御史赴山东佥宪以何澄所画云山求题》:“君不见泰岱之云起肤寸,常向人间作霖雨。”“作霖”原指人为救旱之雨,而添以“出云”二字,“云”就成为天意的代表,润泽万物,普降福祉。再如杨荣《瑞应麒麟诗》:“如云之行,如雨之施。……雨顺风调,民安国泰。”行天下、润苍生,云之瑞兆在成为台阁诗人歌颂对象的同时,也寄托了一种政治理想。除了和雨相关联之外,诗人也常将云和雪联系起来。雨和雪都与农业生产有关,而农事吉凶又常与国运休戚相关。《诗·小雅·信南山》云:“上天同云,雨雪雰雰。”朱熹注曰:“冬有积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润泽,则饶洽矣。”故而台阁诗人也常在歌颂瑞雪兆丰年的诗作中并举云这一意象,例如杨荣诗云:“维时严冬气凛冽,同云布空阴霭结。天教三白应奇祥,一夕都城飘瑞雪。”“腊前密雪昭和畅,天际同云布渺茫。玉屑瑶花应作瑞,赤麟丹凤谩称祥。”
除了表示具体的瑞象,台阁诗人还在其他场合用云来表示一种泛指的吉祥气象,进而抒发美好的祝愿和心情。例如金幼孜《奉和学士胡公春日陪驾同游万岁山》其一:“香雾浮高树,祥云丽碧空。”黄淮《冬至》:“丹心逐云物,呈瑞绚晴霄。”杨荣《度野狐岭》:“心知圣寿齐三祝,目极祥云丽九霄。”在这些诗句中,云已经被固化为一种富贵闲适的表征,虽非祥瑞之象,却含祥瑞之气。
再看露。用露表示祥瑞,最典型地体现为“甘露”。“甘露”本是雨水的美称,但这种蒙赐天恩的自然现象经过演变,最终总会与帝王功业联系在一起。到台阁诗人手上,“甘露”已经变成较为固定的讴歌君主德行、称颂太平盛世的祥瑞载体。例如胡广《圣孝瑞应歌》:“甘雨瑞雪交腾骞,继以甘露如屑璠。”此诗列举了许多因感应帝王功德而降临的祥瑞现象,甘露也位列其中。杨士奇《从狩阳山和胡学士韵》诗云“甘露满林歌瑞应”,自注:“是日甘露降阳山。”杨士奇以“甘露满林”描绘狩猎之景,展现雍容气度。又如金幼孜《瑞应甘露诗》:“煌煌瑞牒难备录,又见甘露来兹辰。皇心乾乾尚谦抑,德配轩尧与天一。”此诗追寻上古君王之遗德,用以比附今上之恩荣,“甘露”在其中代表上天的表彰。此外,明前期许多台阁诗人还有多首以“甘露”为题的应制之作,可见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这是一种普遍的风气。
云和露共有的祥瑞象征,实际上是它们能够引申出深层政治含义的逻辑基础。《礼记·孔子闲居》记孔子云:“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使自然意象进入庙堂,其根本目的在于政教感化。具体而言,对“云”意象的政治解读,从表现润泽生民的瑞象出发,在长期使用中被赋予一种仰望上天、期盼恩泽的感情,进而再将感恩、称颂的对象从上天悄然转移到君主身上。这种从“天恩”到“君恩”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台阁话语的一种主动选择。这种转变虽然不是从明前期台阁诗人开始的,却在他们手上发展成熟了。然而这种转变也造成了其与原始儒家思想的悖离。在早期儒家学者那里,君主“受命于天”,天是君的制约者,而云和露作为天的行为,代表了天的话语权,并非君王现世功绩的陪衬。然而台阁诗人把云、雨一类天象瑞兆与帝王功业划上等号,实际上就将天权与君权相等同。这一概念偷换,就促成了台阁话语对原始儒家思想的主动悖离,其真实意图在于将君权神圣化,将君与天一体化,从而展现出对帝王崇仰、依附的心态。而针对露,虽然没有如此明确的概念偷换,却也暗藏“心机”,例如杨溥曾将露的祥瑞表征作如下阐释:“《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伏惟皇上以天地之德为德,仁民爱物之心,达之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故霜露所队,日月所照,天地所覆载,咸囿于生。成《驺虞》之见,可以昭皇上好生之德也。”日月所照、霜露之坠,却被杨溥特意解说为君主一人之德行感召,可见其在政治阐释上的“心机”。
在祥瑞象征这一逻辑基础之上,云和露还呈现出两种自成对立的阐释维度。首先是视觉与味觉相对立的感官维度。当“云”进入台阁话语时,被赋予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色彩。例如政途上的“青云”象征士大夫的功名理想;“红云”“绛云”因富有仙道特征,常与皇家的典章仪式联系起来;“五云”一词用以描绘瑞云五色斑斓之貌,被台阁诗人用来形容天子威严与帝都气象。与此相对,“露”在被台阁诗人赋予政治意义的同时,拥有了味觉的想象,最典型的表述就是“甘露”。它常被用来书写明前期的祥瑞风气,展现一种和平昌盛的时代景象。这种通过形象思维将直接的感官体验进行转化,从而造成意象的气质与本义相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台阁话语和山林话语的对照之中。其次是向上与向下相对立的空间维度。云漂浮在天上,台阁诗人对其有一种自下而上的仰望姿态。而云在政治意义上又与君主捆绑在一起,故而当台阁诗人将对庙堂的归属感聚焦于帝王身上时,往往表现为精神上的主动追随。与此对应,露与雨水有关,是一种自上而下降临的恩泽。在台阁诗歌中,露常常表达对君恩的感念。如此一来,云和露的象征意义在空间维度上,分别代表了臣子对君主自下而上的附从,以及君主对臣子自上而下的宠遇,恰好构成了君臣之间的互动关系,共同形成了云和露在台阁诗人意象语言中的象征明线。
二、明线:云和露体现的台阁心理
(一)云:台阁诗人的附从心理
正如前文所述,在政治阐释的主动选择中,人们对“天”的崇拜从地理上的距离感转化为地位上的尊卑差异,天人关系也演化为君臣间的等级关系。因此,在台阁诗人的主观意识里,自下而上的“望”代表了一种靠近和景仰君王的态度,体现臣子对君主的向上追随。“云”则因其与“天”的密切联系而一并成为台阁诗人心中追随的对象,正如金幼孜诗中所云:“世人唯向云中见,遥望天门不可登。”在台阁诗人的创作中,“云”被赋予了与君主同等尊贵的政治象征,寄托了台阁诗人对君主的附从心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云代表附从的对象,直接与帝都、君主、皇家相关联;二是以云象征附从的主体,即以“云从”代表那些追随在君主身后的台阁诗人群体。这样看来,“云”似乎既可以象征君主和廊庙,也可以隐喻台阁诗人自己。其中后者又占据了较为核心的地位,构成“云”意象政治意义的基础。
1.象征附从对象
在台阁诗人的创作中,云意象可以充当帝都、君主和皇家的隐喻。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五云”,即青、白、赤、黑、黄五种云色。《周礼·保章氏》云:“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古人以云色占吉凶丰歉,不同的云色有不同的吉凶含义,五色齐备则意味着祥瑞吉庆。《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裴骃《集解》引应劭指出“五云”与“五官”的对应关系:“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五云与庙堂的关联最晚也可溯源至此。正如众多的祥瑞之象最终总会落户到帝王家,“五云”也不例外,它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表示皇宫、皇陵、帝都等与君王有关的地点。这在唐诗中就已形成传统,如杜甫《重经昭陵》“再窥松柏路,还有五云飞”,以五云描摹帝陵景色;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是时君王在镐京,五云垂晖耀紫清”,以五云指代帝京;杜甫《往在》“天子惟孝孙,五云起九重”,则以五云象征天子本人。这一指向发展到明前期台阁诗歌,更是蔚为大观。
以“五云”象征帝都皇家,在台阁诗人的作品中出现得非常密集。例如胡广《过凤阳》:“九霄日月旋丹殿,五色云霞卫帝乡。”《至清河寺望北京城》:“五云深处望京华,金阙璚楼是帝家。”前一首指明太祖时期的中都凤阳,后一首则指北京,两首诗都明确提到“帝乡”“帝家”。又如黄淮诗云:“钟阜龙蟠第一山,孝陵遥在五云间。”明孝陵是太祖与皇后的合葬陵,位于南京,而南京正是明朝洪武、建文两朝的政治中心,可见“五云”的指向总是与帝王紧密相连。
“五云”有时并不明确具有地理含义,而是泛指廊庙,体现台阁诗人对朝廷的礼赞和怀恋。例如杨荣《送中书陈宗渊致仕还乡》:“惟有丹心常恋阙,时时飞梦五云边。”黄淮《言志》:“梦中犹自陪鸳侣,五色云中拜冕旒。”“五云”在台阁诗作中,有时也会回归祥瑞的含义,与象征皇家的喻义混用,例如黄淮诗云:“五彩祥云起太虚,流辉高映帝王居。”杨士奇诗云:“阊阖九重通御气,蓬莱五色护祥云。”云既用作烘托吉祥气象,又染上独属于君王的色彩,这恰好体现了它从最初的祥瑞象征逐步走向更广大政治意义的一个过程。因此,云也就成为被追随、被附庸的对象,其在台阁诗歌中的大量使用,表达的正是台阁诗人以云为向往处和归属地的附从心理。
2.象征附从主体
台阁诗人的附从心态,使云在不知不觉中也变成台阁诗人自身的象征。其对于自我身份的心理体认,表现为对君主拥护和伴随的姿态。例如金幼孜《次韵答孙孟修》其三:“红日迥浮仙掌动,彩云深拥御筵高。”《晚次白河》:“日晚白河上,千官向此留。天光临御幄,云气护宸旒。”“拥御筵”“护宸旒”等语足以说明,云的动作正是台阁诗人的一种自我隐喻。同时,云在台阁诗作中还用来表示天子仪仗的威严,展示一种宏伟的气势和排场,而这种描写又包含着对自己得以身处其列和附庸在侧的荣耀感。例如金幼孜《次用之梁赞善人日观驾之作》其三:“日丽彩筵金作屋,云回宝仗玉为台。”《和韵答梁修撰》其三:“仗簇青云开雉扇,香通紫禁度鸾笙。”杨士奇《怀来应制》:“彩云飞盖随雕辇,白玉行尊载紫驼。”胡广曾多次陪同成祖征战,其诗作中也常以“云”喻御行之盛,如《铜城》:“彩云迎辇路,红日丽天营。”《回师出三山峡》:“夹道彩云迎日驭,连营喜气动天颜。”云不仅处在伴随的空间内,甚至还展现出一种逢迎的姿态,足见台阁诗人以云喻己的意图。
除仪仗之外,台阁诗人也常以“云从”比喻伴君的行为,此时的云与天子组成有机的整体,表现为一种簇集和拥护的形态。《诗经》中以“如云”言随从人员众多,当其运用到台阁话语时,就可以表达一种追随在君王之侧的志向。例如杨士奇《滁州陪猎次林光禄韵》:“侍从如云陪乐事,郊原霜浄不沾泥。”以侍从“如云”作喻,以“云”展示臣子们作陪侍驾的盛大气势,其中暗含台阁诗人身处其列的自得之意。再如胡广《春日扈从幸北京》:“万马薾云开辇路,六龙扶日度天津。”“万马薾云”之语足见随从之盛,不仅能体现御行之威,还有“开”的动作来迎合。在金幼孜的诗作中,有多处将“冠盖”与“云”相联系的表达,如“冠盖拥青云”“冠盖拂云来”“冠盖随云气”“云气随冠冕”等,“冠盖”借指朝廷官员,而将其在诗句中与“云”或“云气”相结合,则是为了展现台阁诗人附从集会之盛。
综上所述,在表现台阁诗人对君主的附庸关系时,无论是让“五云”代表被追随的对象,还是以“云从”象征追随者本人,“云”无疑都体现了台阁诗人的附从心理。而附从心理实际就是台阁体创作的核心立场,它淡化了传统儒家士人的独立精神,弱化了臣子对君主的制衡能力,将“忠君”的主体意识偷换为“附君”的疲软姿态。后人常批评台阁体内容贫瘠、精神靡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从意象语言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能够清楚地探寻到台阁诗人创作背后潜藏的群体心态。
(二)露:台阁诗人的感恩心理
“露”本身只能说是与自然气象有关,并不直接与“天”相联系。但后来在文学作品中,“露”与“天”构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进而指向天子的恩泽。《汉书·晁错传》云:“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如淳注曰:“覆,荫也。露,膏泽也。”一个“覆”字,就能展现出自上而下的施与姿态,“膏泽”则体现了君主的恩惠。露喻指恩情惠泽,除了“配天象地”这一阐释路径之外,还因其沁润植物的功能而被拓展为对万物的滋养。相传春秋时介子推曾赋诗曰:“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其中以龙喻晋文公,以“四蛇”喻得晋文公宠遇的臣子,以“一蛇”喻被晋文公忽略的介子推,前者“得其露雨”,后者“桥死于中野”,“露”在其中直指君王的赏赐恩惠。正是出于这种滋润和惠泽的色彩,当露被放置在台阁的写作场景中,恩惠的来源自然就转移到君王身上,台阁诗人正是借此表达了他们对君主的感恩心理。
古代诗人对露意象的政治化阐释,可上溯到《诗经》。相比起来,《国风》中的“露”更贴近其自然表征(如《蒹葭》《野有蔓草》等),《小雅》中的“露”则更具有庙堂气质,例如《蓼萧》,《毛诗序》称此诗旨在歌颂天子“泽及四海”,郑玄笺云:“露者,天所以润万物,喻王者恩泽,不为远国则不及也。”将露与天恩相联系。又如《湛露》描绘天子宴饮的场景,以“露”贯穿全篇,郑玄笺云:“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叶低垂,喻诸侯受燕爵,其仪有似醉之貌。”湛露临于草树,意味着王之恩泽临于诸侯,露之湛湛意味着情之殷殷。明前期台阁诗人对“湛露”一词有较多的运用,如胡广《元夕观灯侍宴二十韵》:“既醉又闻歌《湛露》,序贤只拟咏敦弓。”黄淮《癸卯正旦简同列诸公二十八韵》:“《湛露》歌初合,清平曲未终。”金幼孜《和胡学士立春日韵》:“宴酣歌《湛露》,深荷宠恩频。”《元夕赐午门观灯》其二:“从臣忝预传柑宴,既醉犹歌《湛露》篇。”台阁诗人在侍宴、集会等场合下常引《湛露》,目的是歌颂升平、感念君恩。
台阁诗人自觉躬逢盛世、幸入馆阁,对于君恩圣情无比感激,“露”是表现这种心态的绝佳承载。而在不同的情景中,君恩覆盖的范围又有所区别:当用于歌颂盛世风貌、称赞君主功绩时,重点在于恩泽范围之广;当君恩的对象降诸个人时,重点则在于宠遇程度之深。
首先,明代洪熙、宣德年间的升平气象使台阁文人自觉承担起相应的文化责任,他们在诗歌中大量称颂君主的功绩威仪以作盛世书写。在其意象语言中,“雨露”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例如胡广《三月朔早发东平上望祭泰山》:“自是时巡宣雨露,只期四海尽丰年。”金幼孜《万寿圣徳诗》其四:“臣民处处腾歌颂,此日均沾雨露仁。”《赠沙同知之官禄州》:“舆图尽入河山壮,海宇均沾雨露多。”这几首诗都提到了天子的雨露之恩,涵盖的范围上及群臣、下及万民,遍及四海,“宣雨露”“均沾”“雨露多”等词语都在凸显天子恩泽范围之广。其广度甚至延及边庭远人,如杨荣《来远人讨不庭二章·来远人》描绘了远人朝见的场景,告诫远人应当“仰聆天语何谆谆,感兹苍穹雨露均”;《送佥宪陈廷嘉之广西提调学校》云“四方乐熙皞,声教达边隅”“皇仁若天地,雨露皆涵濡”,同样是讲天子恩泽已经惠及“边隅”,无远弗届。
其次,台阁诗人多有以“露”感念个人宠遇之深的诗作。三杨之于仁宗,一是有东宫之谊、师生之情,二是有扶位之功,宣宗对于台阁诸人也十分倚重,君臣之间上下友好、相互信赖的局面催生出台阁诗人的感恩心理,“露”便成为表达这种心理的良好媒介。在具体创作中,台阁诗人常用“浓”或“深”来形容君主恩泽对其个人的影响。如杨荣《恭侍御游万岁山四首·小山》:“喜遇太平无事日,共沾雨露沐恩浓。”《赐游万岁山诗》其一:“迤逦云霄近,汪洋雨露浓。”黄淮《舟次济宁柳色未改澹斋有诗因次其韵》:“自是圣恩深雨露,坐令枯朽总回春。”这种恩情表达不仅出现在自抒胸臆的诗境中,还用于士大夫彼此之间的互励互勉。在送别、赠答之作中,诗人常以“露”表示圣情恩泽,并含有相互劝勉的含义,目的是提醒酬送对象不可忘怀君主之恩。例如金幼孜《赠孙博士致仕还丰城》:“三朝偕际遇,涵沐雨露恩。”《赠萧主事之官北京》:“恩露沾新绶,天香染旧袍。”这两例均是以“露”写沐恩之深厚。杨荣《贺许编修父寿日》:“尚期黄发膺嘉祉,更沐天朝雨露荣。”《送侍读曾鹤龄归省》:“载笔久看承雨露,宁亲今喜荷恩荣。”这两例均含赞誉之心,借以感念君恩。
综上所述,云和露这两个意象,在台阁诗人的政治话语中分别象征了台阁诗人的附从心理与感恩心理,构成意象语言中的明线。“云”可以看作台阁诗人对于天子、庙堂自下而上的追随,体现为一种主动的趋向,表现了台阁诗人群体性的精神依附;“露”则多用来表现君主恩泽自上而下的惠及、施与,台阁诗人由主动的追随者变为被动的承受者,“露”成为他们的感念对象和情感寄托。由此,云与露所表现的台阁含义在空间维度中一上一下,恰好体现了台阁诗人与君主之间的互动关系。云与露也刚好构成一组双向的联系,这既是意象之间的巧妙关联,又能体现台阁诗人在意象语言上的艺术特点。
三、暗线:云和露蕴藏的山林内涵
前两节重点考察了云和露在台阁话语下的祥瑞内涵以及它们背后象征的政治心态;然而云和露构成的意象体系还呈现出暗线的使用脉络。云和露都来自于自然界,其本色仍属于山林,因此常出现在模山范水的诗作中。尽管台阁诗人已将云和露那种具有山林气质的“清气”改造得富有“馆阁气”,但有时也会在诗作中略洗庙堂铅华,使云和露回归自然属性,显露出清新淡雅的山林趣味。
如果说典型的“台阁体”诗作代表了台阁诗人创作生涯的主线;那么追求清逸、向往恬静的山林审美,则是台阁诗人创作理想中的副线。左东岭把台阁诗人的心态特点概括为“清慎”,但人们在对三杨等人的诗作进行阐发时,容易强调“慎”在诗歌表达中的中庸、守成,从而忽略“清”的个性在审美追求上所体现的深层意韵。尽管“台阁体”一直因其内容平庸、姿态软媚而饱受诟病,但细读台阁诗人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中也有平淡、清新乃至隐逸、疏荡的山林之作,这才是台阁诗歌的创作全貌。杨士奇曾称赞“王、孟、高、岑、韦应物诸君子清粹典则,天趣自然”,金幼孜也说:“得山水之秀,有烟霞泉石之萧爽,有园池鱼鸟之闲适,触目兴怀,即物起兴,皆可发而为诗。”杨荣《题张真人鸪峰清暑图》写道:“我生性嗜山水幽,忽见此图清兴留。”还有杨溥《为乡友程司务题雪梅》亦云:“圣人体念由自得,乐水乐山非勉为。”“性嗜山水”“乐水乐山”,这些真实地流露出台阁诗人潜藏的艺术品位和生活情趣。杨士奇晚年所作《自赞小像》云:“老子今年七十三,不胜归思在江南。天恩若许辞簪绂,犹办纶竿钓石潭。”也透露了台阁诗人在长期背负文化重任的压力下,有时也会疲于仕宦,期望能够返璞归真。事实上,可供表达山林审美趣味的自然意象有很多,但前述用于台阁场合的云和露在此时竟然也能顺畅地发挥出象征山林的作用。这种在两重话语下的意象选择和灵活调用,透露出台阁诗人在真实创作场景中的复杂心态。
(一)云意象的山林内涵
《淮南子·原道训》云:“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我们前面说,带有政治色彩的云很多都是着色的,这是源于视觉层面的再创造,例如与“无色”之云相对应的“五色”之云,就用来代表祥瑞和作为皇宫帝都的象征;然而云的天然颜色是未经点染的白,故而“白云”这个意象就较为固定地在台阁诗人的创作中被还原为云的山林本色。观其作品,我们能发现台阁诗人已经有意地把云的台阁政治内涵和山林审美追求分隔开来,意味着他们对其中的复杂关联也有所察觉。将“青云”和“白云”这组表述对照起来,正能看出这种用心。
“青云”代表一种向上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个人对富贵功名的向往,是一种理想心的象征,而这些都与“白云”所代表的山林追求相冲突。这里需特别列出杨士奇的诗歌,在其创作中,“青云”与“白云”的对立程度十分鲜明,且呈现出比较的关系:
二十承官累荣勋,腰间宝剑动星文。老辞淮水归文水,闲谢青云向白云。(《送淮安刘千户致仕归吉水》)
得谢青云向白云,绯袍象简拜天恩。从来荣宦心如水,况是名家学有源。(《送吕大理致仕兼寄王孟坚》)
天恩初下许辞官,拜别金銮晓出关。应到牧羊山下望,青云何似白云闲。(《送王文英典籍致仕归金华》其二)
杨士奇乃是三杨首辅,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他为官严谨,举止恭慎,在官场和文场都有极高的地位,钱谦益称其有“太平宰相”之风度。然而在台阁诗人的创作中,杨士奇对于山林逸趣的着墨却是三杨之中最多的。这或许能流露出他潜在的真实审美情趣。这一点从青云和白云的有意对立之间也可看出。显然,这位台阁重臣是有把馆阁空间和私人写作区分开来的主动意识的。“青云”代表台阁诗人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同;而从“青云”走向“白云”,则意味着台阁诗人从台阁走向山林,向往自然、书写逸趣的主动选择。
与此类似,杨荣也有诗云:“白发自甘生计拙,青云无梦世情疏。身随野老同来往,意与岩云共卷舒。”在这里,“青云”和“岩云”也呈现为对立的两极,与杨士奇的“青云”“白云”之对立如出一辙。除“青云”之外,云意象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达,如“风云”“云衢”“云霄”“云日”等。“风云”意味着官场竞争,台阁诗人作为翰林前辈、朝廷重臣,对此多有感慨,如金幼孜《二月廿五日夜写进士榜复命》:“花隐兰灯夜,香浮虎榜春。飞腾瞻日月,感会在风云。”“云衢”本义是云中之路,在台阁诗人的笔下常脱离仙道语境,成为名利场的象征,如杨溥《观安城张氏家什赋》:“良气不可藏,抱艺登云衢。”杨荣《寄翰林编修龚良器》:“一从辞家上天阙,平步云衢依日月。”“云霄”喻指高位,而“向云霄”则代表着奋斗向上的理想心,如杨溥《挽秦府郑教授》:“昔年芹泮拥皋北,旋向云霄振羽仪。”“云日”是将云和日组合起来,用于渲染富贵场景,烘托功成名就的华丽雍容之态,如杨荣《送宪副徐廷谟复任云南》:“锦袍照云日,珂珮声锵锵。”《送大参连士平考绩还江西》:“衣冠照云日,诗礼相继承。”
无论是“五云”还是“青云”,在表达政治立场的时候,往往站在山林的对立面。正是在这种参照之中,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本色之“云”所保留的原始“清气”,这种清气也会酝酿在台阁诗人的私人化写作中。在闲暇之馀,台阁诗人会暂时告别朝廷公务,到山水之中寻找逸趣,如杨士奇《滦河道中同杨太常宣夏二员外小酌柳下观鱼二首》其二:“云白山青护四围,水边杨柳翠如帏。人间无处无幽境,何补明时独未归。”其中“云”被赋予“白”的特征,以自然景物的本来面貌承续了古典诗歌中书写山水之乐的传统,反映了台阁诗人的闲适意趣。又如黄淮《忆旧游吟》:“西飞轮公道,谁饶头上雪。可怜有足不得骋,此心直与云飞越。”心与云齐,与云飞越。在台阁的话语中,其所代表的是臣子对君王的追随和附庸;但在怀念旧游之作里,它体现的就是黄淮对山林真趣和旧日风采的怀恋向往,甚至还有不得重回的惋惜与感慨。
另外,在台阁诗人的一些送别、酬唱之作中,“白云”也会作为山林或家乡的隐喻,表达对回归山野的向往。例如杨荣《送叶俊太守致政归乡》云:“退休之适安以舒,嗟君之乐兮世所无,白云为侣鸥为徒。”山水樵渔之趣见诸诗间,体现了杨荣对于友人致仕归乡的欣羡和感叹。又如杨士奇《姚山给事求山居六咏·埜亭》云:“飞鸟去无极,白云相对闲。”此诗以白云烘托归隐之意,表达山居的幽趣。
“白云”意象最富有意趣的表达出现在台阁诗人的题画作品中。该题材能够精巧地反映“白云”意象在台阁与山林两种话语之间的矛盾情形,体现独属于台阁诗人的创作心理。杨荣《题陈德逊青山白云图》:”东风三月春正好,白云有意还山早。多情更赋还山吟,愿与山人乐熙皞。”金幼孜《何将军山林图诗》:“濠梁谷口未应远,白云流水还相期。明当乞假向天子,锦衣快着归乡里。”这两首诗都用到“白云”意象,诗人借助这一山林气味颇重的景物,说出对“还山早”的期待以及对隐逸生活“还相期”的情怀。但我们不能忘记,题画诗实则不出台阁话语的范围。题画虽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行为,但画中的山林是间接的、二次的山林,脱离了现实的接触与体验,成为抽象的符号,与真实的田野存在距离感,其中到底体现了多少确实的隐逸精神,仍有待商榷。可以说,台阁诗人虽缺乏山林的实践经验,却拥有山林的审美眼光,这种“亲山水而不近山水”的态度,恰好符合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创作心理。台阁诗人对于山林的向往,归根结底限定于台阁身份中,那是一种想象趣味的表现,而不是一种精神理想的坚持。他们的“山林”终归不是隐士亲历的“山林”,而只是士大夫审美的“山林”,是修身养性的“山林”。这种山林审美或许只是符合台阁诗人所秉持的道德标准的一种艺术装饰,因为清高淡远、意志孤洁并不是台阁诗人的人格追求,但从某种程度上却符合了他们的艺术追求。
(二)露意象的山林内涵
“青云”和“白云”的对立关系,在“露”身上也有体现,具体表现为“甘露”和“清露”的对立,只不过这组意象的对立色彩并没有“青云”与“白云”那么显著。“甘露”依赖于味觉的想象,其目的是赋予“露”以美好的祥瑞意义;“清露”则保留了山林的清兴,“清”字也基本上仍属于视觉层面的描述。“甘露”重在味觉上的甘甜,引申为“雨露”之润泽,从而站在台阁立场上表现对君恩的感念;“清露”则重在视觉上的清爽,引申为“风露”之旖旎,多用来描绘自然风光、呈现山林逸趣。由此,从青云到白云,从甘露到清露,视觉、味觉等多种感官在不同场景的参照中得到重新开发,使台阁诗人在同一意象的不同意义指向之间不停徘徊:一面在山林的意象本色上赋予其台阁的象征意义,以适应政治上的表达需要;另一面又在许多闲暇之作、日常诗篇中保留上述意象固有的山林意韵,扩大了台阁诗歌的审美范围。
在台阁诗人的创作中,“清露”“风露”要表达山林意韵,常出现于山水游兴的题材中。如杨荣《溪山清晓》:“云际落飞泉,谷口闻啼鸟。怪底风露清,微茫楚天晓。”从云际落下飞泉,可知此云为盘桓于山林之中的“岩云”,第三句用“清”描写“风露”,也重在描摹风光,岩云和清露共同描绘了清晨溪谷的清幽宁静之貌。即便是羁旅之作,“风露”也多可表达山林之乐而非羁旅之愁,如杨士奇《江上早行》:“乘月不知行处远,满江风露湿人衣。”清晨时分的“风露”含着一种自然的清气,易融入到整体氛围之中。在赠答题材中亦复如此,如杨士奇《题陆伴读伯阳草书后》:“兰绕春庭露气清,往年同咏谢宣城。龙蛇满纸看遗墨,忽乱山阳笛里情。”诗中用“清”形容“露气”,将读者带入“往年同咏谢宣城”的回忆诗境中,尽显台阁诗人的艺术情趣。
最后,为了更加突出地体现云和露在台阁诗歌意象语言中的独特地位,本文特选“霞”这一意象与二者作对比。选择霞意象,是因其也拥有台阁和山林两方面的话语特征。在台阁场景下,“霞”可作景色渲染描绘一种雍容升平的盛世景象,如杨士奇《赐游西苑同诸学士作》其二:“霞明翠浪成漂锦,风振琼林协奏韶。”《从游西苑》其二:“太液丹霞漾绿波,荣光五采贯银河。”金幼孜《山佛窟寺偶成十诗奉简》其十:“丹霞浮御气,宝树散天香。”在山林的场景中,霞也可以表示一种清新闲适的山水趣味,杨士奇《同蔡骐尚远尤安礼文度朱智仲礼杨翥仲举蔡胄用严游东山得剪字》:“是时微雨收,轻霞澹舒卷。”《题严氏光远堂》:“窈窕烟霞护丘壑,共羨知几返真乐。”杨荣《陟屺卷》:“昼锦何时归养日,寿觞潋滟泛流霞。”然其不同之处在于:首先,“霞”没有形成自古流续的祥瑞传统。称颂霞的状貌只是意在描述一种美好的气象,而不像“庆云”与“甘露”在创作传统中已被固化为特定的祥瑞符号,故霞不像云露那样拥有进入政治话语的逻辑基础,因此它只能作为盛世描绘里的点缀素材,而没有形成个性的意象特征。其次,即便与云类似,例如“紫霞”“丹霞”这类着色之霞也拥有和帝王廊庙关联的机遇,然而这种关联乃是源于“紫”和“丹”两种颜色蕴含的皇家和仙道色彩,霞自身并没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这与云和露都构成了本质区别。最后,“霞”从自然景物进入台阁话语,不仅没有像云一样暗含天权转化为君权的心机,也不像露一样可以抽象为君主的恩泽,所以离帝王较远。其在山林与台阁间的转换,并没有改变自身的根本特质,只是适应写作场景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局限在物象的修辞范围之内,并没有台阁诗人主动的创作动机。
综上所述,云和露作为诗歌中的意象语言,被台阁诗人大量使用,在台阁的政治心态和山林的审美趣味间不断进行选择与调整。它们首先以象征祥瑞进入台阁话语,在此逻辑基础上,云表现了台阁诗人追随君主的一种附从心理,露则反映了台阁诗人承遇君恩的感恩心理。然而云和露在创作中又没有完全失去其自然本征,在台阁诗人“亲山水而不近山水”的审美态度里,这两个意象恰好迎合了山林趣味,体现出台阁诗人稍显另类的创作侧面。
注释:
①关于“台阁体”的概念辨析,可参考汤志波:《明永乐至成华间台阁诗学思想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上海古籍出版2016年版,第18-52页。
②考察现有研究成果,一方面,就台阁诗歌而言,史小军、张红花《20世纪以来明代台阁体的研究评述》(《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梳理了自20世纪初以来台阁体的研究成果,其综合评述可作参考。近年来,台阁体一直是诗文研究的热点领域,仅就2020年而论,即有如陈文新《明代诗坛上的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袁宪泼《明初文艺制作与台阁文学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张德建《台阁文人的自我约束与审美贫乏》(《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黄鹏程《论清初“台阁”“山林”文学的关系形态》(《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等几篇重要成果。然而目前学界关注点仍是以台阁诗歌的外部研究为主,尽管有少数个案研究涉及到台阁诗歌的创作论、本体论、风格论等问题,但涉及其内部的意象语言研究几乎仍是空白。同时,基于云和露两个意象的研究已分别有相应的成果,但它们都未能与台阁诗学关联起来,尚未拓展到这一领域。关于云意象的研究,或主要立足于某一特定诗人的创作,或重点作断代与宏观的理论探讨,例如刘艳芬《从唐诗看浮云意象的佛禅意味》(《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3期),王张林《魏晋诗歌中云意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侯智芳、吴丽君、崔英杰《云:一个古典意象的文化剖析》(《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罗兰《“云”及“云”参构语词的语义分析及文化探析》(福建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关于露意象的专题研究则更为少见,可以张保远《唐诗宋词中露意象初探》(东北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徐慧《魏晋诗歌中露意象研究》(辽宁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为代表。
③(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中华书局2020年版,下册,第1730页。
④(梁)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67页。
⑤(梁)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册,第1814页。
⑥葛兆光:《禅意的“云”——唐诗中一个语词的分析》,《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第82页。
⑦(东晋)陶渊明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1页。
⑧(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1页。
⑨⑪⑬(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二一、卷八〇、卷三四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258页、第871页、第3877页。
⑩(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旧唐书》卷二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6页。
⑫(唐)宋之问撰,陶敏、易淑琼校注:《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7页。
⑭(唐)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1页。
⑮(战国)屈原著,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6页。
⑯(宋)刘秉:《清风十韵》,(宋)杨亿编,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4页。
⑰(宋)杨亿:《再赋七言》,(宋)杨亿编,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132页。
⑱(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4页。
⑲㊷(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五、卷五,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62页、第430页。
⑳(宋)黄庭坚撰,(宋)任渊、(宋)史容、(宋)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外集卷十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87页。
㉑(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5-126页。
㉒(明)王直:《建安杨文公集序》,《抑菴文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1册,第133页。
㉓(明)余继登撰:《典故纪闻》卷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2页。
㉔参考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第四章《嘉靖祥瑞风气与士大夫疏表的骈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361页。
㉕杨伯峻撰:《列子集释》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7页。
㉖方向东著:《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卷七,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13页。
㉗㊵(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第7页。
㉘(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三十二章,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1页。
㉙㊲(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二二、卷五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1427页、第1617页。
㉚(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0册,第593页。本文凡引用金幼孜诗,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㉛(明)杨荣:《文敏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0册,第6页。本文凡引用杨荣诗,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㉜(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五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9册,第444-445页。
㉝(明)杨士奇:《东里诗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8册,第309页。本文凡引用杨士奇诗,均出自此书《东里诗集》与《东里续集》,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㉞(宋)朱熹集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卷十三,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40页。
㉟(明)黄淮:《省愆集》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0册,第448-449页。本文凡引用黄淮诗,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㊱(明)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28册,第610-611页。本文凡引用胡广诗,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㊳(明)杨溥:《杨文定公诗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6册,第466-467页。本文凡引用杨溥诗,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㊴(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二六,《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819页。
㊶㊸(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五、卷十六,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46页、第1178页。
㊹(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四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册,第2296-2297页。
㊺(秦)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28页。
㊻㊼(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卷十、卷十,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30页、第231页。
㊽左东岭:《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92页。
㊾(明)杨士奇:《玉雪斋诗集序》,《东里文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8册,第54-55页。
㊿(明)金幼孜:《吟室记》,《金文靖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0册,第775页。
[51](汉)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9页。
52(清)钱谦益撰集,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乙集第一《杨少师士奇》,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