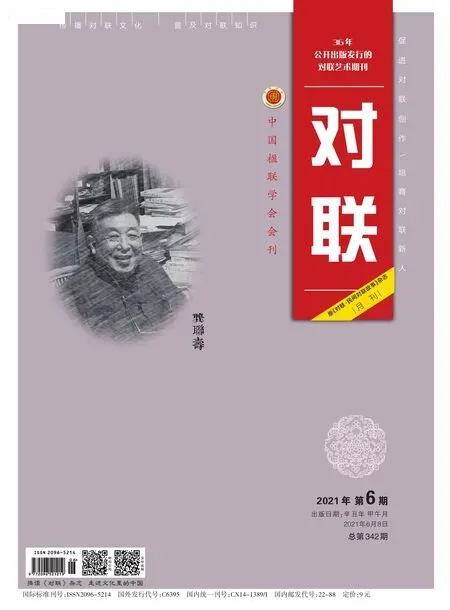从《文心雕龙》看刘勰的史学观
2021-11-11文||高科
文 ||高 科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从分析《史记》的体例入手,高度评价了《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反映了其撰史“得事序”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刘勰极其认同我国古代史学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赞扬了司马迁“实录无隐”,并从理论上将其上升为撰史的原则;但从另外一方面,刘勰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主张“男尊女卑”“尊贤隐讳”等思想,这又使得他所谓的“直笔”原则大打折扣。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史传》中对我国晋代以前的史学发展做了总结,对有代表性的史书如《左传》《汉书》《史记》等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修史主张,《文心雕龙·史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文章。本文提取了《史传》对于司马迁和《史记》“得事序”“实录无隐”这两点重要的评价,从深层次上分析了流血对于撰史的“得事序”的基本原则和“实录无隐”原则。
一、称赞“得事序”是撰史的基本要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高度评价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认为“得事序”的这种方式是撰史的基本要求。“得事序”顾名思义就是使得读者在阅读完之后对于事件可以得到清晰的认知。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史记》:“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候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得事序”这三个字既是刘勰对《史记》叙事艺术的评价,又是刘勰对撰史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历史事件是纷繁复杂的,牵涉到历史发展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材料,把众多的事件处理的得有条理,即“得事序”,这关系到史书的结构问题,主要是涉及史书的体例问题。
其实在《史记》出现以前的先秦时代,就出现了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但是这种编年体却存在几个不容忽视的缺点,近代学者吕思勉在他的《史学四种》中提到:编年体的另一个短处就是“朝章国典,无所依附。”这个意思是指由于只按照时间来罗列历史事件,这就导致这类史书缺少“书、表”等体例具有总结性的特质,使得事件之间缺少汇总。另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对于一些跨年度的大事,它不得不在不同的年份里做记述,如此一来所记事件就不够集中,前后因果关系也就会缺失。而《史记》所采用的纪传体是以本家、列传、书、表等体例为主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一种纪传方式。采用这种方式记史,既可以在每篇撰写启示等如“太史公曰”一样的作者评价,又可以使得整个事件内部关系明确,逻辑清晰。
总之,通过对于对于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记录历史方式的比较研究,我们清晰的感受到了司马迁《史记》的这种记录方式的科学性,也真切感受到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对于《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的高度评价。通过纪传体的这种记录方式,使得后人对于人物和事件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清晰,使得《史记》中的文字更平添了一份温情,一份虽跨越千年但仍对于历史人物的命运颇有感触的人情。
二、认同“秉笔直书”的撰史原则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史传》篇中通过对于司马迁“实录无隐”优秀品质的书写,体现了他对于我国史学家“秉笔直书”的撰史原则的认同和肯定,所谓“秉笔直书”就是“记录历史要根据事实而写,从不胡乱编撰”。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用“实录”二字来概括司马迁记史特点的是扬雄,他曾在《法言·重黎》中写道“太史迁实录”,而关于“隐”,孔子曾在《春秋》中写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无隐”。这些都是前人对于古代优秀史官的高度评价,刘勰集各代评价之所长,用之在《史传》篇中用“实录无隐”来评价司马迁,最后将“实录无隐”理论性的定义为史官撰史的基本原则。
首先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通过对于“实录无隐”作用的描述,来表现史官“实录无隐”的重要性。他在《史传》中写道:“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彰善阐恶,树之风声”“世历斯编,善恶谐总”。简而言之,刘勰认为史书是具有十分强大的社会功用,它包含了许多真人真事,有好的有坏的。写这么多内容,主要还是为了借古讽今,希望后人可以以此为鉴,对于现实世界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通过刘勰对于史书社会功能的描写,让后人明白史书对于社会而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而刘勰在《史传》中写道“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这段话深入浅出的阐释了史官记史真实的重要性,他们的身上可谓是担负着社会重任。所以史官能否做到“秉笔直书”,将决定史书所产生的影响力的大小和好坏。
其次刘勰通过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对于对于历代史官“秉笔直书”精神的书写,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过程中这种精神也在影响着刘勰本人的价值观,通过观察他在《史传》中对于史书语言的描写,我们可以了解到刘勰本人对于撰史的有自己的原则。首先他认为撰史应该“文非泛论,按时而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编撰史书的内容并不是在进行论说,可以随性而发,反而应当是一句一字都是按照真实的历史进行书写的”。这句话可以看到刘勰要求编史应是真实性和客观性两者的统一。其次他认为:“文疑则阙,贵信史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编撰史书要保证内容的可信度,切勿为了博人眼球,而去书写一些闲闻野史,在内容书写之前一定要确保是所书写的内容能否让自己信服。最后一点是要求:“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他以历朝历代优秀的史官为范例,向后世阐明了成为所必备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像准绳一样鞭策着后来的人,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史官传统。
三、刘勰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曾写道:“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大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他过了3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梦见了捧着红漆的祭器,随着孔子一路向南而行,早上醒来,便感到十分的高兴”。这句话,表达了刘勰见到孔子之时内心的喜悦之情,由此可以推断出刘勰内心对于孔子的思想等是十分推崇的。
至于儒家思想对于刘勰个人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他曾表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在《史传》篇中他还指出:“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诫与夺,必附圣以居宗。”这就是刘勰所认为的“尊贤隐讳”,简而言之,刘勰认为不管什么什么内容,当出现与圣人的思想相背离之时,我们应该摒弃摒弃自己的观点,去追随圣人的观点。圣人思想之所以先进,是因为这个思想在当时社会具有很强的先进性,很明显,圣人的思想在现在看来,并不是一直具有先进性,也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的,过分推崇圣人的思想,只能使自己迷茫缺失方向,失去自我主见,甚至有时圣人的思想有可能对于个人的思想产生误导作用。
在刘勰的思想中除了“尊贤避讳”这个具有一定的落后性之外,他“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也为世人所诟病。刘勰从孔子的“正名分”思想出发,对于女性专政深入批判,更批判司马迁为吕后立《本纪》,所以他在《史传》中说到:“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为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宣太后扰乱了秦国的国政,吕太后危害了汉朝的政治,让女人不该管理政治,就算是给她们名号也应该慎重”。这句话是对于女性的极度不尊重,更加的反应了他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他反对为宣太后和吕雉立纪,认为她们是“牝鸡司晨”,可以看出刘勰的思想深受儒家“正名分,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正是由于刘勰本人博览群书,文学、史学、儒学的思想才逐渐影响着他的思想观念,使他形成了《文心雕龙》中所呈现的史学观,也就是“既得事序”撰史的基本要求,“实录无隐”撰史的基本原则,但“尊贤避讳”等思想又使得他的思想大打折扣。刘勰《史传》中所记录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史学观,更是一种史学家撰史的做事精神和品质,这些精神就像宝藏一样,指引着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指引着我们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