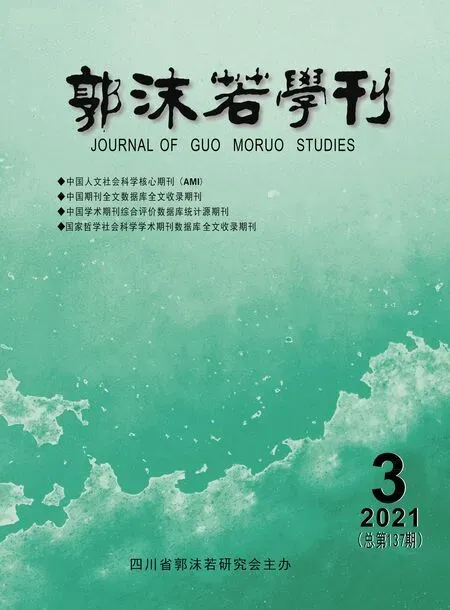郭沫若诗话(二)
2021-11-11蔡震
蔡 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大轰炸的记忆
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 年起,日本侵略军对重庆进行了持续五年的轰炸,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留下了惨痛的历史记忆,这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郭沫若在那时为此创作了若干篇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作品,他们就是这一集体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其中有几首诗的相关创作史迹,仍然需要说一说。
《罪恶的金字塔》是一首自由体诗歌,发表于桂林《诗创作》1941 年9 月第3、4 期合刊,后收入《蜩螗集》,现收录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但保存下来的郭沫若手稿中有一篇抄录清晰的该诗手稿,透露了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历史信息。
这篇抄录清晰的手稿,显然是一份誊录稿,因为一同保存的还有几页手稿,是这首诗的创作草稿。那么这份誊录清晰整齐的手稿,应该是为发表所用。而这篇誊录的手稿署名作“河芷”。也即是说诗人拟用“河芷”的笔名,发表这篇诗作。“河芷”之名,大概与《离骚》有关。屈原《离骚》中有“扈江离与辟芷兮”句,芷是香草名,“河芷”当是生长在江河中的香草之意。但该诗发表时的文本有一些改动,且没有使用“河芷”的署名。
在这篇手稿之外,没有见郭沫若以“河芷”为笔名的其他文章作品,这与前篇写到的“老丘八”不大一样,或者只能称之为拟用笔名吧,但不妨也做个立此存证。
这篇手稿值得注意的另一则信息,是关于该诗创作时间的问题。作者于手稿文末所署的创作时间为“6 月8 日晨”,没署哪一年。几页草稿是没署时间的。
在收入《郭沫若全集》的该诗文末,所署创作时间为“1940,6,17”。该篇题注亦写明“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桂林《诗创作》三、四期合刊”。那么“1940,6,17”这个日期从何而来?何以一篇即时性非常强的时事题材的诗作,写成一年多之后才发表出来?这起码不符合郭沫若作品创作发表的常态。
查看《诗创作》原刊,《罪恶的金字塔》发表时文末署“(六月七日)”。《郭沫若全集》是按照诗集来辑录诗歌作品的,《罪恶的金字塔》辑录在《蜩螗集》名下,再查看1948 年群益出版社初版本《蜩螗集》,该诗文末署创作时间为“(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也就是说“1940,6,17”出自《蜩螗集》。就三处文本均署为“6 月”,但日期的不同而言,并非多大的问题,甚至称得上为寻常事,从创作到定稿发表会有个过程的。但署“一九四〇年”是怎么一回事呢?
《蜩螗集》是郭沫若自己编的,其实作者将发表时未署年份的该诗创作时间,即使署为1940年,虽会让人疑惑,但也难强说有误。不过在《蜩螗集》辑录的《罪恶的金字塔》文末,作者附写了这样一段话:“这首诗是为大隧道惨祸而写的。日寇飞机仅三架,夜袭重庆,在大隧道中闭死了万人以上。当局只报道为三百余人。”这段话是该诗在《诗创作》发表时没有的文字(当然手稿、草稿上亦没有)。《诗创作》于该诗文末附有一则“编者按”,道:“郭先生来信说:‘……最近很少写诗,尤其是新诗,……x 月x 日大隧道惨事发生,曾亲往洞口看运尸,写了这首印象的东西,……恕我不加解释吧。……’”
看来郭沫若是在1948 年辑录《蜩螗集》时,想到了将创作该诗的缘由以文字附于文末,事由就是该诗发表时他给《诗创作》信函中所说的重庆“大隧道惨事”。
抗战期间日寇对重庆长达数年持续轰炸的史实,现在已经有了清晰的历史记述。虽未必能记录下每一次轰炸的情况,但是有几次轰炸,人们是有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的,譬如:1939 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而造成大隧道惨案的那次轰炸,发生在1941 年6 月5 日。也就是在这次轰炸之后,作者方可能“亲往洞口看运尸,写了这首印象的东西”。这个日期与《罪恶的金字塔》发表时署创作月、日为“六月七日”,或誊录手稿所署的“六月八日”,是可以吻合的。诗成后,于9 月发表在《诗创作》(该期刊物出版于1941 年9 月18 日),考虑到这是《诗创作》两期的合刊,于郭沫若而言,应属正常情况的创作发表周期。
看来该诗创作时间的问题,应该是郭沫若在辑录《蜩螗集》时记忆有误,把时间搞错了。特别是把大隧道惨案发生的年代记错了。其实还有一例亦是这种情形。在一篇未完稿《防空洞里人》中,郭沫若也写到制造了大隧道惨案的那次轰炸,却把时间写作“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这种记忆上的错误,大概与日军轰炸重庆的次数太多了有关,曾身临其境的人会记得那些惨痛的史实,却未必记得清每一次轰炸的具体日期。那么确切的创作时间,按照最初发表时所署月、日,加上年份,即:1941 年6 月7 日为好。
《惨目吟》、《轰炸后》是郭沫若创作的另外两首大轰炸题材的诗,均已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 卷。他还有几首大轰炸题材的诗未曾收入单行本集子,所以也就未收入《郭沫若全集》,是为集外作品:《五用寺字韵》《母爱》《警报》等篇。
《五用寺字韵》是郭沫若在1939 年间所创作的十几首寺字韵诗中的一首,约作于10 月间。这首诗是旧体诗的形式,但是用了叙事的方式。“无边浩劫及祠寺,机阵横空作雁字。由来倭寇恣暴残,非我族类其心异。”诗句写的是1939 年5 月3日、4 日敌机连续两天轰炸重庆市中心的情形,罗汉寺、长安寺就是在轰炸时毁于大火之中。事实上,诗人所写的十几首寺字韵诗,基本上都是在对1939 年间发生的一系列时事作历史叙事。
《母爱》发表于桂林《文艺生活》1941 年10 月15 日第1 卷第2 期,抒写的是诗人在一次敌机轰炸后所见:
走上观音崖的坡道上,
有两位防护专员
扛着一架焦结着的尸体。
一位是年青的母亲,
身体虽然全部都焦了,
但青春依然透露着。
右侧的乳畔
焦结着一个婴儿,
怕仅仅五六个月的光景?
左侧的腹部
又焦结着一个,
也怕还不到两岁吧?
母亲的两只手
——那多么有力的手呦!
各各和幼儿焦结成一片。
这是新的三位一体,
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画,
不是更要庄严吗?
后来诗人又以这首诗为本,改作成散文《芍药及其他》的一则,仍以“母爱”为题。
看来这种针对时事,具有鲜明纪实性的题材,更适于创作自由体诗歌。
《警报》是郭沫若在1941 年创作的另一首以大轰炸为题材的自由体诗。诗中没有写悲伤、沉痛,而以非常乐观的情绪,描写了人们在敌机来袭,警报拉响后从容应对的情景。
此外,郭沫若还有一些诗作间接写到与大轰炸有关的史实、史事,如:《敬吊寒冰先生》《游缙云寺和田汉诗》等。
郭沫若当年创作这些诗作,实为“书所见如此,以志不忘”。它们或许如诗人自谦的所说,“作为诗并没有什么价值,权且作为不完整的时代纪录而已”,但这是历史叙述的文本所难以见到的纪录。
送西北摄影队
《迎西北摄影队凯旋》是《蜩塘集》中收录的一首自由体诗歌,作于1940 年12 月。这是郭沫若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为欢迎往西北拍摄电影《塞上风云》外景归来的摄影队而举行的欢迎宴上所作。
其实差不多一年前,1939 年岁末那一天,郭沫若为这支将赴西北拍摄《塞上风云》外景的摄影队,还曾题赠了两首送行诗:《叠用寺字韵赠别西北摄影队》。这是未收入任何集子,甚至不为人知的两首旧体诗。诗写道:
(一)
纯阳洞外喇嘛寺,
一塔嶙峋列梵字。
电影制片厂其邻,
精神时代全相异。
初由武汉迁入岷,
斩山刊崖生訚訚。
防空洞深营三窟,
敌机虽暴如鸦驯。
惨淡经营几二载,
辛勤换得巍峨在。
列宿明迷光丽天,
方人聚集江湖海。
感心最是梦莲卿,
寄子远举俗尘惊。
欲把风尘写塞上,
艺功当与佛齐名。
(二)
远征将访百灵寺,
帜题西北影队字。
于时凛冽届隆冬,
雪地冰天风俗异。
艺界勇者辞涪岷,
抗战建艺气殊訚。
不入虎穴焉得子,
岂得甘心羊兔驯?
此去凌寒将半载,
不教耳鼻徒健在。
若无伟绩震寰区,
抚抱坚冰眠瀚海。
众情慷慨迈苏卿,
我亦瞠然自叹惊。
三唱诸君万万岁,
千秋青史垂芳名。
中国电影制片厂前身为国民党“南昌行营政训处”下辖的汉口摄影场,成立于1935 年。1938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武汉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是时任三厅厅长。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制片厂于1938 年9 月西迁入蜀,至重庆观音岩纯阳洞。这就是郭沫若诗开篇写到的地方。
《塞上风云》原是阳翰笙1937 年创作的一部话剧作品。1938 年至1940 年间,该剧先后在汉口、上海、香港、昆明、桂林、重庆、广州等地上演,颇受好评。1940 年初改编为同名电影,由应云卫导演,黎莉莉、舒秀文、周伯勳等出演。影片故事是发生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以抗战为时代背景,制片厂特别组织了西北摄影队去大草原拍摄外景。
外景地即诗中写到的“百灵寺”,应该指“百灵庙”,诗为寺字韵,故用寺字,寺庙之谓。百灵庙作为地名,指百灵庙镇,因庙得名,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境内,是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政府的驻地。1936年,在这里曾爆发过百灵庙武装抗日暴动和百灵庙战役。或许正是因此,这里被选为外景地。
时届隆冬,天寒地冻,往西北地区拍摄,工作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郭沫若高度赞扬摄影队队员们为艺术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称赞其慷慨豪迈之气胜过古代历史上在北海持节牧羊十九载的苏武。
影片全部制作历时两年,于1942 年2 月首映于重庆。
1939 年间,重庆文化界盛行作寺字韵诗,郭沫若在这一年内写了十余首,这两首大概称得上是他当年寺字韵诗的收官之作了。
“老郭不算老”
“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这两句叫打油诗也好,叫顺口溜也罢,很多人听到过,但都是口口相传,查郭沫若的诗歌作品集或整理他的佚诗,并不得见,所以也有人疑其为调侃戏说的文字。也有误传为“文革”期间题写给红卫兵的,或说是在一次科技大会上发言所讲。事实上这是一首诗中的两句,确实为郭沫若所作。诗先是随手写在一封信函上,后录入一篇短文。文章虽发表了,但后来并未收入《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所以随时间流逝,诗句有人记得,且口口相传,诗文的创作及出处却鲜有人知了。
那是1958 年末的事情。12 月18 日,郭沫若收到《文艺报》文学组编辑的一封约稿信,信中说:“今天《人民日报》第8 版上有一组《孩子的诗》,我们看了觉得很好,有一位小诗人还写道:‘快马加鞭赶郭老。’编后小语里也提到:‘后生可爱,他们是会超过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不知郭老和其他诗人们以为如何?’因此,我们想请您写千多字的小评论谈谈这些诗。”郭沫若接读约稿信后读了《孩子的诗》,随即草拟了一篇评论短文。文中写道:
《人民日报》(1958 年12 月18 日)第八版有一组《孩子的诗》,我读了。我同意编者的话,真是“后生可爱”。十二首里面有一首叫“小作者”特别提到了我,那诗是:
“别看作者小,
诗歌可不少,
一心超过杜甫诗,
快马加鞭赶郭老”。
是工农中学一年级刘玉花作的,特别是第三句,气魄可真不小。编者认为这些小作者是会“超过我们这一代的诗人的”,问我“以为如何”?我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完全同意,他们一定会超过我们,特别是超过我。因此,我作了一诗来答复那位小作者。
撰写这篇短文的同时,郭沫若先在约稿信上用红笔写下几句诗:“老郭并不老/诗歌实在少/少还不要紧/既少又不好/快马再加鞭/老小同赛跑……”诗未写完,斟酌一番,最后改成五言四句,写在信的页眉上,并录入短文中:
“老郭不算老,
诗多好的少;
老少齐努力,
学习毛主席!”
郭沫若于18 日夜作成短文《读了〈孩子的诗〉》,19 日晨即送出稿子。大概因为《孩子的诗》是《人民日报》第八版编发的,所以郭沫若把自己的评论文章先送到《人民日报》第八版编辑那里,并在手稿上附言,告以:“这是《文艺报》要我写的,请您们看了,即转《文艺报》。”不过,《人民日报》编辑看后却留下了郭沫若的短文,20 日发表在自家报纸上。
诗的末句“学习毛主席”,指学习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倒并非套话或虚应之词。1957 年《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18 首诗词。郭沫若看到后由衷的欣赏,即作《试和毛主席韵》词三首:《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和毛泽东所作《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与《水调歌头·游泳》。不久,又撰写了《一唱雄鸡天下白》一文,称赞毛泽东诗词“是有高度的创造性的,意境开阔,声调宏朗”。
郭沫若这四句口语体的诗,看似是为呼应“孩子的诗”而作,其实反映了他此时正大力提倡新诗创作要学习、吸收民歌、民谣创作的优秀传统。他与周扬合编了一本《红旗歌谣》,认为“新民歌对新诗的发展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他称今天的民歌、民谣是“今天的新‘国风’”,相信“新时代将会有从新‘国风’的基础上创化出来的新‘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