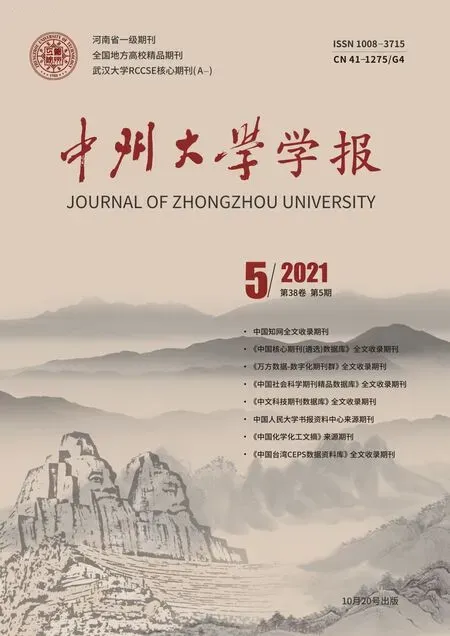河南省农村留守女童的积极发展、学校适应与成长困境调查分析
2021-11-08程绍珍张小丽
程绍珍,张小丽
(1.郑州大学 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黄河科技学院 社会性别/儿童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63; 3.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史无前例的城乡人口流动催生出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报告统计显示,2017年16 岁以下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达5000多万。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虽然共同面临父母缺席和支持性资源的缺失等不利的留守环境,但其积极发展和社会适应状况存在多元性、差异性的特点,以及留守阶段与未来发展状况相关性,以上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1]。
农村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单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由代理监护人管理或自我照顾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2],目前学界对留守儿童发展研究正在从重视“留守问题”调查向促进积极发展、良好社会适应转型。积极青少年发展观(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PYD) 是利特(litle)于1993年首次提出。2002年之后又经埃克勒(Ecceles,2002)、罗斯(Roth,2003)与勒纳(Lemer,2004)对其完善。积极青少年发展观强调青少年自身蕴含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培育”而非“管理”,是个体和组织促进青少年能力提高的原理、方法和推动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实践活动。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开始关注积极青少年发展的品质研究[3-5],提出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目前我国学者在吸取国内外积极心理学营养的基础上,尝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元素,紧扣积极青少年发展时代精神,提出中国文化背景下积极青少年发展的结构、内涵[6]、理论、干预实践[7-8]。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青少年发展促进体系。
对于青少年,良好的学校适应对身心健康、积极发展至关重要, 学校是青少年除家庭之外的主要活动场所,学校适应是其成长的一项重要发展任务[9]。部分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学校适应和心理适应上均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倾向于发现留守儿童的“问题”,得到了有关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诸多“消极”结果[10]。但另一部分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即使在诸多风险因素环境下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表现出生活自理、助人行为[11]、自强不息、茁壮成长的积极态势[12]。
此外,课题组从性别的维度尤其是女童的视角考察农村留守女童生存环境、发展状况和学校适应,发现相对于男童,农村女童更容易被父母留在家中,她们比留守男童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照料责任和农活负担;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在学校适应和心理适应上均存差异性,一项探讨青少年在学校适应方面表现的差异性和青少年积极发展不同类型的研究发现,女生的积极品格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女生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男生更高;一项初中生学校适应相关研究发现,男生的外显问题、学习问题和内隐问题水平高于女生, 而适应能力水平明显低于女生[13]。这些研究提示,留守儿童群体内存在积极发展及其适应状况的异质性,哪些因素引起差异性及不同的学校适应,这也是本研究试图考察的问题。为此,课题组于2019年4月到2020年10月,对洛阳、周口、潢川留守儿童进行调查,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特点及其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河南省洛阳、周口、潢川4个乡镇随机抽取7所学校15个班级663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删除废卷33份,最终有效问卷份630名儿童,其中留守儿童381名(男生209人,女生172人);平均年龄(M):12.63岁,留守儿童均差(SD):1.83岁。
二、研究工具
(一)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留守与非留守、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监护人情况、假期承担家务劳动状况等。
(二)中国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C-PYD)
采用郭海英、蔺秀云、林丹华等编制共118题,包括品格、能力、联结和自我价值4个分量表。本文采用积极青少年发展——品格分量表,包括“爱、志、信、毅”四个量表,总计42个项目。“爱”分量表共20个项目(如“如果同学有困难,我会主动帮助他”),“志”分量表共9个项目(如“我在学习上很刻苦”),“信”分量表共7个项目(如“我是个言行一致的人”),“毅”分量表共6个项目(如“目标已确定,即使遇到障碍我也不轻言放弃”)。在总样本中,品格量表总体及四个分量表的信度指标范围为 0.83~0.96,以往的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的结构与内涵融入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
(三)学校适应状况采用中国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C-PYD)——能力量表
包括“学业能力、社会情绪能力和生活能力”三个量表,共26个项目。学业能力分量表共12个项目(如“我总是喜欢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学习上的问题”),社会情绪能力分量表共9个项目(如“我知道如何交到更多的朋友”),生活能力分量表共5个项目(如“对我而言,做好个人卫生,如洗漱、洗衣服等,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总样本中,能力量表总体及三个分量表的信度指标范围为0.72~0.95,以往的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四)数据统计分析
全部资料收集后,采用SPSS17.0数据库集中录入,使用一般描述性统计、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三、调查结果
(一)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优秀品格发展状况
首先,以积极青少年发展传统优秀品格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为自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友爱善良、有志进取、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结果见表1。

表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优秀品格发展的差异性分析
(二)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在积极发展水平、学校适应能力状况
以积极青少年发展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社会性别为自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积极发展水平总分和5个维度得分上均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表现为: 留守女童的品格和适应能力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有志进取、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社会情绪与生活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女生的整体积极发展水平相比男生要好。结果见表2。

表2 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积极发展水平、学校适应能力的差异性分析
(三)留守男、女童承担家务劳动状况
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担了较多的家务和田地劳动。研究对381名留守儿童(男女留守儿童分别为209人、172人)假期承担农活家务劳动情况显示,男生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做自己事情分别为110人、99人;女生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做自己事情分别为109人、63人,留守男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人数占留守男童人数的52.6%,做自己事情人数占47.3%;留守女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人数占留守女童人数63.4%,做自己事情占36.6%;留守女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比留守男童高出10.8个百分点。
四、相关讨论和启示
(一)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基本现状
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同样具有友爱善良、勤奋刻苦、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质,这一结果与国内叶枝、赵国祥等学者来自北京、辽宁、河南研究发现青少年积极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趋势结果相一致。显示大部分留守儿童虽然面临父母缺席、城乡分离等不利的留守环境,但是依然有积极、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显示不利的诸多风险生态环境,同样可以进一步激发潜能和自身积极的品质,他们具有积极成长和发展的愿望和固有能力,可以成为自我发展的主导者。依据此类研究结果可以认为,过分夸大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给他们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是不恰当的。要建立“减少问题”与“促进积极发展”双管齐下的留守儿童关爱新思路。
(二)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积极发展品格水平、学校适应状况
叶枝、赵国祥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积极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和年纪差异。具体表现为女生的品格得分显著高于男生。本次调查验证了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留守儿童积极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表现为: 留守女童的品格、学校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 女生的整体积极发展水平比男生好。可能的原因一是社会宏观环境的改变,形成促进留守女童积极发展的外界环境。近年来,中国在深入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破除传统观念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1 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在妇女与教育领域逐步落实“教育性别平等原则”。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小学教育和接受中等教育女孩的在校率提高,乡村女童生存和发展环境有所改善,提高了农村女童教育、发展的机会和能力[14]。其次, 农村家庭对女孩子教育投资趋于增长的态势,相关调查发现,“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趋于瓦解;家庭中的女儿成年后在照顾父母、亲情支持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客观上影响了父母,舍得为女儿的教育投资,使其在积极健康发展中发挥作用并从中平等获益。
此外,已有研究显示个体可能也在自身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行动者角色[15]。获得积极发展的留守女童能更珍惜和有效地调控身边多重社会资源和情境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克服环境制约,促进自身积极发展,为进一步获得适应性成长奠定基础,从而建构自身的生命历程,也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议题。
本研究显示,留守女童学校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与以往研究认为男生比女生表现出更多行为问题的结果一致[16],可能与性别的生物学因素相关,男孩子更容易调皮、冲动、多动,特别是中小学阶段的男生成熟相对较晚,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和控制能力较低,缺失坚毅专注、勤奋进取精神,父母外出打工使他们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适应问题,一些调查已指出,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男孩的学习成绩造成的不利影响更大[17]。此外,可能的原因是来自传统男女角色的刻板印象,遵从“男儿有泪不轻弹”等传统的男孩则倾向于对压力闭口不言,可能导致其缺乏同他人甚至家人的交流分享,不容易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三)留守女童承担家务劳动状况及成长困境
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工输出多样本调查发现,父母外出打工以后,留守女孩、特别是贫困地区女童,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农业和看护弟妹劳动,更少时间参加体育或其他娱乐活动,对留守男孩却几乎没有影响[18]。 放学以后,男孩更倾向于出去玩,一些留守男孩在校外游荡、迷恋网络游戏,甚至涉足“帮派”[19]。还有研究发现,外出打工的父母担心留守男孩的种种“不利处境”,倾向于将儿子带到打工城市,以便更好地管教和照顾[20]。在对留守儿童团体活动分享交流中,更多的女孩坦言,爸爸妈妈外出打工,地里农活、弟妹的看护和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在爷爷奶奶的支配下由女孩承担,祖辈监护对留守男孩形成“管护”空档,对留守女童也难以提供社会支持,留守女童依然面临突出的成长困境。上述情况本身也透视出家务劳动依旧被视为女性的责任,而非两性共同承担。 在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模式和父权制色彩浓厚的中国农村,尽管传统性别规制一度面临“解传统化”的挑战,但留守妇女,包括留守女童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格局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彻底改变,仍会在人口流动、家庭拆分模式中得到延续。
有研究对义务教育阶段后留守儿童的职业发展、生活状况的追踪研究,觉察到在儿童留守阶段中留守儿童性别劳动分化,即留守女孩必须承担一系列再生产劳动,留守男孩则很少参与劳动经历,会提前形塑了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表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习惯、劳动纪律等方面巨大的性别分化,现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具备其父辈在艰辛年代里铸就的勤劳敬业、坚韧隐忍的劳动品质,以频繁地更换工作和逆反行为表达对单调劳动、严苛管理、劳资矛盾、利益纠纷的强烈愤懑和利益诉求[21]。 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有留守经历。相关研究成果和本文的实证发现也许可以为探讨留守经历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如埃尔德的生命历程理论所述,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其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事件塑造着。再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 (Erik.H.Erikson) 认为,个体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如果不能成功地解决周围环境所提出的特定社会要求,将会给其未来的社会化过程留下隐患。从生命动态历程观察会发现,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的留守阶段,可能影响他们未来社会化适应的能力,主体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或背离。如果他们对曾经的经历不能建立起合理的认知,可能导致其成年后面临融入社会的困难。因此探讨不同经历、不同因素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议题。
四、结论
留守男童、留守女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友爱善良、勤奋刻苦、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留守女童的品格、学校适应、整体积极发展水平相比男生要好;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农田劳动。在教育和培养过程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要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界限,倡导家庭性别平等并惠及女童。关注留守男童的积极发展,不断提升他们的积极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