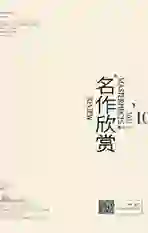《包法利夫人》中的全景敞视和权力规训
2021-10-29吴梓瑶
摘 要: 本文运用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分析《包法利夫人》中权力规训流动的方向和过程。通过构建爱玛作为监视者的全景敞视“监狱”及爱玛作为被监视者的“监狱”群岛两类象征系统,发现在全景敞视“监狱”中,爱玛试图监视男性,但其监视由于下沉的地位而失去力量;而在“监狱”群岛中,爱玛受到来自四周的资本主义和男性话语等多重监视,经历了从他者规训到自我规训与从身体规训到精神规训的双重过程。坚实的“监狱”系统将所有人笼罩其中,这意味着爱玛无法摆脱监视,也就必然导致悲剧结局。
關键词:《包法利夫人》 爱玛 全景敞视 权力话语 规训
福楼拜的著名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塑造了爱玛这一经典人物形象。目前学界大多将爱玛的悲剧归咎于男权压迫,却忽视了她自我压迫、自我监视的行为,实际上,爱玛以外的其他人,无论男女都同时背负着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双重身份并被规训。此前亦有对《包法利夫人》中凝视机制的研究a,解析了文本中的凝视类型。由于监视与被监视二者之间形成了具有张力的相互作用关系,因而不能分开讨论。这就需要将双方对彼此的监视与规训置于一种统一的模式之下,才能比较清晰地观察权力规训流动的方向与过程。
福柯将自己的“权力-主体”理论以及“知识-话语”的形构贯之于空间的生产与创造,形成了“空间权力”这一新思想。b其中,全景敞视监狱被视为空间与权力的极致范例。c全景敞视监狱即圆形监狱,瞭望塔位于中心,四周是被切割为许多个小囚室的环形建筑。社会正如一个圆形监狱,权力以隐匿的形态精准地落到每一个囚室,展现出权力的无形性、监视的主体性、规训的渗透性。爱玛的几个主要生活环境都是具象化的全景敞视“监狱”,身处其间的她逐渐被环境塑造与规训。而爱玛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更是一个巨大的全景敞视“监狱”的象征,所有人无差别地受到权力的监视并为其所规训,又以自己所接受的规训为标准去监视别人。
鉴于此,笔者拟从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出发,对爱玛所受的规训进行分析。通过对爱玛监视者、被监视者双重身份的剖析,发现爱玛作为监视者,其目光成为权力规训的一部分,但下沉的女性地位造就无效监视;而当目光转向其他人时,每个人都作为监视者而构建全景敞视“监狱”,形成一个层层嵌套的监狱群岛,爱玛处于这个群岛的某一隅,受到多人的共同监视,经历了从他者规训向自我规训、从身体规训向精神规训转变的双重过程。
一、监视者爱玛:无效监视
构建以爱玛为中心的全景敞视“监狱”,爱玛处于瞭望塔即监视者的位置,而他人则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中(如图1)。爱玛的监视源于自身受到的规训,她以此为标准去窥视、评价、规训这些与她亲密接触的男性;由于社会中女性权力的缺乏,爱玛的规训从一开始就以想象的形式压抑在内心,她只能在不同男性中做出选择,而不能规训男性使其发生改变。爱玛作为监视者的全景敞视“监狱”是一个畸形的监狱,瞭望塔处于下沉的状态,监视者的目光能够到达各个囚室而不具威力、不被感知,因此是无效的监视。
权力规训借助凝视传达,因此在分析这一全景敞视“监狱”前,有必要简单说明“凝视”。通过对各类建筑的观察研究,福柯发现了一种权力运作模式——“凝视”,放置到监狱中即为“监视”,放置在乡野即为“注视”,它广泛指代通过他者目光的一种权力作用形式。凝视背后是知识和权力的运作,赋予观看者对被观看者的占有与控制的权力。正如布尔迪厄所称:“目光并非如萨特所愿,是客观化所具有的一种普遍而抽象的简单权力,这是一种象征权力,其有效性依赖理解者和被理解者的相对位置以及认识和评价模式的应用对象对这类被实行模式的认识和认可程度。”d爱玛的监视正是其中一种,其相对弱势的地位注定了悲剧的结局。
在“爱玛-监视-他人”这一过程中,爱玛对他人的监视源于自身所受规训。浪漫小说比修道院更有力地塑造了十三岁的少女的爱情观,发扬了少女萌动的春心,为幻想提供素材,促使少女抓住一切机会“武装”自己。婚后她盘算如何改换房子布置,为用果点筹划买漱口杯。宴会上她关注时兴的穿着和贵妇的行为,注意到有几位没有拿自己的手套放进她们的玻璃盏(当时这种行为刚在上流社会兴起)。通过宴会,爱玛不着边际的幻想拥有了落脚点,在婚姻生活里苛求象征“高贵”的细节:回到道特后,她找了一个十四岁小姑娘,要把她训练成贴身使女;她买巴黎的地图,订妇女刊物《花篮》《沙龙仙女》,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她希望死,又希望住到巴黎”e。在不知不觉中,爱玛将巴黎作为行动的指南,将激情作为爱情的表现,其行为贴近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并将过上这种生活、拥有来自伯爵或子爵的爱情视为生活的全部价值和生命的全部意义。爱玛认为自己的行为受个人自由意志的支配,却未能意识到,她的“个人意志”经过资本与男权的规训,裹挟着对浪漫爱情的幻想与对奢侈生活的向往落入陷阱。道特的包法利宅临街,爱玛在家中弹琴,只要窗户打开,村头也能听到;她坐在家中就能够看到戴着青缎小帽的小学校长、佩着刀的乡间警察。这些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监视,宅子内外打通“互视”则为爱玛的监视提供了途径。
爱玛为不切实际的浪漫念头所俘虏,借这个窗口去凝视、衡量身边的人,但由于缺乏权力,这是一种无效的凝视。她无法鞭策丈夫查理使其变成理想中的恋爱对象,也不能左右情人赖昂和罗道耳弗的想法,她只能在三人中“选择”,而无法塑造和改变被社会规训的他们。
首先,对于丈夫查理,爱玛的监视具有无效性。结婚以后,爱玛对查理越来越感到不满:事业上,查理医术不精,被另一个医生当着病人面给难堪,畸形足手术也以失败告终;生活中,他举止粗俗不文,对上流社会无知无识;爱情上,他不解风情,对爱玛的浪漫情怀无觉无悟。因此爱玛虽然肉体上拥有丈夫,心灵上却孤身一人。她一边质疑自己为何结婚,一边在灵魂深处渴望一场意外的爱情。同时,虽然爱玛主管家务,但本质上未能经济独立,她不具备家庭大事的决定权,所支配的收入完全来自查理。而搬家这一类的大事,也全听凭查理做主。爱玛拥有的权力仅限于家宅空间这一狭窄的范围。布尔迪厄指出:“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这是空间的结构,存在着男女对立,大庭广众或市场专属男人,家庭专属女人。”f爱玛与查理自动自觉地遵守了男权社会的分工秩序。但同时,爱玛的管家权还受到婆婆的威胁,她浪漫自由的倾向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都得以放纵,但与婆婆节俭理念碰撞时,即使丈夫在场也无济于事。婆婆作为男权的忠实拥趸,认为爱玛不像传统意义上勤俭持家的好妻子,不能打理好儿子的家务,使其无后顾之忧地发展事业。由于爱玛生活在这样一个男性当家做主的家庭里,她对男主人查理监视的目光被男权所削弱,自然其规训效果也会减弱。这表现为爱玛对查理的冷淡与无爱并未为查理所察觉,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完成了对爱玛想象性的建构。通过虚构爱玛优秀妻子的形象,查理满足了自己对“妻子”这一角色的幻想并找到现实的对应物,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忽视了爱玛的主体性。因此爱玛的监视未能对查理产生较大影响,例如在查理告诉爱玛在会诊时被其他医生羞辱的事,爱玛气得大骂是由于希望查理能够积极进取,挂上勋章,成为赫赫有名的医生,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查理却将爱玛代入想象的贤妻角色,感动不已,带着眼泪亲吻爱玛,只令她更加烦躁。
其次,这种无效的监视在爱玛的情人赖昂与罗道耳弗的身上亦有所体现。爱玛对二者都有过监视,她曾经跟踪赖昂,窥探他的房间,编出有头有尾的故事。但在看似双方都全情投入的恋爱中,赖昂始终保持清醒,并且作为一名前途光明的青年保有退路。爱玛做出的所有努力——“她希望自己能监视他的生活,又想派人到街上盯他的梢”g——全都因双方不平等的性别地位而付之东流。罗道耳弗不将爱玛炽烈而绝望的告白和低到尘埃里去的自白看作发自本心的话语,也不将爱玛视作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爱玛的“监视”再次因为地位的不对等而失效,这无异于对查理无效监视的重复。总之,爱玛是透过他们虚构理想的情人,树立起与查理对比的参照物,然而赖昂和罗道耳弗作为男性,其本质上与查理相一致,在他们眼里爱玛始终没有主体性。爱玛虽然处于瞭望塔的位置,但该位置是下沉的,即低于被监视者的地位,目光虽然能够到达各个囚室,但却是一种仰望的目光,无形之中削弱了监视者的底气,因而爱玛的监视始终是无力的。
对监视者本人来说,无效监视未能获得有益的反馈,因而无助于自身主体性的建构;对被监视者来说,无效监视则未能阻碍被监视者对监视者的反向监视。爱玛不能改变查理、赖昂和罗道耳弗,她无法从中得到利于构建自身身份的反馈,无效监视亦不能帮助她抵挡或削弱来自此三者和社会的监視,也就无法帮助她脱离规训,因而必然走向悲剧结局。
二、被监视者爱玛:双重过程
小说一方面描述了爱玛主动监视他人的举动,另一方面更着力展示了爱玛被监视的情境。将爱玛置于被监视者的地位观照,发现爱玛不仅受到查理、赖昂和罗道耳弗的监视,还受到依托浪漫主义小说、宴会、他人目光的资本与男权的多重监视。与爱玛有交集的人以自己为中心构建一个全景敞视“监狱”,其监视范围会辐射到爱玛,即爱玛所处位置落在“监狱”半径内。与她相关的监视是由多个单向度的监视共同组合而成的,其所处环境正像是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即自己位于瞭望塔位置)构建互相嵌套的多层全景敞视“监狱”——“监狱”群岛(如图2)。修道院、拜尔斗、道特、永镇、鲁昂都是由多个具象化的全景敞视“监狱”构成的“监狱”群岛,能够明晰地看到权力的流动痕迹,看到爱玛从他者规训向自我规训、从身体规训向精神规训转变的过程。
(一)从他者规训到自我规训 爱玛的生活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爱玛所受的规训不完全一致。她先后在修道院、拜尔斗、道特、永镇、鲁昂这五种“监狱群岛”受到规训,其中尤以永镇最为典型。而正是在环境的更迭中,爱玛逐渐将他者规训内化,最终走上自我规训的道路。
在修道院“监狱”群岛中,爱玛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贵族男性的隐性监视。在修道院中阅读的浪漫主义小说是形成爱玛喜爱幻想性格的关键要素,伯爵、子爵的署名映入爱玛眼帘,仿若上流社会高高在上的贵族们、男性们的注视。爱玛被统治阶级借浪漫主义小说之手,以符合贵族阶层利益的模式形塑。正是浪漫小说模糊了爱玛与贵族阶级之间的界限,使爱玛在不满足民主中渴望理想的浪漫和身体的快乐,混淆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h贵族男性通过书写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她“被认可”的贵族生活方式和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对爱情的不合理想象,既强化自身阶级的高贵与独特,又引得少女在心底埋下追逐爱情的种子。他者规训就此开始内化,爱玛逐渐为自己的思想所禁锢。
离开修道院后,爱玛与父亲卢欧老爹一起住在拜尔斗。监视的目光被削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卢欧老爹即是父权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爱玛的话语,代替女儿跟查理商谈婚姻之事。结婚以后,爱玛居于道特。包法利在道特的住宅临街,宅子各处堆着些泥裹腿、废铁、空桶、失修的农具、石膏堂长像等杂乱物品,查理看病的动静爱玛也能够清晰地感知,隐私缺乏的现实让她更渴望书中描绘的世界。宴会的纸醉金迷、推杯换盏,正是贵族话语和男权话语“希望”爱玛看到的内容。她所臆想的生活、物质、丈夫一下子拥有了实体,不再停留在小说的描述和自己想象中。因此,爱玛在回到道特之后,愈发感觉到此处压迫着她那追随物质享受与精神满足的心。她注意到理发师想要把店开到繁华的鲁昂等琐事,并以浪漫小说式的生活为标杆,要求自己也能过上同样的生活,正是她自我规训逐渐深入的体现。
永镇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视线造就一个典型的、具象化的“监狱群岛”——多个全景敞视“监狱”互相嵌套,人们处于监视与被监视之中。爱玛搬过来第二天,“一下床,就望见文书在广场。她穿的是梳妆衣。他仰起头,向她致敬。她赶快点了点头,关上窗户。”i爱玛求赖昂陪她一起去看孩子,黄昏时这件事就传遍全镇;她和赖昂在各自窗口前安置小花圃,能彼此望见;她还可以看见毕耐的旋床,而她向毕耐求助的丑态也被他人尽收眼底。爱玛追求爱情需要瞒着枕边人,意味着她必须绕过这个不太灵敏的“监视者”;但她还需要应对多束来自他者的微观权力的监视:自我的、情人的、他人的、社会的。在爱玛被监视的过程中出现不少流言,这种来自周围人的话语构成对她无形的压迫,而她自己也认同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因此在行动时小心翼翼,并非无所顾忌。
在鲁昂,爱玛得以过上被规训后的“理想生活”,和赖昂幽会,在鲁昂置办两人的居所。爱玛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苦求不得的爱情、自由、巴黎人的生活、无拘无束的激情,然而这正标志着对爱玛的规训已经完成。爱玛为了梦想中的自我,购买了大量用不上的衣物和装饰品;为了梦想中的生活,买了精致的碗碟器具;为了梦想中的爱情,花费大量金钱置办寻欢作乐的场所,编织谎言。爱玛接受了以巴黎上流生活为核心、以男性话语为导向的话语体系,她的肉体自由自在地游荡在鲁昂,然而其爱情观、价值观、现在和未来都已经被置于隐形的监狱之中。爱玛将用并且一直用规训的眼光审视自我,变成监视自己的主体,最终走向崩溃与毁灭。由于鲁昂距离永镇并不太远,爱玛还得小心谨慎地避开认识她的人的目光。例如杜法赦受包法利先生之托给她送披肩,得知爱玛实际上很少去“红十字”旅馆;又如勒乐看到爱玛挽着赖昂的胳膊出入旅馆,都是鲁昂隐藏的他人目光,这目光来自永镇人监视视线的延长和辐射。
他者通过凝视使自我被同化的过程中,固然包括如上所述的想象中巴黎人对外省人的凝视、永镇其他女性对她的凝视等,但表现最突出的是男性凝视。新宅的地理位置再次形成了“互视”的格局:爱玛的一举一动镇上的人都能看到,而爱玛也能够通过监视他人控制自己的行动路径。福柯指出,权力关系就是谁看和谁被看的关系,谁的欲望被合法化和谁的欲望被压抑的关系。纵观古今中外,看者总是男性,被看者总是女性;男人的性欲是合法的,而女人的性欲是隐匿的。因此,男性凝视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女性被物化为性的客体,她仅仅是男性欲望的对象,而不是和男性具有同等人格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充当监视者的角色;爱玛在监视他人的同时也在被别人监视,例如爱玛直接且集中地接受罗道耳弗的规训,正是在掩藏于“监狱”群岛中的某一个以罗道耳弗为中心的“监狱”里。他者的声音和形象从侧面包围爱玛,和她在修道院所受过的教育一起,在障碍—符号体系中发挥作用。福柯认为,障碍—符号的首要作用是遏止人们犯(某)罪的欲望,将犯罪的危害广为流传,最终形成一种关于犯(某种)罪是罪恶的话语模式在民间流传。通过民间流传的话语模式,障碍—符号体系将接收故事的人变为同一套话语的卫道士。爱玛有追求爱情的熱情和勇气,但她也深深为传统的礼法和他人的言语所束缚,她用男权话语教给她的规则审视、束缚自己。这种束缚使得她虽然动心,但克制着自己暂时没有迈出堕落的一步。她感到痛苦、犹豫,前往教堂寻求帮助。然而教士亦是男权话语的持有者,反而加深了她的自我规训。随着时间推移,男性凝视就成为女性凝视自己的唯一视点,最后即便不需要男性参与,女性也内化了男性凝视的要素,从而自觉用男性目光凝视自我,这即是男权社会完成的对女性的塑造与教育。整个社会正是资本与男性搭建的巨大的全景敞视“监狱”,爱玛在这个“监狱”的小格子间里接受了男权的灌输,一步步滑向规训自我的深渊。
像这样,他者规训被爱玛内化,她以此为标准实施了对自己的规训。此后,他者规训与自我规训成为爱玛的双重枷锁,加剧了其被规训的进程。
(二)从身体规训到精神规训 在监视之下,爱玛最先表现出对身体的关注,过分追求衣着配饰为其悲剧结局埋下隐患;来自男性的凝视造就爱玛主体性的缺失,进而实现对身体的规训。在此基础上,精神规训进一步加深,爱玛陷入浪漫小说的爱情骗局中无法自拔,并在一轮又一轮的规训中固化认知,抗拒其他信息的入侵;精神规训又反过来继续指导身体规训,二者得以反复强化。
爱玛所受的规训首先表现在对身体的审视上。身体被置于社会之中时,其所承载的意义反映社会关系、组织模式。由于女性只能通过张扬身体去追求社会地位的符号,因而女性倾向于将注意力持久地放在与美、优雅有关的事物上,不仅限于自身,也包括其丈夫与家人。《包法利夫人》中详细描写的首饰、衣着、器物等都暗示着爱玛对这些物品“美”的要求。爱玛讲究自己的衣着打扮,并厌恶查理的不修边幅。在她和男人的交往中,她注重自己的形象,也注重男人的形象;她要她自己充满希望和绮梦,要为爱情醉不可支,要自己拥有对男子的诱惑力。因此,罗道耳弗没费什么工夫便得到了爱玛,吸引爱玛的正是罗道耳弗身体而非精神上的特质,例如生发油的香味,那令她再度想起一起跳回旋舞的子爵。爱玛对身体“美”的追求直接促使她落入罗道耳弗的陷阱,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对他外貌、他的衣着配饰、他的花言巧语动心,爱玛的堕落正由此开始。同时,为了维持这种“身体”上的美,爱玛养成了不良的消费习惯,肆意购入平时用不上的物品,甚至因此和婆婆产生难以调解的矛盾,而忽视了自身不具有经济独立能力的事实。身体规训既使爱玛在爱情中为表面所诱惑,移情别恋;又令她苛求穿着,挥霍无度,被勒乐设计,最终拖垮了包法利家。
身体更是男性凝视的起点,成为爱玛主体性缺失的又一推力。从查理的想象性建构到罗道耳弗的漫不经心,男性们都未将爱玛视作完整的主体。“尽管圆形监狱式的观察者没有以赖昂的方式把爱玛化约为文学上的陈词滥调——而那也正是她的自我构想和渴望的灵感源泉,也不像夏尔(即查理)那样反映出自己的空虚,可是这个观察者也似乎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看到她的全部。”j无论是查理、赖昂、罗道耳弗还是爱玛自身,都不能将“爱玛”看作一个完整的主体,她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在于破碎的身体部件和零散的衣着饰物。罗道耳弗第一次见到爱玛后,在回去的路上思索:“她很可爱!……牙齿美,眼睛黑,脚轻俏,长得如同一个巴黎女子”k,进而看出爱玛一定厌烦了丈夫,愿意过巴黎流行的那种生活,并注意到她脸色苍白,宣称自己就爱脸色发白的妇女。在这思考之间,他恍惚又看到了爱玛刚刚穿着的衣服已经被他脱掉,于是势在必得地宣称自己一定要把她弄到手。微观权力顺着目光渗透,罗道耳弗在第一次见面的短短时间里就已经借此“考察”了爱玛的身体,品评爱玛的面容才貌,并敏锐地发觉了爱玛那些可以被利用、被规训的特质。于是,罗道耳弗训练、塑造了一个情妇爱玛。在罗道耳弗看来,上钩的爱玛与妓女同质;他在考虑如何勾搭她的时候,就在思考事成之后如何把她甩掉。然而,沾染了罗道耳弗“贵族”习气的爱玛却开始偷用查理的诊费,为情夫送去马鞭、印章、雪茄匣等。她在赠送中收获自我感动,在追逐中迷失自我,罗道耳弗“把她训练成了一个又服帖、又淫荡的女人”l,爱玛又从他那里习得监视身体、顺从欲望的习惯,她贪图享受,喜爱奢靡的习惯也由此成型,进一步实现了对身体的规训。
在身体规训的基础上,爱玛的精神也逐步被套上了规训的枷锁。爱玛从关注首饰、器具、风范,到后来追寻“爱情”的表露,正说明精神规训正步步加深。在道特参加宴会时,她对贵族生活还停留在神往的阶段,她希望靠近,又明确认识到自己将会被排斥的事实,她追求器物的相似,臆想爱情而不会付诸实践。但在罗道耳弗的引诱和影响下,爱玛无法保持清醒,更深程度地陷入浪漫小说营造的虚浮氛围。她为女儿起名,考虑的都是些有意大利字尾的名字,最后因想起侯爵夫人叫一个年轻女人“白尔特”,而定下这个名字;她数次要罗道耳弗直白地表露爱意,要求他半夜钟响时想着她;她在自觉受到婆婆的侮辱后请求罗道耳弗带她离开。因为她自认为无法忍耐这样平凡、不高雅、不贵族的生活,以为“爱情”才是至高无上的追求,在这勇气背后其实是爱玛被规训的残酷现实。正因精神上被规训,罗道耳弗的阴谋才会如此顺利地展开,他看到爱玛对贵族生活的向往,更重要的是像故事中总是等待伯爵等贵族男性的女性角色一样,认为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而只有充斥着光鲜亮丽的城堡、仪态优雅的贵族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也正因精神上被规训,爱玛才牢固地坚信浪漫小说中的爱情是像她这样的女子本该得到的,而无法认清自己所处的现实,误以为罗道耳弗与她真心相爱,最终被对方抛下。
爱玛在加固精神规训时,也更加封闭、抗拒接受自己不愿接受的内容。在被罗道尔弗抛弃后,她精神奔溃,身体也出现问题,倾向于在宗教中寻觅安慰。但是堂长托人带给她的书却被百般嫌弃。她嫌教条太苛细,觉得论战文字太高高在上,认为世俗故事不了解人生。她已经无法接受这些书的内容,因为这有违她既有的认知。爱玛实际上内化了浪漫主义小说爱情至上的内核,并以此来审视其他的书籍乃至一切。这导致她只愿意接受与小说相符合的信息,而排斥与其不符合的内容,认为那并非“真理”。在反复固化和封闭新信息、新思想进入通道之后,精神规训也就更加坚不可摧。
至此,爱玛完全由身体规训步向精神规训,精神规训一边不断地自我巩固,一边又反过来指导身体规训。起初爱玛还能控制自己,将打扮身体的花费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勒乐带来的东西,她看一看便觉得用不上,摇头拒绝;但精神规训得到强化后的爱玛只贪图片刻身体的欢愉,而忽略长久的生存所需,不等勒乐上门,便向他主动提出需要各种各样的奢靡物品。身体规训与精神规训就这样被反复强化,从而令爱玛故步自封于想象的爱情之中。
总而言之,在浪漫小说长期浸染、宴会短期冲击、永镇新的男性交际带来的男权与贵族的凝视下,她不由自主地以如梦似幻的爱情、典雅华丽的建筑、身份高贵的男子为标准,去寻求充满刺激的爱情、打量她目光所及的家中布局、衡量自己与他人的身体,在监狱“群岛”中,从他者规训到自我规训与从身体规训到精神规训的双重过程得以顺利进行,令作为被监视者的爱玛无法摆脱被监视的境地,实现规训。
《包法利夫人》中构建了以爱玛为窥孔的全景敞视“监狱”及以爱玛为核心的“监狱”群岛两类系统。在全景敞视“监狱”中,爱玛作为监视者存在,其监视由于地位的下沉而失去力量;在“监狱”群岛中,爱玛受到资本主义和男性话语等多重监视,经历了由他者规训到自我规训、由身体规训到精神规训的双重过程。全景敞视主义的解读表明,不是资本主义直接塑造了爱玛,而是爱玛接受资本主义的知识和话语,以此作为生活目标和人生意义来塑造自我;不是男性直接对爱玛灌输规训,而是男性首先为规训女性制定了一套方法和标准,爱玛接受了同一套话语体系,以此来自觉地规训自己。同时,包括爱玛在内的所有人都无差别地受到权力规训,又以自己所接受的规训为标准去规训他者。
三、结语
权力不仅遍布公共空间,而且侵入家宅空间,更渗透进个人空间,由此构建了将所有人笼罩其中的“监狱”系统,这意味着爱玛无法摆脱监视,也就必然迎来毁灭。更进一步地说,19世纪的女性乃至今天的部分女性,她们被牢牢地限制在家宅空间中,正如同限制在“监狱”的格子间里,无法获取外界信息,只能接受规训并成为维护者与践行者,最终走向悲剧结局。生存在权力空间中,想要和“监狱”本身这一庞然大物战斗的女性难以取胜,在这场不对称的反抗中,她们仅仅只是抵抗“监视”带来的全方位规训便已经倾尽全力,而悲剧性的抗争往往会带来更严厉的惩罚。然而不抗争的结果又是同爱玛一样,最终走向覆灭。面对无从选择的两难境地,爱玛们的悲剧具有某种必然性。每个时代的个人都身处权力空间之中,而现代女性更清醒地看到被监视的现状,隐藏有焦虑、易怒、躁郁的心态。因此,解读《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及其他人的规训如何进行,对应对社会空间现代性危机,避免重蹈覆辙,脱离女性必然的悲剧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a 董云秋,王芳:《〈包法利夫人〉的凝视机制》,《名作欣賞》2018年第20期,第68—70页。
b 施庆利:《福柯“空间理论”渊源与影响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9页。
c 周和军:《空间与权力——福柯空间观解析》,《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58—59页。
df〔法〕 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第8页。
egikl〔法〕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第244页,第85页,第128—129页,第189页。
h 〔法〕 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74页。
j 〔美〕 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参考文献:
[1] 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M].陈怡含编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2] 加里·古廷.福柯[M].王育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 朱晓兰.“凝视”理论研究[D].南京大学,2011.
[5] 梁婷.“圆形监狱”的隐喻[D].西南政法大学,2006.
[6] 张艳.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D].湘潭大学,2003.
基金项目: 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权力规训下的爱玛之殇:《包法利夫人》中的权力话语探讨”(项目编号202010511070)
作 者: 吴梓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