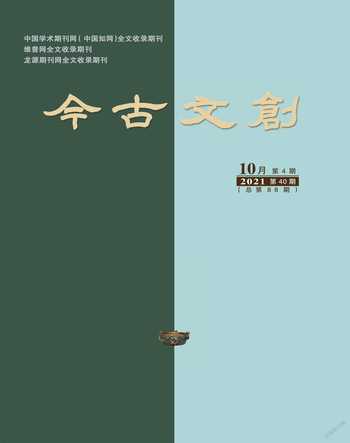论《心迷宫》中的疾病书写
2021-10-26郑洁敏王秋雁
郑洁敏 王秋雁
【摘要】 影片《心迷宫》以独特的非线性叙事呈现了中国乡村的现实境遇,它通过构筑特定的个体生理、心理的病症或是家庭关系的病态,折射出当下中国乡村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挣扎。本文从疾病书写的视角分析影片中生理、精神和文化三个层面的乡村时代表征,展现当下中国乡村焦虑与失调的现象,对乡村发展进程进行可靠性地追问与治疗。
【关键词】 《心迷宫》;疾病书写;中国乡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0-0024-02
电影中的疾病书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上可深入国家叙事,下可探寻本我世界。《心迷宫》讲述了由一具无名尸体引发的人性纠葛,给予观众结构叙事上的新鲜体验。由于乡村影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影片把乡村问题以电影之名再一次旧话重提。《心迷宫》中的疾病世界既存在单一的残缺本体,也象征乡土最本质的元素,如家族秩序、伦理关系、民风民俗等,以充满沉痛感的视角关注乡村困苦背景下的另类生存。同许多谜题电影不同的是,《心迷宫》并没有刻意营造悬疑的氛围来作为吸引观众的噱头,而是通过查尸的全过程再现乡村现实。
一、生理上的疾病
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1]疾病是人类无法避免的生存体验,一个健康且健全的个体往往置身于社会有条不紊的秩序化运作之中,很难关注到生命的背阴面,而一个生病的个体则将其关注的核心聚焦在自身内部的秩序之中。
在影片《心迷宫》中,这种生理上的压制状态最鲜明地凸显在陈自立与白虎身上。陈自立是一个肢体有缺陷的瘸子,随身携带的拐杖是辅助他走路的工具,这根形影不离的拐杖是他对自身疾病状态下身体状况的感知。白虎经常流鼻血,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因而他深夜在小树林与肖宗耀发生冲突时被其一把推倒,也就有了影片谜题情节的铺展。身体障碍在当下乡村是楔入日常的存在,实用主义的罗网笼罩在艰难谋生的底层人民身上。一个生病的个体对于一个家庭不仅是劳动力的缺失,更是压在这个家庭脊柱之上的沉重负担,其內在的结构已然趋向坍塌。
影片在生理疾病书写上输出给受众的是现实世界的脆弱,是农村、农民深陷现代化进程泥沼的无可奈何,身体伤残或是肉体病变都铭刻着低下劳动力的烙印,白虎与陈自立作为在乡村游离的具有代表性的疾病个体,便是当今中国乡村社会浅显且潜在的弱势,并且这种弱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蔓延趋势”[2]。
二、精神上的病态
肉体的脆弱导致了精神的失衡与病态,灵与肉互为归属,当二者被割裂时,精神的病态比肉体的病变更为残酷,更为隐晦,极大程度地偏离了日常生活,到达另一个颠覆的界域。“‘暗疾’就是自知或不自知的隐秘病症,它们可以视为现代人特别是农民精神世界的常态性也是变态性描述。”[3]《心迷宫》这部影片中,这种隐秘的精神病症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心理扭曲和婚姻病态。
生理的缺陷给陈自立带来了莫大的自卑感,固有的男权观念使得他通过对弱者施暴来填补内心的焦虑与不满,辅助他走路的拐杖成了用来殴打妻子的武器。同样是肉身病变的白虎在嗜赌成性的同时,偷窃也成了他习以为常的事情。他在早餐铺子遇到陈自立时,眼红其生意场上的谋利,目光紧盯陈自立的钱包,在偷钱包时没有任何心理上的挣扎。二人生理的困境导致灵魂的破碎与残败。
两人在社会阶层的表征上又有所不同,陈自立在许多村民的眼中是一个在城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商人,而白虎则处于进城不得的尴尬状态,游手好闲是村民们对他的直观印象,努力融合却惨遭排挤。白虎对陈自立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他在早餐店遇到美女在侧的陈自立时,一面笑脸相迎,语气却略带挖苦,明知故问:“刚才那个女的长得不错,她是什么人啊?”眼红、讨好、嫉妒甚至是鄙夷交织共生。以白虎为代表的边缘弱势群体,“他们以破坏城市公共设施、偷窃、群殴等极端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怨恨情绪……农民工因日趋加大的城乡差别、相当困难的生存条件以及种种不公正对待而产生的心理失衡,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其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不容低估。”[4]这种情绪成为横亘在城乡之间难以消融的差异和无法逾越的鸿沟,逐渐生发出“部分农民不妥协、不合作、反社会人格、仇富等病象心态体验”[5]。
疾病书写背后的病态关系也包括病态的婚姻与情欲。黄欢与肖宗耀的情感始终处于怀疑的状态,阶级差异催生了情感中的疑心。黄欢利用假怀孕这个谎言来拴住肖宗耀,直到影片结束都未向其坦白真相。谎言的交织在展现婚姻关系错乱的同时,也增加了影片在疾病书写上的复杂化与多样化。病态的情欲在陈自立和丽琴的婚姻中则是性压抑的痛楚,传统包办婚姻的禁锢导致陈自立和丽琴的婚后家庭生活极度不和谐,两人双双出轨,以满足生理和心理的快感,为影片蒙上一层隐秘色彩。在这个男权至上的村落,婚姻家庭职能是极度不对等的,“极端的不平等来自男人在工作或者行动中具体的自我实现。”[6]陈自立在家庭职能上的价值远超丽琴,婚姻早已在这种不平等的矛盾中土崩瓦解。压抑与愤懑也让丽琴对醉后的陈自立起了杀心,但正如丽琴所说:“我在这里就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如果他死了,我怎么办?”丽琴是一个被现实境况裹挟至失语的农村妇女,身处进不可攻,退不可守的两难境地,出轨似乎成了她最合情合理的解脱,但这种症候是虚妄的,是乡村精神故土失守的哀唱。
三、文化上的困境
法国影评家安德烈·巴赞曾经说过,“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心迷宫》植根于中国乡村现实,不仅揭露着当下中国乡村的外在症状与精神的内在失调,更是凸显着其挣扎无明的文化现状。“在乡土中国下,‘土’是赖以生存的基础,掌管着凡人间的生死。”[7]土伴随着这个落后的偏远乡村度过了悠长的岁月,烧荒草养土成了乡村的既定习俗。在王宝山与丽琴的私会中,丽琴表达了对丈夫陈自立的不满,王宝山笃定地给丽琴献计如何安全地杀害陈自立:“把尸体拖到山上烧了……别光烧尸体,连着周围的荒草一块烧出一片来,就让人误认为是无意中被烧死的,像老孙头那样……”在这个闭塞的乡村,人们利用烧荒草养土来进行毁尸灭迹,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操控规则和生死的手段,这是一种原始性的荒诞,在封闭的乡村空间里,尸体也可以成为养土的原料,伦理、文明开始呈现出被颠覆的状态。
笼罩在这个村落的是“万有的神的观念”[8],村民把自己的愿望都寄托在神灵上,靠神灵来慰藉内心。白虎去庙里烧香拜佛,祈求的是自己赌博能够拥有好手气;肖宗耀的母亲前往庙里替儿子求福;大壮因得知陈自立死亡的真相,回家第一件事便是烧香拜佛……这些人对于神灵的追崇无外乎求财、求福、求庇护、求赎罪,信仰的根本目的本是道德约束、心灵净化,然而却将世俗、功利外化到极致。影片中一系列碎片化的烧香拜佛镜头是贯穿始终且首尾呼应,按照福柯的语境而言,“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9]这个乡村的个体都被置于神像的凝视下,凝视出他们内心的焦虑,他们个人的价值在监视性的凝视下逐渐模糊。同样,这凝视着的也是乡村文化的社会脱节,而这种凝视本身就具有压迫性。影片推翻了现代文明、制度的信任,文化式微导致沉痛的社会割裂感让观众在冷静地凝视与反思中更加能够生发出对于现代文明、现代制度的新诘问。
在这个乡村当中已然积累了太多愤懑,影片的最后对乡村的疾病进行了重生般的治疗。影片结尾,在一片空寂的荒野之上,村长肖卫国与儿子肖宗耀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无人认领的棺材旁,两人相顾无言却彼此都清楚其中故事,最终以双双自首来实现自我救赎。肖宗耀的一声“爸”消解的不仅仅是失序、僵化的父子关系,还有停滞乃至倒退的制度、衰败或是堕落的命运。
四、结语
在《心迷宫》这部电影中,疾病是乡村实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中的疾病书写首先反映了个体生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失调,这是当下中国乡村中,边缘化的小人物生活背阴面所赤裸呈现出困苦自知的生存状态。同时,电影也通过疾病书写来隐喻乡村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从而深入审视和反思乡村的生存现状和文化困境,呼吁大众去探索拯救乡村异化、乡村边缘化的良方与妙药,因此这种充满苦难的书写具有一种更为沉重却珍贵的历史意义。这种“疾病”体验是厚重而深刻的,它的治愈过程也是漫长而深远的。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2]刘文祥.被释放的疾病: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疾病书写[J].深圳大学学报,2019,(6).
[3][5]廖斌.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农民的“疾病”书写[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
[4]康来云.农民工心理问题不容忽视[J].农业知识,2005,(10).
[6](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2[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胡游.乡土中国下《心迷宫》的独特表达[J].名作欣赏,2018,(20).
[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作者简介:
郑洁敏,浙江农林大学中文系182班学生。
王秋雁,浙江农林大学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