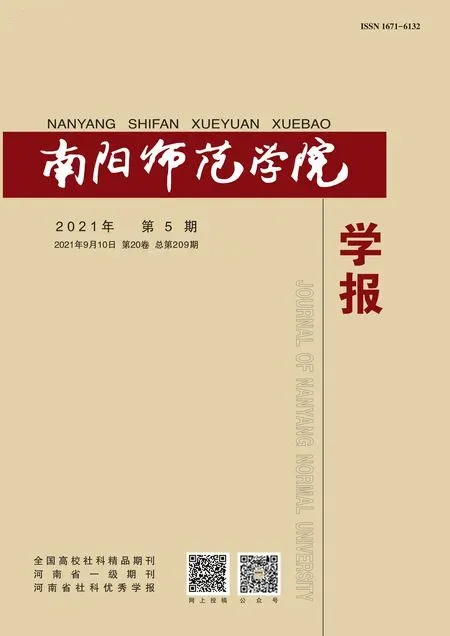绿色发展理念下海洋渔业禁用网具探究
2021-10-24李梦言邵国栿
朱 晖, 李梦言, 邵国栿
(1,2.大连海洋大学 海洋法律与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3.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天津 300012)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追溯至千年以前,其中渔业捕捞是最古老的利用方式。发展至21世纪,人类渔业捕捞的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是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可持续状况的不断恶化,只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捕捞方式弊端尽显。由此,依法治理和有效监管成为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其中特别强调了推动政府工作法治化,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不仅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更是对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同时,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十九大报告绘制了我国绿色发展的路线图,生态文明建设被称为“千年大计”。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渔业捕捞网具标准的各项制度应运而生。原农业部2013年发布了禁用的十三种渔具目录,更清晰地列出了禁用网具的类别名称以及禁用海域。以“禁用网具”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可检索到200余篇裁判文书。其中,2014年“禁用网具”首次被列入裁判理由当中,裁判数量逐年上升。
我国有着广阔的海洋区域和诸多河流湖泊,拥有大量本土特色的水生生物,孑遗物种数目大,生态系统类型也具有多样性。水域不同、目标渔获物种类不同,导致各地对禁用网具的执法标准也不统一。2018年江苏省发生一例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件,因灌南县的渔民在出海进行捕捞毛虾作业时,所用网具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25 mm,而被江苏海警认定为犯罪[1]。检察机关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毛虾这一渔种具有特殊性,用来捕捞毛虾的传统网具本身虽小于国家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但该种网具作业过程中并不会对其他渔类和生态环境产生损害,与禁用网具有本质的区别。最终,经过多方调研和综合认定,对案件做出了撤案的决定。从法律层面来看,尽管针对渔业捕捞方式的规定愈加细致,但对禁用网具的法律性质标准界定依旧模糊。目前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禁止使用双船单片多囊拖网等十三种渔具的通告》中明确禁用了包括拖曳水冲齿耙耙刺在内的实务中常见的四种靶刺类渔具,但拖曳齿耙耙刺仍归在过渡渔具的类目中,没有被彻底禁止。个别省份还在捕捞许可证中核准该网具可以进行作业。由此不难看出,对我国海洋渔业捕捞中禁用网具的界定标准和使用方式仍需要持续的关注和探讨。
二、禁用网具的界定标准
(一) 生物学标准的界定
渔业捕捞可谓人类最古老的生产行业之一,而渔具渔法又是其中最关键、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古老的作业方式逐渐淘汰,不断新生更先进、更科技化的渔具渔法,禁用网具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回顾渔具渔法的发展历程,被限制和禁止使用的渔具有着统一的特征,即不仅能够对渔业资源造成破坏,同时也对渔业水域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最小网目尺寸规则是最早出现的渔业管理措施之一,依据不同渔业资源种类最小上岸尺寸(MLS)制定相对应的渔具最小网目尺寸(MMS)可以大幅度减少包括幼鱼在内的副渔获物。诸多国家在法律中设定最小网目尺寸规则,以此来对渔业捕捞行为和捕捞网具进行规范,保护幼鱼种群。例如,波罗的海的鳕鱼拖网作业最小网目尺寸就从1975年的90 mm增加到1995年的120 mm,以起到促进鳕鱼资源养护的作用[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第三十条对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网具进行捕捞作业这一方式进行了明确的禁止,同时在不同的海域针对不同的渔获物也规定了不尽相同的最小网目尺寸标准。
被列入禁用网具的渔具渔法,多数是因为其对海底生态和鱼类种群会造成双重破坏。其中,耙刺类能够造成海底底质损害,对渔业资源的栖息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不仅如此,使用耙刺会使海底淤泥被冲翻,对海底生存的贝类幼体产生毁灭性的损害。陷阱类主要是用来捕捞幼鱼及小型鱼类,这种作业方式占地面积通常较大,无论是在近海滩涂还是远洋作业,陷阱都会占用较大区域,影响原有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流网类是借助多重网衣的缠绕导致网具的专捕性差、兼捕性强,使用这种网具势必会对渔业种群带来大范围的危害[注]农业农村部《全国海洋捕捞渔具目录》。。
(二)法律性质的界定
我国渔具种类繁多,传统渔具分为十五大类,网具是其中一类,又分为刺网类、围网类、拖网类等。基于规范管理和养护的需要,我国目前把渔具分为准用渔具、过渡渔具和禁用渔具,网具也涵盖在内。准用渔具,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在渔业捕捞中随意使用的捕捞工具。过渡渔具,是依据国家对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状况,将在未来分别转为禁用或者准用的渔具。禁用渔具,是国家明确规定的在渔业捕捞活动中禁止使用的渔具。尽管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渔业法律体系,但目前尚无针对渔业捕捞工具和作业方式的专项法律。《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该规定是我国关于禁用渔具的原则性标准,其中不论是能够破坏渔业资源的渔具还是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都留下了较大的自主空间。这也就意味着,针对不同渔获物种类和不同水域的实际情况,违规渔具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2013年原农业部发布了关于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和捕捞渔具禁用的2号通告,规定了禁用渔具共13种,其中拖网类1种、耙刺类4种、陷阱类4种、杂渔具4种,从而对渔具做出了统一的规定[注]原农业部2013年发布《农业部关于禁止使用双船单片多囊拖网等十三种渔具的通告》(简称《禁用渔具通告》)。。对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渔具进行捕捞的,依据《渔业法》第三十八条予以处罚,对携带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的捕捞渔船,按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处罚。通告所列禁用渔具的共同特点是对渔业资源,特别是幼鱼资源破坏性大,影响鱼类的繁衍和自我更新能力。对海洋生物资源及海底生态造成损害的渔具被限制生产使用。

三、禁用网具界定的争议
(一) 界定标准的变化
梳理渔业保护与管理机制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类对渔业捕捞的认知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在17世纪初发表的《海洋自由论》中提出了“海洋自由”这一观点,该观点认为海洋浩瀚无边,海洋渔业的捕捞理应为一切人所用[3]。在对“海洋自由”最初的理解中,仅局限在各国对海域的使用不应加以干涉,这就直接导致了对海域生态的恣意破坏以及海域内资源的减少[4]。在认识到海洋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后,世界范围内对渔业捕捞的规制和管理理念开始发生转变,新的体系逐渐建立。
1972年,美国《海洋保护、研究和禁渔区法》(MPRS)对在海洋保护区内进行作业的捕捞渔具进行了具体规定[注]MARINE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SANCTUARIES ACT OF 1972 (Public Law 92-532, Approved Oct. 23, 1972, 86 Stat. 1052).。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渔业保护和管理法》,对开发利用渔业资源作出规定,要求防止进行过度捕捞,对过量捕鱼的渔区进行生产控制[5]。挪威在1983年制定《海洋渔业法》,该法授权渔业相关部门对网目尺寸、禁止及限制的渔具渔法进行决定。同时,出台了《关于海洋渔业抛弃副渔获物的规定》,对以鳕鱼为代表的鱼种进行了捕捞网具的网目尺寸规定。除了以上几个综合性的法律法规之外,挪威还有专门针对捕捞渔具的《网目法》,将最小网目尺寸编入法律[6]。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渔业捕捞的规制和渔业资源的养护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首次从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待捕捞方式中存在的问题[7]。公约提出各国在制定海洋生物资源可捕量以及对渔业捕捞方式进行规制时应当采取最为科学的方式,考虑到生态和经济的双重因素,通过限制捕捞的品种、数量、体积等,维持鱼类能够充分进行自身繁殖补充的水平[注]R.R Churchill and A.V. Lowe.The Law of the Sea.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223-233.。
与国际关于渔业捕捞的立法进程相呼应,我国针对禁用渔具渔法的规定也不断革新与完善。1979年,国务院颁布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第四章中限制性规定了渔具渔法的使用[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第十条 现有危害资源的渔具、渔法,应当根据其危害资源的程度,区别对待。对危害资源较轻的,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改进。对严重危害资源的,应当加以禁止或限期淘汰,在没有完全淘汰之前,应当适当地限制其作业场所和时间。,也要求根据渔具对资源的危害程度作出区分。严重危害资源的渔具渔法必须被禁用和淘汰,而对资源危害较轻的渔具则进行计划性的逐步改造。我国于200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海洋捕捞网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同时对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执行标准进行明晰。在法律层面,我国1986年首次颁布实施的《渔业法》就对禁用渔具和作业方式进行了规定,包括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的指标。2000年对《渔业法》的修正中加入了“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明确了规定禁用渔具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免受侵害。总体而言,我国渔具渔法禁用标准经历了从单纯是否能够对鱼类资源本身造成破坏,到是否会破坏海域生态系统整体平衡;从关注“共性”的广泛水域和渔业资源,到关注“个性”的特定海域和具体鱼类品种的转变过程。对拥有较低选择性并且对海洋生态造成较大影响的渔具渔法限制措施正在日趋严格。
(二) 法律适用的争议
我国宪法并没有与海洋渔业捕捞直接相关的规定,但海洋渔业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是为宪法所保护的。宪法第九条第二款[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以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为海洋保护作出了宏观性的指导,为海洋渔业捕捞的专门性立法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律,同样也是在进行海洋环境保护活动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第二条规定了海洋作为自然因素的一种,在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作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手段之一的渔业捕捞行为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和对海洋生态资源的破坏当然受到法律调整。目前对海洋渔业捕捞行为进行直接规制的《渔业法》,其中第三十条对禁用渔具做出了直接规定。但由于在该条款中同时出现了禁用渔具和最小网目尺寸网具,故此在实务中因认识分歧而产生争议。有观点认为小于规定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即属于禁用渔具,应适用禁用渔具的相关法律条文予以规制。有观点认为二者应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虽然二者同时见于《渔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之中,但可以看出立法者在编写法条时分别运用了两种表述方式,将二者并列叙述。在《渤海生物资源养护规定》中,最小网目尺寸网具和其他禁用网具也是分别独立列在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条当中。由此不难看出,立法者认为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分别具有不同的行政法依据,不能轻易等同互换。遍寻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找不到可将“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解释为“禁用网具”的规定。
此外,在鱼类种群较多的海域中,各种鱼类的体型大小存在着差异性,面对特殊的目标渔获物以及特定的水域范围,同样的作业方式可能因为作业海域的不同,而导致渔具结构、网囊网目尺寸的不同,这种现象在华东地区的近海拖虾网作业中尤为明显[8]。捕虾作业是传统的捕捞方式,是维持渔民生计的主要来源,如何做到平衡传统渔民利益与维护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点考量。因此,应当对捕捞传统、捕捞对资源生态的影响、捕捞时节等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评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情况制定更符合发展理念的禁用网具界定标准。
四、禁用网具规制的理论进路和对策
(一) 禁用网具规制的逻辑基准
1.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调的是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平衡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要在合理范围内,保有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不可再生资源不会被使用到枯竭,生态环境的自净力能够得以维系。“可持续发展”这一专业用语首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80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当中,并对此进行了阐述: 人类应当合理把握对生物的管理,使得生物圈不仅能够满足当代人的持续利益最大化,还能维系后代对生物的需求,这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正在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注]IUCN,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Living Resource Conserv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80,p.23.。可持续发展理论将经济发展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有机统一的结合,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全面性发展理论[9]。
从渔业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来看。首先,要在尽可能获得最大、最有效生产的同时对渔业种群自身繁殖能力不产生破坏,保证补充群体有足够的规模,维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需要通过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有和修复,使得渔业资源恢复过程中繁殖的速率超过获取的速率,以此来弥补对其的捕捞,尽可能保持海洋生态系统内部的平衡[10]。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来看,毋庸置疑的是,海洋生态环境的好坏关乎海洋渔业资源是否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我国对海洋环境保护重视程度加大,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别是由于过度利用海洋资源以及陆源污染、围海造陆等活动,使得近海的海洋生态尤其恶劣。渔业种群赖以生存的环境得不到保护,资源的减少是必然的,更遑论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不仅要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更应当注重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
2.生态平衡理论
进入20世纪以来,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社会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化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反思自我,审视过往的种种行为,意识到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生态平衡思想是一种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包括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一种平衡,是生态与社会的平衡,亦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受到污染的海洋环境每况愈下,生态质量持续退化,已经危及人类对海洋资源的正常开发利用,也已然对全球的生态平衡造成影响。若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对生态平衡进行恢复和维系。
海洋生态系统内部的各要素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各种群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一直在进行着物质循环和交换,在这种情况下,海洋生态系统方可保持着结构和功能的相对协调稳定。即便遭受来自外界的一定压力,也能凭借自身的调节能力恢复到一定的良好状态,也就是达到了通常意义上的生态平衡[11]。但任何一个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海洋生态系统也不例外。当外部的干扰已经超出自身调节的范围时,海洋生态系统用以维持自身正常功能运转的能力便消失了,系统内部的有机生物数量降低,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生物资源动荡,海洋生物种类和数量减少。先进的作业方式和不合理网具的使用使得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渔业资源受到严重损害,生态平衡被打破。这不仅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产生影响,还降低了鱼类种群赖以生存的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水平。维系海洋生态的平衡,除了是保持渔业产量稳步增长的需要,也是维持海洋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要求[12]。
(二) 禁用网具规制的具体对策
1.以生态破坏为界定标准
经过工业大发展的浪潮,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对自然生境的无度利用带来的不可逆性损伤开始引发关注。世界范围内开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逐渐淡化,生态中心论随之产生,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正在走进人们的视野[13]。自然资源利用伦理观的转变给渔业资源管理理念注入了新鲜血液,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理念开始被运用到渔业捕捞当中。
全球范围内来看,关于渔业捕捞方式的规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毫无限制的“捕鱼自由”到对渔业资源合理的利用,引入对渔业捕捞方式相应的约束机制。第二个阶段中,各国对海洋的控制权加大,对其海域内的特定资源拥有专属权利。此阶段,在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也开始对渔具渔法采取限制标准,目的是为了对鱼类资源进行保护,特别是针对那些由于国际法缺失而即将面临枯竭的渔业资源。在第三阶段,国际间开始找寻新的生态和经济利益平衡点,各国纷纷建立起防止过度捕捞、进行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开发的机制。对海洋捕捞的关注点由渔业的经济价值转移至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不合理的捕捞方式导致生态破坏的规制力度加大[14]。生态系统方法对渔业的管理,概括来说是综合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对鱼类的种群和繁殖能力进行评估,如确定目标种群未来总可捕量(TAC);二是根据对海洋生态环境因素及各物种生存状态的评估,判断海洋生态系统是否处于健康状态[15]。
2006年,我国就从国家层面提出了“水生生物资源实现良性、高效循环利用的目标”,2013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渔业的发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加强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以生态保护与渔业资源可持续使用为基本理念的渔业资源管理,为渔业捕捞方式的规制开阔了视野,给渔具渔法的标准界定提供了思路。禁用网具和作业方式的界定应当以生态破坏为标准,这里的“生态”不是狭义上的水域环境,而是包括了渔业资源本身。
2.以综合认定为原则
在实务中对禁用网具坚持综合认定的原则,从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传统渔民的利益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全面的考量。
就经济价值而言,渔业资源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不仅能够提供人类所需的食物蛋白,还能创造经济价值,带动就业。我国渔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也常居首位。由于我国海洋面积广泛,内域也不乏河流湖泊,水生生物的种类齐全。有些渔种营养价值高,本身具有特殊性,自身繁殖能力强且生命周期较短。对这些种类使用网目尺寸小一些的网具进行捕捞不会对种群本身造成毁灭性影响,同时还能够获得较高的经济价值。
就生态价值而言,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是使得海洋捕捞业能够有长足发展的前提。若想获得最大并且有效的经济价值,就要保证渔类生物自身的繁殖力不受破坏。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衡的海洋生物系统,有助于海洋生物的繁衍生息,快速恢复生长,进行种群的自我补充。通过控制网具的规格,使得低值、生长周期长的生物种群得以延续生存,保证了渔业资源可持续获取的同时也维护了海洋生物的平衡,兼顾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就传统渔民的利益而言,在科技社会大发展大进步的背景下,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的转变是必要的。由于传统渔业的特性,其对渔业资源的依赖性很强,渔业资源的减少使得传统渔民的生存空间被逐步压缩[16]。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尚存在着数量不少的渔村,那里的渔民世代以捕捞为生。事实上,与现代渔业公司和商业渔民相比,传统个体渔民的捕捞方式对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本身的影响都是较小的。对捕捞网具设定禁用标准,关乎传统渔民的生计问题,在认定时应当充分考虑尊重传统渔民的利益[17]。
因此,在对禁用网具进行鉴定之时,要综合捕捞作业的海域、目标渔获物、传统捕捞方法等各方面的因素,进行全面的评定。评估网具对渔业资源造成的影响时,主要考虑对水生生物生长和发育的阻碍程度,对生物繁殖的影响以及对生物栖息地的破坏。同时,对海底生境进行勘察,判断捕捞使用的网具是否会对水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3.明晰法律责任
对于禁用渔具渔法的行为,我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处罚措施[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 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将构成《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由此对有必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行为人的违法性加以确定,以便符合处罚的正当性。
在渔业捕捞中利用更为先进的网具进行作业,本身是一种开发利用自然环境资源行为,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势必要承担的社会风险。如果在界定法律责任时不能够引入违法性的理论对使用网具的行为进行甄别,而无差别地进行责任追究,捕捞业也就会乱象频生,会令法律失去维护社会秩序的效能。违法性实质上并非一种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不能将违法行为和违法性完全等同。在对使用禁用网具这一行为进行追责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利益的平衡,借助行为违法性这一制度工具兼顾“法无禁止即自由”与“不得损害他人”二元价值,在保障行为自由的同时对法益实施保护。对使用禁用网具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进行判断时,应当在不法事实的基础上衡量更多的因素,比如引入忍受限度理论,判断使用网具的行为是否对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造成了超出限度的损害[18]。
从《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的规定中不难看出,作为镶嵌在社会发展变革背景下的伴生品,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建立在行政不法的基础上的。由此,使用禁用网具可能同时引发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的双重评判,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由行政责任延伸至刑事责任值得探讨。对刑事责任的认定应当引入违法相对论的理念,违法相对论认为违法性的概念共通于所有法域,但由于各个法域所保护的法益和法律效果不同,所以要求的违法性程度当然不同[19]。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和比例原则,刑事违法性应当指:在具有了整体法秩序视角下的“一般违法性”的框架内,在“量”的方面侵犯法益达到一定程度,在“质”的方面符合刑事制裁的情形[20]。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可罚的刑事违法性,就可以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在禁渔期或禁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禁用的方法捕捞的,应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应当将既破坏生态环境又破坏渔业资源的网具列为“严格禁用的网具”,使用这类网具可依据相关规定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而将只损害渔业资源的网具列为“一般禁用网具”,只认定为行政违法,不认定为犯罪。通过精准认定刑法当中“情节严重”的标准,加大刑罚的惩处力度,从而在不丧失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提升刑罚的威慑力。
五、结语
从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的现状来看,期待仅凭借自然本身的恢复能力,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是有一定难度的。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对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规制,才能有效修复生态环境以及保护生物资源。毋庸置疑的是,我国对捕捞工具的限制已经通过立法固化为制度。鉴于渔业捕捞业的不断发展,对禁用网具标准的界定也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革新和完善。在执法的过程中结合实际,对标准进行灵活运用而不是单纯套用,综合考虑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传统渔民的利益。同时,明晰法律责任,加大违法惩处力度。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假以时日,海洋渔业会真正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