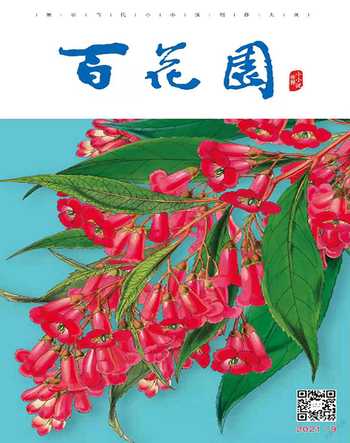追忆与浮现(创作谈)
2021-10-15刘夏
刘夏
少年时代,我跟全国大约一半以上的年轻人一样,也想当个作家。后来从读书到教书,一眨眼就人到中年了。三年前,我在朋友路也的鼓动下开始写小说,重拾旧梦。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之后,我又写了几篇小小说,投到《百花园》,承蒙不弃,也陆续发表了。这次居然又得到了一个发专辑的机会,在“寸土寸金”的《百花园》里,一下子占用了好几个版面,荣幸之余又有些惭愧。
作为一个中年业余新手,我可以用于练习的时间很少,平时需要优先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以及家务……总之,我可以列出多条理由,来为自己的不勤奋写作找借口,虽然这些理由都经不起推敲。这些理由当然也可以拿来解释,为什么我至今只写了一些短篇而没写中篇甚至长篇,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性格原因——我总体上不算是一个热情的人。我敬佩那些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和其他深厚的感情,肯与小说中的人物长时间共处,这是我难以做到的。写短篇的好处之一是“聚散自由”,小小说在这方面优势更大。我把朋友和编辑老师的肯定当作一种激励,这种激励对于一个打“下半场”的业余选手而言,真是宝贵之至。新手上路,谈不上有什么创作经验,我把这篇创作谈当成一个自我梳理的机会。
我相信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写作地标”,无论是基于现实还是虚构。目前为止我写的大都是儿时记忆中村庄里的人和事,那些最清晰最难忘的印象,这次刊发的《周大夫》和《牛得草》也取材于此。当然,我笔下的村庄和儿时真实的村庄并不完全重合,而是被重构了的村庄——鸡鸣村。鸡是村庄里最常见的动物,于是以鸡来命名。儿时的村庄不仅是我生命的出发地,也在追忆中成了我写作的基石。就此而言,我认为个人对生活的真实体验是小说创作很重要的基点,它决定了一篇小说中人物面孔的清晰度和辨识度。如果你对某些人事有长期近距离的观察和“浸润式”的感受,你想要表现的对象就会从万事万物中凸显出来。我在动笔写一个人物之前,通常会反复确认,让他从记忆之海中浮现出来,然后我像个渔夫一样,撒网把他捕获,并提起来展示给岸上的读者看。如果读者看到了,被吸引住,驻足细看,那就算达到了目的。有时候我以为捕获了,但写出来以后发现他像条半死不活的鱼,或者是一条根本没有特色的鱼,那只能先放一放,不断注入回忆,不断翻腾修整,直到人物的活力和特色呈现出来,让你觉得那只能是他。
除了上面所说的,我也同意很多人提到的细节的重要性,没有好的细节就容易写成流水账。就像我们乘坐一辆观光车,不能一直就那么坐在车上看,否则就昏昏欲睡了。我们需要过一段停下车,去某个景点仔细看看,寻找那些独特的美景。细节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也常常是一篇小说的出彩之处。好的细节是小说的徽章,对于小小说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小小说不可能有像长篇小说那样依赖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的浩荡力量。我希望我的小小说有一些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对生活要有静观的能力。
此外,我想对于一个小说作者来说,最不需要的大概就是固有成见或流俗观念。小说作者需要在既定的铁板中发现裂缝,或者对既有的裂缝加以黏合,打破读者对周遭世界的淡漠,让他们不得不停下来,为某个事件或人物重新思考,不再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一个好的小说作者,我想一定是一个有洞察力的智者。洞察力是照亮小说的火把。世界上最有洞察力的智者或许是孩童。我在追想儿时的记忆时,会努力沉潜下来,把自己调整到单纯的儿童视角,尽可能屏蔽掉成见的干扰。这次刊发的《周大夫》和《牛得草》都基于儿时记忆,《床前明月光》虽然取自我成年后的一次真实经历,但真正触动我的是某个人对那首儿时熟悉的诗歌的解构。
最后,虚构的能力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果说真实体验是树干的话,虚构会使一棵树开花散叶结果。有时候为了得到理想的果實,嫁接也是很必要的。我常常把关于村庄里几个人的印象合在一起,重新“组装”成一个人物。或者把当下一则新闻中几千里外的事件,嫁接到几十年前村庄里的某个人身上。这个小辑里的三篇小说内容皆有实有虚,不拘于现实。小说作者有调兵遣将的权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沙场秋点兵的将军,也算是一个文人的越界梦想。
小小说是一艘小艇,轻灵敏捷,不同于中、长篇小说式的大船。然而小小说的小艇中如果是承载一个人物,仍然可以看出其命运的走向;如果是承载一个事件,仍然可以看到情节的波澜。因为每个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事件都是不可重复的,所以小小说的写作,我想不应该有什么套路,而应如水一般,顺势而流。
?
[责任编辑?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