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慈悲
2021-09-06冯祉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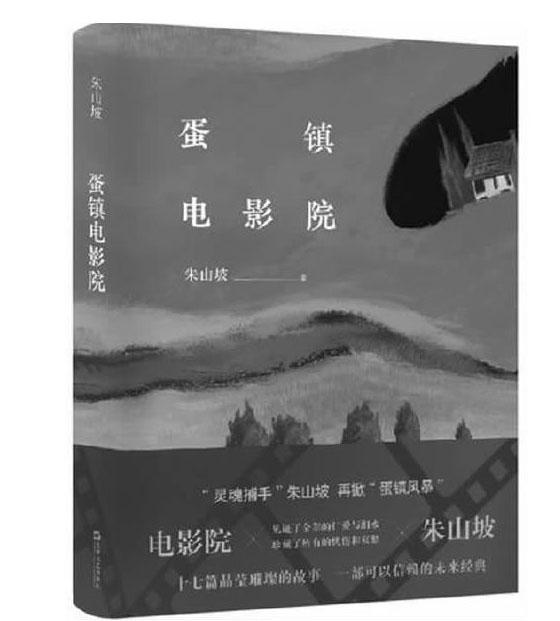

朱山坡,1973年出生。广西北流人。现供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出版有长篇小说《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院》等,曾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多个奖项。
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符号中,地域的聚焦意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被作家们不断书写的母题。这些地理的空间意象往往是以先天的实践为根本书写,并在文学的把控中试图与现实相关联摹仿,形成整体性的观望现象。
很显然,在作家的笔下始终有一个被书写对象——和他们的成长息息相关的一个城镇,但这是不断变形和凝固的,作家们试图摆脱在日常境况中所感受到的含混和幻觉,在影射的状况中不断地确定聚焦的意象,从而完成全新的美学机制思考。在这种地理符号的标记之下,人们所书写的活动是一种信仰式的挖掘,在这些汹涌的对话与记录中,小说形成了伟大的图像记载,从而展现了功能化的审美感应实践。
在朱山坡的小说集《蛋镇电影院》中,朱山坡就将他的书写地点聚焦于乡镇的一个电影院中,以十七个彼此关联又彼此独立的短篇小说,共同驱动形成了一个对于时空的重塑,展露了文学之上的某种分裂和累积。
事实上,小说所尝试的是一种全然相异的叙事姿态,在这十七个故事中,主体始终都在尝试着全然不同的符号实践与生活抵抗,小说吸纳了多重未知的可能性,并借此阐释了复杂的文化细节,将姿态的夸张安放为强烈的整体力量,在这些具体的能量背后,小说形成了汇聚的氛围隐喻,在看似嘈杂的状态中彰显出人物的特异表达。
很显然,小说中始终贯穿且存在于中心的"蛋镇电影院"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投射。它代表着朱山坡对于南方小镇以及小镇中群像的牵肠挂怀,是社会概念之下,人对于事物或者说事件所构建的历史图谱。在这种图谱式样的架构中,小说脱离了自身,在渐变的状况下挣脱了个体的单纯迷恋,转而纳入了环境的力量,在静态的地理层面完成了自上而下的穿透整个历史层面的累积。
一.地理蓝图的意象安放
在当代作家的时代书写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的是对于故乡的描摹与怀恋。作家们习惯将自我的情感投射于涌动的少年时代,不断地呈现出对于时代的挣扎与想象。在这些地理概念的挣扎与思索之中,实际上,所谓的“怀旧”已然超越了对一个地理位置的怀想,正相反,这是一种对于现代时间概念以及历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它意味着某种集体的童话,是对于人类境遇的不断重复和个体缅怀。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地理蓝图下的情感安放,实际上并非仅仅是对时代的怀想,而更多的是一种创作性的精神,是一种对于不可逆转的时间裂谷的隐秘重建,在怀想中不可避免的虚构,能够有效地在断裂的历史中延续无数的缺口,从而令历史的梦幻形成某种重要的价值,在宏观上提出梦幻的注解。
很显然,当作家对童年的回归进行摹仿和试探时,小说就进入了某种驯服的实验性跨度书写中,在这类以地理位置为中心,将人物放置于其中不断书写和探讨的作品中,事件经历了一定的跨度,使得人物主体能够从中抽离,重新地以第三视野来观测过往,在这种脱离与抽身之中,小说实现了真实的对于人的创造和领悟。
事实上,这也必须与人类的记忆同时加以探讨和书写。在我们所习惯的记忆模块中,小说在空间观念上脱离了空间的想象,空间观念中,我们所离得越远,怀念的就越小,但在时间观念中,距离越远,怀念的就越深,因此,故乡和历史也就在此完成了奇妙的错觉媾和,从而在全然新鲜的机制之下开辟出流动的生成。
“蛋镇”在小说中,始终都以一个文学蓝图的意象而存在,朱山坡实际上也从来不避讳这一意象实际上是与他的家乡小镇相关,因此,在朱山坡的笔下,我们能够看到,这座小镇潮湿、封闭、孤独,但同时也善良、温厚,有着天真且极为鲜活的一面。
在蛋镇电影院中,小说构建出了细致且多方位的审美视角,渴望離开蛋镇去美国的胖子、美到能够吸引到所有人的凰,执意要在电影院里生下三个孩子的女人旺兰,这些角色生机勃勃、鲜活淋漓,但同时,也暗含着某种特殊的象征和隐喻,以一种扁平的姿态,呈现出了某种极为鲜明的视角呈现。
实际上,蛋镇和电影院这两个意象都极其具备被书写的价值。从蛋镇来谈,一个阴郁且孤独的南方小城形象,从这部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就显现出来,女孩“凰”貌美且冷寂,执着地等待着一个她认为的不属于这座小镇的男人。在她终于等到了来人之后,很显然,首先感到愤怒的就是蛋镇中的男人们。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即使小说对于此的书写时关于男人们对于外来者夺走了“凰”的嫉妒,但实际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出,这反应的是在独特的精神立场之下,小镇中的人们在自我建构的同时对于外来大背景的排斥与反抗。在这种半真空状况的摹写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在浮躁现实之下小环境内虚构的情感恐慌与情绪茫然。
另一方面,电影院也带有强烈的艺术色彩。首先,电影院原本就是一个商业与艺术所结合的场地,电影作为第七艺术,相较于文学等,需要更多的商业支持和综合建构,更加面向大众,同时也不会有过高的门槛。在这种实践之下,电影院成为了精神匮乏时期的唯一支柱,同时也带有普及艺术思想等的力量,存在于历史的缝隙之中。
不仅如此,乡镇中的电影院实际上展示的是时代情绪下人物的波澜与觉醒,小说所流露的也是一种对于人物情绪的基本探究,在这样的电影院中,人物统统被归置到了若即若离的生活痕迹之中,怅然而悲哀的弥漫书写之下,小说巧妙地切割开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与外在世界,在这种真实迷惘中,我们所能够窥探到的是长久压抑下的隐晦伤痛。当小说将场景搭建在了压抑时代下的开放空间中时,我们就瞥见了看似鲜亮的外壳之下,那层阴郁且灰蒙蒙的内核色调。
事实上,朱山坡擅长在他的小说中不断重构日常的生活碎片,因此,他所进行的一种对生活和文学的分离,实际上是在自我的回溯中不断将属于蛋镇电影院的文学宇宙扩充和构建,在这种模糊的脱离之中,小说既显露了内在者的迷茫与混乱,同时也暗含了粗糙时代背景下群像的奔逃与挣扎,显现出绝对真实的自我解构。
二.时间载体中的情绪转变
在《蛋镇电影院》中,我们能窥探到的是某种对于死寂绝境的展示。当然,蛋镇并不算是真正的绝境,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一地理图景中的人们,大部分都被剥夺或是说剔除了私人的属性,小说所形成的就是一种对于孤岛的驱逐书写,从而使得整部小说形成了某种诗意的纯粹和虚无。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在小说中,电影院以及电影本身,不仅包含了它所带有的艺术力量,更带有神秘的咒语般的魔力,这种魔力隐匿在了画面之间,形成了觉醒的氛围下的杂糅。小说《全世界都给我闭嘴》中,结尾的一段所显露的就是这样一种神秘的魔力。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所有的预想都没有出现。第二天晚上,当我们早早走进电影院时,发现空荡荡的前排已经端坐着两个人。他们紧挨着,亲密无间,像兄弟一样,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耐心地等待电影的开始。
走近仔细一看,果然是袁聋子和荣春天。”
小说所书写的故事秉持了小说集的一贯风格,无厘头的形象表意、诗意且戏谑的惯常表达,袁更凯和荣春天打起来的一幕可笑又合理,但实际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战争仍然具备更加寓言式的显形性质,在电影院这样催眠般的氛围之中,人物的异乎寻常变得有迹可循,现实的抽离也显得极为荒诞。
当小说的最后,荣春天和袁聋子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时,小说所宣泄的就是混乱与虚无之下人物的实体抵抗。电影院所营造的氛围之中,人物被直接地框束在了情绪的白日梦剧场之中,这种狂欢的、抽离了现实的氛围遮罩住了所有真实以及理性的边角,人物也就不得不在真实的虚幻之中挣扎他们所带有的宿命效应。
我们的阅读同样也带有对這种氛围的对接,在前文中提到,小说始终都站在了日常生活的书写之下赋予了生命新的密度,但事实上,我们所阅读的规程却是对于自我生命戏剧性氛围的体验。万物在虚空之中传递漂移,虚空则在固有的时空之中打开便捷,形成全然新颖的氛围重构,这是朱山坡在其小说中重新书写的生命形式,在这样的超越以及转变之下,小说的经验具备了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也就形成了变形的讲述功能。
在十七个故事的书写中,这些讲述彼此连贯却又各自独立且断裂,我们能够在异想天开的诸多事件中挖掘到蛋镇电影院的起点,同时,也能够在细枝末节的想象之中寻找并转移到连续性的生命存在。大众媒体的兴起之后,电影成为了情绪氛围塑造的主体,但在《蛋镇电影院》中,我们仍然看到了经验的可传递性,以及近乎抽丝剥茧式的回溯与找寻。在这些重塑之中,我们窥探到空间虚构后一切的讲述可能,也就完成了对于真理的向往。
《蛋镇电影院》中的人物,我们很难对其找到某种主题的同一性,如果硬要给他们找到一个跌宕的主线的话,或许应该以“逃离”为核心,在这种偏离主题的琐碎之中,小说所形成的是一种偶然转折的故事向度,人物大多琐碎且戏谑,因而,这种毫无头绪般的孤独和内心世界才能显得格外独特,能够在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中闪烁出光芒。
或许,我们可以将《蛋镇电影院》看作是朱山坡给自己做的一场巨大梦境,这场梦境怪诞至极但却也具有极为真实的力量,无边无际的发散之下,小说所隔绝的是一种对于当前事件的清醒认知,作者抛除了一览无遗的初始意志,转而以一种梦态的混沌启动了对于意象的抽象重构,也就将生命想象封闭在了形式的经验之中,掩盖了人世间的悲惨境遇,形成更为神秘且自由的维度和流域,得以成为抵抗现实的乌托邦空间。
三.日常生活粘合之下的欲望想象
在小说的地理空间意象中,我们能够窥探到的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反复惦念和思考,事实上,《蛋镇电影院》所持续展示的都是一种对于人生答案的开拓和倾听。朱山坡试图在他的作品中展示欲望的想象,以期待读者能够在这种欲望的书写模式中抽取属于自己的生命主张。
事实上,我们在小说之中能够看到的是对于自身的独有的注解,故事帮助我们承受对于生命的警惕,同时,也可以想象更为真实的未来。存在于这其中的文本感知是画面式的事件想象。很显然,这也是我们对于精神、乃至生活实践的向度模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或许可以把《蛋镇电影院》当作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寓言摹仿,在这种寓言式的磨合之中,小说所形成的是更具揭示性的未来想象,并且作为了被吸引的力量,提供了对于人物行动力独特的塑形。在文本之中,我们看到,其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封闭的、分离的,一方面,小说所书写的形态是极为日常化和琐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些人物实际上是在阅读经验之外,独立于蛋镇这一形态,并且形成了精神与情感在寓言形式内的演变。要掌控这种动态的体验之前,我们需要不断地改变对于书写主体的认知,也就是在文学的行动之中把日常生活的欲望放置到流动的模式之中,将之实施于全然不同的生活姿态之中。
事实上,我们必须将这类寓言的窥探看作是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塑造,这涉及了我们在生命中所能够感知到的有效欲望,这些痕迹共同编织和塑造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出境,也就改变了我们的存在意象于感知形式。很显然,尖锐的外壳与放空的内部之下,小说撕碎了旧有的叙事教条,转而形成了全新的氛围运动,表达了强烈且真实的情感属性。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小说集《蛋镇电影院》并不是一种全然纯意象的书写,它所采取的是一种类似于拼图解码的形式,将模态之间的自由穿梭尝试着纳入到生活之中,转而营造出时间的隐秘目的,这也就展示出了客观性时空之下本身所隐含的欲望增补,日常的生活欲望将生活的主体变为虚无,而庸俗的世界之中,任何信号的延迟与叠加都带有了渗透的感应价值。
从小说《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中,作者就显现出了一种对于日常生活欲望的想象和寓言式的书写。小说中的人物——胖子章,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扁平却尖锐的角色,展示着他对于美国的好奇,以及孜孜以求的追随。事实上,以一个正常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追随可以说是痴心妄想。更别提胖子章为了去往美国所作出的努力。
在小说中,他不断地做出一些匪夷所思到无厘头的事情,来追求他的美国梦,他送人自己画的美钞,在美钞上甚至有毛主席的画像;他种植橄榄树维护中美和平;甚至要祈求老道士超度自己,以求灵魂进入美国的上空。
在故事的最后,他杳无音讯,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而在老道士以及胖子章的母亲眼里,他飘荡在太平洋的上空。一直到又一次老道士气势如虹的法事过后,他才“顺利抵达美国”。而到小说的最后,在众人眼中的胖子章的归宿显得那样荒诞又奇特。人们把电影中一闪而过的观众角色看作是胖子章抵达美国的证据。小说中的叙事证据不再是一个文学与本源的关系,更多的,实际上是对于想象空间的一个全新的报告。
在小说中,胖子章的归宿即便荒诞不经,但却仍然具备被书写的价值,读者甚至会跟随着众人的感受,从最初的不屑和嘲讽,到最后,真心实意地希望胖子章能够抵达美国。在这种想象空间的重新组合和创造之下,小说重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叙述事件,在这样的空间开启中完成了真实而强大的无限感。很显然,小说所希望完成的是一种对于所有主体性的全然抽离,在这些被消解的弥漫之中,小说完成了对寓意性的诠释,话语成为了真正独立的艺术,人作为欲望本身的主体性也流向存在,在最大限度的冒险中抵达阅读者所能够感受到的个体变革。
四.从容叙事中的群像悲悯
我们需要认清的是,即便在小说集《蛋镇电影院》中,作者始终在以一种戏谑的寓言姿态讲述故事,但事实上,小说中的十七个故事始终都带有强烈的宿命感和悲剧感,由于二元对抗的宿命無从更改也不可避免,因此,小说不得不催动了全然隔膜的投射,来重新聚焦对于群像的书写。
在小说中,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朱山坡对于其笔下人物的悲悯情怀。在他的笔下,人物不仅具备了不可探知性,更在强烈的未知感中阐释出了高能量的毁灭因素。小说在单一空间的极限境况之下提出了黑色的反讽与悖论书写,也从而在这种理性的摧毁之中展露出对于人性的想象。事实上,小说所能够展露出的就是一种对于艺术个体的定义和消亡,在蛋镇电影院中存在着的人们,渴望美、渴望理解,渴望神秘,但值得悲悯的是,他们被剥夺了丰富的意象,只能被异化为需要救赎的悲剧。
我们在小说中所肯定的诗歌意象乃至绝境救赎也正在于此,小说实际上书写了多重的虚无与绝望,冷峻从容叙事之中,蛋镇上生活的人们孤独且绝望、迷惘又失落,但也正是在这些幽暗的状况中,我们窥探到小说对于所谓“旧梦”的书写,这种旧梦的迷恋又通过人们对于电影院的痴迷来加以展现。
因此,我们在谈论朱山坡对于蛋镇中人物的群像悲悯时,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悲悯换言之,讲述为作者对于群像的救赎,救赎,意味着知识向思想的转变。想象是事实的救赎,人们不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弭掉救赎的可能,同时,也不断地在绝境的肯定中尝试相反的精神建设,从而在最接近艺术本身的震颤中完成对于绝境救赎的书写。
我们如何思考世界和讲述世界成为了《蛋镇电影院》所不断书写的命题,在人类文明不断传播同时也飞速变化、飞速消亡的过程中,世界如何依照老旧的叙述形式来讲述新的童话,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文学而言,我们始终在阅读中观测着人物的内心和生活,也正是因此,我们能够在复杂力量的追逐之下体验个人的内心命运。当世界外化为一个孤独且死寂的空间时,电影存留为了这一空间之下的不可理喻,也就是所有荒诞与想象的来源,为情感的生产和调整提供了纯粹的疯狂裂隙。
在《蛋镇电影院》中,我们随处可见人们对于电影的疯狂,《大产房》中的旺兰,执意要在电影院中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深山来客》中的鹿山人和妻子,在台风来临之际,仍然要不顾一切前往电影院;《先前的诺言》中的长毛小子和弟弟,在父亲去世之后,抱着“爸爸攒下的钱是给我们看电影”的想法,兴冲冲地走进电影院。
在这些故事中,电影把灵魂和肉身连接到了一起,即便他们所看的电影大部分时候都代表着大众文化、代表着原始的艺术追求,但小说仍然满足了这种刺激,在复杂的分裂中完成了一种对于感知的原则性体验。在阅读小说时,我们很容易感知到某种对于影像的摇曳不定。很显然,在对“蛋镇电影院”的阅读过程中,我们依然脱离了对于现实的注解,转而试图宣判电影中的虚幻影响,来完成对个人鲜明观点立场的表达。
很显然,小说并不试图书写痛苦,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生命的敬畏和敏感,但值得思考的是,人们对于实体和影像之间的彻底颠倒,以及人物在电影院中近乎破碎混乱的意象形态,都展露出某种已知象征属性之下的积极体验。在这些鲜活却又虚妄的影像中,小说所完成的是一种混沌而汹涌的救赎。人物在那些并不可靠的见证下来过渡小说中人物的独特性,共同编织成为了被救赎的个体,并且,在这些无意识的组织之中,成为了独立于其他人的小部分,颠覆了静默所触及的影像文本。撇开电影的缠绕以及故事的逻辑本身,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作者对于世界的深刻思考:那就是,无论个体的境遇如何,我们永远需要对于自我的界限以及时空的盲限性作出分割,进退在同一之中时,人物才能过渡到真实的镜像,在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痛感并追寻生命的本源。
冯祉艾,出生于1995年。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作品散见于《文艺评论》《百家评论》《东吴学术》《中国文艺评论》《现代文学论丛》《名作欣赏》《中国作家》《青年作家》《野草》《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现供职于《湘江文艺》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