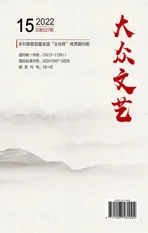新编京剧《金锁记》的古典气韵与现代意识
2021-08-28吴喜梅
吴喜梅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艺术学院,重庆合川 401524)
小说《金锁记》是张爱玲最有名的作品之一。故事以曹七巧的一生为主线,描写了她的心灵变迁和异化过程。重庆市京剧院新编京剧《金锁记》在基本忠实于原著基础上,将深宅大院中,人性的被桎梏被扭曲开掘到了近乎魔幻般的境地,在舞台上呈现出了一种突破文本、充满想象力和创意的强烈个性化风格带来的另一种审美。
一、文本的改编
张爱玲的小说并不以情节取胜,《金锁记》中涉及的人物、人物关系和场景又有纷繁和碎片化特点。因此,选择哪一些事件,采用怎样的结构方式,便成了文本改编首要面临的难题。
(一)事件选择的“取与舍”
《金锁记》小说采用“红楼”笔法,将具有情节推进功能、带来人物性格转折的重要事件,隐藏于日常生活琐碎场景的铺叙中。剧版《金锁记》从众多人物关系和繁复的事件中,进行精心的“裁剪”和“重组”,以曹七巧与姜季泽、曹七巧与儿子长白、曹七巧与女儿长安三条线编织结构,基本保留了“出嫁”“魂荡神游”“分家”“商谈卖地”“裹脚”“长白新婚”“童世舫拜访”等重要事件,完整展示了曹七巧浸泡在病态环境之下被扭曲的人格。
由小说改编为舞台作品,若编创者试图将小说内容事无巨细全部呈现于舞台上,极易带来节奏的拖沓和舞台张力的弱化。剧版《金锁记》对小说部分内容进行了大胆的“舍弃”。比如原小说中,兄嫂登门拜访,曹七巧心有怨怼,尖酸对待二人。在剧版《金锁记》中,编创者去掉了这两个角色,让“曹七巧戴着黄金的枷锁”集中在分家和姜季泽调情两场戏中。从小说道舞台,减去了枝蔓人物,让戏剧场面更集中,也加快了戏的进度。
(二)人物前史的“明场”处理
戏剧作品的场面有“明场”“暗场”之分。“明场”直接呈现于观众眼前,“暗场”则主要通过幕后或幕间处理。
重庆京剧版《金锁记》相对于小说文本,最大的改动在于将曹七巧的出嫁和新婚之夜以“明场”处理。
原小说从曹七巧嫁进姜家第五个年头开始写起,此时的曹七巧,已经饱受苦闷和压抑,并染上了鸦片瘾。
重庆京剧版《金锁记》则从七巧的出嫁开始。
在龙套的圆场表演中,一段抒发出嫁心情的唱词,尤其“小山雀今日里一飞冲天”“从今后堂堂正正活在人前”两句,唱出了17岁曹七巧对未来生活的期许。之后,曹七巧走进了以“门”作为核心舞台意象建构喻指的姜家,并在新婚之夜发现丈夫是一个残疾人,她的悲剧命运和异化人生自此拉开帷幕。
通过这两场戏,观众更直观更完整看到了曹七巧如何从一个17岁花季少女,到幻梦青春落深渊,再到被扭曲成金枷锁下的怪人恶人的变化过程。完整人物弧度的呈现,让七巧这一形象在可恨之外,有了一丝可悲可叹。
二、舞台语汇的丰富性,对“写意美”的遵循与创新
(一)传统戏曲的“写意美”
“写意美”是中国传统艺术最重要的审美特点之一。戏曲也有深厚的“写意”传统:以虚写实、以简代繁、以神传真、以少胜多、一叶知秋。剧版《金锁记》讲述的虽是一个带有现代性的故事,但编创者立足于戏曲的写意性和虚拟性,并把它们作为基本的创作坚守。比如曹七巧的新婚之夜,舞台上并没有演员扮演丈夫这一角色,只是椅子上一件软塌塌的衣服,象征了这一人物的存在。借助一把椅子,通过人椅结合表演,展示主人公最隐秘的内心活动和最强烈的心理欲望。这种极具象征化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戏曲写意留白和虚实相生的特点。再比如曹七巧两个儿女的出生和姜老太太的去世,仅通过两句话“我有孩子了!”“老太太驾鹤归西了!”,完成了规定情境的改变。
(二)剧版《金锁记》意象群的建构
“意象”原本是中国传统艺术学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是艺术的本体,“窥意象而运斤”“意象已出,造化已奇”等,都着眼于意象的心理体验和审美表现的特质,强调其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在中国戏曲中,为了创造戏曲艺术高度和谐的形式和内容,也为了追求真切的诗意之美,创造动人的意境,往往需要借助审美的“舞台意象”。不同于原小说近乎白描式的笔法,剧版《金锁记》创造性设计和运用了一些了舞台意象,建构出一个压抑、触目惊心,又有着强烈悲凉意味的世界。这些舞台意象,并非纯然出自传统,而是带着话剧甚至西洋歌剧的风格。
1.门的意象
剧版《金锁记》用了18道大小不一(最大四五米高,小的一米高左右)、可以移动的石窟门。石窟门不仅是一种舞台置景,它具备了生命,成了一个角色,共同参与了曹七巧悲剧一生的书写。
“门”的意象第一次出现,在“出嫁”这场戏。吹吹打打声中,曹七巧走了进去。沉重冰冷令人压抑的“门”象征着枷锁,也预示了曹七巧之后的命运。
在此后,“门”的意象贯穿了剧版的自始至终,大大小小厚重的“门”依据情节被排列组合为不同形状:曹七巧在姜家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石库门重重叠叠,构成迷宫一样杂乱却错乱的“框”,狭窄黑闷。曹七巧穿堂入室,游走其间,这既是姜家对她无视的直观化呈现,更是压抑备受煎熬人生的意象化表达。姜季泽到来,二人“调情”,曹七巧“神魂游荡”,舞台上四面石窟门在右后侧变换成一个闭合的宅院形状,这是压抑的曹家大院。长白新婚,几面石窟门重新被变换了形状,在右后侧保留着一个由三面“门”围成的宅院,左侧多了两面平行的前后置放的“门”。“门”象征着牢,困顿并压抑着宅院中的全部女性。及至曹七巧的过世,舞台上再次出现和出嫁一样的置景。“门”承载着主人公的一生,也成为其一生悲剧根源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门”这一意象在原小说中并不存在,是导演在舞台演出中的创造性设计。它寄托了编演者对曹七巧命运的解读,深化了作品主题意旨的表达和情境意蕴的展示。
2.月与太阳
张爱玲擅写月亮,她笔下的月阴冷地惨照着世间一切。剧版《金锁记》准确把握到了这一意象,并将其巧妙运用在情节段落的过渡中。从一开始凄凝的夜风中,伴随着苍老的不成调儿的小曲,月第一次出现;到七巧嫁进姜家;到长安被裹脚后;到芝寿的自杀……月亮的意象贯穿始终,“月”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是时光流逝的见证者,是苍凉生命的印照,“月”也为全局增添了一份苍凉之美。而“太阳”则是剧版新创造出的审美意象。七巧过世后,舞台上一轮火红的太阳升起,音乐骤变,长安随着太阳的升起坐起了身,奔着太阳的方向,念了一句“太阳……!”,撕心裂肺的声腔,让人动容,也是这一腔,将剧场观众一直被堵积被压着的情绪释放了出来。
3.极具张力的舞台色彩
剧版《金锁记》在舞台整体色彩上以“黑”“红”两种颜色为主。首先是黑色。不仅舞台极简布景以黑色为主,辅以冰冷的白光,无处不在的龙套,也是黑裤黑袄的装扮,甚至在“出嫁”“新婚”这种欢欣喜庆气氛中,舞台也是以黑色为主色调。极具象征意义的处理,产生了叙事之外的审美。其次是红色。红色是强有力的色彩,它不仅是生命是冲动是希望,在现代许多艺术家手中,它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这是一种激情的力量(这种激情的力量会带来新生,同样会导向死亡),一种被压抑而潜藏的原欲,一种交织着挣扎、躁动、扭曲、痛苦、愤怒、无力、孤独、内疚与窒息的复杂情感状态。红色最典型的运用,在“裹脚”这场戏:层层叠叠厚重令人压抑的“门”矗立一侧,鲜红色的绸子从门内被抛出,七巧用绸子以“裹脚”这一带有仪式感的行为完成了对女儿长安的戕害。
(三)“龙套”的创造性运用
“龙套”是戏曲中的一种角色行当,往往以整体出现,一般四人为一堂,在舞台上常用一堂或两堂龙套,以示人员众多,起烘托声势的作用。
剧场《金锁记》中,龙套不仅构成一种仪式,渲染气氛,更是作品揭示思想内涵的有机成分。曹七巧所面对的社会世俗、家族势力等,通过“龙套”得到了具象化和视觉化表达。
剧的一开场,“龙套”是送亲队伍,是四乡八邻的看客,是围观,也是世俗。曹七巧的新婚之夜,“龙套”是家仆,冷言讥笑和偷窥目光。曹七巧“魂荡神游”时,“龙套”如鬼魅,是嘲弄,亦是意味深远的警示。“龙套”无处不在,在其“圆场”和“捡场”表演中,也都在角色里。编演者将众多龙套和主人公并置于同一场景空间中,以此造成空间的错位和表达内涵的多元性,为观众留下了思索和想象的空间。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张庚先生提出“戏曲现代化”,至今,学界围绕戏曲现代化而展开的关于戏曲美学的讨论和研究日渐深入。在思考中国戏曲的发展之路时,如何在保持戏曲艺术本质的前提下,让戏曲立足当下,焕发时代青春,是戏曲创作者与评论者应该关注的议题。
戏曲的现代化不止限于内容的现代化,即戏曲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对于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人物和情感的反映,也不仅仅只是呈现为技巧和样式的翻新,更应该代表着创作者面对当下的一种姿态和立场,以创新性的舞台表现形式,以传统唱念身段表演艺术体现作品中的新情感和新任务,展示新的格调和审美追求。
然而,“戏曲现代化”在不断地探索和实施中,又极易走入另一个误区,即丢掉戏曲的本体性,以“话剧加唱”的方式完成故事的演绎,或者在舞台上通过写实性豪华布景和装置制造舞台视觉奇观,这是不足取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重庆京剧版《金锁记》立足于戏曲艺术本身,通过高度抽象的写意化、虚实相生的程式化表演、具有象征和隐喻功能的戏剧意象和戏剧意境的营造,充分调动和发掘了戏曲的艺术潜能,作为一部突破文本和某种意识规范的充满想象力和新的创意的舞台作品,是一次成功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