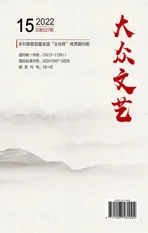《还乡记》中所展现的农民自救的可能
——以冯大生为例
2021-08-28付思扬
付思扬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在《还乡记》中,沙汀塑造了一个被抓壮丁之后从部队中逃出的农民逃兵冯大生,从他的视角反映出四川大后方乡村势力拿着新东西挟持民众,从民众身上榨取油水的社会现状,但是沙汀的重点并非在于表现被压迫的农民的悲惨处境,在他的笔下,这些被压迫的农民固然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们的生活状态——至少在心态上是并不那么“绝望”的,他们再不是鲁迅笔下如祥林嫂、闰土那般的“沉默的国民”,他们会自觉地以四川乡民特有的风趣倔强与压迫者展开对峙。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种反抗精神并非从外界接收而来的,也不是哪个率先觉醒的领头人物带领他们站起来反抗,而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激发出原始的战斗性。其中,以冯大生的转变为例就能看出这种反抗模式的特殊性。
在文中,冯大生一开始从“牛马般的士兵生活”中逃出,凭借自己的毅力返回家中,再到得知妻子改嫁被人霸占,立刻提着斧头前往队副徐烂狗的家里讨回公道,以及最后站出来为反抗保长、乡长这些压迫者企图以打笋子的名义榨取农民劳力和收益而发声,这些情节都表明冯大生无疑是被塑造成一个农民自发反抗的代表。但是,从冯大生起初为讨回公道采取的种种行动来看,他并没有摆脱“旧”的反抗形式:一是不经思考直接提着斧头闯门试图以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与《水浒传》之类的快意恩仇情节并无太多出入;二是当他自行报复无果,便接连向保长、乡长请求主持公道,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有的向位高权重者申冤的习惯,并且文中还特意写道冯大生第一次去见保长时是“依照旧习惯伏下去就叩头”,第二次去找乡长“打过招呼,接着跪下去就叩头”,这个“叩头”的行为就表明冯大生依旧将保长、乡长这类人物当作以往的“官老爷”对待,潜意识中仍然认为他们是高自己一等的可以凭借权力和地位任意左右他人的人。由此来看,冯大生起初的反抗还是旧式的反抗——通过暴力以下犯上或寻求更高位者的庇佑,而非新式的反抗——认识到自己与他人是平等的,自己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事实上,保长、乡长这类人物也是按照旧式的方式来充当着压迫者的角色,虽然他们口口声声“替民众服务”,却只是拿着法令当幌子,凭借权势互相争夺利益,而这恰也是沙汀在回到四川后所深感的“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他们的作用却不过是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一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同时也照应着鲁迅在1934年所说的“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再回到冯大生,当他发现旧式的反抗——暴力和申冤不起作用之后,他自行选择了与保长、乡长这些压迫者划清界限,自己提起山锄铲草,将全身心投入到劳动之中,他开始变得像他父亲冯有义一样“好生把庄稼做起”,坚持租块地烧桴炭,拒绝队副要求的开会,打算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冯大生的这种变化使他逐渐变得独立自主起来,不再是不得不依附压迫者才能生存。在这样的转变下,在最后的打笋子斗争之中,冯大生自然而然充当了农民群众的代表公开与保长、乡长叫板。冯大生开始将自己与保长、乡长放在平等的地位,不再惧怕这些压迫者的威信,认为自己这些农民有权保护自己的利益。冯大生的这种转变让“队副一时间失措了”,让“保长感觉到挫折了”,冯大生的带头作用让压迫者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普通人样”被对待,“好像忘记了他是本保长”。队副与保长父子的反应的转变,说明这种反抗方式才真正打击到了压迫者,也正因如此,冯大生所代表的农民群体才能在打笋子斗争的最后争取到了十分之三的利益——虽然比起冯大生所要求的一半少了许多,但至少说明这种反抗方式是有效用的。
由此来看,《还乡记》讲述的就是一个农民自发反抗压迫者,并在最后取得了少许胜利的故事。吴福辉曾在《沙汀传》中评价《还乡记》是沙汀“第一次从一个种田的‘农民’的角度来反映一切”,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故事”,的确如此,因为整部小说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参与,无论是冯大生的反抗,还是其他农民应和而起的反抗,都是农民群体自发的反应,而非农民以外的其他阶层引导的结果。这样的写作角度不禁让人产生思考:既然要写一个反抗的代表,为什么不将冯大生写成一个接受过进步思想教育的领头人物,比如《困兽记》中像章桐那样的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其实在写作《还乡记》的中途,沙汀也曾经考虑过在其中“安插一个长征负伤留下来的红军战士,作为一场打笋子斗争的‘后台’”,但他最后放弃了这个曾经在他看来“政治鲜明”的设想,认为“他只能按真相去写”,而正是他对“真实”的严格遵照,使得《还乡记》这个“真正的农民故事”进一步让人们产生思考:如果不是进步的思想唤醒了农民,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农民的反抗,让他们在压迫中实现自救?
针对这一问题,其实可以从冯大生的性格特点当中寻得端倪。
首先,文中写冯大生“外表和平老实,一惹毛了,气性可并不小”,“常常硬断不弯”,可见他性格的一大特点就是“犟”。因为性格的“犟”,让冯大生在得知妻子被霸占之后立刻上门讨回公道,让他发现申诉无用之后从此与队副、保长们作对,凭借自己的双手上山砍柴养活自己,以及在最后的打笋子斗争中被保长派人武力制服之后仍不屈服,并与幺爸一起潜逃出去——可以说,正是这种“犟”促成了冯大生的种种反抗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犟”并非冯大生所独有,在其他农民身上都有表现。比如虽然被蒙骗改嫁却坚守自己的一块地,不屈于徐烂狗的无赖,并以死反抗的金娘子,面对队副与保长们的强迫劳动毫不理会,只管自己种庄稼砍柴的幺爸冯立品,还有最后眼见保长们暴力抓捕冯大生,“认真被激动了”纷纷加入反抗的山民们。这样一来,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整个农民群体的反抗,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与冯大生一样,正是“犟”的这种共性,成了这些四川农民自发反抗的力量之源。
实际上,以冯大生为代表的四川农民的性格中的“犟”,追本溯源其实就是一种原始的共性“顽强”,一种靠自给自足生存下去的强韧的生命力。这一点从冯大生自述自己如何逃出兵营就可看出,“讨过口,做过短工,只差了一点没有饿得上吊”,在这样近乎绝望的逃亡中,他坚持了下来,最终返回故乡,他说:“流浪奔波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始观念支配着他,那就是逃命!”可见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一种“原始”的“顽强”。同样的,这种天生的“顽强”也使他在两次声讨公道失败之后,还能坚持不妥协,靠劳动养活自己。事实上,四川农民身上的这种“顽强”的共性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于是在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农民几乎都在劳动,他们自己创造出了一种“换工”的良好制度以克服贫困,对这些农民来说,劳动就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正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冯大生的母亲才会在自己受伤之后为不能参加劳动深感苦恼,幺爸冯立品也因坚信自己的劳动能够养活自己才能我行我素,不怕保长们的再三胁迫。正因身上具备以自己动手劳动生存下去为基础的“顽强”,《还乡记》中的农民才会在被压迫者盘剥,生活困苦的处境下并不绝望,只要他们还能靠劳动换取生存下去的物质基础,那么他们在精神上就永远不会被打垮。
当然,尽管具备四川农民所特有的“顽强”,从冯大生来看,他的反抗也的确算不上彻底,因为从结果来说,他老婆的事到最后也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在打笋子的斗争当中敢于抗议,不再畏惧压迫者的威信,却也只是将保长们提出的“留下十斤”变为“一半”而已,并且最后仍然难免被暴力镇压,以致再一次逃亡。同样的,其他农民虽然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了反抗性,但当保长提出可以“留下十斤”的让步之后,大多数农民开始动摇了,说明在这些四川农民的原始的本性当中,促成反抗的“顽强”与导致妥协的“逆来顺受”是彼此共存的,所以在打笋子斗争的最后,农民只是争取了“十分之三”的微薄利益,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剥削关系,并且压迫者的盘剥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下一届保长的三个候选人全是原保长们的亲戚。但是,《还乡记》所写的这种有限的反抗的意义就在于,它展现了一种农民自救的可能。钱理群认为“鲁迅的启蒙主义和另外一些‘救赎主’式启蒙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就是“启蒙主义者的任务,并不是把外面的东西灌输给民众”,而是要把那些“朴素之民”(《破恶声论》)即普通老百姓内心被蒙蔽了的“诗性”(《摩罗诗力说》)激发出来,“最终引起他们自身灵魂的良性变化”,“成为一个新的自由主体,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还乡记》来看,沙汀正是沿着鲁迅的这种“非救赎主”式的启蒙主义用真实的四川乡土社会生活展示了农民自救的可能,表明冯大生这些鲁迅眼中的“朴素之民”的确具有这种可被激发、可让他们“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诗性”——四川农民原始本性中的“顽强”生命力,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当冯大生再次逃亡,沙汀才会借张大爷之口喊道:“天无绝人之路!……”事实上,“天无绝人之路”是沙汀常写进其小说的台词,早在1931年他最初小试牛刀的三篇小说之一《风波》之中就第一次出现了这句话,那时的沙汀虽然在主观上想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或许自幼接触四川乡镇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经验让他在潜意识中早已有了向民间转向的趋势,因而到了1946年的《还乡记》中,凭借多年对自己所熟识的川西北乡镇社会生活的了解与观察,沙汀更为写实地展现了这种农民自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