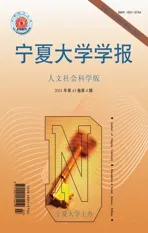牛树梅与擒审石达开事件再考
2021-08-25连振波
连振波
(甘肃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甘肃 定西 743000)
2015年笔者在《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了《牛树梅与擒审石达开事件考》一文,文章基于对牛树梅被破格擢抜为四川按察使的史实,及其著作《省斋全集》中,有关翼王石达开被擒审的过程和记载,结合罗尔刚等人对石达开被擒事件的质疑,肯定了牛树梅对改变四川形势的历史地位。文章提出牛树梅是擒审石达开最主要的人物,“是挽救四川危局的关键性人物,是清军在大渡河前线的主将。清廷能够成功阻击、擒审石达开,是离不开牛树梅这个关键性人物的”[1]。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朱星星的文章《2015年清史研究综述》关注到了这篇文章,并对《牛树梅与擒石达开事件考》一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引述,“时任四川按察使的牛树梅是大渡河阻击战的清军统帅,对稳定四川政局、擒拿石达开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往其功劳之所以会被掩盖,乃是由于他与骆秉章之间的矛盾以及湘军的争功所致。”[2]但是,也有一些读者认为,文章提供的历史铁证不足。为此,本文结合新发现的一些《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等资料,对牛树梅擒审石达开事件,作进一步的考证说明。
一 《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的保存与发现
(一)《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的发现
《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被牛氏后人牛士颖整理收藏。1955年,由其孙牛剑秋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牛剑秋本人也撰写了一篇文章《太平天国翼殿官属印模跋》并附拓片资料,发表于1957年《近代史资料》。笔者在写《牛树梅与擒审石达开事件考》一文时,尚未发现这份拓片资料,因此没有引证。在拙文发表之后,有牛氏后人牛凯新(现居新疆乌鲁木齐市,退休职工,系牛剑秋之孙)向笔者提供了甘肃省博物馆于1955年给牛剑秋的捐赠收据及感谢信,其收据内容为“甘肃省博物馆征集历史文物收据(第329号):兹收到,牛剑秋先生捐赠《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共一册,此据。经手人:刘庆贤。1955年6月13日。”(收据和感谢信原件,均在牛凯新先生处保存。牛剑秋是牛树梅曾孙,牛凯新系牛剑秋直系长孙。)《感谢信》的内容是:
剑秋先生:
承蒙捐赠我馆“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一册,作为博物馆藏品,以便整理陈列,向广大群众宣传教育。热爱人民文化事业,至表钦佩!兹随函送上收据一纸,敬请查收。专函致谢。
并致
敬礼
甘肃省博物馆筹备处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
2019年8月,根据上述材料线索,几经辗转,笔者在甘肃省博物馆历史部书画库内找到了牛剑秋捐赠的藏品。本藏品品相完好,封皮上的标题为“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落款为“通渭牛氏家藏”,封面有方印,内容是“剑秋所藏”。然而,甘肃省博物馆所存资料,与牛剑秋1955年发表在《近代史资料》上的内容有一些出入。据牛剑秋《太平天囯翼殿官属印模跋》一文称载,“印模二十六幅,是1863年(同治二年四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兵败被俘后,解成都受审时所缴的官印,那时我曾祖父雪樵公(名树梅,清道光辛丑科进士)任四川按察使,审结此案后,因奏报时须拓附印模,便另拓一册存笥中。”[3]牛剑秋把二十六张印模拓片的内容、大小、形制作了介绍,并发表在《近代史资料》上。以下是牛剑秋先生整理的26张拓片的内容:
太平天国真忠报国福天侯汪福泰,宽10厘米,长19.5厘米;
翼/殿军功丞相吴图/记,宽6.1厘米,长8.1厘米;
翼殿右拾仆射图记,宽5.6厘米,长8.2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丙班右仆射,宽10.3厘米,长20.7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戎班右仆射,宽10.4厘米,长21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前土师巨帅,宽10.4厘米,长20.4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前策应军仁师巨帅,宽10.1厘米,长20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锐旅指挥,宽8.6厘米,长16.2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副参戎,宽9.3厘米,长18.7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中土师中旅参戎,宽9.4厘米,长18.9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粮廒局中厅正尹,宽9.6厘米,长18.5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饷库局前厅副尹,宽9.5厘米,长18.5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户部租赋科检校,宽9.6厘米,长19.7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吏部记录科检校,宽9.4厘米,长18.8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销磺尹,宽9.4厘米,长18.3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饷库司,宽8.5厘米,长16.3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仁师油盐司,宽8.2厘米,长10.3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甲班右拾指使,宽9.9厘米,长19.6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乙班右拾指使,宽10.1厘米,长19.8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乙班左壹指使,宽9.9厘米,长20.3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丙班左叁指使,宽10.2厘米,长20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丙班左柒指使,宽10厘米,长20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乙班左柒承宣,宽11.1厘米,长21.5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戊班左叁承宜,宽10.8厘米,长21.5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刑部监牢,宽4厘米,长18.8厘米;
太平天国翼殿左掌门,宽9.4厘米,长18.5厘米[4]。
《近代史资料》将26张印章拓片用6个版面刊出,其中第一张有6枚印信,其余全部是4枚,其顺序与牛剑秋文章(下称牛文)所列文本顺序相同。
(二)牛文拓片与甘肃省博物馆藏本有出入
据笔者查找,牛文拓片与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拓片版本有明显出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数量不符。牛文发表的数量是26张印信拓片,而甘肃省博物馆只有23张。
2.装帧不同。牛文每页4枚印章,第一张6枚。甘肃省博物馆藏则最多3枚,最少1枚,其余都是2枚。其中石达开翼王印信拓片是后来补入,并没有装裱其中。
3.牛文对印信的尺寸有详细说明,而甘肃省博物馆拓片没有其印信尺度说明。显然,牛剑秋手头还有更详细的资料。
4.内容不同。一是牛文没有文字说明,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段牛树梅亲笔说明,即“逆首石达开之印,亦系长方真书,长二尺六寸,宽约四寸,曾于所获放伪官执照中见之”。二是牛文没有翼王石达开本人拓片,但甘肃省博物馆拓片中有之,并且是单独存放。三是牛文中有“太平天国真忠报国福天侯汪福泰”“太平天国翼殿戎班右仆射”“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锐旅指挥”“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副参戎”四人的官印拓片,不见于在甘肃省博物馆存拓片中。
二 问题与辨析
根据上述比较,笔者以为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辨析明白,一是石达开翼殿文武印模拓片同为牛剑秋整理捐赠,为什么甘肃省博物馆藏与牛文发表的资料会有如此大的出入?二是作为最重要人物石达开的印模拓片,为什么牛剑秋在整理的过程中没有发现,甚至在发表牛文时没有见到,反而在捐赠的藏品中出现?是谁发现石达开印信拓片并存放博物馆馆藏的?三是牛树梅为什么要在石达开翼殿文武官员印模拓片上,写明这样一段话,注明这样一个历史存在?
(一)拓片出入的问题
《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据牛文载:“我曾祖父雪樵公(名树梅,道光辛丑科进士)任四川按察使,审结此案后,因奏报时须拓附印模,便另拓一册存书笥中。后经我叔父芮青公认为有关太平天国史料,装裱珍藏。前年我乡土改时遗失了,又经我多方访询,才从我村一农妇手中赎回,现归甘肃省博物馆。”[5]牛剑秋,本名牛锟(1881—1955年),字剑秋,号习补斋主人,父亲牛士英,祖父牛瑜,曾祖父牛树桃,牛树梅是其伯曾祖父。民国十二年(1923年),牛剑秋任甘肃省榆中县县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任甘肃省政府秘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任甘肃省会宁县县长,与甘肃省原省长邓宝珊关系密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通渭县文化馆馆长,是一个文史研究专家。故他的这个说明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是可信的。那么,装裱这份印模拓片的芮青公是谁?他是牛瑗之子牛士颖,牛瑗是牛树梅之子。牛士颖是清乙酉年拔贡,甘肃省首届参议会参议员。他们对这份资料的文献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后来,牛氏后人多流落他乡,只有牛剑秋在本地工作,《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由他收集保存,其来龙去脉是真实准确的。
然而,为什么牛剑秋先生一人经手的拓片资料,数量和图片均不能相符?
笔者以为,该拓片最少有两本,牛剑秋捐献了一册,自己手头还留有一册,但两份拓片内容不尽相同,而牛剑秋手中的一份更加详细。但是,从资料上看,牛士颖在装裱拓片时,并没有见到翼王石达开的官印拓片,牛剑秋在整理这份资料并向《近代史资料》投稿时,也还没见到翼王石达开的印信拓片。石达开本人的印信拓片,是后来发现并补存进甘肃省档案馆的。那么,是何人发现了石达开的印信拓片呢?这个人还只能是牛剑秋,因为其他人不知道牛剑秋把《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存在甘肃省博物馆,也就无法把石达开的印信拓片补存进甘肃省博物馆。
(二)牛剑秋对翼王印模拓片的发现
与牛文不同,甘肃省博物馆藏拓片中,有翼王石达开本人的印模拓片。虽然字迹较模糊,但仔细辨认,还是能够看清楚“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的字迹。此拓片单独夹存,没有被装裱在其他拓片之中。按理说,石达开印模拓片的发现,牛文应该会重点关注的,但在牛剑秋写《太平天国翼殿官属印模跋》时,显然没有见到翼王石达开的印信拓片。那么,牛剑秋发现了石达开印信拓片后,为什么仍没有修正他文章的观点呢?笔者认为,其原因如下。
从时间上看,牛剑秋先生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对拓片进行细致分析和再整理,并对他的文章进行研究修改。因为牛剑秋是在1955年6月13日把拓片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的,同年,牛剑秋先生去世。但牛文《太平天国翼殿官属印模跋》在《近代史资料》上发表的时间在牛剑秋去世两年后的1957年。这说明牛剑秋没有时间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份资料,并依据新材料修改自己的文章。
从工作上看,牛剑秋当年有更重要的工作,腾不出手来对翼殿文武官员印模拓片作进一步整理。据其孙牛凯新回忆,他在去世前,在赶时间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我记得小时(7~8岁)在兰州,我爷爷(他当时是通渭县文化馆馆长,有工资)和我奶奶在兰州治病。当时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知道后,让他租住在距邓不远的地方(兰州市广武门外后街37号,巷底是邓家公馆,记得冬天时我曾跟人到邓家去抬回一个取暖用的大铁炉子)。我只记得爷爷天天从早到晚伏在屋里一张很大的八仙桌上写东西,靠墙一面堆了约2尺多厚的文稿,桌子满满的全是正在写的文稿,我们吃饭只能在炕桌上。爷爷也从未顾上和我们说过话,只记得是四五月份带我和弟弟去澡堂洗了一次澡,爷爷才和我们说过话。大约一年我就到咸阳我小姑家上学了,后又过了一年多,照顾我爷、奶生活的我家一个远房亲戚领着我奶和我弟到咸阳来了,我爷去世了。后听我姑讲,爷爷在兰州花费大量时间是在整理《石达开狱中日记》。可是到后来我看到爷爷捐给省博物馆的只有太平天国翼王官印拓片的收据,而没有《石达开狱中日记》的收据。现在想,如整理捐赠官印拓片并不太费事,也不会有满桌子那么多的文稿了,那么爷爷在整理《石达开狱中日记》是毫无疑问了,只是不明白的是此文稿在哪儿?
按理说,石达开的印模拓片放在《石达开狱中日记》一起是合情合理的。牛剑秋在整理《石达开狱中日记》发现翼王印信拓片后,把拓片补入他捐赠的甘肃省博物馆藏品内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只是牛文发表的时候,斯人已作古,已无法修正“翼王之印,当时未获”[6]的错误。另一方面,牛文关注的重点在翼王行军过程中的新定官制的情况,并未讨论牛树梅是否擒审了石达开,是否是大渡河前线清军统帅的问题。
(三)牛树梅对翼王印模的说明
甘肃省博物馆藏拓片资料的第1页有一行说明文字,为牛树梅亲书:“逆首石达开之印,亦系长方真书,长二尺六寸,宽约四寸,曾于所获放伪官执照中见之。”但在牛文拓片中并无此行内容。而牛文在文章中引用了此条,只是删去了“逆首”二字,显然,牛剑秋是见过此行文字的。
可以肯定,牛树梅记载的翼王印信尺寸是与事实相符的。这说明牛树梅所言属实,他是最早见到石达开金印的人,结合《省斋全集》所载,“石逆轿帷风帽皆用黄,上绣五龙,妻妾数人抱子投水,并擒者一五岁子耳”[7]的翼王形象,我们能够相互印证,“牛树梅能够描绘出石达开最初到清营的服装和用度,我们可以确定第一个见到石达开的人是牛树梅,石达开要见的第一个人亦当是牛树梅。”[8]然而,有人质疑石达开翼殿文武官印不全,那应该是自然的。一是石达开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关头,将士有的被打散,有的阵亡,有的已经投降,跟着翼王的人,是为数不多的要与翼王同生死、共进退的“死党”而已。二是据骆秉章奏稿,在大树堡“是夜以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伪官二百余名,悍贼二千余名同时围杀”[9]的石达开军二百余名官员,是随军在职的,并没有随翼王进入清营,其印信自然不在上交之列。
又另据骆秉章《援江官军大捷击退石逆大股折》中讲:
贼遂两路溃走,官军收队回城。是役毙贼二千数百,溺死者不知其数。生擒百余,夺马百数十匹。阵斩逆渠伪忠贞报国敦天燕张姓,伪春官又副丞相元勋张姓,伪翼殿右十承宣谭姓,伪指挥吴姓,伪承宣承尉李太有杨两万,伪将军罗再田,皆剥取绣龙袍,绣龙凤帽马褂,伪印执照等件呈验。据生贼供称,逆渠敦天燕是金田起事巨目,名号仅下石逆一等,不知其名。比提验所获伪印,比石逆伪文所盖之印,仅短小数分[10]。
仅此一役,阵亡将士如此之多,如何能保证翼殿文武建制完整呢?但牛树梅为什么要在拓片上写明这样一段话?他想传达出一个什么信息?
1.石达开翼殿文武官印是统一上交,而非清军战斗所获。何以见得,牛树梅的记载中有“执照”二字[11]。所谓执照,就是配合印鉴颁布的正式书面凭证(如图1),根据太平天国的官制,每个官印都有与之相称的文书,即执照或曰职凭。官员的印信和执照是一体的。如骆秉章称“皆剥取绣龙袍,绣龙凤帽马褂,伪印执照等件呈验”就是明证。既然翼殿文武官印随执照一同送达,则更说明石达开与牛树梅已经就纳降达成了共识或默契,文武官印与执照是随翼王一同抵达的。所以说,翼殿文武官员的印信,是由翼殿官方行文移交给清军的,不是清军抢来的。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证明石达开“舍命以存三军”是确有其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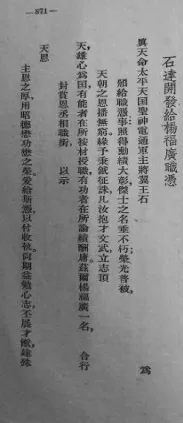
图1
2.臬司衙门上报翼殿文武官印及拓片时,翼王官印已不在牛树梅手中。作为“义降”,石达开“轿帷凤帽皆用黄”,坐轿来到清营之后,与牛树梅达成“义降”条件后,上交印信是自然的。而印信应当与石达开一起,是由参将杨应刚押送成都报“首功”的,但半路上被唐友耕等劫走石达开,翼王印信落入唐友耕手中,这与当时的情境与历史事实基本吻合。牛树梅注此一笔,不是说“翼王之印,当时未获”,而是在强调翼王官印的去向。
三 《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发现的意义
(一)进一步证明牛树梅“义降”翼王石达开
牛树梅与石达开虽然处在两大阵营,但英雄相惜,双方都给予了对手相当的尊重。石达开人称“义王”,作出“舍命以存三军”的高义之举,虽说走入绝地,但数万军士,尚足以鱼死网破。若非“舍命存三军”,又怎么可能在大渡河盘桓二十余天,且把自己文武官员的印信一并交于清军?那么,他为什么选择向牛树梅“义降”呢?笔者认为他们二人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
1.格高品贵,尊重对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诸王中少有的具有大局观的英雄人物。骆秉章在奏稿中说:“伪翼王石达开在粤逆起事首恶中,最为狡悍善战”[12]。但牛树梅在《省斋全集》的记载中,却是完全不同的感情色彩:“达开狡悍善战,与洪秀全等同时起事,在伪六王之中最为雄杰。鸱张十二年,蹂蹭十二省。”[13]牛树梅用“雄杰”评价石达开,算是十分中肯的。牛树梅没有直接记述石达开之死,但他在《省斋全集》中,间接表达了对石达开的钦佩:“启就擒,至成都,磔之。伪启王每叹创业难,或诱以降,则曰:‘吁!似此不忠不孝之人,安所用之!’临刑不跪,亦无惧色,相貌更伟于石逆云。”[14]而石达开对牛树梅的认知是怎样的?按照前文所论述,那份石达开被张冠李戴的《致骆秉章书》,按照内容、时间和当时情境判断,应当是写牛树梅的。
石达开不可能不对所要“义降”主帅作研究。根据“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禁止欺凌”[15]的措辞,石达开应该对牛树梅作了深入研究。“胞与为怀”的赞誉只适合像牛树梅这样的关陇理学大师,岂是对骆秉章、唐友耕说的?严树森评价牛树梅:“绩绍文翁,学宗关洛。循吏名儒,声闻海域。”[16]曾国藩说:“牛雪樵廉访树梅,述其父愚山先生作麟之言也,真挚坚韧,为近世讲家所不及。”[17]牛树梅作为晚清关陇理学大家,张载的“民胞物与”是其一生追求和遵守的信条,石达开“胞与为怀”的赞扬,岂是随口给任何人能说的?另一方面,牛树梅作为四川掌管刑狱的主官,他奉行“原情重于质律”[18](有“原情犹急于质律,释此当思其冤彼,勿淹时日,勿滥株连”的表述)的律法思想,“决狱明慎”,不枉杀一人。牛树梅循循善诱,以说服教育为主,民人不管原告、被告,均能心悦诚服,川民呼为“青天”。石达开徘徊川黔之间多日,在隆昌、彰明等处有牛树梅的德政坊至今尚存,不会不知道牛树梅的政声和为人。因此,“格外原情”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指向的。
2.棋逢对手,斗智斗勇。石达开“鸱张十二年,蹂蹭十二省”,在鄱阳湖曾逼得曾帅几至跳江,其军事才能自不必说。牛树梅赋闲十年,清廷忽然以要职重新启用,是否只是循吏名儒,造福百姓?当然不是,牛树梅具有十分突出的军事才能。牛树梅三次从军,朴诚廉干。咸丰三年,清廷曾“诏参陕甘总督舒兴阿军事”。咸丰八年,被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联名举荐。同治年间,牛树梅上书陕甘总督林远村“任用甘军平叛”策:
军兴以来,剧寇皆南勇所扫荡。今金积堡既平,河州水土犹恶。若参用本省黑头勇,其利有六:饱粗粝,耐冰霜,一也;有父母、兄弟、妻子之仇,有田园庐墓之恋,二也;给南勇半饷,即乐为用,三也;无归之民,收之,不致散为贼,四也;久战狄、河一带,不费操练,五也;地势熟习,设伏用奇,无意外虞,六也。后总督左宗棠采其说,主用甘军,卒收其效[19]。
石达开攻占四川,其“意欲由川南袭成都”并不是没有胜算的军事冒险。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司马错取西川,邓艾下成都,都是乘蜀中混乱,走“鸟道”偷袭成功的。石达开遇到在宁远经营多年,军民一体,山川了然于心,且“决狱明慎”,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牛树梅,就不会有“奇袭”成都的机会。牛树梅善于窥破案情,如经叠控叠诉十七年,由督府、藩司、臬司、道、府、县衙审结的“高恒篡霸张学赞霸田案”,牛树梅不到一天便窥破案情,仅“两造一堂”让真相大白,凶顽得到惩罚。况接任四川按察使(暂摄藩司事),怎么可能对石达开部掉以轻心。“发贼数万,自云南之巧家厅,分股深入,其前股为兵团摧败,昼夜狂奔,直从龙安窜入文县地界,转与汉中合股矣。其后股已近大渡河……现已重兵防堵,沿岸隰远,不知能否周密。”[20]这是牛树梅写给同乡杨凤山的信,前文已经论述,牛树梅在宁远明察暗访、整饬铜务、抗震救灾、筹备军粮、体察民情,与汉彝等各族军民、土司乡绅无不相知相亲,那里的山川原了然于心。石达开侦得的“鸟道”岂能瞒过牛树梅?对石达开的用兵谋略,牛树梅也是了然于心的,石达开“先以中旗赖裕新(即赖剥皮),一股冒险内窜,昼夜狂奔,直走汉南。而自率大队数万乘之,意将使川兵疲于北而失备于南也”[21]。
3.重义爱民,不计个人得失。石达开“窃思求荣以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22](据罗尔刚考,唐鸿学为给其父亲脸上贴金,把这封书信,编入《唐友耕年谱》)这与牛树梅“莫将报国说精忠,驾返双龙愿总空。若得淮阴成汉统,何妨笑入未央宫”[23]诗的表情言志有共鸣,二人不计个人荣辱与得失,也算有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在爱惜民力方面,二人也是心性相通的。牛树梅自不必说,川民在彰明立德政坊,牛树梅以“魏忠贤我也”极力反对。而石达开的起义初心,也是反抗暴政,体恤安民。如其“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给《涪州四民人等训谕》中说:“化民屋为灭烬,恶焰薰天,委巷市于祝融,炎光烛地,致苍生无托足之区,赤子有破家之叹。无心失火,为官者尚奔救,恐逆有意延烧,抚民者何凶残?至此伤心惨目,我见犹怜,饮泣吞声,人孰无恨!”[24]虽是有倾向性的批评,但也是见到了人民的真正疾苦。
(二)厘清了石达开被歼与牛树梅归隐的历史真相
1.石达开被歼大渡河
石达开是在同治二年四月被剿灭的,据癸亥六月《清实录·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载: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初四等日,贼众屡抢渡,均被我军枪炮轰击,无一生还。贼遂图扑松林小河,以冀直趋天全。叠经土千户王应元扼河力战,毙贼数千人。十二、十三等日,督司庆吉,土司岭承恩等,率兵夜劫贼营,毙匪无数。遂将马鞍山占据,绝贼粮道。石逆自知陷入绝地,倾巢而出,直赴大小两河。唐友耕等督兵迎剿。击沉登筏贼匪多名。二十三日,石逆亲拥大众,水陆分扑。官军沿河,用火弹火箭投射。适督司谢国泰、参将杨应刚等,由松林小河马鞍山两路齐进,直扑紫打地。将贼巢一律焚毁。其逃窜之贼,复经汉土兵练,两面夹击,贼众坠崖落水,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余计。石逆率余党七八千人,奔至老鸦漩,复为土兵截杀。石达开等进退无路,仓皇失据。经杨应刚等将其擒获。解省讯明,极刑处死。并于起解该逆之夜,将其余党二千余人,以火箭为号,同时围杀干净[25]。
这个实录是根据骆秉章奏稿写的。但从实录的内容看,至少有这样几个信息是明确的。一是在大渡河让石达开陷入绝境的主力是以土司为主的川军,最后擒获石达开的也是川军和土司武装。杨应刚本身是川军参将,越西厅督司。二是删去了骆秉章奏稿中“该逆无路逃生,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士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并余党至洗马姑乞降”[26]的过分不实的谎言。根据牛树梅藏《太平天国翼殿文武官印拓片》,“宰辅”“中丞”“恩丞”均属以前称谓,翼殿文武官员则称“仆射”“巨帅”等。三是石达开余部二千余人被“围杀”,完全是在不知情的突然袭击之下,这充分说明二千人实际上是在放下武器的“已降”状态,清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杀戮。当然,通过骆秉章的奏稿,更能看出这次屠杀的细节。
二十七日,将石达开五人羁留在营,讯明新被裹挟及老弱者,发给路票,遣散四千余人。尚有二千余名,半系该逆五标悍贼,临阵用以冲锋。遂派文武卞兵及土司岭承恩之弟岭承高押至大树堡,复经唐友耕派督司唐大有等带队过河,约会副将张福胜、督司庆吉等四面驻扎弹压。于五月初一日,先将石达开父子、曾士和、黄再忠、韦普成押令过河,唐友耕派游击龚定国带队,并蔡步钟所派知县阮恩涛等护解来省。臣前于二十八日得报后,虑其余党歼除不尽,将遗后患,札饬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委办善后事宜。乃石达开等于初三日起解,蔡步钟的密派各营于初四日过河,是夜以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伪官二百余名、悍贼二千余名同时围杀[27]。
从上述奏稿可以看出,从五月一日起,“把石达开从欲到成都报首功的杨应刚手中半路截获”,石达开与翼王金印被湘军接手,直达川督骆秉章。这与《越西厅全志》记载:“杨参府带石逆由纳耳坝至富林,意欲径至省城报首功也。而唐军门、蔡知府邀之于路不得前,遂将石逆交二公而回越隽云”[28]是完全符合的。所以,牛树梅在呈交翼殿文武官员印模的时候,无法见到翼王金印,就重点标注了一句。通过骆秉章奏稿,我们看出石达开与其部属五人,是在四月二十七日被“羁留”清营,骆秉章是二十八日“得报”,再次确定石达开不可能向事后才知的骆秉章“义降”。而唐友耕在大渡河对岸,围堵炮击石达开是真实的,但与石达开谈判并招降是不可能的,据奏稿看出,他派员过河都是为事后争功与杀降。刘蓉是事后被骆秉章“札饬”派往大渡河善后的,“围杀”二千已降兵将或出自其手,但与“义降”石达开却和他没什么关系。但刘蓉是布政使,是能够制衡牛树梅的唯一人选。因此,《清实录》:“此次川省将士,人人用命,将积年巨憝,一鼓生捦。并将全股发逆殄灭,实足以申天讨而快人心。太子少保四川总督骆秉章,运筹决策,调度有方,深堪加尚,著赏加太子太保衔。尤为出力之总兵唐友耕,著记名遇有提督缺出,请旨简放。”[29]实录并不说是谁擒了石达开。四川将士“人人用命”,但却只奖赏骆秉章、唐友耕,且都是虚衔和承诺,显然清廷对骆秉章的奏报,已然洞若观火。而是让意见严重分歧的川臬牛树梅“牛树梅着即来京,交吏部带领引见”[30]。
2.牛树梅选择归隐山林
牛树梅再度出山是受川督骆秉章力荐。按理说,骆对牛有知遇之恩,但是不到半年,二人的关系就不融洽,这是为什呢?因此,研究并明晰二人的关系与渊源就十分重要。
同治元年正月初八日上谕:“兹据骆秉章奏称,该员历任地方,循声卓著,此时需才孔亟,似此恺悌益民之吏,岂容置散投闲?”[31]事实上,骆秉章是道光十二年进士,早已飞黄腾达。而牛树梅一路坎坷,直到道光二十一年才中进士。这中间胡林翼于道光十五年,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左宗棠参加完道光十五年的会试后,便放弃科举之路。骆、牛二人在仕途、科举等方面都没有太多交集。那么,为什么要举荐自己并不熟悉的牛树梅呢?其实,是因四川无人,鄂抚胡林翼临终时,与河南巡抚严树森向骆秉章全力秘荐了牛树梅。“比及蜀都,骆宫保言胡中丞曾以弟与面言,则亦犹是阁下之言也。而胡中丞亦既溘逝矣。”[32]众所周知,胡林翼在中兴大臣中,荐人知人冠绝一时。且在咸丰八年,与湖广总督官文联署,力邀牛树梅赴鄂,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33]之叹。然而,骆秉章并不懂牛树梅,二人的矛盾因徐璋案凸显。牛树梅在《与刘霞仙藩司论平反徐璋案说帖》中以为“徐璋有功无罪,郭安邦以投降之贼,挟嫌诬禀。问官复挟嫌以构成之。”[34]为此,川督骆秉章、藩司刘蓉与臬司牛树梅的矛盾公开化,一直闹到朝廷。据《清实录》载:
至游击徐璋被投诚之郭安邦控诉营私舞弊等情,前经骆秉章奏闻,当将徐璋暂行革职,交骆秉章严审究办。兹据有人奏,系郭安邦因要求不遂,起意诬捏。与骆秉章奏,系属两歧。并据声称徐璋久历戎行,声名卓著,所到之处能保卫地方,利益生民,为舆情所爱戴。并称郭安邦所控各情,业据臬司牛树梅亲讯,尽属虚诬,但骆秉章狃与郭安邦一面之词,必欲锻炼成狱,与牛树梅意见颇有龃龉各等语。川省当兹军务需才之际,如果徐璋才尚可用,郭安邦所控,讯属虚诬,骆秉章谅不至以参奏在前,意存成见。唯所奏各情,是否属实,并着骆秉章秉公查讯。[35]
从《清实录》看,朝廷驳回了川督骆秉章对徐璋的弹劾奏稿,支持了其下属川臬牛树梅的观点,这是极为少见的。甚至说出了“骆秉章狃与郭安邦一面之词,必欲锻炼成狱”的话,这是任何一个封疆大吏所难以接受的。通常情况下,朝廷总会顾及总督颜面,一般以严斥下属了事,但为什么这次朝廷偏向了臬司牛树梅,而让制宪骆秉章、藩宪刘蓉咽下了这口恶气呢?难道是被牛树梅“第念古人有为白匹之冤,几于身陷大戮而不顾者。既居此官,无所辞咎”[36]的精神感动?显然不是,牛树梅能看出的案情,骆秉章、刘蓉同样一目了然,但他们的关注点不同,其取舍自然不同。
湘军入川,与川军多有龃龉,且屡有败绩。川督骆秉章在咸丰十一年,先后参劾了布政使祥奎、中军副将张定川等一大批官员,据《清实录》载:“据骆秉章奏,祥奎履任六七年,贿赂公行。于阕分委署,军功保举,防堵报销,均需索使费。复任听僚友家丁讹索……张定川狡诈柔佞,省城武职,非其义子门生,即所亲厚,督署内外,遍置私人……其子张廷奎及张正伦,戴廷超、刘华之类,皆其私人,着一并査参。”[37]先后有数十官员被参,川省人心浮动,但是,这还不足以全面掌握蜀地军政大权。徐璋案牵扯出张定川案,显然是有人故意虚诬,扩大了打击面。
牛树梅此次出仕,实在是受到道义感召,不忍国家糜烂。自己称能报国者,只在于一个“苦”字。因此,虽然是川督骆秉章举荐,但心中只有国家百姓,不会阿谀钻营,成为私人党羽。而川民奔走相告,称“牛青天”再至,如报私喜,清廷需要牛树梅这样一个能聚拢四川民心的核心人物。因此,牛树梅才秉笔直言,据理力争,保住了像军徐璋、罗必超、黔军颜佐才等的性命。愿意牛树梅作为四川按察使(且暂摄藩司事),事实上成为四川官民的精神领袖。川黔官民重新聚拢在牛树梅“民之父母”的大旗下,朝廷和四川需要“牛青天”这样一杆大旗。然而,一旦石达开被擒,牛树梅在四川就成为“鸡肋”,川督骆秉章再也没有好的脾气和柔软的身段,任由其下属“义降”石达开,从自己手中抢走这个天大的功劳。于是,就有了刘蓉、唐友耕赶赴大渡河的“善后”。甚至上疏称:“唯办事才短,近复健忘,交审案件,未能随时清结。川省狱讼繁多,臬司一缺,非该员所能胜任。”[38]牛树梅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弹劾,骆秉章只好说牛树梅“办事才短”,这一次朝廷当然要给这个“鼎定”了西南半壁江山的封疆大吏颜面,于是,就有“牛树梅着即来京,交吏部带领引见。四川按察司,着蒋志章补授”的上谕。
当然,朝廷和同治帝怕是心中有太多的谜团,需要当面问询解开,但牛树梅的选择是第三次归隐林泉。因为牛树梅“义降”石达开,必不为杀之而后快,更何况石达开还带着年仅5岁的儿子。另一方面,杀“已降”这样的事,绝不是牛树梅这样的关陇理学大师所能接受的,但石达开的命运,已经不是牛树梅所能够改变的,于是,他拒绝了“面圣”邀功的机会,而是选择归隐。牛树梅在《省斋全集》中,专门写了当时的心境:“回忆沈朗亭先生有言,既不欲仕,俟到任一二年后再告。今不自告,而如此轻轻放下,殊可笑也。翌晨,李西邨同年曰:‘我昨一夜睡不着。’自笑曰:‘自昨日得信后,看本人似不堪失意者,而汝却如此,何为乎?’然毕竟辗转达曙矣!”[39]这段话也表现了牛树梅一贯超脱且又有不甘的心境。虽然无意与人争名逐利,但毕竟“辗转达曙”,到底意难平。因此,同治之后,牛树梅再没有写一首诗歌咏怀言志,并立誓不登衙门一步。后来寓居成都,任锦江书院山长。他把与石达开有关的文献资料,像《翼殿文武印模拓片》《石达开狱中日记》等,能经手保存的还是收藏保管了,并没有被全部销毁。这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让我们能够窥见一些历史原貌。
(三)拓片显示了独特的史料价值
1.研究翼殿官属结构的新材料
一是石达开出走后对太平军官制作了调整。在太平天国官职表中,只见“顶天侯”“护天侯”“佐天侯”“补天侯”“卫天侯”,不见“福天侯”,“太平天国真忠报国福天侯汪福泰”应该是翼王出走天京后所新设。在拓片中,“太平天国翼殿戎班右仆射”“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锐旅指挥”“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副参戎”等,这许多称谓均不见于太平天国官职体系,如丞相的设立,太平天国是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名目,分为正丞相、右正丞相,副丞相、右丞相,没有“仆射”一职,由此看来,石达开离开天京后,在官制上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而石达开本人的印信,也有不同,由原来的“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变成“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
二是能够了解翼王翼殿官员体系的基本组织构架。根据拓片可以看出,翼殿文武的组织机构是相对健全的。主要分为指挥系统、评价监督系统、后勤与保卫保障系统。指挥系统大约由侯、仆射、巨帅、参戎构成,根据其班次排列,可以看出是一个机构臃肿庞大的决策指挥系统,或许这与其农民起义,需要分官许愿来笼络人的性质有关。从另一个方面,也能够说明为什么三军陷入大渡河绝地,徘徊二十余天而迟迟没有强渡大渡河,最终全军覆灭。其后勤保卫官员,如“太平天国翼殿粮廒局中厅正尹”“太平天国翼殿饷库局前厅副尹”“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饷库司”“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仁师油盐司”等岗位的设立,也是一个班次林立、政出多门、人浮于事的后勤保障体系,难怪设在大渡河马鞍山保证三军性命的储粮地,都被清军土司烧毁,使大军陷入无粮杀马的绝境。
三是可以通过官印的尺寸,判断文武官员的品阶。以前在文献常见的“中丞”“宰辅”等,在翼殿文武官印上没有,而是以“仆射”“巨帅”出现。他们的官职大小,也与官印的大小规格一致。其次是按照承宣、仆射、巨帅、指挥、检校、参戎等岗位顺序依次排列,如右仆射印,宽10.4厘米,长21厘米不等,而承宣略大,其印信宽11.1厘米,长21.5厘米,品阶略高。最小的两枚是“翼/殿军功丞相吴图/记”和“翼殿右拾仆射图记”分别是宽6.1厘米,长8.1厘米和宽5.6厘米,长8.2厘米,此二人应该是书记员之类的文职人员了。然而,“太平天国真忠报国福天侯汪福泰”之印,其宽10厘米,长19.5厘米,与承宣、仆射相当。
2.证实《石达开狱中日记》存在的可能
石达开是儒将,文韬武略,常以诗文抒怀。然而,他的《狱中日记》,一直受到人们关注。晚清时期,已经有人讲到石达开的《狱中日记》的事:
洪秀全诸将,兼资文武者,洪大泉而外,唯翼王石达开。达开之入蜀也,意欲由川南袭成都。宁远府万山中,有一鸟道,亘古蓁芜,未通人迹。由此北行出山,即在成都南门外。达开侦得此路,轻骑趋之。会辎重在后,迷路相失。士卒皆饿莫能兴,遂坐困为土司所获。达开在狱中,述其平生事迹,及洪秀全作乱以来,与官军相持,始终胜败得失之由。为日记四册,记载最详。今其书犹存四川臬司库中,藩库亦存副本。官书记载,用兵时事,率多为官军回护。掩败为胜,迥非当时实录。昔李秀成被获后,手书供词,凡七八万言。为曾军幕下士,删存什之三四。计其关系重要之语,已芟薙尽矣。达开此书,倘有人录而传之,其有稗史料者当不少[40]。
按理说,牛树梅作为四川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是最有条件收藏这本《石达开狱中日记》的。因为当时的四川布政使刘蓉忙于军务,从来就没有在四川布政使任上干过。同治元年四月,骆秉章弹劾了中军副将张定川和四川布政使祥奎,以“附生署布政使”的刘蓉,在龙孔场大战蓝大顺、李永和,而骆秉章还被阻在重庆万县,“是年八月,余暂摄藩司事”[41]。牛树梅身兼藩司、臬司两职,实质上主持着四川的军政。根据《清实录》同治二年癸亥六月载:“刘蓉谙习军务,如能赴汉南调度,较可得力。”七月便“以刘蓉补授陕西巡抚”,并让“着骆秉章速催刘蓉驰往汉南”[42],一直未能到四川藩司任上。所以,四川布政使位置上,实际上一直在由按察使牛树梅“暂摄”。因此,牛树梅是最有可能保存这本日记的人。然而,由于时代变迁,其后人牛剑秋整理的《石达开狱中日记》现在何处,尚待学者进一步
搜罗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