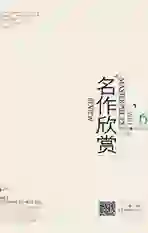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深切呼唤
2021-08-03彭海影
摘 要:个体精神自由是五四时期“别立新宗”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贯穿整个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关键词。《爱,是不能忘记的》从描写柏拉图式的爱情这种超越个人利害得失而最能体现个体精神自由的审美情感入手,深切地呼唤婚姻中爱情和心灵的自由。与其说它是对爱情的呼唤,不如说它是对个体内在心灵与精神的关注及其自由的深切呼唤。将《爱》置于五四新文学和新启蒙运动的双重背景下重新审视,其间隐含的对五四“立人”思想的回归在叙事学及文本意义上都更加显豁。
关键词: 张洁 《爱,是不能忘记的》 个体精神自由 爱情 立人
《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简称《爱》)发表于1979年,作品一发表,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一热情一直延续到今天。一方面,能如此迅速地引起学术界论争的作品必然凝聚着百废待兴的社会转折时期人们对于文学与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另一方面,时过境迁后,离开了《爱》产生的历史现场,读者的阅读热情和学者们的研究热情仍在延续,这让我们感到《爱》所承载的不仅仅是问题小说的时效性,而是关联着人类更为纵深的部分。王蒙是最早感知到《爱》的这种艺术魅力并对当时紧紧围绕小说中的婚姻爱情进行社会学角度的研究提出质疑的人,他说“小说写的是人,人的心灵。难道人的精神不应该是自由驰骋的吗?”a小说不止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伦理道德大讨论,甚至不止于写爱情,而是从描写柏拉图式的爱情这种超越个人利害得失而最能体现个体精神自由的审美情感入手,同时又超越爱情,深切地呼唤婚姻中的爱情和心灵的自由。这种对个体内在心灵与精神的关注及其自由的深切呼唤,即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呼唤,既蕴蓄着张洁思考爱情及人生的精神内核,又是她在不同创作阶段创作风格嬗变的基点;既链接着新启蒙运动对传统封建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双重叛逆,又隐含着当代作家对五四“立人”思想的回归和延续。
一 、一个超越爱情的爱情故事
在新时期新启蒙的人文主义思潮背景下,张洁用“爱”的话语描绘了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凭借这个爱情故事中的凄苦去透视人的精神受束缚所造成的悲剧。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超越爱情、关怀人的精神困境的爱情故事。
张洁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这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故事,用伤痕般的笔调渲染母亲这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凄苦,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受着反思性视角的观照和审视。正像谢冕曾谈到的,张洁的作品并不是以揭露伤痕为最终目的,而在于通过伤痕的揭露以唤起疗救的紧迫感b,于是我们总在深情的叙述和描写中读到母亲的反问、追思和嘱托。文中写到“为什么还要像孩子一样地忘情?为什么生活总是让人经过艰辛的跋涉之后才把你追求了一生的梦想展现在你的眼前?” c母亲对自己无法与老干部因相爱结合而长期处于凄苦的思念進行了反问和追思,这种追思的结果在母亲临终的叮嘱话语里就很显豁了,如母亲曾冒出过一句“珊珊,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自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d 母亲基于自身痛苦的情感和生活体验,告诉女儿即使年轻,也要去了解去探寻自己追求和需要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强调的或许不只是女儿的婚姻里到底有没有不需要道义和法律来维持的爱情,而是更突出有没有向内的自我探寻、自我认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必须是不受任何外力的压迫的自由自主的过程。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伤逝》中子君那一句坚定而激愤的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e子君处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大变革大探索的时期,而文中的母亲与“我”也是处于大变革时期。从苦难中走来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新生活呐喊出新的期待和声音。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选择从爱情这个最能体现人的觉醒,最能激发人的个性的领域入手去呼唤人自由自主地选择自己伴侣和人生的权利,都强调选择的自由。而在《爱》这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故事里,张洁则更强调选择过程的自由,更注重心灵的自由。由此,文中母亲的临终嘱托更像是对子君呐喊的隔代回应,是对“五四”所提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跨时代呼唤。在这个层面上讲,标题“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爱”是超越爱情这种体现个人内在空间和选择的情感,更多地指涉个体的精神自由。由此,“爱,是不能忘记的”既是指母亲与老干部已然发生的客观存在的爱情故事,又是一种超越爱情的对个体精神自由的主观呼唤,是一个超越爱情的爱情故事。
二、 深切的“立人”诉求
李泽厚先生说起新时期文学时,写道:“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都围绕这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f。对“人”的启蒙、觉醒、自由的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与五四最深刻的相似。《爱》正是在重新发现“人”,呼唤“人”的新启蒙思潮中应运而生。
张洁曾在一次访谈中谈道:“《爱》写的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爱情悲剧,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相互关系上投掷阴影的种种社会关系……我要批判的是造成不正常的人与人关系的传统社会意识。”g这段访谈记录明确地提及了传统的社会意识的危害,它操控着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影响着社会关系网中的每一个个体的选择,进而在无形中抹杀了个体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过程。这种传统旧意识对个体精神自由起着最强有力的阻挠作用。鲁迅先生曾在《我之节烈观》中以犀利的言辞直指封建文化中“节烈”这种旧意识对女性的残害,真正的刽子手并不是那些庸众杀人团,而是深刻镶嵌在他们意识里的传统封建旧意识。这种旧意识常常化身为世代口耳相传的道德约束,弥漫在历史的角落却对人进行无形地施压。这种旧意识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规训,其核心是对个体精神进行专制,剥夺个体独立思考的精神空间,并常常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多数人对少数人或个体的舆论压迫。《爱》中母亲对老干部的爱是触犯基本社会道德的,存在着一个社会道德要求与个体情感诉求的矛盾和冲突。很多学者正是由于小说似乎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更倾向于满足母亲的个人的情感诉求和私欲而对小说的格调进行诟病。事实上,小说通过“我”之口质问“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 ”不是对靠法律和道义来维护婚姻家庭的简单否定,而是基于自己痛苦的情感经验对被逐渐淹没的个体精神自由及个人声音的补充和反思。母亲悔于与父亲的结合并非建立在个体自主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在这里,知道自己追求什么、需要什么是个体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个人觉醒的表现。别人的起哄在无形中淹没了个体的思考和感受,催生着群体的无意识。这种个人的觉醒和群体的无意识冲突同样呈现在“我”的身上,“我”纠结是像老学究那样去追究婚姻的本质还是照大多数的家庭那样生活下去。文本始终充斥着个体与群体的声音,个人精神自由与传统旧意识两个互相排除的矛盾体。文章的最后写道:“这悲哀也许该由我们自己负责……还得由过去的生活所遗留下来的那种旧意识负责。因为一个人要是老不结婚,就会变成对这种意识的一种挑战。”h裹挟着家庭主义的封建旧意识与个体觉醒冲突,在母亲与“我”两代人身上引起了挣扎与反思,在母亲爱而不得的痛苦经验中,个体的精神自由被凸显出来。于是在小说的结尾出现了反叛传统封建意识和庸众杀人团的深切“立人”诉求——“我真想大声地疾呼地说: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i。
三、反思性叙述视角与呼唤个体精神自由
《爱》中对个体精神自由的“立人”呼唤,不仅与文本外部的新启蒙文学思潮和社會背景接轨,而且蕴含在文本内部的叙述话语和叙述视角中。李书磊注意到了《爱》独特的叙述方式,他将《爱》的内聚焦叙事称作间接叙事,注重分析间接叙事中作家与接受者的关系,最终指向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j事实上,《爱》的文本内部就蕴含着一种反思视角和呼唤结构,这种反思视角和呼唤结构体现在“我”这一内聚焦叙事视角的精心选择和独特功能上,体现在自由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中。正如张洁自己就曾谈到的“我还是想按我自己的路子写,因为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k。这种反思性视角和呼唤结构的文本形式是为内容而服务的,是呼唤个体精神自由在形式层面的呈现。
《爱》运用内聚焦叙述视角,选择三十岁未婚的“我”作为叙述者,叙述“我”所看到和理解的母亲与老干部的爱情故事。一方面,作为见证人的叙述者“我”既是母亲血脉相连的亲人,本能地关心母亲的情感,也是面临着婚姻选择并追思婚姻本质的大龄剩女。叙述者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叙述必然带有对母亲爱情故事的反思与评价。另一方面,内聚焦叙述对感知范围和视角的限制,使我们只能在叙述者“我”的感知和观察中了解母亲与老干部的爱情故事。文本用大量的笔墨叙述母亲的深情与苦楚,而老干部的形象只在叙述者零星的童年记忆和母亲的笔记本中被塑造,在这里,对老干部叙述是模糊的,留下了许多空白,但这些空白的出现并非让我们根据已有的叙述去推测和重新勾勒。恰恰相反,这种对内聚焦的叙述视角的选择体现了张洁独具匠心的叙述选择,即在形式层面宣告叙述的重心不在于剖析老干部对他与母亲爱情故事的确切态度和情感变化,不在于还原两人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具体细节,而在于“我”这个叙述者对他们爱情故事的叙述、反思和议论。因此,我们看到张洁既没有选择母亲这个有着深刻情感体验的爱情女主角作为叙述者,也没有选择老干部这个爱情男主角,而是选择“我”这个见证他们精神恋爱,同时有婚姻困惑的大龄剩女来充当叙事者,使他们的爱情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在“我”这个旁观者、反思者、追问者的视角中展开。正是在故事次要人物“我”的叙述下,内聚焦叙述带有了反思、追问的意味。
但这种叙述者的反思性视角又不是单向的,它与文本中的叙述接受者相互照应,形成一种亲密的交流关系。此时,叙述接受者成为叙述者和读者之间交流的可靠中介。“我”相对于母亲与老干部的爱情故事是一个外叙述者,于是,在文本的叙事层面上,有一个隐含的外叙述接受者,并且这是一个群体叙述接受者。我们会在文本中看到“如果我们都能够互相等待……我们会免去多少这样的悲剧哟!”“这悲哀也许该由我们自己负责”……从“我们”这一称呼可看出叙述者始终把叙述接受者看作与自己共同思考的同质朋友。外叙述接受者与读者的位置非常相似,以至于有学者越过叙述接受者直接感到这是一种作家、读者平等的叙述。正是叙述接受者与读者有相似的位置,使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叙事文内在的交流过程,即在作者与读者中间的文本内的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对话。l而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对话常常使用自由间接引语这种话语模式进行,这种话语模式既浸透了故事主人公母亲在爱火中煎熬的痛苦,又熔铸了叙述者“我”在转述中的思索。构成了文本中“母亲”自观,叙述者“我”看“母亲“的爱情,叙述接受者既看母亲的爱情又看到“我”看“母亲”的多重“看”的结构。从这独特的“看”的重重设计,也可看出文本正是要在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对话结构中凸显这种追寻、反思的过程,而不单单是鼓吹“爱”或是展现“爱”在现实中的绝望。而这种“看”的结构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呼唤,一种对个体心灵的呼唤。因此,也就在这种对话中将文本的超越爱情层面,引向一种自我的追寻,一种个体精神自由的“立人”诉求。总之,张洁苦心经营的文本形式与文内的意义是相辅相成的,谁叙述与怎样叙述都在文本形式上为我们提供理解《爱》的突破口。
《爱》看似写的是对传统封建旧意识的挣脱,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故事。但正如《涉渡之舟》所说的“一个‘丰满而匮乏的旧日,移交给后人的是重生、补偿的嘱托与许诺”m。《爱》所呼唤的精神自由是融入了对现代化进程中文明的思索,是向着未来和明天的。小说曾写到“在商品生产还存在的社会里,婚姻,也像许多问题一样,难免不带着商品交换的烙印”,原本婚姻伴侣是依靠个体精神自由选择的,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却惨遭等价交换原则的冲击与同化。这种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力度让“我”在追寻婚姻本质时满带质疑,类似“我为什么要钻牛角尖呢” n的对自我追寻的质疑贯穿着全文,甚至于让读者感到切肤的悲哀。我们既不能完全摆脱时代的限制存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也不能完全失去自我受限于现实,但并不代表《爱》中描写的几乎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爱就无意义了。相反,《爱》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未来的、活着的,可能会在历史的严寒中僵硬缩瑟的生命们留住本可能一去不返的诗意、温暖和理想。o《爱》既是对“五四”时期“立人”思想的回归,又是对未来的期许与呼唤,它本身就存在着一股力量。
a 王蒙:《〈北京文艺〉短篇小说序选》,《王蒙文存》(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b 谢冕,陈素:《在新的生活中思考——评张洁的创作》,《北京文艺》1980年第2期。
cdhin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潮汐文丛》,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102—122页。
e 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f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页。
gk何火任:《张洁研究专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351页,第116—117页。
j 李书磊 :《〈爱,是不能忘记的〉叙述观察》,《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6期。
l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m 戴锦华:《涉渡之舟·同行者与涉渡之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o 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
作 者: 彭海影,河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