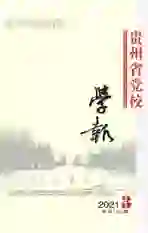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前提条件、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
2021-08-02吴岸英林艺芳
吴岸英 林艺芳
摘 要:2018年《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机制,赋予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为保障监察证据的合法性,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有着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意义。然而,因立法规定不明确和实践运用不协调,导致监察证据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存在困境。如两法规定的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种类不一致,两法在具体的取证程序方面存在区别,监察程序中缺乏证明非法取证的手段以及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监察证据排除难的问题。对此,为构建和完善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完善两法关于监察证据的规定,明确非法监察证据的内涵和范围,新增非法监察证据的证明手段和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指导理念,以保障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
关键词:监察法;监察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监督制约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3 - 0066 - 10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事关全局的政治改革,它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办理工作。对于职务犯罪而言,如果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这就涉及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在此过程中,产生于监察程序中的监察证据也将随之转化为刑事证据,并受到刑事诉讼中各种证据规则的约束。在当前工作中,由于立法规定和理论研究的缺漏,监察证据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成为现实难题之一。监察证据如何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应符合何种证据合法性标准、应如何实现非法证据的排除等,这些问题在现实办案中仍然让人疑惑重重。
为此,笔者将围绕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问题展开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下文简称《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监察证据在监察程序中也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过这并非本文的研究范圍。本文研究的是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如何适用具有刑事司法属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问题。笔者以《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的相关规定为基本出发点,阐明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探讨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困境,随后针对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寻求合理路径,以期为实践操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前提条件
(一)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条确立了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机制。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粗略,并且《刑事诉讼法》未就监察证据转化问题予以进一步规定,因而究竟监察证据可以直接未经审查便转化为刑事证据,还是应当经过特定的审查机制方能转化为刑事证据,目前仍有一定的争议。解决这一问题,是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性前提之一。
关于何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学者们提出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监察证据可以未经审查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因为该款是一项授权性条款,即授权司法机关可不对监察证据再行收集固定,而直接对其进行审查判断,并依审查结果将其作为指控或定案的依据。[1]但是,有学者对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作为证据使用的资格问题持保留态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要求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两法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但并未直接赋予监察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而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应以《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为宜。[2]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应当被理解为“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其效果为“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再次履行取证手续”。[3]在立法层面赋予了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资格,有利于解决两法衔接中的证据适用难题。为了落实中央打击贪污腐败工作的开展,监察机关依法调查取得的监察证据毫无疑问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为了避免实践中监察机关、侦查机关因重复取证破坏证据的完整性从而影响案情的进展,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两法衔接的不顺畅等问题,所以以法律形式赋予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资格就显得尤为必要[4]。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监察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直接取得证据能力。换句话说,监察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还应当经过必要的审查判断机制,接受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检验。[5]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还得视这些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其中,证据能力考察的是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即证据的取证过程是否符合立法要求,有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我国立法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此即对定案证据必须具备证据能力的要求。监察证据虽然获取于监察程序中,但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已经取得刑事证据资格,司法机关应当对其“一视同仁”,需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和认定,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约束。
(二)监察证据取证规范与刑事证据要求相一致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显然,该条明确了监察机关调查取证应遵循《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范。[6]从该规定可知,立法者没有选择在《监察法》中构建独立的监察证据体系,而是采用证据体系借用的方式,将刑事证据的概念、类型和规则引入到独立监察程序之中。《监察法》毕竟是一部新的法律,其关于取证程序的规定仍然难以完全适应现实办案需要。相比之下,我国刑事诉讼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一套完整、严格、细致的证据制度和标准体系,并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中。借鉴刑事诉讼的相关证据要求与标准,特别是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将有助于监察机关顺利完成证据收集、固定、审查、运用任务。另外,就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程序而言,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监察机关应当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此时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将发生衔接关系。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共用一套证据要求和标准,也有助于二者之间实现顺利衔接。[7]再者,从审判中心的角度出发,为了确保后续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审判阶段法院能对监察机关取证行为进行有效的审查并排除非法证据,要求监察证据的取证过程符合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为确保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监察机关应当严格按照刑事审判的要求和标准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使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在证据资格、证明力和证明标准方面与审查起诉、刑事审判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目前,关于《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有不同的理解方式。笔者认为,对该款可作如下理解:一方面,监察机关应当首先严格依据《监察法》的规定进行调查取证。这主要体现在《监察法》第四章和第五章里面。另一方面,如果《监察法》对有关取证程序未予以明确规定的,监察机关则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执行。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该规定在《监察法》中并不存在,那么在具体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则可以借鉴侦查程序。简而言之,监察机关应当贯彻“监察法规为主导,刑事诉讼法规为补充”的原则,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使监察证据材料程序合法、内容真实,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经得起证据合法性审查环节的检验。这么一来,监察证据达到刑事证据的要求和标准,有利于排除监察机关收集的非法证据,规范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合理运用。
(三)《监察法》明确监察证据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约束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由于该款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学者们針对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提出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根据《监察法》第三十三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针对监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无论是在监察调查程序还是后续刑事诉讼程序中,均可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由监察人员违法取得的证据。[8]但是,有学者认为《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仅规制监察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明确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后能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条规定并不能完全解决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后的证据审查和证据使用问题,导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对此,笔者主张对《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作广义解释,不管是在监察程序还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监察证据都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处的“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既指监察机关在监察程序中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也包含司法机关对非法监察证据予以排除。监察证据作为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的桥梁,理应在两个程序中都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9]一方面,根据该条的规定,监察证据在监察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无疑义;另一方面,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层面上,“案件处置”不仅包括监察机关“监察、调查、处置”职责中的处置,也包括检察院和法院对案件的处置。因而,“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也应包含刑事诉讼程序中司法机关对监察证据的审查,以及对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的监察证据予以排除的决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调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获取的监察证据也随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必然离不开证据获取违法等原因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司法机关不可避免会对监察证据进行审查和认定,并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监察机关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所以,《监察法》明确规定的监察证据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在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均应予以适用。
二、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性
(一)防止监察权力滥用,实现程序监督和制约
因监察程序具备独立性、密闭性和特殊性特征,为保障监察证据和刑事证据的顺利衔接,保证职务犯罪案件的有效开展,监察证据应当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10]监察程序奉行的是调查不公开原则,其运行呈现出高度封闭性特征。该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允许律师介入调查程序,无法为被调查人提供法律帮助;二是采取的强制性调查措施期限较长,且调查地点具有相对的封闭性;[11]三是监察程序的启动、运行和终结均由监察机关内部决定和具体实施,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任何权力都可能被滥用,监察权力也不例外,况且监察权力作用的范围较广泛并且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而监察权力一旦被滥用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权具有权力属性上的优势,带有政治性色彩。当监察机关在监察程序中带有某些人格化取向时,就可能在履行职权时发生立场偏离问题,将手中的公权力作为谋取部门利益的一种工具。为了职务犯罪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处理,使被调查人得到刑事制裁,在证据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大都依赖被调查人的供述而被调查人不予配合的情形下,监察机关很容易采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另外,监察程序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使得非法监察证据难以排除。虽然监察机关设有专门的干部监督机构,但实际上在监察程序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权责没有明确划分。表面上各监察部门的设置有体现监督制约的意识,但实质上监察部门之间容易发生怠慢和互相推诿的情形,增加了监察程序中排除非法证据的难度。再者,律师无法介入监察程序,同样使非法监察证据难以被发现。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律师可以通过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以及调查取证等方式遏制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律师的介入是有利于诉讼制衡,能够督促侦查机关合法收集证据。相比之下,《监察法》没有规定律师介入问题,是因职务犯罪案件调查工作正处于证据尚未确定阶段,律师的提前介入存在极大的证据风险,这种风险可能导致应该被查证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然而这么一来,监察程序显得更加封闭,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权益遭到侵害后也难以被发现。因此,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防止监察权力的滥用,有效实现对监察程序的外部监督和制约。
(二)降低监察证据错误率,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由于监察程序具备封闭性和秘密性特征,监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权力滥用和非法取证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恣意调查和非法取证行为不受任何形式的约束。监察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以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如果监察机关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在监察程序中未予以排除的,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必然受到司法机关对监察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通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监察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有利于正确和有效打击职务犯罪案件。运用该机制规范监察权力的合法行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监察证据的错误率,以查明事实真相和保障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
(三)缺乏证明非法取证的手段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对非法证据的证明手段包括录音录像移送和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出庭作证。而在监察程序中并不存在上述证明非法取证的手段。《监察法》仅于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监察机关在调查阶段的重要取证工作实行全程录音录像,但并未要求将相应的录音录像随案移送至刑事诉讼程序中。另外,在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监察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时,对调查人员应否出庭说明情况,立法没有予以明确规定,无疑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难度。
1.录音录像移送问题
相较于《刑事诉讼法》对录音录像的有关规定,《监察法》扩大了录音录像制度的适用范围,且为调查人员应当履行之职责。全程录音录像可实现对监察调查行为的有效监督,并证明其取证行为是否合法。但是,关于录音录像是否移送问题,《监察法》规定的是“留存备查”,意味着其并不会随案移送检察机关而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同时也会出现后续检察机关查核、审判机关调取的困难。在此情况下,因录音录像未能随案移送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庭便缺乏判断证据合法性的有效手段,对排除非法监察证据这一机制便缺少制度设计和程序保障。
2.监察人员出庭问题
《监察法》未涉及监察人员应否出庭作证问题,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就有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其中,监察人员是否属于“其他人员”的范畴并不明确,则需要立法作出进一步的解释。此外,为保障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监察法》是否有必要要求监察人员出庭作证以说明其取证合法性问题也亟待解决。
(四)实践中可能存在监察证据排除难问题
我国目前的国家机关体系形成了“一府一委两院”的架构,监察委的地位高于司法机关,特别是监察委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更加提升了监察委员会的地位。监察机关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监察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监察机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其中法官和检察官作为履行公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也要接受监察机关的监督。正因如此,司法机关在面对非法的监察证据时,不敢轻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甚至排除非法监察证据。司法机关对监察机关收集的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实际上是对监察机关办案工作的一种否定,这将影响监察机关本单位和个人的评优考核等。因非法证据排除的行为触及监察机关的利益而将遭受阻力,可能被视为司法人员对被调查人的开脱和包庇以及不配合反腐工作,一定程度上会给司法办案人员带来政治方面的风险,导致司法机关在对监察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时不得不持谨慎的态度。
四、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对策建议
实践中监察机关办案以《监察法》为准,并不适用《刑事诉讼法》。如果司法机关仅以《刑事诉讼法》为标准审查并排除非法监察证据,那么程序衔接适用将陷入两难困境。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既需要遵守《监察法》的相关规定,同时也要以现有的刑事诉讼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参照。针对理论和实践中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笔者提出如下解决措施,以实现打击腐败职务犯罪案件和规范监察机关取证行为的有机统一。
(一)完善两法关于监察证据的规定
《监察法》对非法证据排除之规定相对原则和笼统,因此需要从立法方面进一步细化。针对《监察法》对证据种类的规定不规范的情况,有必要对《监察法》有关证据种类概括式立法有准确的规定和理解。第一,就监察证据是否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而引发的理论争议问题,我国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监察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明确赋予监察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以保证《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两法之间相关规定能保持一致。第二,针对《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的“等”字表意不清的问题,我国也应当通过配套文件等形式,明确该“等”字应作“等外等”解释。亦即,该条所指向的监察证据不仅包括明文列举的六种,而且应包括被害人陈述以及其他可能出现在监察程序中的其他证据。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职务犯罪大多侵犯的是国家、集体或不特定人群的法益,但是在特定罪名类型中是有可能出现被害人以及相应的被害人陈述的。例如,在不解救被拐卖或者绑架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中,被拐卖或者绑架的妇女、儿童即可视为被害人。而在食品监管渎职案中,遭受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损害的人也可以视为被害人。这些案件中往往也存在被害人陈述这一证据类型。第三,肯定被调查人的供述及辩解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虽然两种证据分别产生并适用于不同的程序之中,但是从本质上看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不同程序中对涉案行为人的称呼不同。因此,当被调查人的供述和辩解随案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应对标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并對其适用相同的证据规则与证明机制。
(二)明确非法监察证据的内涵和范围
首先,《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在该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有所补充,也即“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该款是对“非法证据”内涵的界定,但相较于《刑事诉讼法》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大量相关司法解释,此款规定显得过于简练,对监察实践起不到具体的指导作用。其次,《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监察证据并未按照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不同进行区分,导致对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排除条件不明。对此,在《监察法》对非法证据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明确非法证据的内涵和范围。
对非法监察证据的认定必须以刑事审判为标准,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18]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非法证据应包含以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以及收集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的物证和书证,也即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限制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或者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将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限制为“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以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对此,非法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也应同样适用该机制予以界定。[19]亦即非法监察证据分为以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和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具体而言,在言词证据方面,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威胁等手段获取的被调查人供述、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而采用引诱、欺骗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应根据其是否会导致虚假供述,是否严重侵害公民基本权利进行综合判断。[20]在实物证据方面,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且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非法监察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三)新增非法监察证据的证明手段
《监察法》规定的全程录音录像有助于保障取证质量,但留存备查意味着录音录像资料无须随案移送,不仅辩护律师无法查阅,司法办案人员也未必能够顺利调取。另外,虽然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监察人员的出庭问题,但监察人员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实际承担着调查职能,监察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难以介入调查过程,当证据材料不能证明监察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时,其有必要出庭就证据合法性说明情况。一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录音录像资料和监察人员出庭便是证据合法性审查环节的有力证明,因此亟须建立录音录像随案移送和监察人员出庭作证机制。
1.录音录像随案移送
录音录像可以高度还原调查取证机关的取证行为,是司法机关对取证机关取证行为合法性审查的有效手段。为保障法庭对证据审查的实质性,有效排除非法证据,可以参照刑事诉讼程序中相关录音录像的做法,在监察程序内建立录音录像移送制度而非留存备查制度。由监察机关制作录音录像,对被调查人进行讯问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落实全程的录音录像,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以供后续刑事诉讼程序的审核运用。
2.监察人员出庭作证
实现证据审查实质化,避免庭审流于形式,是发现违法取证行为的重要环节,是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挥价值的关键阶段。在此,对于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员”是否可包括监察人员,应从保障监察证据审查的实质性角度出发,就此条款的“其他人员”作出扩大解释,将监察人员包含在内。何况从文义解释来看,“其他人员”的确包含监察人员在内。因监察程序具备的特性,以及为落实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这一制度,监察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实乃必要。[21]在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时,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监察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则监察人员有义务出庭就取证行为说明情况,并接受法庭各方询问。
(四)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指导理念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衔接,正是司法机关约束监察权的有效途径,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对监察证据的司法审查,这蕴含着以审判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司法机关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应当坚守刑事法治理念,严格依照刑事诉讼程序规则,不应受案外因素影响而进行区别对待。然而,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监察机关的强势地位,以及司法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性较弱,很容易形成新的“监察中心主义”现象,造成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流于形式。因此,排除非法监察证据是对监察机关取证行为的检视,一定程度上是对监督者的监督和制约。一方面,为了防止出现“监察中心主义”,司法机关对非法监察证据的审查和认定应严格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指导理念,不应受监察机关的影响和干预。[22]为避免“监察中心主义”,最大限度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效,对司法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失职渎职行为,在现有制度模式下应更加谨慎地对其进行惩戒。另一方面,根据《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对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监察机关应当主动配合司法机关进行证据合法性的审查,保障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确保司法机关对监察机关办案的监督和制约。
五、结语
在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中,证据衔接问题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如何保障监察证据的合法性,避免非法监察证据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价值的侵害以及对司法权合理性的削减,将是监察体制改革中制度建构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因而,从立法层面规范《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对监察证据的衔接规定,从实践层面保障监察机关调查取证与司法机关审查认定证据的协调,对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优越性和与时俱进性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此,坚持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完善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让司法机关扮演程序监督者的角色,以排除非法监察证据为手段去监督监察机关的取证行为,不断促进该制度合理化和规范化,努力实现两法的立法目的和法治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卫东,聂友伦.职务犯罪监察证据若干问题研究——以《监察法》第33条为中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32(4):2-9.
[2]程相鹏.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程序之衔接[J].中国检察官,2019(23):31-33.
[3]唐桀,靳学仁.监察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91-93.
[4]邓联荣,高通.赋予监察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研究——以《监察法》第33条第1款为中心[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1):110-115.
[5]艾明.监察调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规范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10):29-38.
[6]姚莉.《监察法》第33条之法教义学解释——以法法衔接为中心[J].法学,2021(1):64-77.
[7]程衍.中国特色独立监察程序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建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56(2):126-135+160.
[8]郑曦.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监察委办理案件的适用[J].证据科学,2018,26(4):420-428.
[9]韩旭.监察委员会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使用问题[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2):91-99.
[10]闫召华,范智凯.监察调查案件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學,2020(3):99-105.
[11]吴建雄.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视域下监察委员会职权的配置与运行规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5):44-53+2.
[12]何家弘.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2.
[13]谢登科.论监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以《监察法》第33条第3款为视角[J].地方立法研究,2020,5(1):45-55.
[14]徐汉明,李少波.《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实施衔接路径探究[J].法学杂志,2019,40(5):1-12.
[15]李世佳,高童非.《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J].西部法学评论,2020(6):49-57.
[16]林艺芳.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配合衔接机制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2(5):50-53.
[17]魏晓娜.职务犯罪调查与刑事诉讼法的适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32(4):21-31.
[18]李海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程序中的价值预期与合理运用[J].法治研究,2020(6):108-115.
[19]龚举文.论监察调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J].法学评论,2020,38(1):51-60.
[20]纵博.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证据制度问题探讨[J].法学,2018(2):119-127.
[21]冯志伟.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5):53-66.
[22]张硕.监察案件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体系:法理解构与实践路径[J].政法论坛,2020,38(6):115-126.
The Exclu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Illegal Evidence to the Supervisory Evidence:Prerequisites,Practical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Wu Anying,Lin Yifang
(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Hunan,China )
Abstract:Article 33 of Supervision Law of 2018 provides for a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supervisory evidence and criminal evidence,allowing supervisory evidence to be used as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legality of monitoring evidence,it is of great function and value to apply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n criminal procedure. However,because of the unclear legislative provisions and the in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practice,there is a dilemma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 If the types of supervision eviden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re not consistent between the two laws,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ws in the specific procedure of obtaining evidence. There is a lack of means to prove illegal evidence in the supervision procedure,and in practice there may be eliminating the supervision evidence difficulties. Therefore,in order to construct and perfect the rule of excluding illegal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dure,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provisions of the two laws on monitoring evidence,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scope of illegal supervision evidence,add the means of proving illegal supervision evidence and carry out the basic guiding concept of taking trial as the center,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duty crime cases.
Key words:Supervision Law;inspection evidence;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supervis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責任编辑:王廷国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