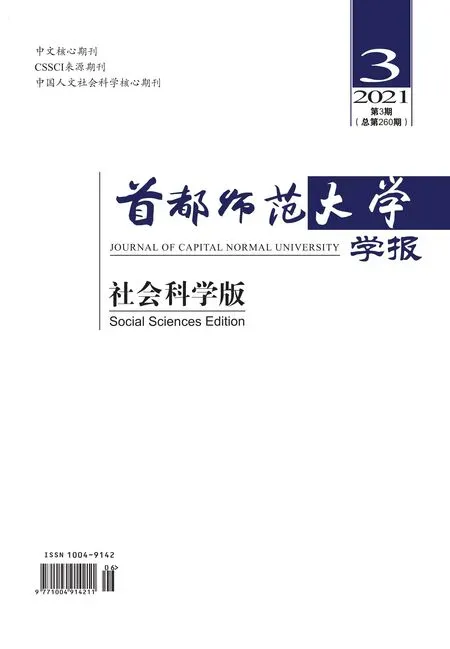瘟疫之于审美的另一种功能:《十日谈》内外的“故事”和“历史”
2021-07-20林精华
林精华
我们知道,人之自然生命极为脆弱,人认识和解决危及人生命的自然灾害之智慧、能力、技术等,虽不断长进,但终究有限,以至于形成恐惧瘟疫的思维定势,“使瘟疫(plaga)这个词长期被当作隐喻使用,指称最严重的群体性灾难、邪恶和祸害,也指众多令人恐惧的疾病”,“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有些时候特别容易提升到‘瘟疫’层次,即不单危及性命,还使身体发生异变,如麻风病、梅毒、霍乱或癌症等”。①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20页。这种情形在文学中有生动的呈现,如英国启蒙主义作家笛福(Daniel Defoe)那部假托1665年伦敦鼠疫之亲历者自述的历史小说《大疫年纪事》,意大利著名作家和剧作家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叙述1630年瘟疫肆虐米兰公国的畅销小说《约婚夫妇》(1827年初版,到1875年仅米兰就再版达118次),真切地传达疫区不是得到救助、患者不是得到同情,而是被憎恶、被视为报应的令人惊悚的情形,从而强化瘟疫及其感染者在人类社会的负面隐喻意义。奇异的是,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àccio)之《十日谈》(Decameron),却超然面对瘟疫肆虐以及疫区和被感染者遭诅咒的隐喻,大胆书写瘟疫及其隐喻压力之下有尊严地活着,才是人之生命价值所在,而享受自然生命乃人生的真谛。这样的作品,一旦被中国发现,就汉译不断。在儒学作为审美主要标准的国度,“发乎情止乎礼”成为日常生活准则的社会,它未被视为下流之作,乃因受益于五四运动倡导人性解放的社会进程。
实际上,《十日谈》甫一问世,因直接正面书写性爱之神奇、魅力、美好,以及否定性描写教会以神的名义阻止他人性爱,虽畅销于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等地,却被教会列入禁书,甚至出现被焚之闹剧,作者遭到教会唆使来的苦修派僧侣咒骂、威胁,他也由此沮丧,想要自毁该作。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中,教会却未能遏制它流行,甚至没能阻止作者受聘于圣斯德望隐修院定期举办关于但丁《神曲》的讲座,作者还得到桂冠诗人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的庇护,并因古腾堡印刷术的推广,《十日谈》被译成法、英、德和西等文字,在欧洲广为流行,虽然流行的是删节版。诡异的是,1958年之后,该作品在中国也被禁,乃因其写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其实,这期间佛罗伦萨等地的富裕阶层还真不是企业家、商人,大部分仍是贵族、教会上层),与中国把它视为“文艺复兴初期资产阶级表现出勃勃生机和进取精神”之意识形态判断相矛盾。如此情形,持续到1980年,它才在中国重见天日。它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与其在意大利乃至欧洲的命运正相反,却又有共同之处——无论怎样阅读这100个故事,皆很少深究在教会主导社会进程和生活方式的岁月中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如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巨大的“极简导论”系列之《意大利文学简史》中,只是在论及文学推动意大利世俗化问题上才特别论述《十日谈》,认为它远比《神曲》要强烈和广泛得多地反对教会干预世俗社会(anticlerical),这100个故事大多是宽恕成人男女性欲、赞赏他们在追求中所表现出的实用智慧。①Peter Hainsworth&David Robey,Italian Literatu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87-88.何以出现这等巧合的理解?
一
不可否认,这部作品中的许多故事,是薄伽丘从法国、意大利和拉丁语区借用来的,而有些故事源自印度、中东、西班牙等地;叙述结构来自印度用梵文书写的《五卷书》(Panchatantra)——在14世纪之前已被翻译成波斯语、阿拉伯语、拉丁语。也就是说,其中的许多“故事”并非作者原创,仅是对坊间流传的故事之汇集、加工、补充或修缮,方便疫情之后读者轻松阅读这些汇集在一起的不陌生的故事。这种重组既有的知识,在特殊境遇下表达新理念的叙事,直观上与这种情势有关,即当时东部教会神学家担心奥斯曼穆斯林进攻拜占庭帝国,携带大量希腊语文献逃到罗马、佛罗伦萨等,由此启发西部神学家们重新认识既有的经典、反思现实生活,而置身于新环境下(教权高于王权)的东部教会神学家也受影响重新认识熟悉的经典,双方共同促成文艺复兴到来;但实际上,《十日谈》成为文艺复兴到来的先驱之一,更与一场大自然灾难有关。
《十日谈》“第一天”序言开宗明义:“靓丽文雅的女士们,每当我停下笔思考你的怜悯天性时,我就意识到,读这本书你们会认为故事的开端太悲惨了,会让人们忍不住凄然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场致人死亡的瘟疫,这场瘟疫给每位见证者、经历者造成了苦难和悲伤。对瘟疫的追述是本书的引子。但如果你感到这痛苦的开端使您读不下去,似乎读下去只会让您不断地叹息和流泪,我会感到遗憾。本书开端虽凄惨,却好比一座险峻、崎岖高山挡住了一片美丽平原:越过这座高山,就是一片赏心悦目的大平原,您会在艰难地翻越高山后,倍感平原给您的快乐。所以只不过是暂时的凄惨——我说是暂时的,因也不过占了寥寥几页篇幅而已;接下来的就是一片欢乐,如刚才预告的那样——要不是这么声明在先,只怕你们猜想不到苦尽还有甘来。说真的,我不愿意劳烦你们走这崎岖小道,但此外没有旁路可通,因不回顾悲惨的过去,就无法交代清楚你们将要读到的许多故事是在怎样的情景下产生的;所以只好写下了这样的开头。天主降生后第1348年,意大利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人不知道这场瘟疫是受天体影响,或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以示处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时间,死去的人就不计其数。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不幸传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预防办法也拿不出。城里污秽之处都派人清扫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发布过了,保护健康的措施也执行了(但灾难仍不断)。”叙述者列举了病情的可怕情状:“有些人以为只有清心寡欲,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方能逃过这场瘟疫……也有人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一切欲望,对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其有效办法”,“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两三具尸体。夫妻俩,或父子俩,或两三个兄弟合放在一个尸架上,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常看到,两个神父拿着一个十字架走在前头,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在后面跟着。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父只为一个往生者举行葬礼,却忽然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下葬,有时还不只这些。再也没有人为死者掉泪、点蜡烛为其送葬;死了一个人,就像死了一只山羊,不算一回事”,“每天,甚至每个小时,有一批又一批的尸体运到市区各教堂,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尤其是有些人,按习俗,要求葬在祖坟地里,情形更为严重。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附近掘一些大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层层叠叠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仍健在的人,只得手里总拿着鲜花香草放在鼻子下,以消除尸体味;或不顾一切地逃离佛罗伦萨,大家互相回避、亲友家人彼此间断绝往来,病者无人照顾、死者无人收尸,人们改变了隆重下葬往生者的风俗,穷人更不幸,或倒毙于路上,或困死于家中,到处是尸体,“从3月到7月,佛罗伦萨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宏伟宫室、华丽大厦、豪华宅邸、从前达官贵人出入之所,现在是十室九空,连一个仆人也找不到!有多少显赫家族、巨大家业、庞大家产没人继承!有多少英俊男子、漂亮女子、活泼小伙子,早晨还同家人亲人一起用餐、十分高兴,晚上则到另一个世界陪他们的祖先……佛罗伦萨城居民相继死亡,几乎成了空城”。①薄伽丘:《十日谈》,方平、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后文所引该作品有关内容,全部出自该译本,不另外注明。如此悲惨的情景让叙述难以为继,叙述者便转而叙述道:在一个礼拜二早晨的弥撒,新圣母教堂(Santa Maria Novella)里只留下7个彼此沾亲带故的靓丽小姐,在教堂一角长吁短叹,而后一位年长者说,“若是我们不把自己生命当儿戏,坐以待毙,在许多人走的走、跑的跑的情形下,我们不如也趁早离开这座城市。不过,要逃避死神,许多人堕落了,我们要避免。我们大家在乡间有好几座别墅,就让我们住到乡下去,过着清静的生活吧。在那儿,我们可由着自己的心愿寻求快乐,但不越出理性规范”,并描述乡间的好处,为逃离死城找到道德理由(更多的人都跑了),“若大家赞成,我们不妨携带必需品,逃出城,从这家别墅到另一家别墅,趁这时光,好好地享受一番。让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只要死神不来召唤我们,我们总有一天能看到上帝怎样来收拾瘟疫的”,大家赞成此提议。凑巧,有三位英俊的青年男子也来到此处,这十人很快达成协议,次日如约离开佛罗伦萨,到郊外别墅躲避瘟疫。

(1492年威尼斯刊行的《十日谈》插图本)
这样的开篇,不只是给后面要说的100个故事提供引子,即不是一种写作策略,甚至不是虚构,而有叙事者对真实历史事件的故事化陈叙。据美国俄亥俄州鲍林格林州立大学教授吉普尔(Kenneth F.Kiple)主编的大型辞书《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得克萨斯州立农工大学健康与人体运动学副教授阿波斯托洛普洛(Yorghos Apostolopoulos)和伊斯坦布尔马尔马拉大学化学系教授索恩梅兹(Sinan Sönmez)主编的《人口变动和传染病》等:1346—1353年发生一场波及亚洲部分地区、北非和欧洲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or bubonic plague),欧洲人称之为“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致命的黑死病”(great mortality)、“举世瘟疫”(Universal Plague)等。这场起源地仍未有明确定论的瘟疫(但最早史料认为始于里海北部和西部流域),肇始于多种野生啮齿动物。1346年蒙古军攻打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港口贸易城市卡法(Caffa)时,已有官兵携带这种病毒。当时城里有修筑防御工事的以及参战的将士,还有热那亚商人、欧洲基督徒。久攻不下的蒙古人,把病死者尸体弹射到城墙内,瘟疫便传入其中;城内人面对日益不利的战事,逃跑者众多,但受到感染者沿途被驱赶,把不知情的黑死病带到君士坦丁堡(即伊斯坦布尔)。此后,瘟疫沿着逆时针和顺时针两条线路传播,与朝圣之路或贸易之途交织,即经由军队、商船、商队、朝圣者、季节性打短工者和其他旅行者,共同促成这次鼠疫快速且大面积的传播。逆时针方向往东到达巴格达、北非和西亚,是年秋天传播到埃及,此后两年蔓延到尼罗河流域,1348年瘟疫先后袭击塞浦路斯和罗德岛、地中海沿岸城市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加沙、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阿勒颇,1349年抵达麦加、亚美尼亚、巴格达等地区。而沿着顺时针方向传播的力度和速度也不减:1347年秋天,热那亚的海船把瘟疫从黑海带到西西里、亚历山大里亚,以及突尼斯、意大利半岛、普罗旺斯,到1348年传播到伊比利亚半岛、巴黎、英格兰南部的一些港口,1349年不列颠岛的许多地区、法兰西北部、德意志南部和西部、挪威等先后被席卷,1350年瘟疫扩散到德国北部和东部、瑞典和波罗的海西岸,1351年到达波罗的海东岸及波兰北部,此后两年波及今伏尔加河区域,1353年夏天蔓延到莫斯科。如此大面积传播,横扫欧洲和中东,商人运输着谷物、饲料、兽皮、皮毛、布匹等,也传递着瘟疫,在每个地方停留半年左右。这种季节性的生态现象,表现为春夏秋季易发并趋于严重,冬季则衰退,如在突尼斯和意大利的疫情最早发生在春季,比在8—9月才流行开来的法国要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并在翌年反复。在这种情势下,教会及其掌控下的公国、城邦等无力抗疫,就转嫁责任,把瘟疫视为异端或生活不洁、道德败坏者所致,是神对罪人的惩罚,进而在疫区内外寻找替罪羊,导致1347—1348年欧洲发生过许多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侥幸死里逃生的犹太人或被流放,或被拘禁,财产被充公,欧洲的犹太人被迫东移,直到瘟疫消失,这类事件才停止。其间,贵族尤其是皇室死亡率不高,但平民人口基数大、死亡率高,1346—1350年瘟疫相继夺去欧洲两千万人生命,欧、亚、非洲共约5500—7500万人死亡,1350—1400年欧洲人均寿命从30岁降到20岁。①吉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37—540页。

本来,相较于欧洲其他区域,包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在内的意大利许多地方,纬度相对低得多,冬季时段较短,客观上,这次瘟疫持续时间要长得多。更重要的是,曾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一部分的意大利北部,此时分裂成不同的王国、自治城市,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欧洲著名城市治理水平低,包括公共用水系统、卫生防疫系统等很弱。面对如此危机,罗马教会所控制的这些各自为政的城市,自然无力应对。薄伽丘的许多朋友,尤其是他父亲和继母,就死于这场瘟疫。著名诗人彼得拉克1327年在教堂邂逅的少女劳拉(Laura),也死于这场瘟疫:此事让当时在帕尔马的彼得拉克不胜悲痛,便用意大利俗语创作了诉诸无尽哀思的抒情诗,成为后来他汇编的《歌集》(Canzoniere)这部传世之作的主要内容:该作品书写世俗生活的悲欢、男女间爱情之甜蜜,而非对上帝之爱。并且,它的影响力,在历史进程中几乎掩盖了彼得拉克作为古希腊文化学家、拉丁语文学家的声望。而《十日谈》中讲故事的那十位男女所相遇的新圣母教堂是实有的(1227年多明我会开始筹建,1246年奠基,1320年竣工),并在这次疫情中救助了大批佛罗伦萨市民。《十日谈》的序言,把这次瘟疫与罗马教会联系起来,那是有智慧的英勇壮举。
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的未完成之作《上帝之城》(DeCivilateDei),把有形教会的“上帝之国”,与靠征服建立、靠欺诈和暴力所维持的地上之城(civitas terrena)区分开来,构想出基督教会乃上帝在人世间营建的天国。此说为教皇此后近千年坚称作为使徒彼得后继者和基督在世上之代表而拥有神圣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一代代教会法学家和红衣主教们把这一要求,演绎成法律语言,套用古罗马帝国法律加以阐明,并从数百年前虚构的教皇判例中找到依据,伪造《格拉蒂安教令集》(DecretumGratiani),使罗马教廷拥有至高无上和普世司法权的法理依据,教皇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干预欧洲事务、各国世俗问题。诡异的是,这样一来教会把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国”变成了欺诈和暴力的地上之城。教皇通过拉丁文和教会制度垄断话语权、控制真实信息,导致西欧尤其是罗马及今天意大利的信徒,无法知道“上帝之国”和“地上之城”的分界,仍寄望教皇负起道德楷模和救助信徒之责任。但疫情发生后,一向借助神学去控制各国或城邦、治理社会的教会,自然束手无策,并且教会还限制信徒进行医学探索,更不会提高诊疗手段、开发医药、建立卫生防疫等,这导致人们认识瘟疫的水平极低,以至于置身于1348年鼠疫中的法国外科医生肖亚里克(Guy de Chauliac)只是告诫人们,“快速逃离,远离疫区,不要着急回来(Fuge citom vade loge,red tarde)”;法兰西国王腓力六世下令巴黎医生须查清这场瘟疫来源,但最终收到的报告是这样的,即瘟疫肇始于土星、水星和火星于1345年3月20日下午1时相遇。①See Anna Montgomery Campbell,The Black Death and Men of Learn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1,pp.50-52.如此愚昧的认知,即便展开所谓用外科手术抗疫,也只是切开患者静脉放血、减少血液在人体的流量(实际上,这不仅加快感染者死亡,而且医生也容易被感染);至于预防,就只是用火或熏香法净化空气,医生出诊时由男孩举着香炉随行,以净化空气,人人手里拿着浸泡了醋和香料的海绵放在鼻前。这些救治措施,自然显示不出教皇的神力,教会和世俗权力机构对疫情都束手无策,只是封城或隔离受感染人群,或被动实施禁止外人入内、城里人不能走动这类简单的原始措施,如此既导致大量的次生的人道灾害频生,又未能阻止有钱人和大批医生逃离,只是更多底层患者被无情地困在家里等死,以至于疫情高峰期的1348年,佛罗伦萨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昔日美丽繁华的都市,变成上述惨不忍睹的地狱。与此同时,教会及其所任命的市政团队,却借机加强权力、扩权,造就疫区的疫情和行政腐败、道德沦丧同步增加,这就是《十日谈》的序言和引言所说的情形,尤其是那位女子所倡言的“请记住,正大光明地走出去,比许多女人放荡不羁地住在城里更好些”。这些都表明,这十位青年要逃离的不仅是瘟疫,还有教会带来的秩序奔溃、城市衰败,逃离佛罗伦萨不只是保住生命,更是有尊严地活下去。进而,读者读到其中三位女性的名字为“艾丽萨”(Elissa)、“涅菲丽”(Neifile)、“劳拉塔”(Lauretta)等,就很容易联想起维吉尔、但丁、彼得拉克等伟大文学家所分别塑造的维纳斯、贝阿特丽采、劳拉等高贵女性形象,而“菲娅美达”(Fiammetta)、“菲洛梅娜”(Filomena)、“伊米丽雅”(Emilia)等名字则使读者能想起薄伽丘此前讴歌爱情之作的光彩形象,如叙述基督徒少妇和青年异教徒冲破宗教藩篱而获得爱情幸福的散文体罗曼司《菲洛柯洛》、抒写在爱情陶冶下粗野的牧羊青年转变为品格高尚者的《佛罗伦萨女神们的喜剧》、把歌颂德行和赞美爱情相结合的长诗《爱情的幻影》、描写女性恋爱和失恋之复杂心理的传奇故事《菲亚美达的哀歌》、讴歌女神和牧羊人不顾黛安娜女神阻扰而矢志相爱的《菲埃索拉的女神》等。由此,在《十日谈》里,这十位男女各自讲故事或主持讲故事的过程中,就显示出人之不同层面的优秀品德,而不是在疫情之下丧失人之尊严,以避免第一天序言所说的情形再现:“(疫情导致)一个女人不论以前多么文雅、俊俏、高贵,病倒后会毫无顾忌地招聘一个男佣人,不管他年纪老少,并且只要病情需要,会毫不害羞地在另一个人面前露出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痊愈的妇女,日后往往不如以前那么贞洁,也许和这种情况有关。”
教会无力掌控疫情的事实,客观上动摇了包括教皇在内的罗马教廷在信徒心目中的地位,导致这场瘟疫,无论其源于哪里,结果被隐喻化:不虔诚的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和穆斯林等,皆视之为神对人背离神之旨意的惩罚。这就使更多的人,放弃了对教会的坚定信心,并放纵自己,甚至放弃宗教信仰。在这样的情势中,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薄伽丘,意外成为名作家。他出生并成长于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的商人之家,得益于其父被任命为那不勒斯的一家银行经理,他有机会在银行当学徒,其父鼓励他在那不勒斯大学读法律、赞赏他的文学写作,他由此创作出上述《菲亚美达的哀歌》这部书信体的现代小说(菲亚美达形象相当于但丁的贝阿特丽采形象、彼得拉克的劳拉形象)。那不勒斯发生鼠疫,他逃回到佛罗伦萨(为此错失在那不勒斯和彼得拉克见面的机会),但佛罗伦萨也很快被殃及,他被迫移居拉文郡。在这场疫情中,慈父和多位亲人、友人往生。正因为如此,他在《十日谈》中说及疫情的文字不多,却表述得刻骨铭心;十位青年逃离疫区,绝非逃跑,而是要重新选择生命方式,去有清澈泉水和悦目花草的乡间,那里有长廊、壁画、地窖里还藏着香味浓郁的美酒,他们以讲故事的方式,还伴随有唱歌弹琴和跳舞散步,愉快地度过劫后时光。而论及讲故事,这自然是文化生活不丰富和没有现代科技的岁月,人们享受精神生活最常规的方式,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而被报纸、小说所替代,在20世纪因为电影、电视、网络等先后兴起才进一步消失。《十日谈》如是叙述这十位青年男女坐在绿草茵茵的树荫下,轮流主持每一天的故事主题,每人每天围绕主题讲一个动听故事,幸福地生活了十天。由此,这100个动人故事之产生的背景极为重要,这就是《原序》所说的:“……多情善感的妇女最需要别人的安慰,命运对于她们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多少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这本书里讲百个故事——或是讲了百个‘寓言’,百篇‘醒世小说’,百段‘野史’,你们怎么说都成。这些故事都是在最近瘟疫盛行的一段时间中,由一群有身份的士女——七位小姐、三位青年分十天讲述的。故事以外,还有七位小姐唱着消遣的好些歌曲。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谈到情人们的许多悲欢离合的遭遇,古往今来的一些离奇曲折的事迹。淑女们读着这些动人的故事,说不定会得到一些乐趣,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因借这些故事,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这么说,这本书多少会替她们解除一些愁闷吧。要是真能做到这一步,(但愿天主允许吧!)那么让她们感谢恋爱之神吧,是他把我从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给了我力量,为她们的欢乐而写作。”这里明确了要理解这100个故事,首先需考虑这场瘟疫,即故事意义不能限于叙述的能指符号层面,阅读不能停留在这些故事本身,而要关注何以要讲这些故事的所指——彰显人的自然生命之可贵,性欲正是人的生命力表现所在。这就把基督教会及其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推到前端,由此呈现爱情作为生命本能之不可遏制性,对异性产生性欲的冲动乃人之本能,爱情乃生命之必然;并且,爱情不单是人的天性,也是能改造人、重塑人的崇高性的正面力量(第五天第1个故事叙述西蒙因爱情而聪慧起来),为爱情而抗争是悲壮的;而试图遏制这种人性的制度或话语是荒谬的,那些神职人员借职业基督徒身份,由道德训诫转为放纵欲望。作者在跋中也辩解道:本作品涉及太多男女之事,无论是近乎猥亵,还是戏谑成分太多,皆显示出在脆弱的生命中,情欲、性欲、爱情是人性的自然组成部分,需要有尊严地实现;否则,是对人自身的背弃。故言及此,读者就很容易明白《十日谈》中100个故事诉诸的是瘟疫和教会双重压力下人如何有尊严地获得人生、表达爱情。《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在论述薄伽丘时,不同程度地顾及了这些。①Peter Brand&Lino Pertil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Cambridge,et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76-78.
可见,《十日谈》在看似粗鄙的叙述中,极富挑战力地表达人生目的不是死后永生,而是现世有尊严的生命,规避了教会关于人生而有罪之说。这些叙述,大大突破了此前但丁的抒情诗《新生》用拉丁文书写对邻居少女贝阿特丽采痴迷的精神恋、长诗《神曲》依据神学体系诉诸意大利社会和人的问题,甚至比彼得拉克的《歌集》用十四行诗书写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要具体得多,与稍后的艺术世俗化转型相呼应,包括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油画《维纳斯的诞生》用明快色彩凸显美神的少女胴体和肌肤之美,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把基督教神学转化为世俗认知的《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等,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直接呈现女性身躯之美的油画《裸女照镜》,提香(Tiziano Vecelli)的《酒神祭》把古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旁边的仰卧美女画得宛如人间美少女,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之《哀悼基督》《大卫》《创世纪》《摩西》《最后的审判》等把圣经中人物具体化为人的生命……诸如此类共同促成了把人之自然生命视为最为可贵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且,为吸引市民阅读的兴致,薄伽丘另辟蹊径地开启了弃绝使徒行传的模式,选用故事套故事的叙述结构,用他出生地俗语即靠近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方言(Tuscan vernacular)书写,如第四天故事序言中叙述者所解释的:“这些故事我是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成的,而且还不是韵文。”赋予被正统观念和制度所压抑的语言以活力,使读者能直接体验到生命能量,其效力为拉丁文所无法企及,客观上又和但丁的《神曲》等一道,传播了人文主义价值观,为意大利语从方言转换为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也为标准意大利语在未来的最终确定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尤其是很快启发了1372年出使意大利的英格兰作家乔叟(Geoffrey Chaucer)阅读该作后,用中古英语创作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并和后来所发现的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叙述方式一致(该著作1717年译成法文,是欧洲最早译本),甚至比《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人文主义经典更具先驱性,还比它们更关注促成人自身解放的自然界力量。
二
另一个问题又来了:该作序言已然明示是“借这些故事,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其第四天序言和跋也解释写作原因,以图捍卫写作动机。在《麦克米兰意大利文学词典》(1979年)所论及的《十日谈》内容,十分重视这些序言(epilogues)描述那场瘟疫才引出这十位男女讲述100个故事的背景,认为由此才使“故事”能真切呈现出人的慷慨(magnanimity)、大方(liberality)和忍耐力(endurance)等美德,用俗语提供了文学之有效且持久的教训,创造了最流行的文学景观。①Peter Bondanella&Julia Conaway Bondanella,Th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Ltalian Literature,London,etc.: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9,pp.61-62.同样,这些有关瘟疫才引申出100个或幸福或不幸的爱情故事,在享誉国际学界的“世界文学及其时代”(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Time)系列之七《意大利文学及其时代》关于薄伽丘的论述中,得到了特别重视。②Joyce Moss,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Times 7:Italian Literature and Its Times,New York,etc.:The Gale Group,Inc.,2005,p.120.然而,在基督教会越来越不能左右读者的审美观之大势下,实际上各国读者大多忽视了这个序言之作用,如汉语读者特别专注于看似直接指向教会限制人的爱情或情欲或婚姻之故事。何以如此呢?
原来,这与翻译有关。回首历史可发现,该作品流行的不是全本,而是删除包括这个序言在内的删节版:1620年,英格兰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伦敦一个法庭翻译官弗洛里欧(John Florio),乃莎士比亚的朋友、通意大利语的语言学家,翻译的就是删节版《十日谈》——删除原作序言和跋,还修改了有公开性描写的第五天第10个和第九天第10个关于同性恋的故事;1702年,伦敦的雕刻师和出版商萨瓦奇(John Savage,1683—1701)翻译的《十日谈》,删除的内容包括原作序言和跋、第九天第10个故事等;174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英国医生贝尔盖(Dr.Charles Balguy),匿名刊行了英译本《十日谈》,删除的内容包括原作序言和跋、第三天第10个故事和第五天第10个讲述同性恋的故事等,却没妨碍它广为流行且多次再版;1855年,凯利(W.K.Kelly)这位在今天看来属于北爱尔兰的英国高产作家,翻译的《十日谈》是英文版中接近全本的,仍删除原作序言和第三天第10个故事、第九天第10个故事。不过,即便1886年英国诗人和翻译家佩恩(John Payne)翻译了第一个全本英文版《十日谈》,上述不同的删节版《十日谈》仍流行,而且1930年美国的意大利文学翻译家魏因娃(FrancesWinwar)还是刊行了删除了序言的《十日谈》……英文世界流行删节版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另有隐情:该作品出版之际,乃罗马教廷严厉控制欧洲的时期,如人文主义语言学家瓦拉(Lorenzo Valla)著文《论快乐》(1431年)提倡享乐主义、批评斯多葛的禁欲主义而声望赫赫,却因用拉丁文著述《论“康斯坦丁赠礼”》(DonatioConstantini),论述作为教皇的世俗权力之依据的《君士坦丁赠礼》,不是用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时代的拉丁文撰写的,而是用公元八世纪拉丁文伪造,断言它乃显而易见的赝品。此说因危及教皇权力的正统性,使他遭到宗教法庭所追捕(幸亏西西里国王阿尔封沙庇护才使之幸免于难),该作品直到1517年才用德文出版。是年,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宣布《九十五条论纲》,这两个文本分别从法理上动摇了罗马教皇统治西欧的依据。后来还有许多人因异端思想而遭受教会法律严惩,或被禁止从事思想活动、文学艺术创作。如此情势,改变了意大利的文学艺术导向,即用拉丁语书写基督徒题材的文学回潮: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耗时30年用拉丁文创作骑士史诗《疯狂的奥兰多》,并且刊行仰赖红衣主教依波利多资助;塔索(Torquato Tasso)因其耗时多年(1575年开始创作,1578—1585年被关进疯人院期间问世)的拉丁文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Gerusalemmeliberata),被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授予“桂冠诗人”。相应地,用俗语书写的《十日谈》则遭遇厄运:1497年,天主教会焚烧了包括《十日谈》在内的许多倡导世俗生命意义的图书,薄伽丘晚年在致信友人时也深感后悔,甚至使用教会批评之语说,这是缺乏道德感之作,完全不希望这位朋友的太太阅读该作品,其此后写作,包括论但丁之作,风格大变,切近中世纪惯例(medieval conventions)。①Peter Hainsworth&David Robey,Italian Literatu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88.即便如此,1559年《十日谈》还是被罗马教廷列入禁书清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所幸,此书影响力巨大,烧不尽烧,甚至问世(1371年)之后30年还再版10次。当然,多是删节版,尤其是1582年开始流行的那个删节版——删除了包括序言和诸多“色情”内容的故事;16世纪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哪怕《十日谈》用意大利语言书写,仍有助于意大利脱离罗马教会统治而形成自己的民族意识。由此可知,英文世界何以流行的是删节版,16—19世纪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的《十日谈》,也多是删节版,甚至1893—1894年俄国科学院院士维谢洛夫斯基(Алексáндр Веселóвский)这位著名的意大利文学教授翻译该作(帝国科学院印刷所分两卷本印行)时,删节版依旧在俄国流行,即更多的读者看不到那些序言。
实际上,《十日谈》屡禁不止,在相当程度上首先是因其呈现瘟疫下的意大利人的真实生活情态及其思想解放趋势。这场瘟疫,甚至改变了教皇伊尼亚斯·希尔维尤斯(Aeneas Silvius)本人的神学认知方式:他目睹了疫情的恐怖,1462年便离开罗马,不再坚持在圣彼得大教堂(St.Peter’s Basilica Church,即圣伯多禄大教堂、梵蒂冈大殿)这座宗座圣殿处理宗务、主持神学工作,而是躲到阿缅达山峰,和罗马教廷的廷臣们寓居在半山腰的伦巴地修道院,在大自然之美中享受生命过程,和枢机主教们愉快地讨论神学、人生,有意识发掘、领略和讴歌意大利半岛的自然风景或人文景观之美,他用拉丁文书写的《回忆录》,生动叙述了从山上眺望到的周遭风景,包括弯曲的河流、河上的拱桥,峰峦叠嶂的山脉和点缀在山脉中的别墅、修道院,波涛起伏的亚麻地、漫山遍野的金雀花、神奇的城堡等。教皇在疫情时期看到生命之可贵,而佛罗伦萨政治家布鲁尼(Leonardo Bruni)的《佛罗伦萨城市颂》,在疫情之后直接捍卫财富的价值,认为财富是个人行使道德、群体抵抗自然灾害之基础。更重要的是,这场瘟疫正如意外加速促成文艺复兴到来一样,也迫使社会发生普遍的变革,“仅从医学界来看,清扫街道、收集垃圾、清理下水道、掩埋尸体、管理食品销售和对船只隔离,哪怕对阻止瘟疫的传播之功效不大,但从护理麻风病人延续下来的公共卫生意识得以加强。瘟疫过后,基督教发生在教堂外关怀人的变革,促成一个又一个教会医院和世俗医院建立起来;一些护理病人的宗教规则颁布。拉丁语不再是重要文献的唯一语言,医学和其他书籍开始用各国自己的语言书写”,“疾病预防成为潮流,出版饮食、卫生、衣服及卫生保健的书籍”,医生职业地位大幅提高、外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成长起来。②吉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页。所言极是:1348年威尼斯建立了第一个公共卫生局(Proweditorialla Sanita),在此后的流行病中该机构经常重建,从1486年以来一直存在至今;1379年在威尼斯殖民地拉古萨地区,首次尝试实施检疫制度;鼠疫之后,原本相互提防的城邦,开始了防疫工作各领域的日益深度合作。正是在瘟疫促使社会整体进步中,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都灵、米兰、威尼斯等城市的居民,日益重视人的生命价值、正视社会现实问题:1539年由教皇保罗三世任命的红衣主教本博(Pietro Bembo),作为神学家却写出十四行诗《白话散文》《抒情歌集》等肯定拉丁语口语合法性、讴歌人之生命价值的杰作,甚至正面提及《十日谈》,从而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家;佛罗伦萨政治家和外交家曼内蒂(Giannozzo Manetti),其人文主义之作《论人的美德与尊严》,直接对抗教皇和教会把尘世生活视为罪恶的正统话语、神学认知;那位语言学家瓦拉之《论快乐》(Devoluptate,1431),以伊壁鸠鲁派学者和天主教徒对话的方式,强烈对比出追求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孰优孰劣,而其《论自由意志》(Deliberoarbitrio,1439)就宿命论和自由意志之矛盾展开论述;佛罗伦萨人巴蒂斯塔(Leon Battista)虽然曾厌世,却著述了四卷本《家庭篇》,赞赏金钱、时间的价值,肯定财富之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主张每个人不能让时间白白流失,时间的意义发生由上帝掌控,转向具体个人支配,并且他本人身体力行这些大胆主张,如设计了许多著名建筑,成为富裕的人文主义建筑师;人文主义诗人博亚尔多(Matteo Boiardo)用通俗语言而非拉丁文书写《歌集》(又名《三部爱情树》)和史诗《恋爱中的奥兰多》。而更有文学天赋的薄伽丘,借助已有的丰富文学经验,在瘟疫过后人文主义勃兴的潮流中,创作《十日谈》——把人的生命价值、尊严置于遭遇瘟疫和教会双重压力的现世生活过程中展示出来,这和疫情激发科技进步、现代医学诞生、人文学科问世等一道,共同促成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初版)所论的情形:“在现代国家中,意大利最早出现了文明生活习惯,他们讲礼貌,重视言辞,服装整洁,居住舒适,注意教育和体育”,“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看到了许多艺术家,他们在每个领域都创造了新的完美作品,并且他们作为人,也给人留下了最深刻印象。他们从事艺术之外,还对广泛的心智学术问题深有钻研”,“自14世纪以来,在意大利生活中就占有如此强有力地位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是被当作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生存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一部分也是公然反对以前倾向的一种反冲力,这种文化很久以来就对中世纪欧洲发生着部分的影响,甚至越过了意大利的境界”。①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1页、第167页。面对自然灾害,不是退缩,而是不断反思人之存在的问题、意义,较之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神学大全》(SummaTheologiae),《十日谈》更重视人的现世生命价值,倡导人要有尊严地活着。
然而,这部凸显瘟疫之下的人之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杰作,在此后的欧洲历史进程中,其影响力为何完全不及《神曲》《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戏剧?这首先与意大利历史进程有关:公元395年以后,意大利四分五裂,南部属于拜占庭帝国,北部先后属于西罗马帝国、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一部分;12—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统治瓦解,这里分解成教皇所册封的王国、公国、自治城市和封建领地;15世纪末,法国和西班牙展开争夺亚平宁半岛的斗争,意大利诸城邦、教皇国、西欧各主要国家以及奥斯曼帝国卷入意大利战争(Guerre d’Italia del XVIsecolo),战后意大利大部分领土先后被法、西、奥占领;如此情势持续到18世纪,意大利民族精神才觉醒,19世纪才开始意大利统一(Risorgimento)进程,即意大利复兴运动,1848—1870年意大利人展开反抗占领者的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The Wars of Italian Independence),领土才得以统一。在这样的历史困境中,薄伽丘此后没有持续书写瘟疫压力之下人之解放问题,或瘟疫的启示录意义,而是转而顺从罗马教会的神学主张,打算把《十日谈》付之一炬(若没有彼得拉克的成功劝慰,可能这部书就消失于人间),他放弃《十日谈》的写作风格,采用梦幻文学这一教会所确认的正统文学样式书写短篇小说集《大乌鸦》,按教会观点把爱情写成淫荡的肉欲,这种淫荡在女人那里尤甚,女人的性欲乃世界的邪恶之源。即便如此,他故去后,坟墓被掘、墓碑被扔。更严重的是,彼得拉克和薄伽丘之后百年,在英格兰、苏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等孕育民族国家意识渐成潮流,地方语言替代拉丁语乃大势所趋,如英格兰出现詹姆士一世钦定的英文版《圣经》、德意志出现马丁·路德用德文翻译《圣经》,但意大利产生拉丁语回潮,哪怕市民语言和民族语言已在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等城市成为通用语。不可否认,1453年拜占庭帝国沦陷于穆斯林土耳其,在这之前大批古希腊罗马古籍或对其的研究著作,运回到罗马、佛罗伦萨、米兰等地,在欧洲重见天日,为人文主义出现提供了启示和资源,却也激发重新运用拉丁文讨论古典文化复兴问题之热潮,“对古代文化推崇备至,承认它乃一切需要中的首个和最大的需要,除15—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人之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不见的”①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7页。。当时许多贵族家庭给子女取名阿伽门农、米诺尔娃等古希腊人名字;人们津津乐道古希腊罗马作家风格上的细微差别,西塞罗的著作被认为是最纯正的非韵文典范。虽然许多文学家清楚西塞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严重不足,但仍竞相模仿其书信体和叙述体风格,并颂扬古希腊语言和拉丁语的绝对权威性。上述城市建造了许多缅怀古希腊罗马的纪念碑、墓地、勋章,设立维吉尔勋章(Publius Vergilius Maro,BC 70-BC 19)、在科摩城大教堂正面竖起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和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的塑像等。在这样的情势下,薄伽丘和但丁、彼得拉克那些用方言书写的作品之文学地位,相应地,被罗马教会所贬低,只能在市民社会流行。
意大利的如此历史进程,正值现代民族国家在欧洲形成、确立之时,以国语书写的民族文学,作为既有的经典(classics)或新产生的经典(canon),得到了所在民族的有意识彰显。其中,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放弃本笃会修士,转而成为医学士,1532年以笔名“亚勒戈弗里巴·奈西埃”发表法文书写的《巨人传》(LaviedeGargantuaetdePantagruel)第一部(《庞大固埃之父、伟大的卡冈都亚生平》),因彰显人之世俗生活美好而风行一时,却遭索邦神学院指责和教会查禁;第二部(《可怕而骇人的大巨人卡冈都亚之子、著名的渴人国国王庞大固埃事迹》)哪怕被法院宣布为禁书并被索邦神学院继续指责,但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授权继续刊行作品;1537年拉伯雷获蒙彼利埃大学博士学位,尤其是1545年国王特许,他以真实姓名出版《巨人传》第三部《关于好人庞大固埃的英雄事迹的第三本书》。不否认,国王死后,其小说又被列为禁书,他本人被迫外逃,1550年才获准回国后,却很快任两个教区神父,其间完成《巨人传》第四部、第五部。这部充满着巴黎方言和法国人俚语、俗语之作,却先后得到法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1530 年成立)、法兰西学院(L’Académie Française,1635年创建)、法兰西学会(L’Institut de France,1795年创建)这些权威机构,在确立标准法语、建立法国现代学术制度、张扬法兰西价值观之过程中的认可。这种用民族语言彰显本民族审美价值的行为,与莎士比亚这位以英格兰中心论创作历史剧、悲剧和喜剧,从而于1740年英格兰教会在王室西敏寺最显眼位置为其安放一块壮观的嵌壁纪念碑,有异曲同工之妙。包括《十日谈》在内的意大利语作品,在长期不存在作为国家的“意大利”之历史进程中,显然就没有这种幸运,即得不到正面传播;14—15世纪意大利政治上的不稳定,引起当时杰出人物对爱国的厌恶,虽然但丁和彼得拉克一厢情愿地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其所有儿女们的最高奋斗目标,相较于最早表达德意志爱国主义情感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an I)及其后代的人文主义作品而有明显不足,“自罗马时代以来,德意志就比意大利更早地具有真正意义的国家。法兰西的国家统一意识,是从和英格兰人的冲突中得来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关系密切,但西班牙在合并葡萄牙问题上始终未获得长久的成功。就意大利而言,教皇国之存在及其赖以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是意大利国家统一的永久障碍,似乎难以消除。所以在15世纪政治交往中,当共同的祖国概念偶尔被着重提及时,在大多数情形下会引起其他意大利公国的郁闷。16世纪最初几十年,即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对爱国主义复活是不利的,享受文学艺术之乐趣、生活之舒适和高雅、发展自我的无限兴致,破坏或阻碍了对于国家的热爱。直到统一的时机过去,这里挤满了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接着德意志军队征服罗马,人们才又听到对于民族感情的极为严肃、悲哀的呼吁”②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1—142页。。这种情形导致即便1870年意大利统一之后,相较于《神曲》直接书写了意大利政治纷争、分崩离析问题,并表达意大利统一的思想,《十日谈》仅是积极叙述人如何超然于瘟疫及其隐喻的普遍性问题,其之于意大利文学史的价值,自然略逊一筹,在文学教育中得到彰显的力度,不及《神曲》。意大利处在这种分裂和战争中,而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法国和英国等分别主导欧洲乃至世界的现代文明进程。如此一来,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经典,其文学史意义,也就无法企及西班牙作为国家所极力彰显的《堂吉诃德》、英格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王室和人文学界共同推崇的莎士比亚剧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令人疑惑的是,在疫情肆虐的情势下,《十日谈》中十位青年却能如此乐观地叙述生命的美好、倡导要睿智克服那些抑制生命的体制或观念,并且叙述过程妙趣横生,这种情形却没有随着医学进步而得到发展,相反,人们反而由恐惧瘟疫,演化为对疫区和感染者的敌视,再也没有积极面对疫情的文学作品。本来,瘟疫伴随人类历史进程,在1348年黑死病之前,就有如法兰克王国史学家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法兰克人史》所描述的,公元540—590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大瘟疫(史称查士丁尼瘟疫),一天死亡超过千人,整个瘟疫导致东地中海约2500万人死亡,也差一点让拜占庭帝国大伤元气,查士丁尼企图恢复罗马帝国光荣的梦想也因此失败,成为影响其后200年内最致命的鼠疫①See Gregory of Tours,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Harmondsworth:Penguin,1974.;1348年瘟疫之后,灾难并未减轻,人类文明虽然不断进步,黑死病、天花(smallpox)、慢性传染病(chronic infectious diseases)等不断造访欧洲和亚洲许多区域,威胁着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如黑死病在1417年、1430年、1630—1633年的意大利此起彼伏(佛罗伦萨尤甚),1575—1577年威尼斯再次发生瘟疫……其间,教会一直宣称,疾病是上帝对人类罪孽之惩罚,虽然中世纪大学开设神学、法学和医学,却不把瘟疫当作疾病对待,这就加剧了社会把瘟疫视为恶魔降临人间、是对人背离神的惩罚:赋予瘟疫以对患者更严厉惩罚的隐喻意义。不否认,一次次疫情发生,相应地促使医学进步、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促成现代文明的成长,如14—15世纪欧洲瘟疫,欧洲大学开始增设修辞学、哲学、天算学等,大量涉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古典的学问,从而孕育出所谓“人文学科”(studia humana)……伴随这些研究世俗世界现象的人文学科发展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兴起和加速发展,但人面对疫情的思想解放却有限,出现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威尔士史学家凯斯·托马斯爵士(Sir Keith Vivian Thomas)在《人与自然世界:英格兰不断变化的态度,1500—1800》中所描述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瘟疫肆虐英格兰时,那里的人普遍相信快乐、信神的人不会被感染瘟疫,对活着时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慰藉,又不接受死亡乃生命之自然过程的人而言,瘟疫致死是令人害怕的神秘之事、不可控制,这种把因瘟疫及其引发的生理疾病看作心理疾病,自然导致这种病是不能治愈的隐喻。更有甚者,1700年之后,尽管医学进步和公共卫生防疫体系逐步完善,欧洲人口死亡率下降,但肺结核病作为传染病到20世纪仍被隐喻化,如1920年卡夫卡致函友人说,他患的是心理疾病,肺部的病不过是心理疾病之蔓延而已,直到最终找到治疗结核病的诊断方案和药物后,这种疾病的隐喻才停止;不过,把癌症与情绪消沉以及缺乏自信和丧失对未来的信心相关联的情形,延续至今,尽管正如肺结核的隐喻那样,也是站不住脚的。②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人类对自我生命认知的有限性,对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或无法医治的疾病,都会赋予其隐喻意义,内心所恐惧的腐败、腐化、异常等现象,则被视为与这类疾病相关联的隐喻,如鼠疫被视为对宗教、道德、社会安全等产生致命灾难,患者就被视为是疾病本身,患者本人也认为是羞耻的,其患病是亵渎神灵的后果,是妖魔附体的形式,疾病成为拥有可怕负能量的隐喻,这些负能量会损害自然秩序。这些看法进而导致把某些传染病视为劣等民族或受诅咒地区的病,如梅毒这种于15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传染病,英格兰人称之为“法兰西的花柳病”(French pox),巴黎人称之为“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对佛罗伦萨人来说则是“那不勒斯病”,甚至后来盛产梅毒患者的日本人把这种病称之为“支那病”(Chinese disease)。正因为如此,被视为最杰出经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作《罪与罚》,在其结尾叙述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梦见瘟疫——整个世界皆遭天谴,陷入一场肇始于亚洲腹地、席卷欧洲的可怕又奇特的新瘟疫之中,即欧洲正遭受亚洲的致命瘟疫之害。在这位作家的意识中,这场瘟疫即亚细亚霍乱,欧洲这个原本理当免于疾病的现代文明区域,却要被来自亚洲的疾病所殖民。诸如此类对疾病的想象,与对被冠名的异域之间,建立某种隐喻性关联,从而阴险地把邪恶与异族等同起来,这些他者被视为是污染源、致瘟疫的邪恶族群。这种非理性对待瘟疫及疫区,在后来甚至和政治正确相关联,如在纳粹德国意识形态宣传中,德意志人血液中若混有其他种族的血,结果会像梅毒患者,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人,希特勒《我的奋斗》中就常提及犹太人多患有梅毒,这为排犹提供借口。在这样的历史变异中,《十日谈》这部未把瘟疫隐喻化之杰作,即便后来仍持续畅销,却在传播过程中不敌瘟疫被隐喻化的历史进程。只关注文学叙述内容,而不把文学叙述本身置于人的自然史语境中的阅读,则是现代文明的伴随物:据英国史学家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同为科学:“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实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心灵科学则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对科学而言,自然(界)永远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却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学必须看透它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纯粹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存在着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皆是思想史”,“与自然科学家不同,史学家不关心各种事件本身。他只关心成其为思想之外在表现的那些事件上,而且只是仅仅就它们表现思想而言才关心着那些事件。归根结底,他仅关心着思想;仅仅是就这些事件向他展示了他所正在研究的现实而言,他才顺便关心着实现的外部之表现为事件”。把自然过程视为历史,需要假定自然过程也是由成其为它们自身的思想所决定的行动过程,即自然事件也是思想的表现,或上帝旨意或恶魔栖身于大自然,但自然科学家否决这类假说,神学家则不同意这类假说:“就我们的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而言,组成自然世界的事件的过程,在性质上和组成历史世界的思想过程是不同的。”①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2—306页。如此论述,的确符合启蒙运动和科技进步所塑造的人对世界的认知:自然灾害本身并没有思想,而战争、政治纷争、城市化等背后有着人的思想所推动、设计;或者说,正如一个人由于自然原因而故去,医学只须根据外部现象宣布死亡和说明死因即可,无须再对这种自然生命现象进行哲学论述,而史学研究的对象则不仅要触及死亡,还必须讨论死亡这一历史事实对当时甚至后世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观念,影响到对文学艺术史的认知——大大遮蔽了自然灾害之于文学艺术发展史的意义:人们只关注文学作品书写的人,如论及文艺复兴时代文学,人们关心的是那些作品如何呈现人之解放的故事及其审美表达方式,对肇始文艺复兴的瘟疫及其隐喻之压力,自然也就在阅读过程中缺席了。《十日谈》不被充分经典化的命运由此被确定,尤其是这种损失,在冷战时代西方所锻造的诸多科学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中,即脱离语境的修辞学阅读、形式主义理解,则更进一步降低了这部故事体之作的美学价值、历史意义,人们不会特别考虑瘟疫在叙述中的强大功能。
总之,《十日谈》这部奇书显示,那场黑死病意外促使人发现自己,并且激发了人热爱生命、享受生命和尊重生命,还把文学书写由拉丁文转化为意大利语言,意外催生了民族国家文学。这远非薄伽丘个人在瘟疫中毅力超群、智慧出众所致,而更得益于疫情推动意大利这个缺乏以国家力量践行教会意志的族群,得思想解放之先机。遗憾的是,《十日谈》的价值正在于正面叙述瘟疫促使人积极直面生命尊严,但在后来的阅读和翻译史中,其却未能如瘟疫反而激发人珍视自身作为社会生命之价值的现代人文学科、人作为自然生命之医学的诞生那样幸运,而是被降低到在反教会层面上倡导人性解放的水平上;《十日谈》所显示出的积极面对瘟疫的人生态度,未被后世文学所承续,哪怕医学持续进步、国家在抵御瘟疫中的功能加强,它也未能帮助社会消除瘟疫被隐喻化的错误——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即仇视疫区、敌视感染者、牺牲被感染的族群、把患者或疑似患者当作敌人等,从而使这部关于威胁人之生命存在的瘟疫如何促成人的自我发现之通俗作品,被误读为人民反抗教会制度之人性解放的经典(实际上讲故事的人全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