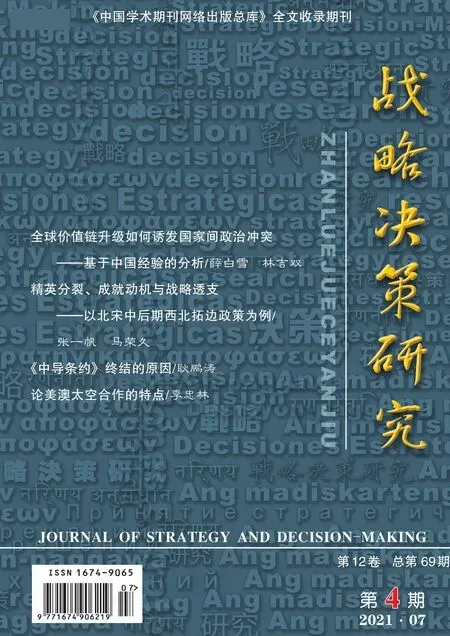精英分裂、成就动机与战略透支
——以北宋中后期西北拓边政策为例
2021-07-17张一帆马荣久
张一帆 马荣久
回顾国际关系史,多有崛起国或霸权国由于在对外战略中出现透支现象而走向衰落抑或败亡,诸如拿破仑帝国的对外扩张、一战时期的德国的“世界政策”、二战时期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①关于德国、日本的崛起与衰亡,参见埃里希·雷德尔著,吕贤臣译:《崛起与毁灭:纳粹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川田稔著,韦平和译:《启微:日本陆军的轨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出现过度扩张与资源损耗,进而引发战略透支。②Anthony H.Cordesman,Salvaging American Defense:The Challenge of Strategic Overstretch,(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Hall Gardner,Averting Global War:Regional Challenges,Overextension,and Options for American Strateg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章珏:《目标偏移、止损失败与大国战略透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5月,第18页。苏联也在自身经济萎靡的情况下卷入阿富汗战争,出现了严重的战略透支现象,最终拖垮了自身国家发展。①宋亚光:《“苏联的越南”:美国与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6期,第82-92页。大国战略透支现象并不仅存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中央王朝在处理边疆事务或与周边王朝的关系时,也容易出现战略透支行为。诸如秦朝一统之后不惜民力大兴土木、加之对外征伐频仍,致使其崩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扩张战争极大损耗了汉初休养生息的战略积累,最终导致严重的军事挫败与国家危机;北宋中后期为开疆拓土而进行的扩张战争也使其出现了盛世而亡的悲剧;而季汉北伐战争、唐朝安史之乱、明朝万历朝鲜战争等等无不向今人诉说着战略透支的隐患。为什么中古史中大国战略透支频现?这些战略透支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与历史学不遗巨细的全面解释不同,本文寻求从战略层面来理解大国对外扩张的国内政治机理,从而删繁就简、发现贯穿历史而长存的关键因素。北宋在多方面与近代民族国家最为相似,其中后期推行扩张政策,出现了内忧外患的战略透支,并最终由此衰亡。本文以北宋中后期西北拓边政策为例,探讨战略透支的成因,并解释这一局面为何难以扭转。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界对于战略透支问题的研究仍处于发端时期,仅有部分学者试图提供理论框架来进行系统性的解释,也有学者使用这一概念对当前中国具体战略进行政策分析。②冯传禄:《“战略透支”抑或“战略生长”——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定性分析》,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5期,第1-24页。时殷弘强调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总结战略透支形成的因果关系的重要意义。③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57-68页。关于战略透支的成因在世界史、国际关系以及战略研究等领域已经给出了相当多的解释路径。而在具体研究中战略透支概念往往存在多种理解方式,譬如在世界史与美国战略研究中往往使用“过度扩展/扩张”来指代大国在对外扩张战略执行过程中的战略成本超过收益并最终导致国家由盛转衰的现象。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本文对于战略透支的成因的文献回顾分为国外与国内研究来阐述。①国外研究以美国学界为主,由于冷战后出现了关于美国是否是“帝国”的讨论,所以出现了一系列对于美国帝国是否陷入了过度扩张及其根源的理论讨论。国内研究则是伴随着中国外交转型开始的,所以相对而言缺乏完整的理论讨论而更为重视实践性。参见章珏:《目标偏移、止损失败与大国战略透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5月,第2-5页。
在讨论大国兴衰与世界政治变革的宏观问题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指出了大国由于在对外扩张过程中的军事技术的扩散与抵抗联盟的出现会使得即便大国本身的扩张成本不在上升,其维持扩张成果的总成本也会超过收益,最终导向过度扩张引发大国衰落。②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章。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则提出了过度扩张概念,认为如果大国过分扩张就会存在“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为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的风险。③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朱贵生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其著作中较为完整地归纳了既有理论对于过度扩张起源的解释类型,在此本文也使用这一区分方式来归纳国外学者的既有研究。
其一是现实主义的解释。现实主义者往往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促使国家追求安全,由于安全本身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时往往出现目标过高的现象。④米尔斯海默的著作是这一理论的最佳代表,参见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但这一解释本身带有的决定论色彩与逻辑问题使其并不能很好地与现实切合。⑤从逻辑上讲,无政府状态所鼓励的均势会惩戒过度扩张行为;而现实主义所暗示的决定性推论为所有国家均将出现过度扩张的行为,现实显然并非如此。
其二是认知路径的解释,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代表,强调诸如信念体系、认知一致与错误归因等认知心理,容易使决策者做出一系列错误决策,从而导致过度扩张。⑥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但这一解释并不能解释为何有些决策者在失败历史或实践失利中会更新、转变自身认知,另一些却不会。⑦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和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6页。并且正如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所指出的,很多情况下决策者认识到了战略存在的问题,但却仍然没有出现战略上的调整。①Charles Kupchan,“Empire,Military Power,and Economic Declin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4,Spring 1989,pp.48-49;Charles Kupchan,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库普乾对于肯尼迪与多兰批评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被理解为,将过度扩张简单地归咎为决策者自身问题是不恰当的。查尔斯·多兰(Charles Doran)则将过度扩张归咎于决策者无法预见形势变化,或者无法使用非线性的思考方式。②Charles Doran,Systems in Cri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但这类基于纯粹的认知路径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战略执行过程中的失误与缺陷也并没有太多帮助。
其三则是国内政治的解释,主要来源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回答。霍布森、列宁以及熊彼得等人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帝国主义利益集团劫持了国家,从而把国家政策扭曲为对于个体利益的追求。③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和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8页。斯奈德也基于国内政治给出了基于国内政治联盟的解释,其通过设置国家体制的“卡特尔化程度”来说明国内利益集团的相互勾结,并且将其与“多米诺骨牌理论”等帝国迷思的观念相联系起来,从而劫持国家走向过度扩张。④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和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69页。
也有部分学者从国内政治层次出发进一步完善了关于过度扩张的解释。比如,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Taliaferro)在斯奈德的基础上引入前景理论,回应了“为什么民主国家也会出现过度扩张”的问题。⑤Jeffrey Taliaferro,Balancing Risks: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而布劳利(Mark R.Brawley)则通过国内制度中的“路径依赖”与“余晖效应”来解释战略调整的滞后所引发的过度扩张现象。⑥Mark R.Brawley.Afterglow or Adjustment: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Responses to Overstretch(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另外也有许多学者对于针对某个单一国家的战略根源与陷入过度扩张危险的可能性进行讨论。⑦由Thierry Balzacq,Peter Dombrowski,Simon Reich开启了一项新的研究议程,其通过将战略研究与国别研究相结合来探讨具体国家大战略是如何在国内行为体、政治机制与外部环境下形成的,从而形成了称之为“比较大战略”的研究。参见Thierry Balzacq,Peter Dombrowski,Simon Reich,Comparative Grand Strategy:A Framework And Cas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时殷弘率先分析了战略透支现象之后,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重视。①2017年,《战略决策研究》编辑部举办了“当前中国外交战略思考”学术研讨会,就中国对外战略中的战略透支问题进行了讨论。参见《当前中国外交战略思考》,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3页。蒲晓宇则对国内学者的讨论进行了总结,Xiaoyu Pu,Chengli Wang,Rethinking China's rise:Chinese scholars debate strategic overstretch,International Affairs,2018,Vol.94,No.5,pp.1019-1035。其一是基于战略组成要素的解释,战略要素在此主要包含战略目标、战略手段与国家实力等等。时殷弘将战略政策(手段)区分为战略经济与战略军事,将战略透支与战略手段联系起来,其指出“中国在近几年同时推进‘战略经济’与‘战略军事’两大政策,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从事‘多线战斗’,可能导致‘战略透支’的风险日益增长。”②时殷弘:《中国对外战略的最新变迁:从“战略军事”为主到“战略经济”为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第22页。高程、徐进讨论了战略目标设定与资源投入的匹配程度所引发的透支现象。③高程:《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战略透支”问题探析》,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49-55页。徐进:《从艺术的角度看待战略透支》,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42-48页。徐秀军认为,由于目标的设定脱离实际,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战略基础支撑,便会出现战略透支现象。④徐秀军:《战略过载、战略透支与大国的衰弱》,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1期,第13页。阎学通、陈积敏认为,当主导国或崛起国急于追求更多权力或高估自身实力而做出超出国家承受边界的冒进举动时,国家便会陷入战略透支的困境之中。⑤阎学通也区分了国家类型与战略透支、战略冒进两者之间的关系。参见阎学通:《外交转型、利益排序与大国崛起》,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页。陈积敏:《中国外交应警惕战略透支风险》,载《中国国防报》2015年1月20日,第22版。
其二是基于战略发展过程的解释。孙学峰认为,崛起国在其崛起进程中的不同阶段需要谨慎的战略选择,否则将陷入多线作战并且恶化崛起困境,进而诱发战略透支。⑥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崛起国战略透支》,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31-41页。章珏、徐进基于战略执行与调整过程做出了更为精细化的解释,将战略过程概括为制定、实施、反馈、调整和再实施五个阶段,并从决策心理的角度归纳了目标偏移与止损失败两个导致战略透支的主要因素,并给出了导致两者出现的心理因素。⑦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51-83页。
其三是对于特定案例所开发的特殊性具体解释。⑧由于本文使用个案的特殊性,本文也可被视为针对北宋这一特殊案例的解释。比如李隽旸分析了公元前415年雅典西西里远征这个案例,将过度扩张的决策出台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经验池,并对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的“撒托耳珀—萨缪尔森定理”进行修正与广义推论,从而解释了这一特殊案例。①李隽旸:《西西里远征:过度扩张的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第28-67页。焦世新针对美国在二战后反复出现过度扩张的问题,给出了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超地区霸权战略的解释。②焦世新:《美国为何会“过度扩张”?——超地区霸权战略模式的解释》,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2期,第119-131页。姜鹏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发现海陆复合型大国没有利用海权国的“知觉警觉”与陆权国的“知觉防御”是其陷入“腓力陷阱”式的战略透支的原因。③姜鹏:《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4-29页。顾全探析了在一战前德国进行海军扩张行为的原因与机制。④顾全:《大陆强国与海上制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版。
也有学者针对古代中国的战略透支现象做出了一些解释。陈拯阐释了系统时间效应上的不一致对战略演进和战略透支的作用;并且由此解释了汉武帝时期战略透支的成因。⑤陈拯:《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27-49页。王剑锋则研究了东汉帝国的战略透支现象,认为大战略“手段与目标相抵牾、资源投入与目标的推进难以为继”,是导致东汉帝国走向战略透支的原因。⑥王剑峰:《战略透支与帝国衰毁:东汉帝国败亡的大战略机理透析》,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6期,第3-21页。前者属于从战略发展过程与时间效应来解释古代中国,后者则是阐释了东汉大战略的运行机理,两者均强调了战略制定与执行过程的关键性,以及重视古代中国战略资源积累的角度来认识问题,但也缺乏对于具体客观因素的探讨。
从国内外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界定过度扩张和战略透支这两个概念;二是揭示过度扩张和战略透支的形成机制。本文的研究属于第二种。在既有研究中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于战略透支问题的回答往往聚焦于国际体系、政体、认知心理等影响决策制定的具体因素,而国内学者则更关注战略自身的内涵:诸如目标、手段、过程等要素。①笔者发现国内多数研究将战略本身的目的、手段、资源调配视为诱发战略透支的自变量/成因,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本质上仍是对于战略透支的一种类型化区分,事实上并未揭示现实中的哪些客观因素会诱发战略透支。但在具体研究中则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在具体的单要素的解释中,往往认为国际体系决定了进攻偏好,抑或偏向于认为国内政治为“铁板一块”,不存在任何变化。这就使得单要素的解释倾向于表现出宿命论的逻辑,而缺乏对于战略过程中变化的理解。其次则是部分研究虽强调将物质资源与认知偏差联系起来考虑,但却并没有讨论两者的相互关系,仍旧只侧重其中一方。再次,战略透支并不完全属于近现代国际关系的特有现象,在古代中国史与世界史中也出现了多次的国家战略透支现象;现有理论中多数难以适用于这些较为特殊的案例。与此相关的是,既有文献中关于战略透支形成的因果机制的开发仍属少数,即便是明确表示属于因果机制开发的研究也最终走向了比较案例研究或者引入干扰变量的研究。②区分比较案例研究、干扰变项的研究与过程追踪的区别,可以参见Derek Beach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Process-tracing methods: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24-32。
而针对本文所考察的案例,既有理论均不能给出相对适配的回答,因此我们就需要重新设定另一种因果逻辑,来解释这一特殊现象。③关于既有理论为何难以解释本文案例,在后文中进行了替代性解释的排除。故而本文寻求基于国内政治角度下给出一种战略透支形成的多变项机制,并且通过北宋中后期的拓边政策这一案例,说明国内政治中的精英分裂、决策者的成就动机心理将同样可以引发国家的战略透支;并且在更广阔的总体中,这一因果机制同样可能存在。
二、大国战略透支的国内政治逻辑
(一)战略透支的概念界定
吉尔平在指出,大国最大的危险是过分承担义务,逐渐耗尽国力。④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6-185.吉尔平没有强调决策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导致了这种危险。保罗·肯尼迪与杰克·斯耐德大抵延续了吉尔平的看法。保罗·肯尼迪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它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为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①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朱贵生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斯奈德则将“过度扩张”概括为“自我包围”与“帝国的过度扩展”,即“激发其他国家组成反对本国的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联盟”与“由于在远离中心的地区的不断扩张,以至所花费的成本超过了其所获得的收益”。②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和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其中第二种情况就属于本文讨论的战略透支现象,而“自我包围”很有可能是战略透支形成的外部原因之一。③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54页。
而库普乾则敏锐的指出国家意图这一问题:很多情况下决策者会认识到过度扩张的问题的存在,但却没有调整(目标或手段);这一问题比为什么过度扩张会形成更为重要。④Charles Kupchan,“Empire,Military Power,and Economic Declin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4,Spring 1989,pp.48-49.这也就说明,战略透支现象不仅仅是客观形成的,也是主观造就的;战略的执行与调整过程对于战略透支至关重要。同时布劳利也指出,库普乾的理解只关注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过度延伸,而没有关注到吉尔平与肯尼迪所强调的经济内涵;⑤Mark R.Brawley.Afterglow or Adjustment: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Responses to Overstretch(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ter 1,p.29.布劳利将过度扩张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静态来看,在任一时间上的安全过度承诺而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实现;其二则是动态来看,由于伴随着时间的国家实际资源的相对衰落而不能维持原有的承诺,从而致使突破最大可维持的承诺下出现透支情况。布劳利设定承诺为C曲线,实际资源发展为R曲线,最大可维持程度为S准线;第一种透支即C>R的情况,第二种则为C>S的情况。⑥Mark R.Brawley.Afterglow or Adjustment: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Responses to Overstretch(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ter 1,pp.6-7.(见图1)

图1:布劳利对战略透支的曲线表示
刘丰将战略透支的概念界定为大国在执行扩张性对外战略时,战略投入显著超出自身的资源承载和动员能力,必须以损耗其他战略目标的方式持续汲取额外的内部和外部资源,从而导致其短期和长期战略目标难以达成,最终导致国力损耗和衰退;并给出了三个递进指标。⑦刘丰:《战略透支:一项概念分析》,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27-28页。由此可见,多数学者认为战略透支即在对外扩张战略中的战略资源投入成本超过了其扩张所带来的收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战略透支这一概念中的国家意图、时间效应以及安全与经济相关联等特点。
因此本文综合前者的概念界定与思考,基于集合论将战略透支概念区分为三个维度的表现形式。①关于过程追踪法中为何要求集合论界定概念的讨论,参见Derek Beach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Process-tracing methods: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45-51。
其一是补偿缺损,即战略收益的获得难以补偿战略成本的损耗。这一维度主要可以表现为国家对内部资源的过分汲取或者大幅度的向外举债,从而维持国家在对外扩张中所需要的战略资源供给;国家在执行扩张性战略时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或者其他战略发展的停滞;同样也有可能出现由于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而导致的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出现国内社会的政治抗争活动。
其二是战略长时段特征,战略透支过程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本文赞同前文中布劳利所提出的第二种战略透支形成的可能,即长时间的战略补偿缺失没有得到调整。即便第一种补偿特征出现,但在短期之内由于战略上收支平衡的恢复得以缓解,这种情况并不能被视为战略透支,因为在短期内的战略透支或许是由于资源汲取的短时缺失或者战略手段的提前执行而导致的,而并不属于绝对意义上的缺损。
其三是战略向度特征,国家必须执行的属于扩张性战略,这一向度确保了国家意图层面的主动性。在反抗对外侵略战争中国家也会出现战略资源的匮乏难以维持支出,但这种情况并不属于战略透支所讨论的范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主动性的国家意图,这种情况属于被动的战略反应。此外,这一向度也可以保证在讨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出现战略透支现象的同时,没有否认小国出现透支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小国出现的战略透支现象在经验上被观察到的可能性远不如大国,因此本文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会选择大国而非来进行经验检验。①小国也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战略透支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中小国家间冲突或者小国主动挑战大国等情况中,但由于其国家体量限制了扩张产生的国内影响,所以也造成了经验观察上的困难。
根据以上三个维度的表现,我们可以直观的通过观察历史而得出一国是否出现了战略透支的现象。这为我们之后的针对北宋中后期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可能,而这些特征也将揭示北宋晚期远非我们常识中的“积贫积弱”,而其最终败亡于“靖康之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的战略透支问题。
(二)精英分裂和成就动机引发战略透支
战略研究与对外政策分析往往认为,战略决策与执行往往是基于国内政治要素做出的。而众多的国内政治要素中,较为主要的有:领袖人格、政体差异、利益集团与党派以及公众舆论。根据本文所选取的特殊个案,我们排除了政体差异、公众舆论两个要素,这是因为公众舆论在封建王朝时代的对外政策中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封建王朝政体的集权制影响主要通过领袖个人体现出来,而政体本身也相对稳固,在同一个案中我们无法判断政体本身存在的影响,因此不予讨论。②在这里我们并非否认这两个因素对于北宋对外政策的影响,而是由于案例本身的时代性与单一性,在此无法进行深入讨论。另一种角度上,封建时代的政体影响往往与领袖个人存在显著的共线性,而社会普通的公众也往往难以参与到决策之中。
而领袖人格、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则与本文案例较为契合,因为在封建政体中,参与战略决策与运行的往往是领袖与统治集团的政治精英。因此本文也基于此出发,通过对于集团内部的政治精英与领袖个人的考察,来看待大国是如何走向战略透支的。
首先,施韦勒对于政治集团精英的凝聚与分裂给出了相关讨论,其认为在国内层面,政治精英绝非铁板一块,如果精英分裂程度较高,即使存在着对(外部)威胁性质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的共识,国家也不大可能采取一致的政策。③Randall L.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46-62.施韦勒这一讨论也直接指出了精英分裂将直接影响国家战略手段的执行。
在政治学中,精英分裂经常被用于讨论国内政治秩序、政治体制转型以及政体合法性等问题。在精英分裂的研究中,亨廷顿最早对于政治转型中的精英团体的分裂进行了划分:支持/反对政府;前者包含民主派、自由派、保守派,后者则涵括温和民主派与极端激进派。①奥唐纳、施密特等也做了类似的区分,参见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1页。O'Donnell,Guillermo,and Philippe C.Schmitter.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p.15-17。伯顿(Michael G.Burton)与希格利(John Higley)通过研究精英间和解的可能性途径,从而区分了精英共识联合(consensual unity)与精英分裂两种精英间关系,并且认为后者是指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上,精英间不存在或只有很少的共识,并且各派别间只在部分领域有少量的互动。②Michael G.Burton and John Higley.Elite Settlement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1.52.No.3,1987 pp.295-307.事实上,精英凝聚/分裂是一个变量的两个取值,因此本文只在此基础上对精英分裂给出相关定义,精英分裂是指两种可能:首先是内部分裂,即党派内部成员之间的分裂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同一党派内成员出现意见相左、行动不一致等相互颉颃的现象。其次是外部分裂,统治集团精英与反对派精英的分裂,其主要表现为由于党派排挤导致部分精英集团离开体制,或者由于体制没有及时吸纳而造就的反对体制的精英集团;除极权国家之外,统治集团与反对派精英之间的分裂情况在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中都相对普遍。两种情况下的分裂双方的信息与行为互动都会出现缺失或者不对称的现象。
而之后则需要回应的一个衔接式问题:精英分裂如何影响国家战略执行?在精英分裂的第一种情况中,精英内部分裂会导致在战略执行过程中的各自为政与权力分散,这便会造成信息不对称或沟通缺失以及战略执行过程中的不切实际,将导致战略手段的低效甚至失效,进而引发战略资源的无效投入与浪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将领导人也视为精英之一,具备某种党派立场与偏好。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反对派精英并不掌握国家战略执行的权力,因此这种情况仅在反对派精英上台执政时才有可能影响国家战略;这种情况下出现由于反对派精英的上台而导致的战略手段的逆转或废止,同样使得之前的战略手段失效,这将使之前国家对于战略目标的努力成为泡影,而这也将造成大量的战略资源的浪费。(见图2)

图2 因果链条1:精英内外分裂—战略手段低效/失效
其次,在制定对外战略时,领袖人格将极大程度上影响战略决策,尤其是战略目标的设定。斯奈德认为在民主制与单一寡头制的政体中,过度扩张较少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程度也并不会那么极端。①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和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译序,第10-11页。同时,其也认为在独裁政体中,国家最终是否过度扩张取决于独裁者自身属于扩张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②斯奈德并未就独裁政体为何走向战略透支做出更为清晰的回答,而是简单地将其归因为领袖个人偏好。由于本文使用的个案属于独裁政体,故而也可以被视为是从这一路径出发的探讨。但独裁政体中的领袖并不能简单的区分为扩张主义/理性主义,领袖往往具备理性基础,并且在战略过程中完全可以作出目标的调整与运行手段操作。③后文案例中也将展示神宗、哲宗等具有成就动机的领袖并非缺乏战略常识与理性认识。
既有关于领袖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个体偏好、性格与风格等问题上,而直接与政治行为与决策相关的则是领袖本身的心理动机。④David G.Winter,“Assessing Leaders'Personalities:A Historical Survey of Academic Research Studies”,In Jerrold M.Post ed,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p.11-38.政治动机理论是政治心理学中关于领袖人格研究比较成熟的概念,起源于麦克利兰的领袖动机理论,并经过戴维·温特(D.G.Winter)的改造后用于评估政治领域的领袖动机。⑤David G.Winter,Personality: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ves.(New York:McGraw-Hill,1996);Winter,D.G.The Power Motive.(New York:Free Press,1973).温特指出,成就动机、权力动机、归属动机是领袖所具备的三种基本动机,权力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关注如何掌控权力;成就动机注重政绩,追求成功;归属动机则注重人际交往,关注亲朋好友的感受。在温特的理论中,领袖虽然与权力为伴,但其行为却是出自不同的动机,领袖一般同时具有三种动机,但并不一定全部表现出来,而是侧重于其中一种或两种。①国内关注领袖动机的研究相当稀少,相关评述与研究参见季乃礼,阴玥:《30余年来我国政治心理学研究述评》,载《学习论坛》2020年第3期,第36-46页;阴玥,季乃礼,李雪超:《从特朗普的政治动机看美欧关系》,载《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1期,第1-8页。温特将成就动机的表征界定为“成就动机意象是指在文本或其他口头材料中,当提到卓越,做一个“好”或“更好”的工作,或执行一些独特的成就或创新行动时,会在文本或其他口头材料中评分。”②David G.Winter,“Measuring the Motives of Political Actors at a Distance”,InJerrold M.Post ed,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pp.154-156.温特同时指出,表现出成就动机的领袖极其重视胜利、成功或者伟大的成就,并且这种类型的领袖具有极强的自控力、充沛与持久的坚持能力,对于成功的概率会反复计算,但这并非是理性计算的过程且最终的胜利无关,这类领袖面对失败往往以负面、消极情绪或者反击行为来回应。③David G.Winter,“Measuring the Motives of Political Actors at a Distance”,InJerrold M.Post ed,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pp.155-156.
本文在此并不着重分析领袖的个人人格表现,而仅仅是强调具有成就动机的领袖更容易形成扩展型战略目标以及推动对外扩张战略的执行。④相关领袖人格对外交政策制定与战略决策的影响的研究,参见:Valerie M.Hudson,Benjamin S.Day,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Lanham:Rowman&Littlefield,2020),pp.62-64.Eric Singer,Valerie M Hudson,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Routledge 2020),pp.79-134。因此本文侧重于成就动机的表现形式,并将具有成就动机的领袖这一变项定义为:在行为中并不注重对权力的控制或个人的社会性关系,而是侧重对某些荣誉、威望或者业绩的追求的领袖,其往往会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对于战略目标的设定起到关键作用,并且由于其基于成就动机的人格将长期执着于这一目标,而在战略执行过程中也会加以干涉战略执行过程,谋求最快或者最有效完成自身成就。根据这一定义,便可以得出具有成就动机的领袖如何影响战略决策与执行(见图3),温特同时还指出,动机通常是通过对人们富有想象力的言语行为的内容分析来间接衡量的,这样一种评估方法很容易使其适合于远距离测量政治领导人的动机。⑤David G.Winter,“Measuring the Motives of Political Actors at a Distance”,InJerrold M.Post ed,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pp.153.本文中同样使用相关领袖的直接表述来证明其成就动机的存在。

图3 因果链条2:成就动机-目标固化/僵化
由此,基于之前的讨论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相对复杂的因果逻辑链条(见图4);并且根据过程追踪法对于案例检验的要求以及前文中对于两个因果链条的梳理,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个相互连接的关于这一因果机制的预期:

图4 完整因果逻辑链条
1:精英的内部分裂将导致战略执行中的权力分散以及各自为政,从而导致信息沟通上的不对称,这将使得原本的战略手段的低效。
2:具有成就动机的领袖会呈现出偏好更为卓越的战略目标,这将导致战略目标的设置明显较高;此外,由于领袖对于外来的收益抱有信心且极具耐性,在战略受挫时并不会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导致战略目标的长期固定与僵化。
3:在面对精英外部分裂所形成的反对派精英上台之后,会废止或者逆转之前的战略手段,这将造成原有战略规划的失效,同时舍弃(浪费)原有的战略资源投入。
4:战略目标固化/僵化的情况下,加之战略手段的低效/无效化,将造成战略资源的长期浪费,最终引发战略透支。
此外,国内政治的决策环境也对于决策本身存在着关键影响。对于本文所探讨的案例,其决策环境则主要是受到政治话语与战略文化两种要素的影响。而在既有研究中,已有学者针对北宋这一特殊案例,从这两方面做出了讨论。
例如在历史学研究中业已有所讨论的“汉唐旧疆”的政治话语影响了北宋中期神宗以降的历代皇帝与政治精英,从而影响了其战略目标的设定的影响。①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载《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24-39页。曾瑞龙曾经指出,北宋中后期的拓边战争具有两项政治目的:一者是抵御入侵,北宋自熙宁(神宗时期)以后,这一目的是基本成功的;即便是弥兵息战的元祐时期,基于其对西夏的实力优势,也没有让步的必要。二者是恢复疆土,在这一目标上北宋的对外行为是否成功则是一个吊诡,因为理念层面“旧唐故土”所指的地方自中唐就已经被吐蕃蕃部吞并、内化,从而使得简单地用收复“旧唐故土”的政治话语来理解拓边行为总是存在一定隔膜。②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而战略文化是战略主体长期存在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对于战略目标、偏好与选择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③相关研究可以参考: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Princet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ix;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inKatze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基于这一路径出发,张一飞提出了传统中国所具有的“自修”战略文化如何在大一统与准分裂时期影响国家战略的运行;并且诠释了北宋仁宗以降的统治者重视“唯实力”与“唯优势”主义,而忽视战略资源的积累,从而深陷战略透支的泥潭。④张一飞,《中国战略文化中的“战”与“和”:“自修”文化的两种战略选项》,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8年6月。但其同时也指出,战略文化并不能解释所选取案例的全部,并且单一的双变量线性关系也相对薄弱。
之所以在本文中不讨论这两个变量所存在的影响,并不代表否定这两个因素,而是因为战略的制定与执行是受到有限可控以及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制约,谈及决策环境中的战略话语与文化会使得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间关系出现复杂共线性,我们无法厘清变量间相关问题。⑤并且由于战略文化的定义过于混杂,不同学者对于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界定与限制,使得其本身难以作为单一有效的解释变量存在。参见:张一飞:《中国战略文化中的“战”与“和”:“自修”文化的两种战略选项》,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8年6月,第6页。此外,根据定义战略文化相对稳定,其也不适用于对于理解本文案例中的战略逆转时期。①既有研究大多认为北宋战略文化属于一种进攻性强现实主义,但这一逻辑并不能解释北宋为何会出现“澶渊之盟”与“元祐更化”时期的战略妥协。为了更直观的考察北宋案例中国内政治的理性因素影响,所以本文只选择前文所提及的两个变量,谋求解释其相关关系。②本文并不是对于北宋这一案例进行完美的解释,因为笔者认为纯粹完美的解释将走向历史描述,而后者是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
(三)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北宋中后期的拓边行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对于本文所提出的因果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并不寻求建立对于北宋衰亡的完全解释,而是侧重于利用这一案例说明本文提出的特殊的国内政治逻辑。
首先,宋朝可以作为国家行为体样本进行考察。第一,宋朝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自身的政权;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与陶德文(Rolf Trauzettel)指出,在十二世纪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民族主义”。③Hoyt Cleveland Tillman,Proto-Nationalism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The Case of Ch'en Lia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79,Vol.39,No.2,pp.403-428.Rolf Trauzettel,Sung patriotism as a first step towar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John Winthrop Haeger.ed,(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5),pp.199-213.“中国”观念更为频繁地被用来描述自身,这一点有别于唐朝及其之前的“天下”观念,这一观念更为清楚地表明统治者以及上层精英认为自身属于一种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国家。④关于宋代关于“中国”观念的讨论,参见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载《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12页。此外,宋朝也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将自身政权范围、文化与民族相联系为一体考察。⑤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载《文史哲》2005年第5期,第57-64页。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出现萌芽的宋朝在内部政治观念上是存在对于外族的区分的。第二,宋朝存在明确的政权间地理疆域边界。在宋初以前的王朝统治时期并不存在明确的政权间地理边界,无论是汉唐两代统一王朝对于北部与西部边界的模糊界定,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内部政权之间的纷争都没有诞生明确的疆界界定;而在十一世纪后期,即宋仁宗、英宗在位时期,对于疆界的界定工作逐步展开,且重要的是宋代第一次诞生了政权间协商决定的地理分界线。⑥这直接受到“澶渊之盟”的影响,相关宋代疆界的产生以及与前代的内涵区别,参见Nicolas Tackett,The great wall and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border under the Northern Song,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2008,No.38,pp.99-138。地理疆界的明确使得宋朝作为“国家”的特质得以凸显,其标志着从“天下”想象到边界分明的华夏国家的转变。①[瑞士]谭凯著,殷守甫译,《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30页。但是也有观点反对将宋代“中国”观念与所谓的“近代性”关联起来,参见黄纯艳,《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载《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第22-40页。第三,稳固的边防设施成为政权间边界稳定的保证。宋朝边防不同于以往,在唐以前王朝边境防御往往是由多种方式的武力存在构成,但宋朝由于特殊的地理与政治形势,则在宋朝中央政府的主导下于边境线形成了由完整且相互连接的线性边防军备。②相关研究可以参见林瑞翰,《北宋之边防》,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70年第19期。这一点与前两点相联系,共同为将北宋视为可供参考与比较的案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也是本文之所以没有选择宋代之前王朝战略透支现象的首要原因,这并非是指讨论两汉、西晋或者隋唐王朝时期的战略透支是错误的,而是仅仅强调了宋代及其之后王朝更具有作为现代国家对照样本的独特性。③针对中国历史上的战略透支问题的讨论,可以参见陈拯,《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27-49页;王剑峰,《战略透支与帝国衰毁:东汉帝国败亡的大战略机理透析》,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6期,第3-21页;张一飞,《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第4-40页。以上三点是我们考察宋王朝的大战略的关键前提,因为只有当战略在观念与物质边界两个层面上被理解为是对外取向时,它才对于今天的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研究具有对照意义。④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北宋时期并非大一统王朝,而是分裂格局下的中心-外围体系,因此并不能视为两极国际体系。但是笔者认为,王朝政权彼此间的相互否认正统性是一种必然,这一现象并不能作为视宋辽金夏为整体中的个体的判断标准,因为即便在大一统时期,中央王朝也会否定外部政权的正统性;文明边界与地理边界的一致性才应当视为判断是否属于分裂时期的标准。前者参见孟维瞻:《国际关系理论之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的适用性问题》,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22-31页。另外,部分学者指出北宋神宗时期的对西夏战争并非属于国家统一战争,而是有着明显杀人侵地的特征。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7页。
其次,宋朝案例提供了较低的先验性概率。这一点是基于过程追踪法对于案例检验的要求。⑤比奇指出,大部分定性研究中研究这并没有指出先验概率与似然比的问题,这也使我们很难直观感知某一项定性研究所带来的理论信心变化。参见Derek Beach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Process-tracing methods: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87。宋朝在常识上属于“积贫积弱”“文盛武衰”的一代,其出现战略透支的缘由似乎可以通过前人的替代性理论进行解释;因此我们一开始对于本文所提出的因果机制的先验性置信度并不高;而伴随着对案例中证据的发现,本文说明这些证据增加了对于本文理论假说的信心,从而提高对于理论机制存在的后验概率。①关于在过程追踪中使用贝叶斯逻辑进行理论推演的讨论,参见Andrew Bennett,Jeffrey T.Checkel,Process tracing: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276-298;Derek Beach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Process-tracing methods: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83-99。
最后,宋朝对西北地区的拓边行为长达几十余年,跨越三代帝王(实际上是四代政权更迭),这样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以及近年来史料的重新发现为我们进行个案研究提供了可能。已有研究中对于长时段进行过程追踪并不常见,但这并非可以忽略的,战略透支问题本身的时间限度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一个长时段历史事件进行考察;此外,北宋后期三代(神宗、高太后、哲宗)统治者的不同策略及其转变也将这一个案分为三个子案例,从而避免单一案例的单薄。
本文主要使用过程追踪法,分别对于北宋中后期的对外过度扩张案例进行过程追踪;本文将其区分为两个阶段:神宗时期与元祐更化之后。但本文并非典型的基于要素的案例内历时性差异比较,而是对于这一长时段进行共性比较。两个阶段都经历形成了战略透支现象,因此可以更好地对于本文所提出的因果机制进行检验。比奇(Beach)与佩德森(Pederson)指出,对于个案内因果关系的考察并非基于密尔法或者概率论,②相关密尔法的讨论,参见释启鹏,《方法论视野下的比较历史分析:应用逻辑与国内进展》,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4-89页。而是基于决定论与机制论的思考。之所以不寻求负面案例或者反面案例进行比较,是由于我们无法期待在没有出现自变项与因变项的案例中发现本文提出的因果机制。③对于因果机制的检验如何选择案例的问题至今仍不存在绝对标准,相关案例选择标准的讨论可以参见约翰·吉尔林著,黄海涛,刘丰,孙芳露译:《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加里·格尔茨,詹姆斯·马奥尼著;刘军译:《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另外,叶成城、周亦奇、唐世平等开发了“半负面案例”考察方式,其核心在于选择进行到一半的因果机制进行考察,这一方法类似于比奇与佩德森所强调的基于“最不可能”案例的“辛纳屈推断”可以有效提高我们对于某项因果机制的信心。参见叶成城,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22-47页;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32-59页。本文选择将北宋中后期分为两个时间段进行考察,则是基于两者具有时间连续性且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战略透支,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我们对于前文因果机制的信心的考虑。①但本文并不否认这样做的弊端,即:相互连接的历史中出现相似机制的可能性很高,对于提高我们在更广阔的样本中出现类似机制的信心并没有太多帮助。之后的努力需要进一步挖掘是否在其他符合本文X-Y因果关系的样本中也存在相同机制。可能的案例包括魏晋时代蜀汉北伐扩张过程、隋朝远征高句丽的战略扩张行为、19世纪初欧洲拿破仑战争、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太平洋战争等等。
三、案例分析
宋辽鼎立时代是东亚地区少见的稳定的均势国际秩序,而最终两者均在新兴崛起国(女真)的挑战下走向败亡,两者衰亡的原因不尽相同,但都为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留下了许多谜团。②这是一种特殊现象,近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均势体系的瓦解与动荡往往是来自于体系内部,即原有均势体系内一方的实力上升与战略意图转变,但宋辽均势体系却是瓦解于体系外的新兴崛起国家得益于近年来宋代军政关系、宋王朝对辽夏关系等领域的史学进展,本文对于北宋中后期长达几十年拓边的战略行为进行案例研究,进而揭示北宋灭亡的大战略机理。
通过这一案例的详细考察,本文将证明北宋绝非亡于“积弱”亦或是金人勇武,而是在领袖的成就动机导致战略目标僵化的情况下出现了:(1)精英内部分裂导致的权力分散,从而出现信息不对称,进而战略手段没有得到调整、而使得战略手段低效;(2)精英外部分裂导致的战略手段逆转,以及完全放弃战略成果,从而使得前战略手段失效。在两种情况下最终患于战略透支的根本顽疾。
(一)北宋中后期战略透支的判定
首先,对于补偿缺损与长时段战略过程,北宋中期之后均符合这两点特征。北宋仁宗时期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整顿吏治,以及之后的英宗时期恢复武举、大量征集兵丁。但这一时期的北宋王朝已经开始出现与西夏的局部战争,虽然并未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且最终走向和解,但仍然造成了北宋国库的亏损。③苏辙曾指出当时情景:“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参见苏辙:《元祐会计录序》,《栾城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50页。
神宗继位后,一者为改变国库困窘境况,二者为实现帝王功业。从而开始谋求新政。神宗早期同时任用司马光与王安石来处理国家财政困窘问题,王安石认为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理财无法”,司马光则认为是“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显然,司马光的主张一语中的,神宗“上深开纳”。①司马光:《司马光集》卷39,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77页;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126页。而神宗急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其目的仍然是以强兵为主,富国不过是维持北宋国家机器运转的手段而已;因此,神宗皇帝最终选择了承诺通过理财实现富国强兵的王安石。王安石变法虽然为北宋充盈了国库,但是正如王夫之《宋论》中提到的“神宗之误,在于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安石用之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并且判断,北宋灭亡也正是从此开始。②“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可于此而决之矣。”参见王夫之:《宋论》卷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3页。由此可见,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神宗朝之前的透支问题,反而急于求成,通过“理财”来实现强兵拓边的战略。在北宋中后期的战略执行过程中,由于精英内部分裂导致的战略信息沟通不对称,从而使得战略手段没有及时得到调整,为此后战略手段的失效与资源浪费埋下祸根,使北宋战略透支问题愈演愈烈。在此后的高太后“以母改子”的短暂时期,王安石新法相继废除,但是这一时期的北宋出于精英外部分裂的党争,致使新法与拓边行为无论好坏、成果如何均遭到一刀切式的废除,而与此同时反对派精英却没有提出替代性举措,仅仅是与民休养,缓和了透支的进度,没有在根本上解决此前资源短缺的透支问题。而哲宗主政之后,又盲目的重新恢复王安石新法,并且再度开始大规模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这一时期的精英分裂更为复杂与严重,北宋深陷对外过度扩张与内政损耗所构成的战略透支的弊病。
其次在战略向度上,北宋早在太祖、太宗时期为恢复幽云地区就反复发动对辽战争,但早期宋王朝并没有一套开疆拓土的政策,其对外战争主要是出于巩固王朝边界的战略目的以及领袖个人偏好,因此只能算作零星的对外武力使用。北宋中后期的大战略是针对西夏形成的,北宋自神宗以降的国家对外战略基本是围绕着“拓边西北”展开的。由于自真宗朝确立“澶渊之盟”,宋辽之间鲜有军事摩擦;而在神宗继位后,北宋对外战略的重点就集中在了对于西北“河湟”地区的拓边上。相较于军事行动本身的意义,史学与军事学研究大都强调这一系列行为本身的政治与战略含义。①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绪论。北宋中后期正是在这样的对外大战略下,无法克服之前提及的补偿缺损的问题,从而深陷“战略透支”的泥潭。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北宋对西北地区的拓边是由跨越三代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所组成的,因此在后文中主要谈论历代构成“河湟开边”的战略行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内政党之争,并从中考察由于领袖的成就动机所导致的目标僵化、精英分裂所导致的手段失效/低效从而致使其行为失败的历史事实。
(二)第一阶段:神宗时期的过度扩张
由于宋朝在真宗、仁宗时代形成了稳定的外部和平局面,不同于宋初太祖、太宗时期的对辽战争,“澶渊之盟”后东亚地区形成了辽宋并立的权力格局,宋朝极力维持与辽对等关系,以及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和平局面。②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30页。但这项政策在神宗时代形成了极大转变,③在宋英宗时期已经出现局部对西夏的战争,大部分是范仲淹与韩琦所主导的小规模战役,而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神宗皇帝经略西北,力求收复河湟、攻克西夏,在根本上扭转宋辽并立局面;从而完成恢复“汉唐旧境”的壮举。
真宗、仁宗与英宗三代,长期的和平局面为神宗皇帝的扩边行为奠定了稳定的国内基础。在神宗皇帝继位后选择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谋求通过国内改革来增强国家实力、支持对外战争。其中主要的经济改革与军事改革相互匹配,为增加政府收入以及增强边防军备提供了有效的战略保证。诸如市易法、将兵法等等制度最早均是为了服务于西北拓边战略而开发的。
但在此中,部分措施实际上存在战略隐患,而精英的内部分歧与外部分歧叠现。在改革派主政前提下,内部不辨真伪地打压其他意见致使决策集团并未收到真实有效的信息,盲目地推进其所构想的开边设市的战略手段,虽然拓边行为收获了良好的收益,但维持边地却加重了北宋的经济负担。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神宗即位,英宗时期已有的拓边主战派看到了希望。①韩琦最早提出使用武力拓边、收复故土,但英宗皇帝并不倾向在边境动武,因此作罢。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二、卷二〇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在神宗皇帝的秘密支持下,陕西地区的种谔、薛向招降横山豪酋嵬名山,并且进占绥州城,引发了宋夏之间的战争。②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页。司马光记载“向者干进之士说先帝以征伐四夷,开边拓土之策”也佐证了这一时期的宋朝战略出现转变。③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页。准确地说,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平戎策》的出现是北宋对外战略关键转折点。王韶上书神宗,其中提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史称“神宗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④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八《列传第八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79页。这一战略观点支撑了神宗一朝对西夏的总体战略方针,也成为之后北宋大战略的基本原点。
而宋神宗的成就动机也在治平四年的时候就可见一斑。为扭转长期以来北宋北部边防的被动僵局,其刚刚即位便下诏访询“边防戎事之得失”,⑤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帝系9之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并且明确表明“慨然欲更张之”的态度,⑥徐松辑:《宋会要辑稿》1之7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8页。《宋史》中则明确表明其上位伊始“励精图治,将大有为”,⑦脱脱,《宋史》卷十六《神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4页。并且神宗于熙宁元年先后召见富弼、范纯仁等询问边关军备,⑧脱脱,《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55页;卷三一四《范纯仁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83页。又有记载宋神宗诗句:“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⑨脱脱,《宋史》卷一六五《太府寺》,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08页。由此可见神宗皇帝的对于开边拓土成就的渴求。北宋神宗时代盛行的“汉唐旧疆”的政治话语则进一步促进了神宗时代“拓边西北”的战略目标形成。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对于幽云地区以及更为广阔的汉唐时代疆域就表现出强烈的求索感,⑩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载《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24-39页。宋真宗就曾指出“幽蓟之地,实为我疆,尚隔混同,所宜开拓”,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31页。而在真宗、仁宗、英宗时期对于河湟地区封以藩镇名号,明确认为其属于“汉唐旧疆”。②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载《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25-29页。在神宗朝之前,河湟地区、吐蕃、幽云地区以及交趾等地区都被宋王朝认为是“汉唐旧疆”,且一直存在于北宋对外战略的讨论范围内,长期被认为是应当恢复的地区。宋神宗个人表现出对成就的渴求以及长久以来的宋辽、宋夏关系不满,在“复汉唐旧境”的战略文化与话语框定以及王韶《平戎策》的启发下形成了清晰的战略目标:即攻克西北,通过控制吐蕃与西夏之间的河湟地带,打击甚至是攻灭西夏,从而在西北形成对辽战略部署,扭转长期以来的被动防御局面。③此战略目标与王安石变法息息相关,王安石变法中市易法的出台便是最早直接服务西北拓边战略的执行。参见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第3-14页。
熙河之役前王韶提出“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④脱脱:《宋史》卷三二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79-10580页。《宋史》卷一七六,第4276页。这是王韶主张神宗可以进行熙河战争的主要前提,由于西北地区本身可耕种地区较少,因此在以往战略规划中西北地区向来被视为蛮荒之地、攻克之后也难于坚守的地带,所以庆历年间韩琦、范仲淹西北拓边艰难万分,只能在部分关键寨垒据守。而王韶的进言则让神宗皇帝确信西北地区的拓边行为的收益是稳固的,而王安石等改革派为证明新法切实可以富国强兵,也选择支持这一提议。王韶开边河湟的战略构想是利用西北地区万亩良田养兵备战,即通过市易法来聚拢商贾,从而使得汉人聚集来耕种土地,从而保证军需,来稳固拓边西北地区的战略收益。在神宗与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开始进行熙河战役,王韶确实完成了西北拓边的目的,也带给神宗巨大的成就功业。据记载熙宁五年(1072年),“帝志复河、陇,筑古渭为通远军,以韶知军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罗角、抹耳水巴等族。……径趣抹邦山,压敌军而阵,……洮西大震,……复击走瞎征,降其部落二万。更名镇洮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远为一路,韶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神宗皇帝也由于“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所服玉带赐之。”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22页。
但王韶的构想显然是空洞的,首先是河湟地区当时并没有良田万顷无人耕种的局面,而这一信息则由于精英分裂并没有上传到领导者,史书记载“经略使李师中言:‘韶乃欲指占极边弓箭手地耳,又将移市易司于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补所亡。’王安石主韶议,为罢师中,以窦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实。若愚至,问田所在,韶不能对。舜卿检索,仅得地一顷,既地主有讼,又归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为罢舜卿而命韩缜。缜遂附会实其事,师中、舜卿皆坐谪,而韶为太子中允、秘阁校理。”①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八《列传第八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79-10580页。李师中时任王韶的上司,也是最初支持王韶拓边倡议的一方,双方仅在是否设立市易司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却引发改革派精英内部的分歧,直至将其罢免。这一现象表明,在改革派精英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王安石为维系王韶倡议,不惜先后罢免李师中、李若愚以及将帅郭逵,而选择韩缜来欺瞒附会。关于在秦州是否设立市易司的问题上,新旧两党也相互攻讦,形成了明显的外部分裂。以至于对王韶提出反对意见者,无论是否属实,均会受到王安石的贬谪,文彦博直言“王安石不知边事”,要求罢免王韶,但最终也不了了之。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52-5458页。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也形成了精英的外部分裂,大量关于是否适合在秦州设立市易司的关键信息无法送抵最高决策者,盲目相信王韶对于西北拓边的可行性评判,这也为熙河战役之后北宋出现战略资源大量浪费埋下了伏笔。
在熙河战役之后,在熙河路地区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央管辖下的政权几乎是妄谈,宋军对于这一地区的占领没有任何的社会性基础,只能依赖于营寨与军事壁垒,军事供给上依赖于中央政权对于这一地区的定向资源支持。熙河地区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不断对于北宋仅有的几座城池进行骚扰,而木征、董毡等面对暴露杀人侵地目的的北宋军队也选择投靠西夏、不断骚扰熙河路。而在军费供给上,“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人,军食皆仰给他道。”③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八《列传第八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81页。“自开建熙河,岁费四百万缗”,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71页。由此可见,熙河拓边行为实际上加重了北宋的军费开支,而北宋为保证这一新扩疆土,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固。直至熙宁十年(1077年)董毡归降之后,熙河路才逐渐趋于稳定,但仍旧使北宋面临严重的资源缺口。
熙河拓边在精英内部分裂的情况下,形成了信息的不对称现象,战略手段建立在虚无的信息之上,因此即便这一时期的拓边行为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却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且使得武力拓边战略手段行为失去了原本预想的战略效力,而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又使得北宋需要投放大量战略资源在熙河路的巩固上。这一现实也印证了我们的第一个预期。不可忽视的是:明显的战略透支问题已经在北宋王朝出现。
在国内与之相匹配的经济改革中,也出现了官僚之间各自为政的精英分裂,内部分裂造成的改革派内部信息沟通不对称,王安石变法措施建立与现实脱轨的构想之上;外部分裂则致使保守派对于改革措施的疯狂反击,严重迟滞与动摇了国内匹配的战略手段。
熙宁七年(1074年)全面推行市易法、免行法之后,受到统治阶级与保守派的反对,而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反对与分歧的声音。其中改革派主将曾布、魏继宗(后者是最早创立市易法的改革派)攻击推行免行法的市易司。①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这一行为本身是由于改革派内部关于改革方案的分歧,但内部并未做到相应的沟通与协商,使得变法措施本身的弊端演变成为废立二分的选择。此后王安石去相,推荐吕惠卿之后,昔日的改革派主将吕惠卿为着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提拔和任用自己的亲族和亲信。另一方面又打击与己政见相异的士大夫、排斥异己。②张祥浩,《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再探讨》,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43-46页。诸如本就与现实情况相违背的“手实法”、“以田募役法”,吕惠卿为取悦神宗,一意孤行推行出去。③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34页。致使“朝廷纲纪几于烦乱,天下之人复思荆公”。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336页。而此间曾布与吕惠卿之间也发生了分歧,一度出现神宗不得不居中调停的局面。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159页。改革手段在吕惠卿时代成为把控朝政、打压异己的途径,而改革派精英内部的分裂也使得国家新法这一战略手段震荡不止。由此可见,改革派精英内部并未做到“勠力同心”,反而愈发深化的分裂造成了的内耗损害了改革战略手段的有效性。
此后,神宗皇帝在亲自主持变法时期同时启用改革派王珪以及保守派吴充来平衡新旧两党,以期保证改革成果并且减少保守派的阻力。但是在这一时期北宋对外大战略的目标并未改变,仍旧是通过国内改革富国强兵的同时对外积极扩张。这一时期神宗主动出击交趾与西夏,寻求进一步扩宽北宋边疆地区控制范畴。由于神宗的坚持,保守派等外部精英并未对此后的西北拓边再行干涉,但是却出现了主战派精英内部的分歧,元丰四年(1081年)北宋宋再起五路攻伐西夏进行西北拓边。①五路征伐行动是北宋王朝武功达到最盛的一次代表性军事活动,在北宋“将从中御”的体制下,主要将领并不能左右战局,而是只能按原有部署行动。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则出现了明显的精英内部分裂:在出征后不久,就发生了将帅不睦的情况,致使五路大军并没有按照预定战略进行军事行动。②[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199页。而随后的永乐城战役,则是神宗朝最后一场对西夏的战役,发生于兴灵战役之后一年,因此也属于兴灵战役的一部分,但正是这场战役彻底地暴露了神宗朝严重的战略透支,神宗皇帝也因此一蹶不振,骤然早逝。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672页;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6页。由此可见,离开了改革派的神宗仍然对于扩疆具有强有力的执着,其个人的成就动机是北宋对外扩张战略目标长期固定的主要原因。这也印证了我们的第二个预期。
总的来说,北宋通过王安石变法以及王韶拓边两个相互匹配的战略手段实现了西北拓边部分战略目标。直至熙宁九年,王安石改革中各项新法所得现钱共计2700万余贯,而其中有高于1500万贯储存于沿边军事重镇,用于维持军费开支与市场经济。④朱舸:《北宋社会经济的再认识》,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第171-173页。由此可见前者通过改革国内农业经济与市场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略资源的积累,为后者在西北与神宗后期在交趾与西夏的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在现实案例中我们也发现,精英内部与外部分歧导致的信息沟通不对称以及战略手段摇晃十分明显,而这也进一步损害了北宋大战略执行;在神宗皇帝强烈的成就动机驱使下,北宋对外战略目标固定甚至是僵化于富国强兵、对外扩张之上。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之下,北宋在西北地区投入了大量的战略资源,但收效甚微,仅仅是拓宽了熙河一路的控制范畴以及周边军事重镇。而长期的对西北地区扩张使得国家与地方经济疲惫不堪,史料记载陕西地区“自军兴以来,关内人情震惮,多全室逃亡”。①徐松:《宋会要辑稿》官职5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562页;食货70,第8316页。而反复扩张行为也亏损了北宋军事实力,“昨来西师入界,及永乐覆没,官兵、民夫及赍送之人,冻饿而死亡者,无虑数十万。”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108页。
神宗朝就此深陷与过度扩张所导致的战略透支之中。而这无疑是在领袖的成就动机人格所主导的战略目标规划下,由于精英内部分裂而导致的战略手段的低效甚至失效所导致的;神宗朝原本由王安石变法所带来的战略资源的积累也难以弥补战略手段掉所带来的浪费,由此便出现了严重的战略透支。
(三)第二阶段:元祐更化
神宗朝后经历了两代政权实质性更迭,一是由高太后主持的元祐时代,二是哲宗主政之后的时期。这一时期北宋对于西北拓边的战略手段做出了更为强烈的反复调整,而在西北拓边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这样的反复调整无疑加增了战略资源的浪费,最终深陷战略透支,更使得随后的徽宗、钦宗时代的宋王朝业已难以扭转这一困境,最终走向败亡。首先是元祐更化时期,由于精英外部分裂致使战略手段出现巨大动荡,战略妥协与退让成为主流,严重的外部分裂甚至使得神宗时代的战略成果尽数被抛弃、荡然无存。神宗在永乐之战后郁郁而终,年少的宋哲宗继位后则由高太后把持朝政,其任用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反对派,废除新法并且转变对西夏政策,史称“元祐更化”。保守派为贬低王安石变法所取得的成就,故而大多支持完全放弃西北新拓的熙河地区。需要说明的是,纵使熙宁、元丰时代的宋夏战争功败垂成,但宋王朝仍然获得了熙河地带、兰州、米脂、葭芦寨等关键堡寨的实际控制,从而可以直接威胁灵州以及西夏首府兴庆府,西夏也在元丰年间的战争中苟延残喘,也已经是奄奄待毙的状态。③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3页。因此即便我们认为神宗朝出现了战略透支的困弊,但是其西北拓边的战略仍有很大的收益。④感谢匿名评审指出这一问题:如果神宗没有早逝,是否北宋可以在后续完成富国强兵与拓边的大战略,并且转而实现战略收缩,从而避免长期的透支问题?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进行反事实推理。
而司马光上台后摒弃了所有的王安石新政,保守派“务要罢尽一切新法”的主张甚嚣尘上。①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诸如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在熙宁、元丰年间极大扩充了府库财源的战略措施均遭到废除;并且保守派对于改革派进行了疯狂打压,蔡确、章惇等改革元老为维护新法与司马光进行辩驳,但却被保守派指责为“言虽近公,意则非正”,②关于元祐年间旧党对于变法派的打压,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92-8933页。最终被罢免,精英外部分裂以至于“一人茕立于上,百尹类从于下,尚恶得谓元祐之犹有君,宋之犹有国也!”。③《宋论》,卷七哲宗。而废除新法造成的影响相当广泛,苏轼、苏辙等都指出新法中的部分法令需要维持,以避免国家战略与秩序动荡,但司马光一意孤行,正如范纯仁所说其“宁欲扰民”,也要罢免新法。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39页。苏轼则指责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⑤苏轼:《苏东坡全集·奏议卷》卷三《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91-792页。保守派的反扑摧毁了熙宁新法,但却并未提出改善国家财政与战略资源积累的手段,甚至实行“五年并增法”来增加税收,以至于税收过高“岁课不登”的局面,⑥保守派对新法的废除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017-10032页。这一时期事实上并未改变北宋战略透支的弊病。
此后,由于1085年之前宋朝在熙州、兰州、米脂等地军费高达三百七十余万,长期的军费来自于青苗法、助役法等新法筹措,新法的废止也使得这项军费归结于坊场等原有的财政支出之上,国家财政陷入困局。新旧党争的精英对立、边境新疆土长期入不敷出的现状使得旧党意图放弃新得疆土,这也引发了元祐年间最大的一次关于对夏政策的辩论。⑦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57页。由于旧党当政,这次辩论几乎没有任何支持继续拓边的声音,而是围绕如何消弭战火、与夏交好展开的,其中关于神宗朝所得西北疆域归属的争辩尤为激烈。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也并没有人否定神宗朝“拓边西北、开拓河湟”的战略目标,而是仅仅在现实条件下主张暂时停止战争。
对于西北新得疆域的归属,司马光、文彦博等主张放弃所有新得疆域,①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三五,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0-384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18-8848页。此时宋朝内部形成两派,处在两难境地,但在高太后与旧党的主导下,认为“弃地议和”最为妥当,②相关参见李华瑞,《论宋哲宗元枯时期对西夏的政策》,载《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第145-149页。仅有孙陆、安焘、穆衍直言放弃领土与达成和平并无必然关系,反而是放弃这些领土将使宋朝在之后对夏战争中处于不利局面。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八,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890-7912;卷三八二,第9298-9322页。
最终元祐四年(1089年)宋朝决定放弃米脂、葭芦、安疆、浮图四处营寨,而保留兰州;宋朝要求西夏遣返战俘,并且花费大量金帛来赎回。④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0页。这一政策看似折中,实则是对神宗朝仅有的战略收益丢弃。这虽然某种程度上减缓了北宋因过度扩张出现的战略透支,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困窘。由此可见精英外部分裂致使的国家战略手段剧烈震荡,使得原本的大战略收益亏损殆尽,几致出现了“成本-收益”两个维度上均处于净损失状态。这也佐证了我们在之前的预期3。
在哲宗绍圣亲政之后,元祐时期放弃边疆地区由于与兰州等地区的边界不明确,加之哲宗继承神宗遗志重拾熙宁时期富国强兵与拓边大战略,元祐更化的对外政策实际上为之后宋夏战争埋下了祸根。这些原本已经消耗大量战略资源获得的地理战略优势,此时一经放弃,在哲宗时代又需要重新动用武力去夺回。
(四)第三阶段:哲宗主政后的重新拓边
北宋晚年的主要对外战略体现则是绍圣时代的重新拓边行为。元祐更化之后,哲宗亲政,其也表现出对于成就的极度渴求。这一点直接体现在其年号更替上,“绍圣”宋时语义指“绍述”,即“遵照先贤之道”。在宋时高级官员私人笔记中记载了哲宗得知神宗功败垂成、郁郁而终后的伤痛。⑤王铚:《默记》卷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哲宗继承神宗遗志,重新启用章惇、吕惠卿等新党,重新谋划进行西北拓边与对夏战争。⑥宋哲宗同时肃清了元祐旧党,并对于元祐年间的“弃地弥和”深恶痛绝。参见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265页。宋哲宗更是直言“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①脱脱:《宋史》卷四七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11页。
绍圣元年(1094年),北宋与西夏之间关于西北地区的领土谈判还在进行当中,因此哲宗并没有直接动用武力。次年,西夏斩杀北宋使者,哲宗旋即召回宋朝代表,恢复宋夏战争。绍圣三年(1097年),宋朝在鄜延路抵挡了大量的西夏军队进攻,与此同时钟传与王文郁进筑西城,孙路进筑安疆寨(此前元祐时期放弃的堡寨),哲宗时期的对夏全面战争开始。直至元符二年底,西夏遣使求和,并在宋进筑的地区重新界定疆界为止,北宋以全胜的战绩完成了绍圣元符开边的活动。但是朝廷为支援宋夏战争拨付的钱物仍不少,据记载,绍圣三年(1096年),出元丰库缗钱四百万于陕西。②苏辙:《栾城后集》收支叙,载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五,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12-713页。哲宗时期对西夏作战耗费了战略资源,为重新取得对夏战略优势地位,宋廷连下五敕,将诸路封桩钱物的大部分调往西部边境充军费,即所谓“天下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运之于西边。”③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1页。
这一时期精英分裂也愈发剧烈,即便哲宗皇帝重新启用曾布、章惇、吕惠卿等熙宁年间的主要改革派成员,但其内部仍旧存在严重的分歧,诸如曾布出任知枢密院事主管军事改革与章惇存在严重分歧、近乎貌合神离,重新恢复新法也在不断的内部分裂中踽踽独行。④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261页。而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外部分裂也仍旧明显,绍圣年间吕大防、范祖禹等相继被罢免,甚至并算不上保守派的苏轼也因故获罪。哲宗亲政进行“绍述”神宗未竟的大战略,但改革派忙于打压异己与热衷权位,并非北宋富国强兵与对外扩张的大战略。精英的外部分裂使得北宋国内改革与对外扩张的战略手段几近扭曲成为相互攻伐的工具,这严重影响了政局改善以及重新执行熙宁大战略的进程。⑤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266页。
从元祐年间的精英外部分裂后反对派的上台,战略手段逆转成为战略退让,损耗了原本的战略优势的同时也浪费了神宗一朝长期的战略资源投入。而宋哲宗绍圣年间的重新开边又不得不重新投入新的战略资源以求获得在西北地区的战略优势与主动权,这就与前一阶段共同佐证了前文对于精英外部分裂引发战略手段失效的预期3。并且绍圣时期改革派复辟后的行为进一步证实了精英分裂对于战略手段的影响;哲宗亲政后,战略手段的波动与目标的僵化使得北宋这一国家机器再一次颠倒重来,战略透支问题则在政局的汹涌波涛之下由神宗时期的“病在肠胃”发展至“今在骨髓”。
总的来看,北宋中后期三代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相对固定,但反复推倒重来的战略手段造成了长时间的战略停滞与资源浪费,原本在短期内通过部分战略透支即可完成的战略目标反而成为穷年累月的跋涉,最终成为北宋积重难返的痼疾,由此也证实了前文中第4个预期。
事实上,在元符三年哲宗病逝之后,宋徽宗并未终止北宋对夏战争。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褒扬神宗“中国强而蒸民乂,边鄙辟而狄戎威”,以及想要实现“声教暨乎遐荒,威武畅乎无外”的追求和“殊乡异域,请命下吏,继其武也”的动机。徽宗时期则是出现了王厚、童贯、蔡京与章楶等精英间相互争斗,围绕变法展开的新旧党争演变为争权夺利的派系纷争,并且主战与主和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的局面。徽宗时期虽并未进行大规模拓边,但其借立新法与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为由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引发了包括方腊、宋江在内的多次农民起义。这一时期的北宋已经再无战略转圜的余地,僵化的战略目标成为不切实际的战略虚幻,精英纷争演变为争权夺利,北宋最终深深陷在国家崩溃的边缘、战略透支的泥潭之中。
(五)案例讨论与替代性解释的排除
宋朝中后期,中央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宋王朝的拓边加重了民众负担,近40余年对西北等边疆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此时社会危机也伴随着财政危机开始出现。北宋富国强兵与对外扩张的战略目的最终没有实现,反而是极具成就动机的领袖使得这一目标近乎僵化,而精英分裂造成的大战略手段震荡与失效,致使北宋“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最终在哲宗时期形成了“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为然矣。”①王夫之:《宋论》卷七哲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29页。
历史往往是特殊的、复杂的。必须承认在北宋衰亡的历史进程中存在诸多复杂因素与偶然性;北宋中后期大战略是一个整体而复杂的交互系统,其中领袖与精英的主体能动性在此战略执行中的作用尤为明显,这些因素在此中是必然的、并且与北宋衰亡有着紧密的联系。
通过上文的个案内过程追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案例内证据支持本文所提出的理论逻辑。需要说明的是,案例内经验活动的具体表现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机制内系统部件有所差异,比如也存在精英外部分裂致使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但总体而言,案例支持了前文的因果机制。
下面我们就基于贝叶斯逻辑对于该理论机制进行讨论,排除其他可能对于本文案例的理论解释,并对于部分偶然因素进行反事实推理,从而评估这一机制实现跨个案因果推断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基于文献回顾中所提及的理论视角来认识北宋王朝对外扩张导致的战略透支行为,我们会预期出现以下几种可能的现实:
1.现实主义视角中:无政府体系下,宋王朝的安全需求难以满足,因此走向对外扩展战略,并且基于对于权力的需求选择不断地进行扩张从而引发了战略透支。这种解释很明显无法解释北宋中后期这一案例,宋辽“澶渊之盟”后长期维持和平关系,宋王朝很明显不存在安全的稀缺;此外,现有史料证明在宋辽东亚均势体系下,北宋中后期的西北扩张行为也并没有受到辽王朝的制衡。
2.认知主义的维度下:理论预期,宋朝决策者会出现错误归因、认知一致等错误知觉。这一解释对于本文案例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度,因为北宋的战略透支与衰亡在某种程度上与宋神宗早期缺乏军事经验、无法知人善任、对外部环境存在错误认知有着直接关系。但我们无法判断北宋统治者或决策集团是否对于西北拓边具有归因偏差或错误认知,就现实情况来看,无论是战略目标的制定(王韶《平戎策》中的战略思路)还是战略手段(武力拓边,筑城推进)都是合理的。即便是错误认知的解释是成立的,但是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哲宗上台之后并没有更正原有的战略目标或手段?为何原有的错误认知没有在元祐时代得到更正?以及是否元祐更化时代也存在另一种错误认知从而导致放弃已获得的战略收益?
3.基于国内政治的维度,本文在此考察三种解释:帝国主义论、斯奈德联盟政治论以及布劳利路径依赖论。
帝国主义论将预期北宋内部的利益集团将挟持国家进行对外过度扩张,这一解释途径明显不适用于本文案例,北宋中后期内部非但没有单一利益集团完全把控朝政,反而是出现了大范围党争与利益集团间的争端。尽管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新旧两党在不同时期对于国家政策的把持是符合这一预期的,但历史现实并不支持其促使了北宋的对外扩张行为这一逻辑,因为通过历史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北宋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因并非来自新旧两党,而是来自于领袖个人心理动机。值得反思的是,与常识不同,北宋案例中精英分裂并未扭转战略透支的进程,反而精英内耗加重了北宋的战略负担。
其次是斯奈德联盟政治与“帝国迷思”的视角预期宋王朝内部会出现利益集团的相互联盟勾结情况,为了克服单一利益集团势单力薄,其将会形成互助联盟,从而推行一种更具扩张性的对外扩张战略。但事实是北宋中后期内部党争相对激烈,并不存在一个或者几个互助联盟;并且北宋对西北扩张的战略目的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也并不符合“进攻有利”或“纸老虎”等帝国迷思的界定。而斯奈德论述联盟政治理论在单一寡头政体中的验证情况时,其使用了明治日本、希特勒德国以及斯大林与赫鲁晓夫苏联三个案例,并且也承认联盟政治在解释其中现实情况时出现了偏差。其预期单一寡头政体中不存在任何单一政党、部门或局部的利益可以在对外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寡头在避免过度扩张的成本方面具有统括性利益,因此会积极避免过度扩张,从而制约了战略行为中的冒险性,减少了代价高昂的扩张政策的出现。但在本文中无论是之前的仁宗时代,还是神宗与哲宗两朝都并未出现领袖个体为规避成本高昂而选择抑制扩张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案例中也出现了类似民主政体中的相互制衡的国内利益行为体,但国内精英的相互制衡并未使得北宋选择相对克制,反而由此引发了战略手段的动荡,造成了战略资源的浪费,加深了北宋王朝的战略透支。
最后,在布劳利“余晖效应”的视角下:王朝官僚政治的延续使得战略措施不会调整(布劳利“余晖效应”视角)。这种解释同样不适用于解释北宋中后期西北拓边行为引发的战略透支。元祐更化时期,由于精英外部分裂、反对派精英的上台,北宋出现了明显的战略手段调整,并且对于前者战略手段与成效尽数废除与放弃;而在之后则出现了哲宗重拾拓边战略。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案例也并未证伪这一理论,因为北宋中后期的历史现实并不符合布劳利对于官僚政治延续的命题。
另外,针对本文所提出的案例,还需对是否为偶然因素所导致“战略透支”的结果进行简要的反事实推理,从而排除本文中战略手段的动荡是由于“帝位更迭”(如神宗、哲宗的早逝)“以母改子”(高太后垂帘听政)等偶然因素所导致的。①本文在此仅进行简要的推理,而不做过多的分析;关于国际关系中反事实推理的研究与运用可以参见 Frank P.Harvey,Explaining the Iraq War:CounterfacturalTheory,Logic and Evid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张波,张嘉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反事实推理法》,载《理论探讨》2015年第6期,第170-173页;牛长振:《国际关系中的情景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3期,第61-83页。即神宗没有早亡与高太后没有以母改子的情况。这一情况相对复杂,因为在河湟拓边后期北宋经历了一系列军事失败,使得神宗晚年身心俱损、无心边事,“于是亦息意征伐矣”。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〇,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945页;卷三五三,第8457页。由此可见,神宗如果没有早亡,其有极大可能放缓甚至停止西北拓边的战略;这一点早在王夫之《宋论》中业已提到,“使神宗有汉武之年,其崩不速,则轮台之诏,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谏。盖否极而倾,天之所必动,无待人也。几已见矣,势已移矣。”③王夫之:《宋论》卷7,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03页。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反事实推理在明清时期的史评中多有出现。关于汉武帝时期的战略透支与调整的研究,参见陈拯:《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27-49页。而是否会出现高太后时期的“全盘废止”的战略手段剧烈动荡则是另一个问题。神宗逝世后,元丰年间一直被打压的元老旧党纷纷跳上舞台,极力鼓吹祖宗之法以及重文抑武的传统国策,对于变法一派的人物疯狂打压,并且要求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事实上,神宗的早逝与高太后当政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契机,精英集团间对于拓边行为的分歧借助这样一个契机所表现出来,即为打压对手集团而彻底决裂、放弃客观判断标准。及至哲宗主政之后亦是因此翻倒重来。由此可见,战略手段的动荡是由于长期积压的精英分裂所导致的,而并非帝王早逝等偶然因素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的早逝确实使得潜在意义上的战略收缩可能并没有成为现实。
至此,本文案例已经排斥了很大部分的既有解释,尽管无法排斥全部的既有理论,但多数是由于理论前提的限制以及案例本身缺憾。所以在进行有限的过程追踪后,提高了对于本文提出的因果机制存在的信心。而对于更广阔的其他样本,本文同样抱有信心。首先是本文案例已经足以证明这一因果机制的运行是可能的,因此在其他样本中出现相同的变项与机制时,也会有可能出现战略透支这一现象。其次,本文关于战略透支的概念界定,延续了既有研究中关于“收益于资源投入相匹配”的核心,而造成资源消耗成本过高的原因并不一定是投入过高,还有可能是浪费过度,因此在其他出现这一机制的案例中,有大概率也会出现收益与投入不相匹配的现象,因此战略透支的结局便是可能的。
针对本文的特殊案例,历史学的既有研究中也有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北宋衰亡的结局,如北宋官僚与军事制度、重文抑武的传统国策、积弱的社会风气等等。本文提出的因果机制并未讨论其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互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北宋复杂的内外环境以及另类的国家建构途径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领袖个体偏好以及精英关系。众所周知,两宋相对于与汉唐时代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历史转变,可能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帝国版图局限性等都称得上是特例;宋王朝在这一环境下形成了异于汉唐时代的国家文化环境,而正是在这一文化环境内滋养了“强干弱枝”“重文抑武”等宋王朝的特色;而这也进一步通过政治精英与领袖左右了国家战略偏好与选择。
四、结论
国际关系学与战略研究中,战略透支往往被用来讨论霸权国或崛起国的衰落或战略失败的过程。对于战略透支形成的原因也多有研究成果,但大多数研究或聚焦于体系的限制、或从中观视角出发讨论国内政治的统一性对于国家的挟持、抑或从微观视角来解释决策失误的可能,而没有关注到即便在国际体系相对稳定、国内政治缺失一致性的情况下,国家仍有可能出现战略透支现象。
本文首先回顾了既有研究中对于战略透支形成的既有解释,并且结合既有界定对于战略透支给出了三个维度的表现特征。通过选择国内政治范畴下的精英分裂与领袖的成就动机人格而构建起了一套关于诱发战略透支的因果机制,并且给出了相关的中间环节与可检验的假设。此后选择了该机制存在的先验概率较低的中后期北宋这一特殊的前现代国家案例,并且使用过程追踪法进行案例分析,来发现其是否符合我们最初的预期,从而提高了我们对于这一因果机制存在的信心。
本文提出的因果机制在当代世界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国家在多元体系背景下均有可能出现过度扩张与战略透支现象,无论是均势体系、霸权体系抑或是“崛起-霸权”关系中均有相关的历史现实。北宋这一前现代国家在均势体系下由于国内政治因素所致使的战略透支,与其说是一种特例,更是一种必然;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北宋追求富国强兵与对外扩张从一开始或许就注定是以悲剧结局收尾:神宗励精图治,虽然出现短期的战略透支,但或许可以通过后期调整与收缩得到缓解,但颉颃龃龉的精英分裂模糊了国家战略的本意,领袖强烈的成就动机使得战略目标走向固步自封的僵化,最终造成了北宋王朝晚期行将就木的悲剧。对于当代中国外交而言,则需要警惕切勿出现战略手段的反复不定,而使得原有战略手段失效,进而陷入战略资源投入流失的循环。中国外交应当在谨慎、理性的基础上制定战略的同时,提高战略执行力度,避免战略资源的浪费。即便出现短期的战略透支,在可接受的程度下也应当保持战略一致性,从而保证可以避免手段反复不定造成的资源浪费;只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身战略目标并在之后进行及时调整,就可以避免国家长期陷于战略透支而诱发其他危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