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元稹《行宫》
2021-07-16黄天骥
黄天骥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
——元稹《行宫》
在中唐,诗坛名声最大的,自然是白居易。而在当时,能与白居易齐名的,则是元稹。
元稹和白居易诗风接近,被称为“元白体”。他俩是好朋友,据白居易在元稹墓志里说,当时元稹的诗轰动海内外:“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白居易的话,未必是夸大的。据说唐穆宗当太子时,知道妃嫔们都会念元稹的诗,后来当上了皇帝,又看到了他写的《连昌宫词》和其他的一百多首诗,“大悦,问稹安在”,当得知元稹“今为南宫散郎”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六)。看来,元稹的诗作,竟流传进内宫,而且成为他升官的垫脚石,足见影响之大之广。
元稹,字微之,一生写了许多诗,他告诉白居易,从十六岁开始,到三十三岁时,已有诗八百余首。在《全唐诗》里,存诗二十八卷,数量不可谓不多。但说实在话,他真正写得好,到现在还被传诵的诗,并不算多。
在文学史上,元稹真正备受赞扬的,是他悼念亡妻的《遣悲怀》三首和《离思》(其四)。那“贫贱夫妻百事哀”和“曾经沧海难为水”之句,到如今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言。

元稹像
除了这几首写得情真意切的诗外,他受到诗坛瞩目的就是长诗《连昌宫词》,以及短诗《行宫》了。这两首诗均抒写唐玄宗旧事,具有咏史性质。而在这同属一个题材、一长一短的两首诗中,又以只有四句区区二十个字的《行宫》最受人嘉许。清代诗评家潘德舆甚至认为:“‘寥落古行宫二十字,足赅《连昌宫词》六百余字,尤为妙境。”(《养一斋诗话》)这话没有错,《行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平的确高于《连昌宫词》。
为什么《行宫》这首短诗,竟有此扛鼎之力,这值得我们仔细探讨。
元稹生活的年代,正是在安史乱后。那时李唐王朝侥幸站稳了脚跟,却又一落千丈,无法恢复过去的辉煌。包括唐肃宗在内,后续的几任帝王,即使有些人想有所作为,却又一筹莫展。更多的皇子皇孙,或是疯狂享乐,或是庸碌无能,唐室无日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军阀割据、人民困苦,构成了整个中、晚唐险恶的环境。党派内讧、边患窜扰的状态,也像梦魇般压抑在人们的心头。整个统治集团包括许多士大夫,或惶惶终日,或竭力搜刮。然而,也有不少来自下层的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窳败和人民生活困苦,当他们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以后,和一些希望稳定整个王朝利益的政治集团联合起来,力图有所改革,特别是期望削弱贵族特权阶层的势力。这一来,整个中、晚唐时期,改良派的士大夫和以宦官为代表的特权集团的斗争,从未中断过。
元稹出身贫寒,据他对皇帝说:“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兄母乞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同州刺史谢上表》)后来,他入榜科举,得到赏识,当了几任地方官,并在朝廷任过要职,官至尚书左丞。他也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在诗歌中写道:“强豪富酒肉,穷独无刍薪,俱由案牍吏,无乃移祸屯。”(《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在政治上,他有改革的追求,但也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常被名缰利锁。他有正直的一面,狠切地揭露过宦官的罪行,于是被罢被贬;有时,则又依附宦官,由此得到升迁。你说他很虚伪吗?却不是,因为无论对宦官是攻击还是依赖,他都是真心实意的,还自以为是在为朝廷做好事!这情况,和他对待婚恋问题的态度一模一样。他的确深情地爱着妻子韦氏,所以,韦氏亡后,他能写出感人肺腑的《遣悲怀》。而转眼间,甚至在娶妻之前、妻在之时,又爱上了别的女子,制造了不少绯闻。我认为他深爱韦氏,完全出于真心,但是深情和专情,在他完全是两回事,何况在当时一夫多妻是合法的。而且士子为了改变命运,抛弃糟糠、攀附高门的婚恋行为,在法理上也被认为是情有可原的。总之,元稹的行为,仕宦是如此,婚恋亦如此。他的性格和表现,实际上反映出中、晚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与动摇性。

《行宫》一诗,是元稹在元和四年(809)写成的。那时他正在洛阳当监察御史。唐王朝在洛阳所建的行宫,名为上阳宫。元稹在《行宫》里所说的“古行宫”,指的就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诗的最后一句,还直接点了唐穆宗老祖宗唐玄宗的名,抒发了一番对世事和兴亡的感慨。
在封建时代,许多王朝规定,在文艺作品中不准涉及本朝皇帝的事情,不准提及本朝皇帝名字以及出現其形象,否则要受到极为严酷的惩罚。后来明成祖还规定,“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岂止不准刊行,“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不过在中、晚唐倒是例外,人们可以直接谈论本朝皇帝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种种得失,甚至还可以公开谴责。像元稹在《胡旋女》里就说过:“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可见唐代人对当朝先帝的批评,无所忌讳。所以当唐穆宗读到元稹狠批他老祖宗的《连昌宫词》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立即给他加官晋爵,让他能自称“今日俸钱过十万”了。
我认为唐王朝之所以如此开放,究其原因是儒道佛三教分立;儒家的思想,不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人们包括封建集团的最高统治者,都认识到当下危机重重,感知到杜甫所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充实”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可复返。当安禄山叛变,“渔阳鼙鼓动地来”时,各种矛盾迅速并持续暴发,弄得山河破碎,整个封建体制一蹶不振,摇摇欲坠。也幸亏当时的帝王和宰辅们,明智地前后对比,有所醒悟。严酷的社会局面,以及延续封建统治的强烈要求,迫使最高统治集团不得不进行反思,不得不思考是谁端起了祸水,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不得不对“天宝之乱”罪魁祸首的种种行为,有所认识,有所鉴戒。
在封建时代,能具有反思精神,也是不简单的。这也是唐王朝虽然每况愈下,却仍能延续其统治长达一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元稹也有过改革的意愿,他的《行宫》乃至后来写的《连昌宫词》,或含蓄或鲜明地批判唐玄宗,表明他在诗坛上也参与到反思的行列,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反思作品。
其实元稹在写《行宫》之前,早就写过和上阳宫有关的诗了,这诗名为《上阳白发人》,而且标明是“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之作。
李校书即李绅,他写过题为《上阳白发人》一诗,但失传了。据韩愈在《顺宗实录》记载,贞元二十五年(805)三月,“出后宫三百人于安国寺”。可见李绅那首有关上阳宫人的诗,是和“永贞革新”改革旧政、释放宫女的政策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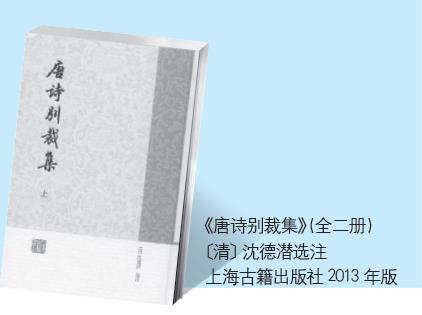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早就和元稹结交的白居易,也写过《上阳白发人》。显然元、白两位,是受到李绅的启发,于是竞相写了同一题材甚至同一题名的诗歌。据白居易在诗中原注云:“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白居易明确地说明,他创作这诗的题旨在于“愍怨旷也”。他为那些被驱逐到上阳宫并被监禁起来的宫女打抱不平。同样,元稹的《上阳白发人》也写到“十中有一得更衣,永配深宫作宫婢,御马南奔胡马蹙,宫女三千合宫弃。宫门一闭不复开,上阳花草青苔地”。显然,元稹和白居易一样,也是怜悯一辈子被幽禁的宫女,对王叔文推行的“永贞革新”表示支持。
当元稹来到了洛阳,再一次吟咏唐玄宗旧事的时候,其心态和当年写《上阳白发人》时又有所不同了。
首先从诗的题目看,只有“行宫”两字。而这时,他在洛阳所见到的,正是唐高宗时所建的那座宫室,那也是他在几年前曾经吟咏过的“上阳宫”。按理这诗也应以《上阳宫》命名,但是元稹却把宫室的名称虚化,只以“行宫”一词概括,让它成为一般性的泛指,这意味着此诗并非只就“上阳宫”而写。显然在诗的题目命名上,元稹有着深远的考虑。
“寥落古行宫”,从诗的首句开始,元稹便把句中的主语落实在“宫”字上面。
本来,帝王的宫室应该是富丽堂皇的,但是诗人以“寥落”一词形容行宫,是要让读者感知这里是冷清清、静悄悄的去处。接着,诗人再下一“古”字,表明这里是过去帝王所建的宫室。上阳宫确是在唐高宗时代建成的,在唐玄宗时代也派上了用场。到唐顺宗时,几十年过去,已被废置不用,真的成为老古董了。于是,面对寥落的“古”宫,诗人便告诉读者,这宫室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一下子就展现与兴亡有关的念头。
元稹在“宫”字之前,再下一“行”字。我们知道,古代帝王在京城里居位的地方,称为宫。行宫,则是指帝王到外地巡视或游乐时居住的建筑。这一类专供皇帝享用的居室,各朝各代,在各地建有不少。像在盛唐时期,并非只在洛阳才有上阳宫,在临潼不是还有著名的华清宫吗?元稹把他面对的审美客体,只称为“行宫”。那么他所说的,便是泛指皇帝在都城以外的所有宫室。这一来,这诗所指的地方,既是具体的,可以理解为上阳宫;又是模糊的,可以理解为包括唐王朝帝王其他的居所。这样做,便让这诗的指向更具广泛性。于是在这句诗的五个字里,实际上包含几个不同层次和内涵的形容词,也让读者从一开始便明白诗人描写这“行宫”的用意。
当元稹把他所要描写的行宫做了整体性的描画以后,便引导读者把眼光移到行宫的里面。
進入古旧的行宫,依然可以看到以往留下来的许多东西,起码还有树木、椅桌之类。但元稹让读者注目的是古行宫里的花儿。这就有味了。因为寥落的古行宫日益破旧,它已没有生机,但古行宫里的花还在生长着,它毕竟是有生命的存在,依然随着季节变换,长出了红色的花朵。
在这里,作者偏偏选择了红色的花,而不说花具有其他如黄色、白色之类的别种颜色,这除了押韵的需要以外,还有深意在焉!人们都知道,在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中,红是代表热闹、热烈和充满生命力的颜色,诗人们不是写过“日出江花红胜火”“红杏枝头春意闹”等表明红色所展现的意趣吗?元稹写在宫苑里,依然有日益生长着的鲜丽的红花,这正好和日益衰败的古行宫构成对比。再者,按惯例,花也是和女性相互联系的,人们从来都用鲜花比拟女性。既然行宫里还有鲜花,也意味着这古行宫里面还有女性存在。这一来,便为下一句诗中宫女的呈现,预先作好铺垫。
不过元稹又立即对读者说明,这红花却是寂寞地开放着的,它活自活,红自红,没人陪伴,没人赏识,更不存在杜秋娘所谓“花开堪折直须折”(《金缕衣》),提醒人们及时争取幸福生活的问题。它只在冷冷清清、孤独地顾影自怜。其实作为植物的红花,并没有感觉,说它寂寞地开放,不过是诗人把自己对古行宫的感受寄寓在花上面。于是行宫周遭寥落的环境,与色调热烈的花,又构成了对比。相形之下,反更显出这古行宫的凄冷与寥落。
紧接着第三句:“白头宫女在。”元稹在描写了古行宫里的环境以后,笔锋又转,让读者把目光从“宫花”推进到古行宫里面的“宫女”。这些宫女,是白了头上了年纪的宫女。从下一句写宫女们在聊天的情况,可以看到留在行宫里的宫女,也不是只剩一个人,而是还有好些人,否则就没有互相交谈的可能了。上文提到在唐顺宗时,不是还释放了尚幽闭在安国寺的三百宫女吗?元稹明白地说:被禁闭在行宫里的宫女们,都是老宫女。诗人强调她们是“白头宫女”,既和第一句“古行宫”相互照应,又和第二句的“寂寞红”相互映衬。当然,在唐王朝鼎盛的年代,宫女们有过如花的红颜,而红颜易老,白发如霜,加上如今行宫寥落,面对寂寞但仍开出红色的花朵,不是更显出她们都成了凋敝的残花吗?诗人在第二句末,让“红”字与第三句句首的“白”字紧紧连接,这意象似是顺手拈来,其实分明是着意的安排。
请注意,这句的“在”字下得极佳。你看宫花也在,宫女也在,但宫花尚红,宫女头白了;行宫仍在,宫女仍在,但行宫寥落,宫女也寂寞了。更重要的是,宫女仍在,而过去到过行宫游乐玩耍的主人,和宫女需要对他殷勤侍候,甚至“承恩望幸”的皇帝,却化为尘土,全都不在了!于是,这“在”字,实际上等于宣示许多方面“在”与“不在”的变化,包含着几许沧桑之感!
还要注意的是,在诗前面三句,诗人让“宫”字三次重复出现,这做法打破了近体诗用字重复的禁忌。于是,从“行宫”到“宫花”,再到“宫女”,这每句连贯出现重复使用过的字,便让读者感到诗人是有意引导着人们的眼光,紧随着他的笔锋,步步深入的。可见元稹的这首短诗,在选择意象和遣词用句方面,给人以率性而为的感觉,实际上颇费心思。
到了第四句“闲坐说玄宗”,元稹便直奔题旨了。承接上句,他写那些在古行宫里,摆开了龙门阵唠唠叨叨的人,正是那些闲极无聊的白头宫女。
在过去,当玄宗皇帝来到行宫的时候,这些宫女管你老的少的,俊的丑的,忙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如今这些宫女们人老珠黄,无所事事,于是随随便便,东拉西扯,说着唐玄宗的往事,打发空虚的日子。诗人使用“闲坐”一语,是指明这些宫女,不是一边工作一边说话,而是“坐”了下来,懒懒散散地聊天。轻轻松松,絮絮聒聒,啰里啰唆,你一言,我一语,东一句,西一句地围绕着玄宗的话题瞎扯。这些白头宫女,也许有些人连唐玄宗也没见着、没碰着。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长恨歌》)的情况下,她们不过是戴着宫女头衔的低贱婢女。杜牧不也在《阿房宫赋》中说过“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吗?当然,杜牧说的是秦朝,而实际上所指也包括唐朝。不过元稹单挑出玄宗来说事,也正是他在掌权的前半期做过些好事,让百姓过了几天好日子。后来却胡天胡地,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把唐朝弄到崩溃的边缘。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段难忘的往事,宫女们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于是唐玄宗成了众矢之的,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柄。这也是作者有意的安排。
在《行宫》里,元稹只是撮取了一個生活的片段,以白描的手法,平淡地描绘了一幅留在古行宫里的老宫女过着闲散生活的图景。这幅图景究竟要说明什么?元稹不设答案,只任由读者想象。至于在这寥落的古行宫里,寂寞的老宫女们面对寂寞的红花,闲悠悠地说了些有关唐玄宗的什么事情?诗人也没有写。也许她们在唠叨唐玄宗在某月某日来到行宫游乐,有过什么趣事、丑事或琐事;也许说到他和杨贵妃、梅妃乃至虢国夫人之间的纠葛,也许说到他英年的得意和晚年的昏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元稹只任由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思考“闲话”的内容。
但是,无论她们说了些什么,这曾经繁华而现已寂寥的行宫,曾经有过青春年华而现在已经白了头的宫女,一经诗人整合,读者就从简单而平淡的画面背后,体悟到它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寄寓着复杂的情感,让人意识到人世盛衰的变化。
在这里,诗人在写老宫女们“闲坐”的基础上,选择了一个“说”字,来表现她们如何聊天的情状。
这“说”字,是很寻常的动词,它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诗人以它表述宫女们的谈话,显得很平静、很随意。元稹对她们说话的表情也不作任何描写,只是客观地记录这些宫女的举动,任由读者自己想象宫女们有什么样的表情。更让人意外的是,实际上元稹连宫女的表情也没有写,她们只像局外人那样,聊聊往事。
但是,想深一层,元稹下这似乎是很轻巧的“说”字,又有千钧之重。
在过去,盛唐气象,如花似锦,当王朝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的时候,宫女们可有时间“闲坐”?她们有胆量在牙缝里说皇帝的半个不字吗?或者有心情拿宫禁的往事来开涮吗?而现在,日居月诸,盈虚变化,一切都不同了,那曾不可一世的玄宗,竟成为可怜的白头宫女用作打发时光的话靶。这行为的本身,便有着说不出的滋味。显然,当沉重并且可怕的历史被翻了过去,成为人们消闲的谈助时,这本身实在就相当可悲!诗人没有写宫女们带着感情地“说”,而且连他自己也不带感情去描写宫女的“说”,这表明人们对惨痛的经历,虽然没有淡忘,但头脑已经麻木。
头脑麻木,这比什么都要凄凉!正如鲁迅先生在《祝福》里,写那可怜的祥林嫂,老是对人说“我真傻,真的……”然后把自己极其悲惨的命运,像说别人的故事那样反复向人诉说时,她的心已经麻木到连痛苦的感觉也没有,这让人情何以堪!
元稹的《行宫》所写的白头宫女们,是经历过虚度青春和国破家亡的痛苦的。当一切已成过去,连痛苦的感觉也麻木了,只在空落落的行宫里,以不堪回首的往事打发时光。因此,元稹越是把宫女的表情淡化,越是写她们不把玄宗当作一回事来扯谈,实际上是说她们对往事都已麻木。同时,作者对玄宗那一段历史,在经过深刻思考以后,表现出淡薄心态,这也是他自己在思想上产生了变化,是经历过沉重的沧桑之感后情感的异化。所以,他越是以平静平淡的笔触写古行宫里的景象,其背后实在是隐藏着一丝不易觉察的黍离之悲。
这一点,便让《行宫》的二十个字,胜过千言万语,让评论家赞叹不已。宋朝著名学者洪迈说:“白乐天《长恨歌》《上阳宫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元宫禁事最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绝……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容斋随笔》)沈德潜也说这首诗: “说玄宗,不说玄宗长短,佳绝!”(《唐诗别裁集》)为什么语少意反足,而不是说语越多则意更足呢?为什么不说玄宗的长短,而意反佳呢?这都很值得我们思考。元稹,恰好正是要求读者们对此进行深入思考。
元稹的《行宫》,是以“闲话说玄宗”的宫女作为主要的审美客体。
在唐代,诗坛从来有描写宫女的传统,像王昌龄写得最好的《长信秋词》(其三):“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把宫女得不到皇帝宠幸的幽怨,写得入木三分。与元稹处于同一时代的王建,竟还写了《宫词》一百首,其中有写到帝王宫廷的荣华生活,更多的是抒发宫女们的怨恨之情。其中的一首《宫人斜》,还写到宫女命运的悲惨:“未央墙西青草路,宫人斜里红妆墓。一边载出一边来,更衣不减寻常数。”王建以辛辣的笔触,谴责帝王的荒淫。宫女死了一个,埋了一个,又再来一个新的,轮番接替。总之,宫女的数目一个也不能少,以满足帝王的私欲。当然,写宫女的怨恨,往往也是诗人们怀才不遇,借以抒发自己对封建统治者的怨怼之情。
至于白居易的《长恨歌》和《上阳白发人》,以及元稹也写过的《上阳白发人》,连同那首《连昌宫词》,都历数唐玄宗的失德,对唐王朝错误的施政和奢侈的生活,做了生动而详细的铺陈描叙,并且历数玄宗种种错误的行止,态度鲜明地进行谴责与批判。而就诗歌的写作手法而言,它们也都采用了“赋”的传统。
“赋”和“兴”“比”不同。据郑玄在《周礼·春官·大师》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政教善恶。”中唐时期,在变文和传奇小说等叙事性文学蓬勃发展的影响下,诗坛也逐渐更多地采用赋的创作手法。白居易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亦即侧重于“体物写志”“叙物言情”,即以叙述的形式,用浅近的语言来表达作品思想內容。同样,《行宫》一诗,元稹也只描画了一个画面,写的也是宫女们在“说玄宗”这么一件小事,虽以叙事的面貌出现,实际上也是“赋”,是“叙物言情”的赋,不过它是以很简约的笔触来表现而已。
和《连昌宫词》不同的是,《行宫》对所叙的事,点到即止。正因如此,元稹便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他只告诉读者,宫女在“说”。至于说的内容、说的神态,诗人一点也没有写。其实,“安史之乱”,首先让千万百姓生活惨痛,流离失所,也导致唐王朝和唐玄宗命运的变化。在行宫里,玄宗的行为,也一定给宫女们留下深刻和痛苦的记忆。但风云的变幻、世事的沧桑、血火的煅炼、荣辱的更替,经过岁月洪流的淘洗,一切已成过去,成了宫女茶余饭后用以打发日子的话题。
在明代,杨慎写过著名的《临江仙》一词,他在淋漓尽致地慨叹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以后,不就说到“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吗?《行宫》的意味,与此相近。不过元稹的写法,却显得态度平静,也更含蓄,耐人寻味。
元稹是纯客观地描叙古行宫吗?也不是,诗中出现“寥落”和“寂寞”两词,已多少流露出凭吊的情绪。但写到“白头宫女”的表现时,则只是写宫女们平静地在“说”,而把她们经历过的痛苦视为与她们无关的故事那样,只简单地以“说”字表露。这样做,反而愈能让人们产生种种的联想,甚至会由此想到各朝各代,历史上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转眼间,白云苍狗,成了“摆龙门阵”的资料。于是,在表面上淡泊回忆的后面,又蕴含着多少无奈,多少感伤。人们还可以从中想到更多的人生体验。所以,元稹在《行宫》里,不像杨慎那样强烈地抒发激情,也不像《连昌宫词》《上阳白发人》那样,有着明确的批评指向性。然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诱发人们有更多和更深的思考,从而达到诗词最高的艺术境界。
我国传统的诗词,常有“境界”的称谓。境界亦即意境。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上。”他认为诗作有意境(境界),是诗词创作的最高水平。早在唐代,王昌龄已提出“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诗格》卷中,转引自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
如何能让创作有意境?王昌龄认为要让读者“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这就是说,作者要铺陈自己的想法,从中能让读者产生联想。这联想,由作者描写的意象产生,又超出了作者描写意象的范围,这就是意境。司马光说:“古人之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温公续思诗话》)梅圣俞也说,所谓意境,是“外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金陵语录》,转引《诗人玉屑》卷六)。说白了,所谓有意境,无非是审美主体,通过对审美客体的认识和感受,以文字符号为媒介,而作为审美受体的读者们,则把文字符号反射到自己的大脑皮质细胞中,转化为意象。由于读者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不同,在大脑中反射和联想而获得的意象,自行构成甚至超出了作者设定的范围,这就出现了诗的意境。所以,作者的“不写之写”,在虚写中,含蓄地隐去主观色彩,启发读者自行体悟作品的含义,这比以淋漓尽致的铺陈,要高明得多。
元稹曾向人说过自己对诗歌创作的想法:“常欲得思深意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上令狐相公诗启》)最后一句,自然是客气话。他所谓“意近”,是指语言所要表达的意思很浅近;所谓“思深”,是指诗中所含蕴的韵味很深远。像《行宫》这首诗,他只是平淡地写古行宫的寥落和寂寞,尤其是不带任何形容词记叙宫女的“说”,这就是“意近”。然而,却让读者由此各自在头脑中,联想到更深更多历史和人生的问题,在平静语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丝冷诮与伤感,这就是“思深”和“风情宛然”。因此,《行宫》这诗虽然短小,却能使人回味无穷,进入诗词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