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绘红学内外的历史群像
2021-07-16黄子平
黄子平

喜劇作家梁左(1957-2001)
四十年前,北大中文系的文学七七级,班上有两位“小红学家”或曰“红学新秀”,梁左和李彤。他们俩以本科大学生的身份,联名在报刊发表了好几篇红学文章,锋芒初露,都是跟当时的红学大家商榷这商榷那的。宿舍里同学都笑,说他们重演了“两个小人物挑战权威”的路数,从此要发迹变泰了。他们还组成了“北大青年红学小组”(成员有著名剧作家马少波的女公子马欣来等),被邀请去参加红学研讨会,势头很好。自然,他俩的毕业论文做的也是红楼梦研究(李彤的导师觉得他引宗白华的美学评红不妥,评语里建议他“多读马列”),毕业以后却都不再以此为业。梁左朝着相声和情景喜剧方向发展,成为当代不可多得的喜剧创作名家(全班同学无不痛惋他的英年早逝)。李彤当了大报文艺记者,正好在蓝翎、李希凡的手下干活,报道的却是电影《红高粱》在柏林获奖之类的消息。
移民加拿大多年以后,李彤整理自己以及跟梁左合作的评“红”文稿,想出一本书纪念亡友,因忆起一桩旧事:当年他们见红学大师们为一首“佚诗”忙乎,煞是好玩,就起意写一部长篇小说,以恭王府为背景,将大师们的你来我往虚虚实实安排进去,岂不精彩?这小说没写成,而初心仍在。李彤说而今大师们均已仙逝,回忆录、自传、传记和访谈,各种资料剧增,更重要的是,他跟大师们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此时动笔,就不必绕道“假语村言”,只需径自秉笔直书,发挥资深文艺记者追迹真相的敏锐和捕捉细节的擅长,写成一部非虚构的长篇纪实散文。我想梁左在世,也会拊掌称善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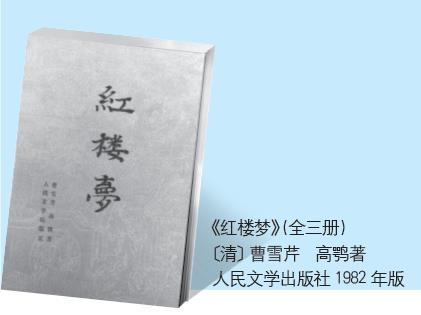
书成,乃一部五十余万字的大著作。老同学嘱我作序,义不容辞(想起梁左当年的口头禅:咱哥们儿谁跟谁呀),临到真的键盘敲字,却不免犹豫起来。犹豫的原因有二。一者,作为当代学术的一大聚焦缩影,一大“话语装置”,我对所谓“红学”一向留意,却也深知“一入红门深似海”,还不是俞平伯所说的“越研究越糊涂”的“红楼梦魇”,而是红学界的派系林立,恩怨情仇难分难解。《红楼梦》可以读,“红学界”不可碰。非虚构而且纪实,不免有所褒贬,直担心李彤如何下笔。二者,坊间此前早有上百万字的“红学百年”或“红学通史”的专书多部,资料多而且全(譬如包涵了此书割舍的“海外红学”部分),百年红学的学术脉络与社会因缘,条分缕析。李彤的新作,恐怕难有新意—我细读多遍,始觉这些犹豫完全多余。
书名原拟《红学鸿雪记》,有“句内押韵”之妙,雪泥鸿爪的轻灵却与书中所叙历史的沉重不称。现在这个书名《红学外史》,同时向两部伟大的古典说部致意,挺妙,而且也点出了著者的主体位置—身处域外,身处红学界外,来描述红学中人的“儒林群像”,谁曰不宜?但李彤对红学群儒有充分“同情的理解”,下笔庄重持平,又与“外史”一词带来的“讽刺小说”的联想不符,这是读者阅读时需要特别留意的。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文本(“荒唐言”),作者(叙述者、批阅者、增删者),创作意图(“痴”和“其中味”),以及对那个能够理解作者苦衷(“辛酸泪”)和意图的理想读者(“谁”)的殷切吁求,仿佛预设了《红楼梦》成书以来,两百年阅读史评论史的基本路径。《红楼梦》设置的重重叠叠的叙事圈套,固然是引发“无边的阐释”的主要原因,但使人(排他性地)觉得自己才是解得“其中味”的那个“谁”,乃至将此变成毕生的名山事业,或许也是一个使多少人深陷其中的致命的蛊惑吧。
这样一个延续百年的竞猜游戏,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吾人若把鲁迅的接受美学,“看”和“被看”的结构颠倒一下,即可从诸多不同的“看见”里,反观出“经学家、道学家、才子、革命家和流言家”各色人等。如是,《红楼梦》就真是一面“风月宝鉴”了,当然吾人从镜中看到的不再是风月,而是一时代的风云乃至风雷。

从“宝鉴”中“抄”出一部《红学外史》,李彤叙写的重点,不在红学内部和外部的学术脉络,而在红学群儒的时代际遇,辛苦遭逢,知识人的节操和人格,在知识与权力、利益之间的辗转人生。于是你读到蔡元培读了胡适击溃“旧红学”的“新红学”大文,一边写文章郑重答辩,一边却帮胡适寻得他遍寻不获的《四松堂集》。你读到胡适将某珍本《红楼梦》慷慨借给素不相识初次见面的青年周汝昌。你读到观点立场完全不同的吴组缃和何其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大课堂,同时开讲《红楼梦》。你读到孙楷第为他红羊劫中流失的百万藏书,郁郁而终。你读到“两个小人物”多年真诚的友谊和令人痛惋的分道扬镳。你读到俞平伯晚年出访香港谈“红”,超水平的精彩发挥。你读到同为当代的小说名家,王蒙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烦透了那个在每一页上哭天抹泪干扰阅读的“脂砚斋”,刘心武却发展出了一个想象多于实证的“秦学”,周汝昌还因此点赞了他的“悟性”。至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诸般“曹学文物”的出土和发现,读来恰似推理小说,煞是好看……
虽说是“外”史,我却读到《红楼梦》诗学幽灵般地内在于李彤的叙写,直接左右了本书的结构和文字。十二篇的章节(“金陵十二钗”?),均以《红楼梦》的对话或诗句来提纲挈领;又以主册、副册、又副册的方式来安排红学群儒的出场次序;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首尾呼应等叙事技巧的纯熟运用,则犹其余事,优而为之。当不同来源的史料有所出入的时候,李彤又发挥了当年评红的考证功夫,略作辩证,尽显学问功底。仗着对北京的历史地理的熟悉,书中常常点出一些毫不相干的事件的空间巧合,令人惊喜。然而本书最可贵的,是李彤将自己出入红学界、亲炙红学泰斗的点滴经历,适当穿插在章节之间,不仅加强了“纪实散文”应有的“实感”,更证明了这不是一部冷冰冰的史料连缀,而是有温度的生命书写。
是为序,并以此纪念老同学梁左,就在这个月,他去世二十周年。
二○二一年五月四日于珠海唐家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