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演员
2021-07-14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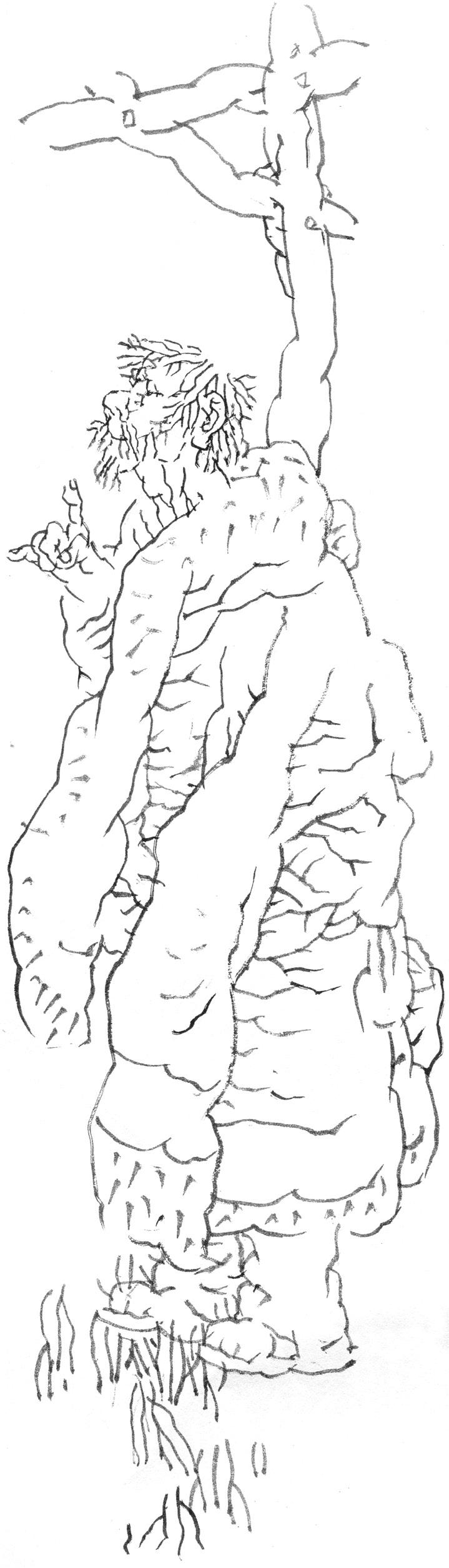
先说说我。
我叫扎西,就是吉祥的意思。
你们可能也听说过我,我在我们这里还是有一点小名气的。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爱跟各种人打交道,朋友们都说我像个万金油,什么地方都能用得上。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来我们这里拍电影、电视剧的剧组里混。往好听里说,我是一个在藏地的影视工作者;往不好听里说,我就是个在来藏地拍电影、电视剧的各种剧组里打杂的混混。在剧组里,我什么都干。什么演员联络、场地协调、制片助理、生活制片助理、导演助理、美术助理、服装助理等,反正剧组里有什么活我就干什么活,说白了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有时候还在戏里客串一下,当个群众演员什么的,自我感觉良好。导演高兴了也夸我两句,说:“那个什么,扎西,你在这方面确实有一点点天赋,以后你应该往这方面好好发展发展啊!”我有点不高兴,问:“导演,我的天赋就只有一点点吗?”导演笑着说:“我们这个汉语的表达很复杂,说你有一点点天赋,意思就是说你在这方面还是有发展的潜力的。我们的汉语太复杂了,那些很微妙的东西你要慢慢领会才知道。”我“哦、哦”了两声,知道这反正是在夸我,心里就美滋滋的,有时候还真想往这方面发展发展呢,想着以后有了点钱就找个机会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进修一下什么的。听说去那里进修学费还很贵!
我也喜欢给各种人讲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故事。说实话,我知道的故事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讲哪一个好,我觉得都很有趣。今天要讲的这个我觉得也很有趣。我讲故事有一个原则,就是从来不胡编乱造。我看很多电影,虽然故事编得天花乱坠,但还是没有我的故事讲得好。
这是去年夏天的事。夏天快结束时,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拍电影的剧组。他们通过各种关系自然就找到了我。他们的制片主任带我去见了他们的导演。导演是个中年人,有点发福,脑门上的头发整个不见了,但精神很好。
制片主任把我介绍给他,说:“这个叫扎西,这边拍戏的一般都找他。他能力很强,各方面关系很好。”
制片主任又看着我说:“这位是导演,黄导,著名导演,你随便打听打听,圈里面没有人不认识的。”
我也立即表现出尊敬的样子,说:“黄导,您好!我的名字叫扎西。”
导演看着我说:“扎、扎西,这名字好拗口,你汉语没问题吧?”
我立马学着电影电视里的人说普通话的样子说:“当然没问题,不然怎么敢在各种剧组里混呢!”
导演立马笑了,说:“你不仅会说汉语,而且说的还是标准的普通话呢!看起来交流应该没有问题。”
我就没再说什么,虽然心里有点不高兴。
导演接着又问:“扎西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
我说:“吉祥的意思!”
导演说:“我知道了,就是‘扎西德勒那个‘扎西,你这名字好啊,希望能给咱们的电影带来扎西德勒。”
制片主任讨好地说:“肯定能扎西德勒,将来咱们的电影肯定能吉祥如意、扎西德勒,哈哈哈。”
看着制片主任的样子,我笑了笑,可能笑容里也有点讨好的意思。我也说:“肯定能吉祥如意、扎西德勒!也肯定能在国内金鸡百花各种电影节上拿大奖!”
导演乐呵呵地笑着说:“借你吉言,借你吉言!是这样的,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一百周年,我们要拍一部电影来讲述当年红军经过草地时跟当地的藏民之间发生的故事。”
我对别人称我们为“藏民”有一点反感!上中学时,我们的一位历史老师就说,“藏民”这个称呼本身就带着一种歧视的成分在里面。我们那个历史老师有点激进,他在课堂上高声说:“同学们,你们记住了,‘藏民这个词是个贬义词,任何把边疆少数民族称为‘藏民‘回民‘蒙民什么的都是带有歧视的成分在里面的!”我记得当时课堂上我们一个学生问:“老师,那我们把汉人称为‘汉民也是带有歧视的成分在里面吗?”我们的老师愣了一会儿,想了想说:“客观地讲,实事求是地讲,把人家汉人称为‘汉民也是带有歧视的成分的!”所以这个关于称呼的话题就永远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了,变得很敏感。
没等我往下想,导演就接着说:“红军长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你们藏民也有很大的贡献啊。你们的格达活佛和我们的朱总司令就是很好的朋友,格达活佛带领当地的藏民当年为红军送干粮送温暖做了不少好事啊,他已经是历史名人了,可惜后来被你们的一小撮反动势力偷偷下毒给弄死了,唉,这可真是历史的悲剧啊!”
导演说话时,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县城的新华书店见过的一幅画。那幅画有点像唐卡,上面是朱总司令和格达活佛,他们高高在上地在画面上亲切地交谈。那时候,很多人把那幅画当作年画挂在家里,印象很深的。也听说有些人家把那幅画当作唐卡在家里的佛堂挂了起来,每天点灯烧香,希望能得到上面的两位大人物的保佑。
看导演在感叹,我就暗地里想这个导演对这方面还是做了一点了解的,不像有些导演,完全是带着一种好奇心和猎奇心来到这里的,问到一些实际的,不仅什么也不懂,还喜欢不懂装懂!
我不失时机地、有点卖弄地说:“导演,那你们这次要拍的是一部主旋律电影吗?”
导演有点惊奇地看着我说:“你,你还知道这个?”
我說:“我以前听剧组里很多人在聊,后来也看了一些电影的书、杂志,就知道这些了。”
导演有点生气,看着我说:“你,你叫什么来着?”
我说:“扎西。”
导演说:“你这名字太拗口了!你前面说你这名字什么意思来着?”
我说:“吉祥的意思。”
导演说:“吉祥,这个顺,我还是叫你吉祥吧,这样也好记。”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他继续说:“那个吉祥,你听着,你千万不要在那些坏的剧组里面学坏,那样你就把自己给毁掉了,记住了没有?”
我赶紧点点头,说:“记住了。”
导演继续说:“你千万不要被这些词汇给迷惑住。电影就是个艺术,电影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分类,什么商业电影,什么艺术电影,什么主旋律电影,都是胡扯,都是放屁!电影只有好电影和坏电影之分!你只要在你的电影里面流露真情实感就可以了!有真情实感的电影才是好电影!”
我有点被导演的话感染了,不停地点头。
导演说:“吉祥你给我记住,我们这次要拍的就是一部表现人的真情实感的好电影!”
我不由得鼓掌说:“好,好!这次我们要拍一部好电影!”
导演有点激动,挥了挥手对制片主任说:“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赶紧带着吉祥去办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事吧。”
我和制片主任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制片主任对我说:“扎西,我们这个电影要还原当年红军过草地时的真实场景,但你们这儿的草原和民居被破坏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去了很多地方,说你们这儿可能还是比较好的,可能还有一些被保留下来的东西。”
我说:“你们算是来对地方了,在我们这儿找不到的,你在其他地方也肯定找不到了。”
制片主任说:“跟那个年代的照片比,还是改变太大了。”
我笑着说:“主任,你这是什么话?改革开放都这么多年了,要是我们这儿还是当年照片上的那个样子,那我们不是在拉国家的后腿吗?再怎么说国家还是很照顾我们的。”
制片主任有點生气,说:“国家就只顾着照顾你们这些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了!”
我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说:“剧组现在需要什么?快说吧。”
制片主任说:“需要一顶那种看起来很原始、很古老、很旧的黑牦牛帐篷。”
我就问了问旁边的几个牧民,牧民们含含糊糊地说:“我们这里哪有那种黑牦牛帐篷,那种东西成古董了,现在找不到了。”
我给他们每人散了一根云烟,问:“那你们这儿到底有没有那种黑牦牛帐篷?”
牧民们慢慢抽起了烟,快抽完时,一个牧民才说:“噢,我记起来了,那种帐篷有是有一个,就怕主人不肯借给你们啊。”
我说:“你快说谁家有,我去借借看。”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个地址,我和制片主任就开着剧组的那辆皮卡车,按他们说的地址去找那户人家了。
制片主任把皮卡车开得飞快,我们很快就看到那顶黑色的牦牛帐篷了,在草原上的各种土房和彩钢房中很显眼。
快到跟前时,制片主任问:“扎西,你确定这就是导演说的那种帐篷吗?”
我说:“是啊,就是那种,现在这种帐篷几乎没有了,能找到一个就不错了。”
我们到门口时,一个头发有点花白、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的老人出来迎接。
我向老人说明了情况之后,老人说:“不借!这顶黑牦牛帐篷是从我阿爸那一辈传下来的,冬天暖和,夏天凉快,从来没有向外人借过!”
我看老人说得很认真,完全没有要借的意思。
我把老人的话翻译给制片主任听,制片主任立马说:“你快告诉他,我们不借,我们租,我们给他钱!”
我把制片主任的话翻译给老人听,老人脸上毫无表情,摇了摇头。
制片主任显得很着急,说:“这下完了,导演会疯掉的。找不到他要的那种黑牦牛帐篷,我们的拍摄会超期的。超期了,预算超了,我也会疯掉的,投资人也会跟着疯掉的!一连串不好的连锁反应!都没办法,这部电影本身投资就那么一点钱!”
我问:“不是说主旋律电影都是政府投资,都很有钱吗?”
制片主任急了,说:“刚刚导演不是说了吗?不要听那些坏剧组乱讲!这部电影虽然听起来像个主旋律电影,但是政府没有投一分钱,是一个曾经当过红军、过过草地的红军老战士逼他做生意的儿子投的。那个红军老战士说当年一个牧民用一块牛肉干救了他,要不是牧民的那块牛肉干,自己早就饿死了。还对他儿子说,要是当年我在草原上饿死了,哪还有现在当老板的你!所以做人不能忘了本!那个当老板的儿子拗不过他的红军老爹,就象征性地投了那么一点点,投资比其他的主旋律电影少得可怜!”
我看制片主任说得很动情,就说:“好吧,好吧,那我去跟老人说说吧,你在外面先抽根烟。”
我把老人拉进了帐篷里。
待我和老人从帐篷里出来之后,我看见制片主任紧张地看着我。
我说:“老人坚决不借黑牦牛帐篷。”
他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了。
我又说:“但是老人答应咱们可以到他这里拍。”
制片主任的情绪马上转了过来,连连说:“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总比没有强!”
老人的脸上也露出了笑。
之后,老人请我们进去喝茶。
我们在宽敞的黑牦牛帐篷里坐下之后,一个看上去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大概三十多岁、穿着宽松藏袍的女子提着茶壶给我们倒茶。奶茶哗哗地被她倒进了我们的碗里,空气里立即散发出一阵阵香味。
制片主任拿起碗,喝了一口奶茶说:“很久没有喝到这么纯、这么浓、这么香的奶茶了!”
说完,又喝了一大口。他碗里的奶茶剩得不多了。
那个女子又过来给我们倒茶。
制片主任看了看正在倒茶的女子,对我说:“到时候可以让老人的女儿到咱们剧组打打杂,挣点零钱。”
女子的脸一下红了,还没倒完茶就放下茶壶跑出了黑牦牛帐篷。
我和制片主任正莫名其妙时,老人问我:“这个汉人刚刚说了什么?”
我笑着说:“他说到时可以让你的女儿到我们的剧组打打杂,挣点零花钱。”
老人一下子不说话了,有点不好意思地对着帐篷的门看了一会儿之后才说:“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老婆。”
老人的回答让我也有点出乎意料,不由得再次细看老人的脸,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制片主任见我的样子,就问我:“扎西,怎么回事?”
我把老人的话翻译给制片主任听。制片主任把刚刚端到嘴边的茶碗拿在手里,愣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老人。
出了帐篷,把皮卡开出一段距离之后,制片主任兴奋地对我说:“扎西,这个老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女人就是他老婆!”
我只是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开始在老人家黑牦牛帐篷里拍,昨天我们错把她当作老人女兒的那个女子从帐篷里进进出出,偶尔跟我照面,就一下子像昨天一样露出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马上躲开我。
导演一早就来了,看着经过美术部门布置的黑牦牛帐篷满意地点着头。拍完一场戏,各个部门在等灯光组布光。拍摄时,导演对两个男女主演的表演不太满意,提出了一些意见。这会儿,两个主演正在拿着剧本琢磨着自己的角色。
制片主任把昨天我们喝的奶茶添油加醋地介绍给了导演,看着导演充满期待的表情,制片主任就让我叫那个女子给导演倒一碗奶茶。
女子端着一个龙碗来给导演倒奶茶。倒完奶茶女子就低着头走了。
导演喝了一口奶茶,不住地点着头说:“太纯了,现在在我们城里很难喝到这么纯的奶茶了,要么就加了水,要么就加了防腐剂,要么给奶牛喂了化学的饲料,哪能喝到这么纯的奶!”
说着说着,导演很生气,连带把城里的空气也骂了一通:“别说吃的食品,就是本来应该最纯净的空气也被污染得一塌糊涂了,未来这个世界就要被人类亲手毁掉了!”
制片主任附和着说:“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太幸福了,每天吃着有机食物,吸着新鲜空气,真是太幸福了。”
我说:“有个笑话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导演看着我问:“什么笑话?说来听听。”
我就笑了笑说:“有些搞旅游的人说我们这里的牛羊吃的是冬虫夏草,喝的是矿泉水,拉出来的是六味地黄丸,哈哈哈。”
导演和制片主任也“哈哈哈”地大声笑起来,说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很有创意。
之后导演又看着我问:“吉祥,你有没有觉得生长在这里自己很幸福啊?”
我挠了挠头说:“说实话,我其实还挺向往在城里生活的,在城里生活多方便啊!”
导演看着我说:“不要向往城里的生活,在城里生活真的是糟糕透了!”
制片主任也说:“扎西,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就笑笑,没再说什么。
老人一早就赶着羊去了山上。现在他回来了,盘腿坐在一边好奇地看我们拍戏。
女子给导演添了奶茶,又去给老人倒茶。这时,导演才一下子注意到了老人。他看了一会儿老人之后,把我叫过来问:“那个谁,吉祥,那边那个坐在地上看我们拍戏的老人是谁?”
我看了看老人说:“他就是这顶黑牦牛帐篷的主人啊。”
导演把演员副导演喊到身边,指着不远处的老人说:“你看到那个老人了吗?看到了吗?”
演员副导演往那边看了看,说:“看到了。”
导演有点生气,说:“你看看,那么好的形象,你怎么不把他放到咱们的群众演员里面?”
演员副导演也有点愣了,说:“对不起导演,我之前没看到他,我也是刚刚才看到的。”
导演骂起了演员副导演:“你怎么搞的!这么好的群众演员放着不用,尽找来一些木头似的看着就来气的群众演员,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才好!”
随后,导演让我过去把老人叫过来。
待我把老人叫来之后,导演仔细地看着老人的脸,像是在欣赏一幅欧洲名画,一边感叹一边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的人生,他的经历,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写在他的脸上了。你们看看,他额头上的每一道皱纹就像是被刀子刻上去似的!你们难道从他额头的皱纹里面读不出点什么东西吗?”
我和演员副导演,还有制片主任惊奇地仔细地看老人的脸,尤其是老人额头上的皱纹。老人额头上的皱纹确实像是被刀一条一条地刻上去似的,纹路清晰可见,每一条皱纹里面似乎藏着一个个故事。
导演看着我说:“吉祥啊,你问问老人肯不肯在咱们的电影里面演一个角色。”
演员副导演说:“导演,我记得咱们的戏里没有适合他的角色。”
导演看着他说:“你就不会往里面加点戏吗?这么好的演员不用多可惜啊!”
导演再次让我问老人。我把导演的话翻译给老人之后,老人说:“我不会演戏。”
我又把老人的话翻译给导演听,导演说:“吉祥啊,你跟老人家讲,他演戏不是白演,是有报酬的。”
我又把导演的话翻译给老人听,老人立马说:“我不会演戏。”
我把老人的话翻译给导演之后,导演像是一下子有了激情,说:“他根本就不用演什么,他只要坐在那里喝喝奶茶,看看远方什么的就可以了,就什么都有了。”
我再次把导演的话翻译给老人听,老人还是说:“我真的不会演戏。”
我把老人的话翻译给导演之后,导演对我说:“吉祥啊,这样,你再单独跟老人家谈谈,他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我把老人带到帐篷里开导了一番,老人看着我不说话,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有点轻描淡写地说:“您随便演一下,他们会给你钱的。”老人有点生气地看着我说:“你也是藏族的吧?”
我马上说:“是是,当然是。”
老人接着说:“那你也应该知道,我们是很忌讳这些东西的,尤其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
我用不解的眼神看他,他继续说:“可能每个地方的说法不一样,我们这里是很忌讳上了年纪的人把自己的形象留在照片上的。”
我还是用不解的眼神看他,他继续说:“我们这里以前有个说法,就是说你生前把自己的形象留在纸片上,那么死后你的灵魂就得不到解脱。”
我这才恍然大悟,之前我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老人继续说:“我这辈子没有照过一张照片,十年前说要办身份证照相,我都躲到山上去了。我到现在都没有身份证。”
我意识到我再说也没有什么用,就出去把老人的想法告诉了导演。
导演摇着头说:“吉祥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这些人的脑子里还保留着这些稀奇古怪的落后观念,你说说你们这个民族将来可怎么办啊?我真是替你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担忧啊!一个民族没有了未来就等于完蛋了,你知道吗?”
正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时,导演又马上说:“吉祥啊,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我是很喜欢你们这个民族才这么说的,要是别人我就不一定这样说真话了。”
这时正好女子过来倒茶,导演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倒完茶,导演看着离开的女子说:“她是老人的女儿吗?她的长相也蛮有特点的。”
旁边的制片主任就忍不住偷偷地笑起来,弄得旁边的导演和演员副导演都莫名其妙地看他。
导演盯着制片主任看了一会儿,制片主任才一边笑一边小声地对导演和演员副导演说:“这个女子不是老人的女儿!”
导演问:“那是什么?”
制片主任还是笑着说:“是老人的老婆!”
导演和演员副导演一下子愣住了,几乎同时喊了一声“啊”。
过了一会儿,导演才感叹着说:“难怪这个老人看上去很有故事的样子!”
吃了午饭,剧组又在黑牦牛帐篷里拍了一个下午,但导演总是不太满意,演员也不知怎么回事,总是不在状态。黄昏时候整个剧组垂头丧气地准备收工时,给我们倒奶茶的那个女子突然变得难受起来,说恶心、胸闷、气短,老人也显得很担心。正好制片主任和我要去县上买点东西,就说:“那她跟我们一起去县上医院看看吧,不要耽误了病情。”
我跟老人一说,老人也很高兴,就对她说跟着我们一起去县上好好看看。老人还交代我说她汉话不好,到了医院要我帮帮她。
临出发时,老人从帐篷里拿出一袋东西交给她说:“这里面是一些酥油糌粑,到了县城交给你老姐吧。”
她“呀呀”地答应了一声,看着老人,老人也用爱怜的目光看着她。这时候感觉他俩真是一对心有灵犀的夫妇啊。
路上她一直都很难受,到了县城医院我就带她直接去了急诊室,制片主任找地方停车。
挂号时一个护士问我,你是她丈夫吗?我立即说我不是,她也显得很不好意思。
做完一系列检查之后,一个医生出来说:“谁是她的家属?”
我站起来说:“我是。”
医生笑着说:“恭喜你们啊!”
我有点莫名其妙地看着医生问:“什么意思啊?”
这时制片主任也进来了,看着我们。
医生继续笑着说:“她怀孕了,呵呵。”
我马上笑了,说:“哦哦,我不是她丈夫,我只是陪她来看医生的。”
制片主任也在一边笑。
医生也笑着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回去告诉她的家人吧。”
我点了点头说:“她没有什么事吧?”
医生说:“没事,她只是妊娠期反应,没有其他病,她目前的这些反应都很正常,不用担心。”
我握住医生的手,一个劲地向他道谢。
制片主任看着我的样子,在一边坏笑。
医生好奇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表情严肃地说:“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一下松开医生的手,瞪着他说:“你不要多想啊,我们没什么关系!”
她似乎也听懂了医生话里的意思,显得有点坐立不安。
医生把我叫到医生办公室,说:“你回去告诉她的家属,这个孕妇年龄有点大,到时候最好到医院生孩子,这样危险系数比较小,不然这个年龄生孩子有点危险!”
我说了声“好”,准备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时,医生又叫住我说:“你回去让她家属早早准备一点钱,到时住院生孩子需要一点钱。”
我问大概需要多少?医生说最好准备个三万元吧,以防万一啊。
从医院出来之后,她问我能不能把她送到她老姐那里,我说当然可以。
她老姐家在县城边上的一排灰突突的平房中间。到了门口,我帮她把老人给她的装着酥油糌粑的袋子扛了下去,袋子有点沉,我扛着都有点吃力。她敲了很长时间的门,门才开了,出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女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但很热情地说:“啊呀呀,你来了啊?我今天睡得早,我都睡着了,快进去吧。”
我说我们明天再来接她,就开着皮卡车去找县上的招待所。路上,制片主任忍不住对我说:“扎西,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女人怀的孩子是不是那个老人的种啊?那个老人年龄那么大,怎么可能让她怀孕呢?”
我说:“这我就不知道了!”
制片主任说:“我觉得不太可能,真的!”
我说:“虽然他们之间年龄悬殊,但我觉得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下午咱们出发之前,我看他俩的眼神就觉得他俩之间不像是那种没有感情的夫妇。”
制片主任感叹着说:“你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和繁殖力也太强了,我要是到了这个年龄,可能连干那个的心思都没有了!”
我说:“这种事情以前也不是没有过,我们藏族有个很有名的画家叫安多强巴,画过十世班禅大师,也娶了个比他小很多的女人,八十多岁了都让人家怀上了呢!哈哈哈,厉害吧?”
制片主任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说:“厉害厉害,你们确实厉害!”
第二天,我和制片主任买了东西之后又去接她。那个老女人出来送她,她们之间看起来也很亲切的样子。
回到剧组,女人下车跑到老人跟前对着老人的耳朵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就跑进帐篷了。
我有点好奇地盯着老人看。
老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的眼里慢慢地流出了眼泪。
这时,导演过来问我:“你们昨晚去医院检查,她没有什么病吧?”
制片主任抢先说:“导演,你绝对想不到是怎么回事。”
导演有点担心起来,说:“她不会是得了什么大病吧?”
制片主任笑了,说:“不是不是!”
导演问:“那到底怎么回事?”
制片主任这才说:“你绝对想不到!”
导演追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制片主任压低声音说:“医生说她怀孕了。”
导演“啊”了一声看着我,说:“她怀孕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说:“其实昨天我就怀疑她可能怀孕了,只是她穿了藏袍没有好好看出来。”
导演把目光转向不远处的老人,说:“这老头太厉害了!难怪他脸上看上去那么有故事!”
过了一会儿,女子出来给我们倒奶茶。导演这会儿好奇地盯着女子的脸看。
趁女子倒茶的工夫,我把老人叫进帐篷,笑着说:“老人家,恭喜你啊!”
老人也只是呵呵地笑,没说什么。
我又说:“老人家,你真厉害!”
老人还是呵呵地笑着,不说话。
我把医生的话复述给他听。
老人听完有点担心,但最后说:“只要她没事,能顺利生出孩子,我就得想办法凑钱。”
我安慰了他几句准备出去。这时,女子提着茶壶进来了,老人就让我坐下跟他一起喝喝茶。女子给我俩倒了奶茶出去了。
老人喝了一大口奶茶,看着我说:“你们肯定对我们这对老夫少妻感到奇怪吧?”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我倒没什么,主要是外面那些汉人觉得很奇怪很新鲜,尤其知道你老婆还怀孕了,就更加觉得奇怪新鲜了。”
老人倒是没什么反应,从黑牦牛帐篷门口看着外面说:“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我就问:“你们之前没有孩子吗?”
老人想了想说:“我其实有一个儿子,但那是我跟另一个女人生的。”
我有点好奇,看着老人问:“难道你还有一个老婆?”
老人看着我说:“是,我有两个老婆。”
我继续好奇地看他的脸。
老人说:“你应该也见过我的第一个老婆了。”
我更加好奇了,自言自语道:“啊!我还见过她?”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就是昨天我让我女人带酥油糌粑去的那个,你应该是见过了。”
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出来给女子开门的那个老女人,就问:“你怎么会有两个老婆?”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怎么说呢,你昨天看到的那个女人是我的第一個老婆,我俩年龄也差不多,我们俩在一起没多久就有了孩子,是个男孩,现在也快三十了。”
老人又停下了,想着什么,我很好奇,就追问:“后来呢?”
老人又开始说了:“后来,二十多年前吧,我那个老婆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她身上什么地方都痛,看了藏医、西医、中医,各种医生都没有办法治疗。最后,没办法了,就带她去塔尔寺见了一个活佛。活佛算了算,看了看她,说:‘她这个病和她前世的某些孽障有关系,世间的医生是治不好她的。我就赶紧问:‘那有什么方法能治好她的病?活佛看了看我俩问:‘你们俩有没有子女?我立马说:‘有,有一个儿子。活佛说:‘那就让他出家当僧人吧,他可以替她慢慢消除孽障。后来我们的儿子就出家当了僧人。”
我好奇地问:“那后来她的病好了吗?”
老人说:“说来也奇怪,我们的儿子出家当了僧人之后,她得的那个怪病也就慢慢地好了。”
我不禁感叹道:“好神奇啊!”
老人却淡淡地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神奇的,你前世造下的孽障,这辈子肯定是要还的。作为子女,能替自己的父母消除孽障,也是一种难得的修行。”
我只是好奇地看着老人的脸,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人继续说:“但后来她的身体还是很弱,我们就在县城买了个房子让她住下了,一来她不用那么劳累,二来她看看病什么也挺方便。儿子出家之后,她也变得像个尼姑了,除了每天念经、烧香、点灯、打坐,对其他事情似乎也没有任何兴趣,我们也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而已。”
我就问:“那你现在这个老婆是怎么回事?”
老人说:“噢,是是……是这样的,后来,她看着我一个人在山上生活很辛苦,就说服她亲戚家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做了我的老婆,我们之间相差二十多岁。一开始她也不愿意,回过两三次娘家,但后来就安定了下来。她很能干,也很善良。她对我很好。”
我笑着对老人说:“就像外面那个汉人导演说的,你老人家的故事可真多呀!”
老人也笑着说:“我这点事在我们这儿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就是一家人,互相照顾着,真的很好。”
我笑着继续说:“真的挺好,真的挺好。”
老人看着我说:“我们一直都想要个孩子,所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
我坏笑着说:“这有什么好谢的,这都是因为你厉害,呵呵。”
老人的脸上也带着一丝坏笑地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早就不行了,没想到还有点用途啊,呵呵。”
我看着老人说:“你就不担心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吗?”
老人笑了,说:“这个你就不用多想了。她比我小很多,这是事实,我也曾暗示她可以去找个跟她差不多的小伙子当相好,但她很生气,她说我人很好,心地善良,她说对她来说这就够了。”
我赶紧说:“那就好,那就好。”
老人笑着说:“其实我们之间还是挺和谐的。”
这时,导演在外面“吉祥,吉祥”地喊我的名字,我就出去了。
导演问我:“你进去那么长时间,你和那个老人都聊了什么?你得赶紧去再联系几个当地的群众演员。”
我看着导演说:“导演,您的眼睛真的是太毒了,这个老人的故事真的是太多了!”
导演似乎也有了兴趣,说:“快说说,他还有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我故意说:“我还是先去找群众演员吧,老人的故事慢慢再讲给您听。”
我找来几个群众演员之后,剧组下午又在黑牦牛帐篷里拍了好长时间。导演对两个主演和群众演员们的表现都不太满意,觉得总是缺了那么一点东西。
第三天,制片主任说让我跟他去县上采购一些东西。我们快要出发时,老人领着女子过来跟我说:“她昨晚上一直不舒服,麻烦你把她送到她老姐那里,让她们再好好检查一下吧。”
我问老人:“你不陪着去一下吗?”
老人说:“我这边还要放羊,事情多,有她老姐帮忙就没事了。”
我们把女子送到县城边上那个老女人家里后就去买东西了。
路上,制片主任说:“我听村里一些小伙子说,刚刚出来的那个老女人是老人以前的老婆,是那样吗?”
我说:“你说得没错,是那样。”
制片主任问:“那他怎么能娶两个老婆?”
这会儿我心里有点烦,就说:“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以后再跟你说吧。”
制片主任就嘟哝着说:“你们这里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真是多!”
我们买了东西回去的路上,皮卡车陷进一块沼泽地里半天也没能弄出来。轮胎越陷越深,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了。制片主任一个劲地说:“完了完了,看来今晚只能待在这个荒郊野地了!”
大概半夜的时候,一辆东风卡车路过这里,司机拿出一根粗钢丝绳拴住两辆车,轻轻一拉就把我们的皮卡车从那块沼泽地里拉了出来。
我给卡车司机让了一根烟,夸了一句:“你的卡车力量太大了,就像酥油里抽毛一样把我们的皮卡车从沼泽地里抽出来了!”
卡车司机也不谦虚,抽着烟说:“你一个皮卡车当然没有我齐头东风车的力气啊,我这齐头东风可是有210个马力的,你看看它们的大小就知道了!”
晚上回到剧组已经是后半夜了,第二天起来得也晚。我到拍摄现场时已经十点多了。
导演看到我说:“吉祥,你终于来了,黑牦牛帐篷的主人,那个老人家一直在问你什么时候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肯跟我说,他说等你来了说。”
导演正说着,我看到老人已经向这边走来了。
待他走近后,我问:“老人家,你有什么事吗?”
老人看了看导演之后对我说:“咱们去帐篷里说。”
我和老人就去了黑牦牛帐篷。
到了黑牦牛帐篷,老人却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我。
我说:“有什么事你快說吧。”
老人说:“昨天你们把我老婆送到她老姐家之后,下午她们去医院做了检查。”
我问:“医生怎么说的?”
老人说:“医生说我老婆年龄大了,现在生孩子危险,还说什么孩子在肚子里的位置也不好,要做手术,得把孩子从肚子里直接取出来。”
我笑了,说:“那叫剖腹产,一个很常见的手术,没有什么危险,你就不用担心了。”
老人说:“我不是担心这个,我也知道,现在科学发达,很多以前治不好的病现在都能治好了。”
我问:“那你还担心什么?”
老人尴尬地说:“我担心钱,她们也捎来话说做手术生孩子最少需要准备三万多块钱。”
我说:“噢,我明白了。那你就把你的羊卖了吧,还是生孩子要紧。”
老人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只有十几只羊,今年的羊价根本不行,全部卖了也凑不到那么多钱。”
我就只好说:“那怎么办啊?”
老人说:“昨天我老婆她老姐捎来话说她手上大概有一万块,我手头也有个一万,加上你们这几天租我黑牦牛帐篷的钱,再有个一万元就有三万多块钱了。”
我马上说:“这样应该够了,应该够了。”
老人接着说:“前两天你们不是让我来演电影吗?如果我演了有多少钱?”
我说:“有几千块钱吧,也没多少钱。”
老人说:“如果我演了,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万块,有了一万块我就不用担心了。”
我终于明白过来了似的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我定不了,这个事情人家导演、制片主任才能定。”
老人说:“那你去问问他们吧。”
我这才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你不是说你不能把自己的影子留在照片上吗?你演了电影就等于把自己的影子留在照片上了。”
老人说:“是是,但是我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笑着问:“那你将来死了灵魂得不到解脱怎么办?”
老人说:“不解脱就不解脱吧,只要他们母子能平平安安就好!”
我有点感动,看了看老人,走出帐篷,对着导演说:“老人愿意演了。”
导演一下子站了起来,说:“太好了,太好了,吉祥,你赶紧让化妆和服装给老人准备一下吧。”
我顿了顿说:“导演,老人问如果他演了能不能给他一万块。”
导演看着我说:“吉祥,你没跟他老人家说吗?预算里群众演员的费用没有那么高啊。他为什么要这么高呢?我看老人家也不是那种很爱钱的人啊!”
我就把老人的情况跟导演说了一遍。
导演想了想说:“哦,原来是这样。”
我问:“那我怎么跟老人说?”
导演说:“你去把制片主任叫来。”
我把制片主任叫来之后,导演说:“吉祥,你把老人的情况跟主任汇报一下。”
我就又把老人的情况跟制片主任说了一遍。
制片主任听完看着导演。
导演说:“主任,能不能给老人一万块的劳务呢?”
制片主任有点为难地说:“导演,咱们的预算都是之前就定死的,只能严格地按预算走,现在看着都有点紧张呢。”
导演说:“那你不能以特邀演员的名义申请一下吗?”
制片主任为难地说:“导演,咱们的预算里没有特邀演员这一项啊!”
导演有点生气,说:“算了算了,这样吧,老人的费用就按群众演员的标准走吧,剩下的部分就从我个人的劳务费里面扣,这个演员我用定了!”
制片主任立马说:“这怎么行呢,这笔费用不能从您的劳务费里扣!”
导演有点生气,说:“那怎么着,这两天拍得都不理想,这样耗着,开支不是更大了吗?”
制片主任看了看我说:“这样吧,扎西,你先答应老人的要求,咱们先拍,我再想办法跟咱们的投资公司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以特邀演員的名义给老人申请到这笔额外的费用。要是申请不到到时大家再想其他办法,目前进度最重要!”
老人正式加入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下午的拍摄。
在拍摄现场,老人显得有点紧张,老是问我:“扎西,你快跟我说说,我等会儿需要怎样表演,你们答应了我的条件,帮了我的大忙,我也得好好帮你们表演才对啊!”
看着老人的样子,每次开机前,导演把我叫到跟前说:“吉祥啊,你跟老人讲,他不用做任何的表演,他就像平常一样,坐在那里,喝喝茶,看看远方就可以了。”
下午的拍摄很顺利,几乎每一条都过了。最后,导演对老人竖起大拇指,说您一坐在那里整个气场就对了。两个主演也过来夸老人,说只要您坐在那里我们的感觉就来了。面对他们的夸赞,老人一脸迷茫。
第二天我们要转移到另一个场地,我们把东西都收了起来,装到了车里,准备出发。
临开车前,我把一万块和黑牦牛帐篷的租金按之前说的交给了老人,让老人在提前写好的收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老人把钱抓在手里,有点犹豫,说:“我不会写汉文,怎么办?”
我问:“那你会写藏文吗?”
老人说:“也就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
我说:“那就可以了。”
我指了指位置,老人就很认真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上面,写完之后还歪着脑袋仔细地看了一眼,显得很满意。
我准备收起那个收据时,老人说:“你们也没有个印泥什么的吗?我最好摁个指印,这样你们也放心。”
我就叫会计拿来印泥,让老人摁了指印。
老人看了看自己沾着红色印泥的手指头,往衣服的袖口擦了擦,又看了看我,似乎这才彻底放心了。
责任编辑 李倩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