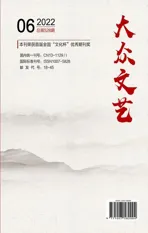从《龙朱》中论沈从文的爱的哲学
——孤独的狮子臣服在初生牛犊的眼睛里
2021-07-12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去爱吧,去爱吧
狮子有最武勇的力,最纯洁的血,最神圣的爱
初生牛犊去放歌吧,去爱吧
将孤独的狮子拢在臂弯
然后相顾万年”
1929年1月,《黑红》的创刊使沈从文的身份从受编辑掣肘的作家转变为能掌握自己写什么的作家兼编辑,这一次身份的转变让一直潜伏在沈从文心中的湘西情节有了宣泄口,湘西那方蒸腾着血性与诗意的土地,一次次成为沈从文构建审美乌托邦的理想之地。发表在创刊号的《龙朱》,沈从文用“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的龙朱开启了苗族族裔身份的认同,以及构建湘西审美乌托邦的历程。在《龙朱》中沈从文用“狮子”,而且是“孤独的狮子”作为主人公龙朱的精神体,这一意象的选择并不仅仅指向龙朱一人,而是从龙朱身上投射出湘西整体的精神特质。而狮子在文中的形象并不着力表现其血性与刚健,而是展露出渴望伴侣的温顺,这隐喻着作家“用爱证明一切”“用爱解释一切”的创作原则。
在湘西小说中,沈从文塑造了一批蕴含着神性的完美男性形象,《龙朱》中的龙朱、《神巫之爱》中的神巫、《月下小景》中的傩佑、《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豹子均可划入这一类形象中。龙朱可以说是代表了沈从文的审美倾向与文学理想。在文本中,龙朱是白耳族族长的儿子,具有非凡的社会地位,但又谦卑有礼,相貌上更是让所有苗人倾倒与称赞,“如日头光明,如花新鲜”。这是所有苗人眼中的龙朱形象,在隐秘的龙朱内心世界中,拥有可以在爱情中绝对优势地位的龙朱却有着忠贞不渝、专一深情的品质。沈从文对龙朱的刻画是毫不吝啬的,无论是正面描写,还是通过他人的侧面烘托,龙朱呈现出来的是有着血性、雄健而又温情、温顺的神圣化狮子形象,龙朱是狮子,狮子也因龙朱的具象化而产生可崇敬,可颂扬的理解路径。
从湘西出走的沈从文,在北京与上海两座大城市中转辗,在经历了社会的疯狂和凋敝,以及个体的贫穷与饥饿后,越发觉得自己“乡里人”与“城里人”的隔阂。外面世界的泡影幻灭后,沈从文也没有选择返回家乡,而是在城市中回望、建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充满血性和自然的湘西。《龙朱》中描绘的苗寨无疑是现实现代社会的一种反照,苗人们狩猎耕种、对歌集会、自然地相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生活在苗寨的龙朱更是一种精神理想,是“情感近于被阉割的无用人”的一种无可比肩的神性存在。龙朱是狮子,卓然不凡的地位、不容亵渎的美貌与之匹配,除了外在纹彩,其内在自由的精神状态才是与狮子相匹配的根源。
狮是百兽之王,是野性、勇猛、刚健的象征。狮子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来源于自身力量的强大,让其他动物恐惧而生敬畏。龙朱是白耳族的王子,是世俗物质观念中的权利上层。但在文本中,沈从文却用龙朱的谦逊和亲切消解了物质权利的压迫,龙朱狮子形象的获得来自他好的风仪,即如神祇的外貌。龙朱的相貌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美,“女人见到龙朱来,识与不识都立起来怯怯的如为龙朱的美所征服。”同时龙朱的美又是不可亵玩,如同神明的存在,这种美离远了女人,让女人们不敢把龙朱当作目标,连做荒唐的梦都不敢,何况是现实中的调情。龙朱的相貌使他成了傲然孤独的狮子,人人都称颂他,但没有人理解他。“一个长得太标致的人,是这样常常容易为别人把名字放在口上咀嚼的。”这种美成了苗人口中的符号,一种具有极高赞美而虚化了其内在的符号,而龙朱的审美理想便在这层符号之下的自由精神中生发出来。龙朱对于爱情的追求是自由的,同样是具有狮子般血性与热烈的。龙朱的精神状态与康德论自由的“我是孤独的,我是自由的,我就是自己的帝王”思想无二,龙朱是独行的狮子,虽然外在客观将他神化而剥夺了被爱的权利,但是龙朱对待爱情仍然是忠贞不渝的,从十七岁到二十一岁,他努力突破一切去寻找爱,也在寻找一位突破一切来爱上孤独狮子的初生牛犊。龙朱无疑能得到配偶,光凭他令人歆羡的地位和相貌,但关乎与“爱”则是难的,是一件大事,龙朱追寻爱情的状态是自由的,一切建构在“我爱”之上,在对歌中遇到了勇敢的花帕族少女的龙朱犹如狮子遇见鲜美的猎物,连看到少女站立之处所生长的野花,也“如同嗅到血腥气的小豹”,为得到少女斫下一只手也不悔;梦到少女便觉得自己业已完成男子之事,更加勇猛有力。龙朱的爱是热泪而具有占有性的,但这种占有性仅仅是出于爱的占有,是完全情感性的。
与狮子龙朱形成对照的是仆人矮奴,龙朱确实是对于现实社会中情感被阉割了的现代人的对照,但矮奴却不是文本中现代人的意象。矮奴对龙朱的颂扬乃至于谄媚仅仅是出于对神明的敬畏,而矮奴借龙朱之光而获得女人青睐的行为也绝不是映射现代人的贪慕虚荣,狐假虎威。发生在苗寨中的一切都是出于爱的驱动。矮奴对龙朱的烘托作用主要体现在以矮奴的滥爱对比龙朱的忠贞,以偷学歌的矮奴来对比用热情音调来表达精纯情感的龙朱,以矮奴的性冲动来对比龙朱狂热强烈的占有意识。
从鲁迅开启的“国民性批判”的潮流,五四新文学潮流兴起以来,作家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共同认知无外乎重建社会价值体系。而沈从文将社会重建的责任寄托在表现爱的新文学之上,认为新文学可以“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在沈从文的创作中,苗族是中国的老地主,就像印第安人之于美国。沈从文回到湘西,回到巫楚文化的原始中,用在山林中用歌声追求心爱女子的龙朱形象去治愈“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懦的大毒”,去“唤起这被现代社会蹂躏过的男子的心”。
用爱解释一切,是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审美倾向。湘西小说中几乎所有篇目都在讲述爱,讲述人性之中爱的善,爱的美。《边城》中悲欢都来自爱,以翠翠为中心的爱;《神巫之爱》因爱不愿做神的仆了,只愿做人的仆,白衣少女的仆;《月下小景》中为彼此保持贞操与纯洁而双双殉情的有情人。爱的哲学在沈从文的笔下,在湘西的土地上展露无遗。《龙朱》中的一切也是因爱而起,因爱延续。如果龙朱不坚定的寻找爱,那就无法构建起完整的狮子形象,就无法引发山头相互试探的对歌,也就无孤独狮子和初生牛犊的爱恋。在文本中,沈从文用爱的权利消解了其他所有世俗的权利,包括社会地位、相貌,乃至时间。龙朱拥有白耳族王子的社会地位,但无法凭借高贵的身份而获得女子的爱情;龙朱长得壮美,是神的权力,但神的权力也仅仅限于此。“至于要女人倾心,是人的事啊!”;从十七岁到二十一岁,齐梁桥洞口没有合龙,痴情的龙朱也没有找到爱侣,时间在爱情前也无济于事。
爱是人最大的权利,这是《龙朱》想要表达的。在苗寨,唱歌是引领男女结合的绝佳手段,龙朱在对歌失势并不是缺乏真实热情,而是在爱的世界里,龙朱所占有的地位、相貌的优势统统不作数,反而成了龙朱拥有爱的阻碍。只有爱,才能在这个世界存活。龙朱热烈追求爱,追求在草席上的疯狂。文本中说“只要是可能,龙朱不拘牺牲自己所有任何物,都愿意。”当然这“可能”绝不是建立在无爱,无愉快之上的,所以龙朱尽可能强来而获得这种可能。龙朱是狮子,人人都认为他是狮子,龙朱也在心底里认可狮子的精神体,也用狮子的血性去追求爱。但刚健的狮子在爱前,在美丽的女人前,器宇轩昂都被女人清冷的目光看得胆怯了。“女人的头发能系住大象,女人的声音能制怒狮。”冲破一切,无所畏惧的龙朱在爱情面前失神失志,焦躁的狮子变得柔顺起来。爱是人最大的权利,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利之上,能冲破一切,所以黄牛寨的三姑娘能俘获青年王子。在文本中可以窥见爱情的原始形态和本真模样。他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或者其他外在条件之上的,而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动。“龙朱既是勇敢追爱的雄狮,也是美好人性的歌者。”
在《龙朱》中,沈从文重返苗族光荣鼎盛的时代,极力构建了一个人神和悦的乌托邦。在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自然生态”中,其中的人们“维持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婚恋心态和情爱形态。”龙朱与黄牛寨寨主的三姑娘在山间以歌传情,两人都是冲破一切利害关系相互靠近,互生情愫然后自然地结合,其中没有任何的纷争,《龙朱》在牧歌情调中纯粹地展示了爱的情谊。龙朱因其对自然之爱的热烈追求而成为一种普世的审美理想形象,而他的谦卑亲切,血性自然,忠贞不渝形象无疑是沈从文注入神性的光辉的结果,这就达成了沈从文“神性即人性”的理念构建。在沈从文的时代,文学就是对神的重塑。“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做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而《龙朱》可看作是这首抒情诗的序言。
《龙朱》和稍后的《神巫之爱》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开端,是沈从文潜入巫楚文化中触摸人性本源的尝试。在《龙朱》中可以看到沈从文建构审美乌托邦的尝试,尝试为国民精神“造神”。用湘西文化,或者更准确地来说是边地文化所蕴含的那种原始、雄壮和生命活力去反观情感被阉割了的现代人,以淳朴的、单纯的生命形式来对抗都市文明的糜烂和腐朽。在《龙朱》的尝试为以后的《媚金、豹子、与那羊》的悲剧情愫的融入有一定的探索,也是最后走向《边城》巅峰的必不可少的一环。
注释:
①沈从文.龙朱虎雏[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本文所有文本引入均来源于此,后面不再一一说明).
②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③黄露.沈从文湘西小说男性形象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9.
④周仁政.巫觋人文——沈从文与悟出文化[M].长沙:岳麓书社,2005:94.
⑤周仁政.论沈从文与巫楚文化[J].文艺争鸣,2016(07):9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