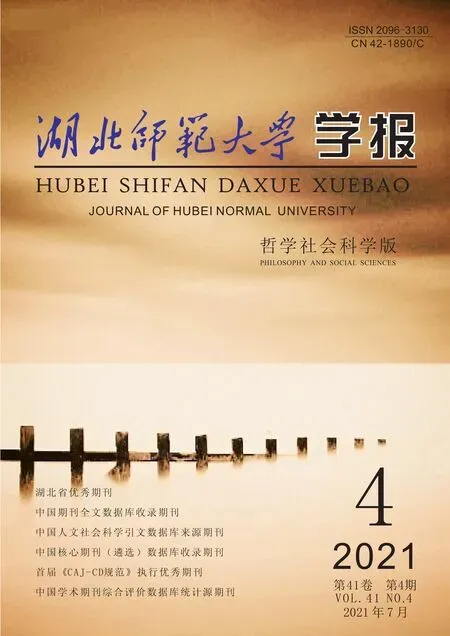盛宣怀是晚清最大房地产商
2021-07-07张实
张 实
(湖北师范大学 汉冶萍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黄石 435002)
盛宣怀对近代中国的贡献,有学者归纳为“创办十一个‘第一’”,包括航运、电报、钢铁、铁路、银行、学校、红十字会、图书馆等。此说流传甚广,反复被引用,唯独不曾涉及房地产领域。[1]
盛氏生前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其详情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据1920年1月盛氏遗产清理小组整理的《估价清册》,其财产总值为银1349.3868万两。其中,上海道契地产估价668万余两,内地地产估价98万余两,合计767万余两,占全部遗产的56.84%。包括汉冶萍公司股票在内的各项股票共估价511万余两,远远不及房地产。据此分析财富来源,盛宣怀这位晚清最大的实业家,首先是个大房地产商。[2]
盛宣怀在房地产领域的经营,无疑是他生平事业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绝非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房地产是一个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行业,它必须投入相应的巨额资金。百年来,对盛宣怀资本专题研究的重大成果不多,似更少涉及房地产经营及其资金来源。盛氏经营房地产,又是与他主持铁路总公司、创建汉冶萍公司等企业同时并行的,而盛宣怀对于他所掌控的这些企业,历来是集财权于一身,资金官商夹杂,中外交汇、数额巨大、范围广泛、来源多途,运作则辗转腾挪、暗箱操作、表里不一、极为错综复杂而又隐蔽、诡秘,散布了许多迷雾,留下了一些疑团。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开天辟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探索他的财富来源和资金运作、积累过程,不仅是实事求是地评价盛宣怀、研究洋务运动的应有之义,对于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也似不可或缺。本文拟就所见的有关盛宣怀从事房地产活动的零星史料,进行初步地搜集、梳理,供学界进一步研究参考,并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杨文骏为盛宣怀在上海吴凇购地
盛宣怀的房地产,主要集中在上海。据《估价清册》,上海道契地产银668.6万两中,除厂房内含机器106.1943万两外,房地计估值488. 2575万两,空地计估值54.1536万两,活本20万两。房地单项估价最高为三新纱厂139.4036万两,其次为通商银行58.4920万两,再次为客利44.6810万两;以下有三新布厂28万余两,静安寺路27万余两,福德里22万余两,沁园、益寿里各19.4万余两;10万两以上的还有西绩效里、修德里、苏州路栈房、五马路2号5号、广福里、福和里、藏书楼等处。空地如西沟144亩余估价20万余两,潘家湾13处计价14.8万余两。[3]
在上海,曾有专人如杨文骏为盛物色、收购吴淞一带的土地。
杨文骏,原籍江苏松江,系杨文鼎之弟。文鼎曾任湖北布政使、护理湖广总督、晋湖南巡抚。杨氏兄弟与盛氏系通家至交。文骏曾任广东雷琼道,因事革职,追随盛宣怀十余年。盛曾先后会奏委任文骏为卢汉铁路汉口分局协理、通商银行总董,使之参与创建铁路公司、通商银行、筹建津浦铁路,并随同盛宣怀从事对日、俄等国的商约谈判。后以道员被安徽巡抚恩铭札派安徽省洋务局督办兼抚署奏折文案。
王尔敏等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计收有杨文骏致盛宣怀函53件,其中约有18件主要汇报或涉及购地问题,可以确定杨曾在上海负责为盛购地。这些信件绝大部分时日不全,又尚未见到盛之相关来信或回复,解读尚有疑难。现将信中透露的有关购地的情况初步整理如下:
(一)购地的一般情况:
1、购地时间:
《杨文骏致盛宣怀函》(以下简称《杨函》)三十五云:
勘凇路约在何时?因前途已去觅地,据云此时银根甚紧,押款均须出售,价必不抬,是一机会。必须先看定地段,然后知所觅之地是否合式。[4]
1876年英美商人曾擅自建筑从吴凇口至上海公共租界的吴凇铁路,后被清廷赎回拆除。1897年盛宣怀奏请用官款再建凇沪铁路,大体仍循原吴凇路走向而延长至河南北路,于1998年运行。
从这些信件的内容看,大致是在盛接办汉阳铁厂、创建铁路公司后,与创建通商银行同时,主要是在1897、1898年(光绪二十三、四年),即凇沪铁路建设前后。
2、购地范围:
主要是沪凇铁路沿线之地,如《杨函》廿七云:
昨谈凇路,此间当在铁马路过去美界外(即洋人打靶处),今日约同友人(即卖地中人)前往踏勘指实,始易商办。惟地系宝山境,小有周折耳。[5]
又如《杨函》十三所言,亦涉及外滩、租界外。
3、购地规模较大:
如《杨函》十二,经买两号粮田,先一票86亩,共合银39560两;后一票45亩余,内除定银2000元外,实找付12538两。另在铁路附近有田20余亩,价每亩约300元。[6]
又如《杨函》五十一,“张园对面沿马路有地一方,计四十八亩,实价银每亩壹千叁百两。”[7]
4、有的可建房出租:
《杨函》五十一云,有地一方,计六亩零,坐落在会审署后新仁庆里对面:
计实银叁万五千两,可包造头等石库门住房一百间,共约费银一万五千两,共合计数五万两正。每月每间可租洋六元,造成核算行一分利息。[8]
(二)杨兼为盛宣怀私人购地
1、界石所用字号:
《杨函》廿五云:
凇地已请经手人去勘丈,惟如何交银?如何立界?契上如何写法?钧乞详示遵办?
界石是产权的标志,地契是产权的凭证。之所以要请盛“详示”,显然是涉及到所有权。又《杨函》二十云,美界外地系“用福寿堂名,不用公司字样”。如此,这些地系为盛所有。表明杨文骏不只是为铁路公司购地,也同时为盛宣怀私人购地。[9]
2、盛宣怀拟组建地皮公司:
《杨函》廿五云:
地皮公司章程应以集若干股?是否造厂栈出租?抑专买进卖出?并求示及,以便代拟。
《杨函》廿一又云:兹将地产公司章程拟呈裁酌,细思亦无多余条款。[10]
当时趁修建铁路之机抢购土地牟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郑观应已在吴凇“自买”之地有50余亩,同时又拟购汉阳枪炮厂外之地数十亩,当得知盛宣怀派他在武汉兼为铁路公司购地后,转思私买此地不妥,于光绪廿三年正月十四日致盛函,报告此地应派人速购。并一再向盛建议“凡经手现买之地应尽归公司,……如有私买,查出撤委,严其赏罚”。但又提出“如经手要地若干亩或入股银若干,准其声明注册”。可见利用职权、假公肥私、囤聚土地已是公开的秘密。[11]
(三)购地的一些伎俩
在卢汉铁路购地前,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九发布《铁路两旁田地严禁争买居奇示》,对公众宣布,“凡铁路经过之处两旁田地,严禁私相买卖及倒填年月、高抬时价等弊,并饬各地方官六个月内不准印契”等;于同年五月十五日又发布《开办铁路收买汉口民地示》,公布所勘地界会同地方官查明平常实价后拟定的官价,一律按官价收买。[12]这些应有的规章制度,在盛宣怀、杨文骏为沪凇铁路购地时,都成了官样文章,经办的执法者在私下里利用职权违法抢购。
1、 秘密行事:
《杨函》三十五云:
此事非但公不能出面,连骏亦不宜出面,恐人知骏所买,价亦必抬。现与友人约定,俟前途告知友人,由友人再同骏往,庶可不露风声。[13]
又如前述《杨函》十五,反复强调:“此事初办,因格外秘密,作为骏所自买,铁路之合用与否,不能明以告人。”“归款后亦不必告人为是,免滋物议。”这就不仅是防止卖方抬价,而是做贼心虚了。[14]
2、抢在铁路建设征地告示前购地:
《杨函》廿六云:
至美界外地,已约定明日天晴即往看视,以便寻觅地主与议。告示咨文,万不可早发,须迟至五、六日,方能有眉目,太促则来不及,至荷至荷。[15]
此信写于廿八晚,“迟至五、六日”当指下月。这是他们购地的一大关节,《杨函》二十亦云:“必须赶办,告示一出,即不能办矣。”
3、利用权术、官势,低进高出:
杨文骏曾一再为盛出谋划策,《杨函》二十云:
鄙意更有一办法,如出示定价以后(不宜过宽)或做不通,用权术用旁人转买。彼时或照用官势急图,稍得价卖出。此一办法,唯不可稍露口气,使人看破,则又不能办矣!
《杨函》廿一又云:
拟用声东击西法,先行列立公司界石,外人不知,必相争买,可以设法卖出。水深水浅一层,请勿为外人道及,并请称道得用,骏即有文章作矣!一经说破,则更难着手。[16]
函中公司系指地产公司。总之,集中到一点,无非是利用修建铁路的权势,倒卖地皮而非法牟利。
(四)导致地价大幅上涨:
由于盛宣怀等人的炒作,加上怡和洋行等的竞争,直接导致上海地价飞涨。
《杨函》廿二云,陶地“据周长庚言又翻议,须三百五十两外,再加费。”
《杨函》十九云,“因周长庚刻来言,吴凇前言三百元者,今非三百两不肯。陶地廿四亩已为怡和还价四百余两。”
《杨函》廿六云:“凇地今日议了一日,不敢放手,前途坚欲照索价每亩四百六十两,不肯减让分毫(已有风声、尚不了了),用钱在外。时不可失,只得允之,即先付定银三千(免再中变)。”[17]
(五)杨文骏为之垫款、认亏,身后亏累甚巨:
函件显示,杨文骏为盛觅地、看地、议价,经请示同意后付定银、丈地、立契、直至付款成交,均是亲自经手办理,有时并为之代付定银或垫款。《杨函》廿五云,“昨代定银三千,系暂时挪付,不可久也”。 《杨函》廿九云:“许家必须见银乃可交契”,“是否即由敝处暂时垫付,将来统行结算,乞示遵。”[18]
吴凇购地,前期曾有周折。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盛宣怀致郑官应函云:
吴凇之地,顷据锡乐巴面禀:北边一百四十四亩,及吾兄自买之五十余亩,均属无用。惟南边一百数十亩,尚属可用。[19]
锡乐巴是铁路工程师。写于“新正十九日”的《杨函》十五,当是文骏对误购无用之地的反应:
此事初办,因格外秘密,作为骏所自买,铁路之合用否,不能明以告人。又因告示不能久搁,促令迅速定议……而使公款虚悬,至贻我公之累。
看来杨既惶急,又委屈。在信中反复认错道歉,最后提出:“现与友人一面筹款,一面设法转押,总使先弥补公款,以清公累。地归于骏,甘认私亏。”[20]
又,《杨函》四十六所述一事,大意是盛在吴凇有块地,长期押在源丰润,该号时来催询欠款,最近催促更紧,“该号明言:宫保交替在即,若不趁此了结,将永无了结之日。并言情愿减折。”所谓“交替”可能是指盛将交卸铁路公司。此地抵押也是杨文骏原经手,杨不得已与凇沪铁路有关人员商议,拟请将此地作为铁路煤栈之用,“务乞宫保始终体念职道因公受累,几及十年”,亲自出面说说话。[21]
杨文骏在广东被革职,曾有“永不叙用”的前科,自言“十年蠖伏,坐吃山空”。为了复职,他费尽心机,多次乞求盛宣怀为之运动、保举;去安徽作幕僚,又得到盛的照顾,为之保留“沪薪”,这都是他对盛宣怀诚惶诚恐、竭力效忠的重要原因。不想他好不容易重新得到了官职,不久便去世。宣统二年春,时为署理湖广总督的杨文鼎写信向盛宣怀求助。原来文骏身后亏累甚巨,其中在通商银行押借一款,现将届期。此前历次息银,都是杨文鼎代付,现在他自己经济困难,“已到山穷水尽”,而“亡弟眷属众多,子侄皆不能自立,全恃薄田数顷为养命之源,万不能不设法赎回”。他提出文骏曾被奏派为通商银行总董,为之效劳“而并未领过薪水,亦未得过利益”,恳求盛主持公论,会商通商银行各董,设法取消此款。[22]
读到杨文鼎此函,便会联想到文骏因为购地而认亏。虽不能确知此项通商银行的押款是否与其经手购地直接有关,也未确知这项押款后来是否取消。但可以确定的是:从事房地产是需要大量资金及时投入的,有时文骏为之挪垫,说明盛宣怀曾屡有力不从心,资金周转不灵;从事房地产投资又是有风险的,此次购地已经出现严重亏损,却是经手人杨文骏不得不为盛大人承担了一部分。
盛宣怀内地的房地产主要在武汉
盛宣怀在内地的房地产,合计估价银98.4090万两,武汉占了大半:房地产估价计银56.3059万两,其中地产42.2495万两,房产14.0564万两。
接办汉阳铁厂的初期,盛便开始在武汉大肆囤积土地。如同乘修建凇沪铁路之机在上海大肆购地一样,盛宣怀亦乘修建卢汉铁路之机在武汉大肆购地,都是利用他督办铁路公司的职权。
(一)光绪三十年除夕夜抢购大智门地皮
京汉铁路通车时的汉口火车站在大智门。据遗产《估价清册》,盛在大智门土名河嘴处,有地1471方,估价银8.8260万两,又在大智门何家墩有地2398余方,估价10.7919万两。[23]
光绪三十年(1904年)盛宣怀设立公顺公司,经营房地产,对人说是众亲友办的。这年年底,黄河铁路大桥已竣工,芦汉铁路南北已联成一线,盛与汉口的大房地产商刘祥作了一笔大生意。
大智门原是汉口城堡的城门,原址在大智路与中山大道的交汇处,本是进入汉口城的主要通道之一。当时在大智门城墙附近,有地6000余方,每方实价洋例银23两,约计银十三四万两,双方初步达成草议,已交定银4000两。时至年底,汉口的原经手人去电向盛报告:“因湖堤兴工,地价骤涨,拟俟自明正加价出售,必须年内成交,方免异议云。”盛认为来电“不言丈量实数,但催成交,殊不合”,于腊月二十六电令汉阳铁厂负责人张赞宸介入此事,与熟悉情况的施子卿督促原经手人妥办。“已汇洋例三万交施,或先立契,付银三万,余款分两期付,均祈酌办,勿生枝节为感。”显然是志在必得。张赞宸不敢怠慢,找施子卿商议,施认为“汉口买地最多轇葛,必须有道契;四址丈量清楚方可成交。”张于廿八日如实向盛复电,以为“为数过巨,总应慎重”。廿九日除夕,张查明了原委,土地并无纠葛,因要年内成契,对方催款甚急:“今日不付定银作罢”,要求即先付半价。张致盛电云:“现已除夕酉时,宸何从另筹数万?顷奉宪电,又切托子卿,渠云地事断不敢经手。究应如何?乞速电遵。”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光绪卅一年大年初一的凌晨三点,迎新除旧的万家鞭炮声中,上海盛宣怀致电汉阳铁厂张赞宸:“先付半价可行,惟接电已过除夕,立契付价可约正初,候速复。”[24]
有必要略作补充的是,日后大智门不仅是汉口火车站的所在地,且面临法国租界和联结粤汉铁路的长江码头。自京汉铁路通车后,辛亥革命后第三年徐焕斗即在《汉口小志》中为之慨叹:“繁盛极矣,南北要道,水陆通衢,每届火车停开时候,百货骈臻,万商云集,下等劳动家藉挑抬营生者,咸麇集于此。”[25]这里成为武汉三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寸土寸金,引领风骚百余年。
这只是盛利用掌握铁路建设信息、进行土地囤积居奇的个案之一。
(二)盛宣怀在汉的房地产大都是黄金地段
在《盛宣怀未刊信稿》中,收录有一篇《椿孙应办应问各事》,时为宣统元年冬月,看来椿孙是他的堂兄弟,驻汉专事房地产管理。[26]
此件涉及的新购地段,分别在汉口谌家矶、张美之巷口、后湖王家墩、大智门外、英租界和武昌戊字段江边等。其中:
谌家矶在汉阳铁厂对岸,为汉水与长江交汇处,是汉江流域物资聚散中心;张赞宸曾在此购地拟建萍乡煤矿码头,张謇、郑孝胥等与汉冶萍合股兴办之扬子机器制造公司设厂于此。在京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之前,谌家矶至玉带门一段铁路就已于1903年率先通车。王葆心《续汉口丛谈》说:“自卢汉铁路开行后,廛居鳞次,则上自硚口,下延直至今谌家矶矣。”[27]
张美之巷是今民生路的前身,俗称六渡桥,南临长江招商局码头,北至中山大道,两侧有花楼街贯通东西,是百年繁华的“老汉口”核心商业区,长盛百年、声名赫赫的娱乐中心新市场(民众乐园)亦在此。
汉口的租界自江汉路起,大体是在今中山大道与长江之间逐渐向下游发展。以英租界为首,据有江汉路至合作路之间的区域,其中与江汉路垂直的胜利街、鄱阳街、洞庭街横贯其间,这里聚集着著名的银行、洋行、钱庄,商厦大楼、高档饭店、西式餐厅,兼有教堂及其附设的医院、学校,集中展示着异国风情的、各具特色的西式建筑,配备有良好的水电供应、邮政电信服务等公用设施,自晚清至民国长期是西方冒险家在武汉的乐园。
汉口最早的市区是在长江与汉水交汇的汉正街一带。京汉铁路通车后,市区扩展的基本趋势是:以今中山大道为中轴线,沿铁路线向内扩张和沿长江向下游扩张相交汇。上述盛所购的这些地段,遍布汉口的东西南北,除王家墩(即今航空路)当时较边远、1930年后曾为军用机场外,皆是当时汉口新建市区的黄金地段。
(三)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地价飞涨
1、卢汉铁路修建前购地的官价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十五日,张之洞发布《开办铁路收买汉口民地示》,宣称对于铁路用地,已派委员会同汉阳县查明民间平常买卖价值,分别高下,拟定官价,一律给价收买。其中:宗关一带民地每亩给官价制钱20千文;玉带门外至皇经堂以上每亩13千文;通济门至上至大智门,下至万家庙每亩10千文;万家庙至滠口、大智门上至玉带门每亩8千文;其内有菜园地分别酌加津贴;不能种麦的沙地、不能种植的湖地每亩4千文。[28]地价主要是按地段区分,兼顾土质。
2、京汉铁路通车前夕1905年初的地价
前述盛宣怀在光绪三十年除夕所抢购的大智门之地,每方银23两。我们注意到,此时土地的计量单位是“方”,即是一亩的六十分之一,而计价的货币单位是银两而不再是制钱。如此,此时大智门之地每亩价为银1380两,约铁路开工前的一百多倍。
3、京汉铁路通车后1907年的地价
(1)刘家庙火车站铁路两侧地价每方约25两左右。
1897年盛宣怀与比利时签订《芦汉铁路借款合同》,次年比国修建铁路工程人员来汉,乘铁路购地之机,在刘家庙火车站铁路两侧,私购民地3.6万平方丈(约合600亩),每亩地价银10两。比国提出在此建立租界,遭到张之洞拒绝,争执达十年之久。1907年张之洞提出赎回比国所占土地,该国领事要价每亩1363两,是原价的136倍多。[29]张之洞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八致度支部电称此地“极繁盛、极昂贵”云:
鄂省前借款购回比商在汉所买租界一段,因该处前滨大江,后跨铁路,北端紧接铁路车栈、马头,为将来振兴商业最相宜之地。正拟修通马路,建造市廛,……三数年后,该地约可值银数百万两,……故彼时向法商及中国商号借银九十万两,费尽无数操纵之力,始将此地购回。[30]
按此九十万两概数估算,此时刘家庙水车站铁路两侧地价已至每平方丈约25两左右。
(2)万家庙沿江每方100两以上。
1907年七月十二日,在汉口经办购地的李道谦致电盛宣怀称 “厂矿亩价已增五十倍。”七月十六李又托李维格向盛电告:“堡垣每方扯价四十五至五十两,万家庙沿江每方一百两以上,不沿江扯五十两,宗关三十五至五十两。”堡垣或城垣,当指汉口城堡的墙垣,时已拆除城墙建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31]
(3)日租界江边分金炉每方120两。
同年七月十八,卢洪昶等去电向盛报告:“东福、分金炉两地二百四五十方,屋岸俱在内,宋伟臣云,索价三万五千两。极力磋磨,总在三万上下,不能再减。厂地与此相连,非得不可,得之以成码头。”后以三万两成交。[32]分金炉在日租界外长江边,按此计算每方价约120两以上,系为汉阳铁厂购买。
4、辛亥革命后地价
随着租界的日趋繁华,租界附近地盘的地价亦趋暴涨。至辛亥革命后两三年间,如前花楼至黄陂街一带的传统市场中心,地价高至每方银400至500两。[33]
5、盛氏遗产清理小组1920年所估地价
按《估价清册》所载数据,现将其中武汉房地产按每方平均价排列,如下表:

类 别地 名方 数估价(两)平均每方(两)房 产张美之巷 281 70375250城内半边街 342 61596180城内太和桥 61 8593140地 产英租界 658 118477180日租界外分金炉 320 44839140大智门河嘴1471 88260 60大智门何家墩 281 107919 45谌家矶沙套4500 45000 10武昌东兴洲外三马路3000 18000 6
试将遗产清册中的估价,与上述武汉地价史料比较,有两点值得注意:
(1)遗产清册中的估价,与十几年前的地价相比,似明显偏低。
如同是在传统市场的中心的张美之巷,其房价估值竟只有十多年前花楼街、黄陂街地价的一半;分金炉之地1907年购价已是每方银120两,十多年后估价仅增加了20两;大智门之地的估价尚不及1907年分金炉、万家庙地价之半,与1914年前后中心市区的地价更为悬殊。在划分遗产时,盛家子孙争着要房地产,一致将股票推给义庄,看来清理小组很难背离盛家主人们的共同意愿,这些武汉房地产的估价,不过是在原契购价上象征性的略加点缀而已,似不能准确反映当时地价的市值。
又,内地常州、北京、烟台、南京的房地产,九江、武昌的铁矿山,《清册》都是“照购进时原价”估价。[34]
总的看来,当时盛家房地产的市值,应比遗产清理小组所估价更高。
(2)日租界外分金炉之地,史料记载原为汉阳铁厂所购,备作码头之用。在《估价清册》中却列入了盛氏的遗产。[35]
盛宣怀被参:“擅售公地、勒买民田”
恭亲王奕诉曾当面对盛宣怀说过:“君以一道员屡参不动,受恩不可谓不深。”盛家以此向人炫耀,不啻是公开承认盛宣怀确系被朝廷包庇。[36]后来盛又一再被参劾,有的就是因为买卖土地而引起。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八,军机大臣接到上谕:“有人奏:商约大臣盛宣怀贪鄙近利,行同市侩,并有擅售公地、勒买民田情事,请旨饬查等语。著端方按照所参,分别密查,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片著钞给阅看。”[37]
六月初二,盛宣怀电令在京的亲信陶湘探听被参的内情。陶奔走半月,从军机处、《北京日报》、及天津袁世凯等处得到的信息是:御史广东人陈庆桂上奏,参劾岑春煊骄蹇不法,有贪、暴、骄、欺四大罪,列了八条,其中多处牵涉到盛宣怀。另有一附片专劾盛,一是“沪宁路旁购地事,谓‘私卖官地,勒买民田’”,另一则是说盛与岑合资经营。慈禧的处理倾向鲜明,将参劾岑的各条“留中”;只将盛的两条摘出来,交给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查办。至于陈庆桂何以有此一参,陶湘打探到的信息是:对于铁路购地事,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等人本来就有议论,此次岑春煊进京极力奏保盛宣怀掌管邮传部,遭到唐绍仪等人极力反对,散布岑春煊出任邮传部尚书是受盛怂恿,而且盛在暗中资助岑。[38]
看来,在丁未年岑春煊、瞿鸿衤几联手企图搬倒庆王奕劻、袁世凯的政争中,不仅铁路购地成为对方反击的炮弹;而且盛宣怀与袁世凯北洋官僚集团争夺邮传部的斗夺,已经白热化了。
九月二日,苏松太道瑞澂移文轮船招商局,引用了端方的札文:
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札:奉上谕,饬查商约大臣盛宣怀被人奏参各节,内有“商约大臣盛宣怀前充招商局督办,用局款购置上海地产,弊端百出,有用本局及总办出名者,有用福昌行出名者,且有假用英商密尔登出名者,皆盛一人经手,价涨视为已业,价落拔归公产。(原参仅此点出数语,并未指出通商银行,亦未须查现有地产若干等等,如△出之语,南洋所查似系原参以外之事。)饬即逐一调查,究竟盛大臣为招商局经购地产共有若干,价值若干,各地产卖主为谁,有无另用总办及福昌行、英商密尔登出名报契之事,该地产既以公款购置,因何不用招商局出名?原奏谓其价涨视为已业,价落拨归公产,究竟该大臣现有地产若干?某股系某年所购,购自某人?有无由招商局总办及福昌行、英商密尔登名下拔归己有之产?通商银行之地座落何处?是否即旗昌抵归招商局之产?(此三语系应查之事,现有地产若干及通商银行,则原参以外之事也。)详细切实禀复,不得瞻徇,致干未便”[39]
上述札文,编者用( )标示者,应是有人在原件上加了符号和批注,比较原参件与南洋来文,明确那些属于调查范围,似系指示如何应对调查。这个批注者可能就是盛宣怀。
九月初六,盛的外甥、总管家顾润章,在招商局会办王存善处见到了瑞道台的移文,向盛报告了王正在拟办复文及其要点。并提出:“查风华公司及五福堂产业,均已抵押在外,由洋人出名,……通商银行之产,现已押在三德堂,道契内过户,由英领事处批注,未知道署底册亦曾批改否?”他打算去领事署探询后,再转告王存善酌复。[40]
九月十三日,招商局回复称,盛宣怀在其督办任期内“以局款置买局产,地契完全,地势合宜,地价逐年增涨,似无弊端,亦无盛大人一人经手用局款、用福昌行出名,价涨视为己业,价落拔归公产,及由招商局总办名下地产拔归盛大人之事”,并将查明的盛在任时“所购局产地段、亩分、买卖主名、年月、银数,计道契、印契共十八起”,据实开单,备文咨复。即针对原参提出的指控,全盘予以否定。而对移文另行提出的问题,回复是:“至通商银行之地,在招商总局南首,非招商局产业。及盛大人现有地产若干?某股系某年所购,购自某人?招商局无由知悉。”拒绝回答,与上述引文中批注的口径是一致的。[41]
十月廿七日,盛奉旨进京前,在汉口以密函致宗子岱。宗是端方的亲信幕僚,又是盛的姻亲,是盛可以委托办事的人。
密函开头说,本来打算从武汉回上海时叩谒端方“面谢一切”。又提到“此次蒙陶帅奏请御赏匾额”,即前一年徐淮海及皖北相继水灾,盛出头协助端方(号陶斋)办义赈,这年秋天赈务结束,盛获得了御赐的“惠流桑梓”的匾额。[42]看来此前盛与端方有过合作,还是有交情的。
密函中说,“道署幕友多方吹求”“遂致误会”,“查来查去,迟迟不复,尚幸莘君于谒见主人之时探明,主人并无意见”。莘君当指瑞澂,字莘儒;主人似指端方。看来其中不无周折,最终还是端方表态才能定案。虽然此信盛是写给宗子岱,有些话其实是说给端方听的,如以第三人称口气说的结论性意见:“总之,该大臣创办招商局三十年,交代时产业值银一千数百万,接办之人即系反对之人,如有丝毫弊病,早已为人所揭,何待今日。”宗一定会原原本本向陶帅汇报。
此密函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盛说得很明白:“通商银行之地,招商局复文查明,非招商局产业,此为紧要关键。”并在“非招商局产业”六字下加了着重号。接着历数通商银行之地的来龙去脉,其中涉及到李鸿章的李守慎堂和盛的五福堂,但“其实早已卖出矣”。最后盛的嘱托是:
主人于该大臣素尚爱惜,曾由尊处询及瑞公如何,意极可感,谅不致忽生波折,但主人公事繁多,或交与幕僚随便拟稿,万一稍不留神,露出“五福堂”三字,便与人以疑窦矣。不怕有心,而怕无心,务乞迅速密陈主人,是为至祷至感。
在署名后又追加了一句:“抄件密览,即付丙丁,或仍寄还亦可。”[43]
此次盛宣怀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四进京,极力活动,被劾之案似不了了之,次年二月补授邮传部右侍郎。但三日后仍令其以商约大臣原差回上海。
在明眼人看来,盛氏在密函中絮絮叨叨地诉说通商银行之地早已卖出,不啻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今天我们拜读盛氏遗产清册,通商银行之地赫然在目,公估时价银58万4920两,居盛氏在上海房产之第二位,仅次于三新纱厂。[44]
盛宣怀投资于房地产的资金从何而来?
当我们了解到盛宣怀拥有巨额的房地产时,自然浮起一个疑问,这些投入房地产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盛曾宣称“某家素有富名”,用盛氏自有资产从事房地产交易,自然是无可非议。关键在于,盛既是官身,又集铁路总公司、汉冶萍厂矿等企业的财权于一身,既具有利用职权大肆倒卖房地产的权力,也控制了巨额的公款,不受监督和制约,有可供挪用的条件。
此类私人从事投机性的经营,资金运作十分隐密;如果是违法的暗箱操作,更难取得确凿的、直接的证据。但也不是没有一些相关的史料,可供我们思考:
(一)盛氏原有家产似不足以供给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
盛宣怀曾有两种极端的说法。光绪十六年向张之洞哭穷,声称早年在湖北办矿亏损,“空赔公款十五万”“宣怀以此败家”。如此说来,当时其家产充其量也不过是数十万两而已。[45]一次是光绪卅三年五月向岑春煊辩解自身清白而炫富:
惟某家素有富名,实不自今日始。同治丁卯,李文忠督两江,即命故父招股开张公典三十余家,以便劫后穷民。癸酉创轮船,庚辰创电报,即替出典当首先入股。又蒙圣恩,关榷十年。故乡田园,浙广别业,多属旧物,斑斑可考 。[46]
据遗产清册中《各公典股本存款清表》记载,13家公典股本、存款合计银35.5928万两余,平均每家股分、存款各一万两左右,规模都不大。[47]袁世凯将电报收归国有时,盛缴出900股,原面值每股一百元,共计9万元。“替出典当”也好,早期掌管海关十年的正常收入也好,恐怕都不足以造就晚清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
(二)家信透露其热中于房地产而无现钱。
《盛宣怀未刊信稿》附录《致妻庄氏家书(十四件)》其中第二、第三、第四件,写自汉口,时间为十一月初一、十五、十二月初三,考其行踪,应是光绪二十四年。盛在十一月初一日信中说:“诵先、葵荪所说房屋,我目今无现钱,回家两年,家用与亏折银数,你当可知道,现已亏欠不少,明年只好售出股票还债”,“总之,我家财运大坏,住房不利,做事无不亏折,须俟搬屋之后,方可做生意。”信末又说:“如有好市房,冬月底我回可靣商。”透露了盛正热衷于投资房地产,有专人搜集信息,但又感到资金支付能力与之不相适应,处于矛盾之中。[48]
(三)盛妻庄氏曾挪用企业公款作投机生意。
光绪廿四年十二月初三日,盛致庄氏的家信中透露,庄氏囤积倒卖米粮,有七千石米价系占用铁路总公司资金未还;光绪廿五年盛赴保定验铁路工程后入都,八月十一日致庄氏函云:“汝所存之纱一千二百五十包,银根太巨(约银九万两),华盛亦难久欠。”[49]华盛当指华盛纱厂。看来盛家私下里挪用企业公款作投机生意是家常便饭,而此次占用的公款,便大大超出了盛拥有的电报股票面值九万元。
(四)盛宣怀安排金忠赞同时兼任铁路总公司和汉冶萍总局两处的收支。
金忠赞,字匊蕃,在《汉冶萍公司呈农工商部注册局文》中,名列“公司创办人,现充厂矿办事总董九人”之一。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七月,盛先后电令金为铁厂和萍矿分别偿还礼和银行、比国郭格利厂、信义洋行等处到期的本息。总局“专管账目,毫无存款”,当时金既是汉冶萍厂矿总局的收支,又兼铁路总公司的收支,身兼二任,动用的是铁路总公司的存款。一笔系“去年十一月寄存在伦敦的英金三万数千镑内”,另一笔系去年“十二月初三交存先令的二万镑”,这五万英镑均作为汉厂、萍矿借总公司之款,按月息七厘计息。此处“先令”是盛控制的一家皮包公司。这些电文还透露了盛正在用铁路经费炒卖外币。[50]
金收支身兼二职,显然是盛宣怀的特意安排。盛如果以权谋私、挪用公款炒地皮,在督办铁路总公司时,最方便的是挪用铁路拨给汉阳铁厂的、每年高达百万的预付轨价。
(五)日领事获悉盛宣怀将企业贷款供私用。
光绪卅三年萍矿与大仓洋行签订借款合同,日本驻沪总领事永泷向国内报告,慎重指出这次贷款“另一部分似将供盛氏自己私用”。[51]在盛交卸铁路总公司之后继续炒地皮,最有可能的是从汉冶萍的对外借款中分一杯羹,此外盛似难以随意调动巨额的资金。
(六)商部对铁路经费使用、铁厂萍矿亏损有怀疑。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商部派人调查汉冶萍厂矿账目,重点了解汉阳铁厂预支轨价及萍矿借款情况。四月十二日商部尚书载振上奏,直指盛宣怀:
至其承领官款一千余万两,除卢保、淞沪业经奏销外,其余动拨各款因不免辗转挪移……路款自以卢汉为最巨,承办各员,往往视为利薮,因之起家,其不无浮滥可知。……
综计厂矿两项,结亏至五百六十九万余两之巨,此中底蕴,已可概见。至于历年收支款目,头绪纷繁,彼此轇轕,非旬月所能钩稽。
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儿子,他的观点很鲜明,但也没有举出证据。
我们对于盛宣怀投资房地产的资金来源提出疑问,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历史事实,盛宣怀自光绪二十二年接办汉阳铁厂,至民国五年去世,二十多年间,汉冶萍厂矿无日不是资金短缺,嗷嗷待哺,供不应求,债台高筑;而盛宣怀也往往是拆东墙补西墙,自称是焦头烂额、穷于应对。怎么会突然冒出高达七百多万的房地产呢?
纵观盛宣怀大肆经营房地产,大体是在创建铁路总公司之后,至辛亥武昌起义之前。这一过程与其主持铁路修建、督办汉冶萍厂矿、组建商业公司相重合。
在此期间,盛控制着两项巨资,不断引起政敌的疑忌、舆论的非议,并一再遭致言官的弹劾:一是户部拨款的铁路专用资金约一千万两;一是独自操作、历年以汉冶萍预收生铁、矿石价款名义从日本银行获得的贷款共计高达2173万日金。[52]这两大项巨资,来源于盛的亲自运作,既由盛亲自控制、支配,使用也由盛亲自审批、报销。在实际使用和支配的过程中,盛是不受制约与监督的。
对于盛宣怀来说,在他的全部经营活动中,资金的运作实际是相互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大可能各自独立、割断相互往来。恐怕谁也不能保证其纯然是用自有资金投资房地产,而与上述财政拨款、企业资金泾渭分明,秋毫无犯。
我们都知道盛宣怀是亦官亦商,他正是充分利用这种特殊身份,一方面效忠慈禧和专制王朝,追逐权势,一方面利用权势来发展经济,追求个人财富的最大化。当他兴办轮电、铁路、煤铁厂矿时,是引进先进生产力,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方式;而当它利用权势从事房地产投机时,这些积极作用便大为消减,而负面影响却大大地突出了。
无论就晚清的法律、官场规则、企业财务制度来说,官员动用公款从事商业投机牟利都是违法的;而将公款购置的房地产据为私有更是贪污犯罪。
盛宣怀后半生以大量精力经营的汉冶萍厂矿,从在建之时起就资金严重短缺。盛宣怀接办后的基本事实是,资金供应始终未能缓解,长期负债经营,对日本贷款依赖越来越深,终于坠入日本侵略者的陷阱,断送了生机。正是在汉冶萍这个长期亏损的穷庙里,产生了晚清的首富盛宣怀,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穷庙富方丈”的先河。
百年来的盛宣怀研究,曾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从怒斥其为“大买办官僚”“内奸”“卖国”;[53]到推崇其在近代史上创办实业等“十一个第一”的贡献,并运用剩余价值规律论证其财富积累的合理性。[54]我们的历史研究,应是一个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识过程。清理盛宣怀的遗产,其实早已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真相:盛宣怀并没有将他积累的财富,大多投入汉冶萍的煤铁再生产,而是利用职权投入房地产投机;他的财富急速增长,也不是由于汉冶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而增加了剩余价值,却主要是由于房地产暴涨而暴富。有的学者曾经给盛宣怀加上了三顶桂冠: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看来还应该实事求是地再增加一个头衔:晚清最大的房地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