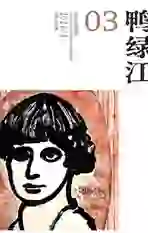诗外文章“诗”“思”“史”
2021-06-30彭定安
在拜读王充闾先生的新著《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的过程中,我就想起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论述的“基底”:“诗”与“思”的一体性以及“诗”“思”“史”三者“生命体”性质的不可分割。这实际上是这部著作的主体性在我的领会中的客观反映。的确,《诗外文章》的思想与艺术分析的骨干和有关的论述,都贯穿着这种思想文化品质。这一点的详细论证,我且留待后续段落里来申说,这里先从著作的产生说起。
惟博学者方能为
打开这部诗歌选本及其诠释,就能感受到,此非一般学人所能作,唯博学者方能为。首先,选择便是一个难题,非浅学者能够胜任。
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谈到“选本”问题时,曾经提出“选者的眼光”这一命题。他的意思是,选者“眼光锐利”和“见识深广”,选本才能准确(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这两个前提条件,这里也暂时搁下不说,且先说这“前提”的前提:要做到這样两点,其前提则是博学。这一条,充闾先生可谓绰绰有余。他家学渊源,幼习诗古文辞,博学强记,积学丰厚,及长又日积月累,胸中自有古典诗词渊薮。常见他于谈话论学中,随口即出适用的诗词典故,它们几可说是他思维与述说的“词汇”。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古典诗词之“知根知底”。这是他完成此著之前提——“选诗”的强劲基础。而其所选,以我的粗浅感受,有许多个“敢”字堪赞:他敢选习见之作(不怕解不出新意);敢选孤僻之作(不惧人谓孤陋寡闻);敢选选本皆不选之作也敢不选习见选本皆有之作;敢选唐宋诸多名家大师之非著名之作;也敢不选他们的其他选本必选之名作;敢选诸多“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之作;敢选虽为名士但诗作并不著称之人之作;等等。他如此作为的基准,就是诗作要符合他的这部著作的标的:富于哲理。不过,通读全书,有的明显地看出其哲理性,有的则初看缺如,而于诠释中揭示底蕴。这些,就看出那种如鲁迅所说的“眼光锐利”和“见识深广”了。比如《诗经》可弃《硕鼠》之类而选“爱情诗”《蒹葭》但作新解;又如对唐宋著名诸家如唐之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杜牧、李商隐,如宋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李清照、陆游等等的作品“选”与“舍”,都表现了这种眼光之锐利与见识之深广。同样,于诗人之取舍上也是如此。如乐昌公主、梁锽、灵澈、花蕊夫人、道潜、冲邈、秦略、偰逊、湛若水、江阴女子之入选以至苏曼殊、邹鲁诗作的收入,也都表现了这种“锐利”与“深广”。
博学——眼光——披沙拣金——剔掘内蕴——深度解析,这就是本著的学术路数与文化内蕴。
“诗”“思”与“史”相融会
至此,再回到前述的“海德格尔联想”。
海德格尔认为,在、人、思、言、诗是同一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其家中住着人。”“必须有思者在先,诗者的话才有人听。”这就是说,“话—语言”有两种形式:“诗”和“思”,它们俩密不可分。而人就活在“话—语言”这个家中。同时,一方面是人创造了“历史”,另一方面,人又生活在“历史”中。所以“诗”“思”“史”是一个生命体,共同构成了人的“家”。这些都很恰当地适用于《诗外文章》的文化内蕴,也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思想内蕴体现了海氏的这些论说。充闾先生笔下生花,剔选出自古至近代的中国富于哲思的诗歌,对其中蕴含的种种哲理与情愫予以剔抉、揭示、并加以言简意赅的诠释。
以上所言之各项,是相当丰富和意味深长的,包含着哲理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文学的、审美的以及创作心理的等等。在这里也表现了博学的特长和优势。书中每一篇的题目就是一个“立项”,揭示一种哲理。诸如“出淤泥而不染” “持盈保泰廉而后可”“人心险于山川”“公道自在人心”“种蒺藜者得刺” “师法自然”“瞬息浮生”“行者常至”“语浅言深” “功成身退”“寒操劲节” “推己及人” “処惊不变” 等等, 几乎涉及中华文化DNA中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生命哲学、人生感悟、社会事理、知人论世、处世哲思等等内涵。这里自然关涉“诗”“思”“史”。
海德格尔还有一个妙论:由于各自语言的不同,所以欧洲人和东亚人“也许栖居在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这是他在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手冢富雄教授的一次对话中表述的。他使用了“也许”的猜测语式,实际他说的很正确。其所谓“东亚”,当然包含中国。而且,中国式的 “语言”这个家,更富于象征、比譬、隐喻、想象的质地;其哲思,或“隐藏”,或象征,或隐喻,或托物寄情,或人与物互渗。其实,中国诗学理论思维中也就有“诗”与“思”会合一体的元素,只是采取点到为止的体察而没有系统的逻辑规范的理论阐述。宋人魏庆之所编《诗人玉屑》中有云:“诗以意义为主,文词次之;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故昔人论文字,以意为主。”这里的“意”“意义”,不就是“思”吗?不过中国“语言”这个“家”,贵在也是好在“句中无其辞,而句外有其意”,读诗解诗,“不可言语求而得,必将观其意焉”(以上所引均见《诗人玉屑》)。充闾先生之所为,就是“剥开”语言的遮蔽,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蔽”,把那些隐含的、象征的、比譬的“言外之意”的“意义”“平易之处”的深意高议揭示出来,并予以恰当的诠释。而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文史哲不分的。所以其诠释,自然地关涉哲理、文学与历史。
充闾先生在解析诠释中,既潜蕴着海德格尔的言说,又运用着中国传统诗话的底蕴,而使“诗”“思”“史”汇融一体,最终和合于他的诗体散文之中。
从“原意”臻于“意义”
罗兰·巴特指出:作品提供“原意”,而读者,经过“读者的工作”,即解读、诠释、扩展、延伸甚至误读,则创获“意义”。《诗外文章》的工作,就是起先解诗的“原意”,然后“去蔽”“观其意”,揭示诗中的“深意高议”,使诗作从“原意”达于“意义”。这里有几步工作:先解其“原意”,而后越过字面,揭示、“挑明”那诗中蕴藏的暗示、象征、隐喻、比譬、托物寄情等等的 “意义”。但对作者的“原意”以及可能存在和足可创获的 “意义”,不会是单一的、“纯粹”的,存在“各执一义”的差别甚至是意义相反的解读。这又需要辨别、解析、“据理力争”,方可得出一个准确的或者仍然待议、可由读者选择的“可能”的结论。这里包含着多方面的讨论、商议、辩驳,这也就是学问见识的考验。清人赵绍祖在《读书偶记》中曾说:“作诗者在当时或为一人而作,或为一事而作,圣人录之,则不为此一人一事也。”而他在《消暑录》中还说:“夫文章有理、有气、有事、有情,岂可一概而论。”这说明了解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这也是对博学的考验。充闾先生在《诗外文章》中经受了这一考验,他广证博议、解意决疑,从外(语义)到内(内蕴),从物到人,从景到情,从历史到现实,从诗人之 “一己”到社会之“众相”,一一解析、娓娓道来,做到从“原意”达到“意义”。但又不止于此。有的是确切结论,有的是结论待定,有的有倾向却不定谳,等等。理、气、事、情皆备, “原意”“意义”俱在,内容丰富,而事理清晰,却又要言不烦,委婉明丽,非博议性论著,是可读性散文。
博采众议而独创
《诗外文章》的解说,博采众议,精彩纷呈;但并不只取一家说,而是驳议论列,分析说理,然后有的定于一谳,有的仅提供思索的线索,由读者思考定夺。这方面也体现了作者的博学。每一首诗都引用了多家解说,从古代到近代以至现今。在此基础上,作者依据诗作及作者的生平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历史环境予以分析,析理明晰、陈义中肯,多数取一种论说为准,或弃诸说不用,而抒发己意。如开篇的《诗经·蒹葭》,就取用了多家论说,而略取钱钟书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企慕之情境”说,但予以发挥伸展:“《蒹葭》中所企慕、追求、等待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我们不妨把‘伊人看作是一种美好事物的象征。”又如对脍炙人口的陶渊明的《饮酒(其五)》,引证自古至今的七位名家之说,又引发陶氏生活情状而“反征”其诗作与哲思,而以标题揭示其“意义”:“此心自在悠然。”
采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作者“敢选众人皆选之作”的表现之一。而其诠释,则有新意。一是将时代背景与作者身世境遇提出,为解诗提供了基准;二是采历代以至今人的解说并融汇之,而立己说:
诗人把自己对现实时空的深切体验,转化为对心理时空的奇妙想象,从而创造出诗歌中的时空来,在今古茫茫、天地悠悠的慨叹中,从心灵深处迸发出凄怆、悲壮的痛苦呼喊。
这诠释,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创作心理、审美心理融为一体,既具古典诗话的传统风范,又有现代艺术心理学的解析。
这类事例贯穿全书,这里只举例而言,以窥全豹。总之,作者博采众议,“颇有斩获”;但是,无众议则薄,仅众议则浅,唯聚众议而议之,且立己说,而具有新意,乃为上。这是《诗外文章》的优异处。
“诗”“思”为文创新篇
《诗外文章》颇具创作新意,获得了新的成就。它具有选诗之新、解诗之新,还有散文之新。称它“依托哲理诗的古树,开放文化散文新花”,并非溢美。这里所说“三新”,前两项上文已经述及,此处只言散文之新。
我以为它开了盛行的文化散文的一种新风。向来的所谓文化散文,大都篇幅延绵、盈盈大观,借史言事、写景抒情,洋洋洒洒说开去,是为大观。作者本人也有多部这样的文化散文集问世,且颇获佳评,成就卓著。但这次他创新了。选解哲理诗,长于说理,未免绵延文字,缕缕行行,以明究底。但《诗外文章》却别开生面,用抒情明丽之笔触,议哲理诗之哲理,“理路”“哲思”点到为止,画龙点睛,而文字潇洒飞扬,说理、解析、抒情,娓娓道来,成可读之散文篇章。即以二例为证,且引两段文字,可见一斑。比如对姜夔《江湖味 故乡情·湖上寓居杂咏(十四首之一)》的诠释:
本诗意蕴,可以“江湖味,故乡情”六字概之。正由于它所抒写的,不是事乃是心,不是景乃是情,不是遇乃是境,因而应从荷叶、青芦等兴象中,体察诗人栖居江湖的凄清情境,咀嚼远离家乡、辛酸寂寞的清苦况味,如此,则庶可把握诗中真髓。
解析以流丽清顺、鞭辟入里的笔触,从艺术心理和创作心理的视觉,对诗的意境予以诠释,从“诗”达于“思”,亦涉及浪迹天涯、终身寂寞的作者生平、性格,而进入“史”,而臻于散文境界。又如对郑燮《别开生面的竹颂·题画竹》的一段解读诠释:
本诗突出强调了主观因素的作用,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极具现实的箴规、针砭价值。
从人生追求、价值取向来说,古往今来,凡是心怀远大目标、有志献身国家民族的人,在声色货利面前总能正身律己,坚守原则,珍重节操,秉持一种定力。而且,淡泊自甘,不慕容华,不媚俗,不张扬,不出风头,不哗众取宠。即使坏风邪气袭来,遭到“蜂蝶”的滋扰,由于自己正气凛然,贞洁自持,也能够不为所动,予以有效的抵御。
我们还可以从中认识到艺术与科学的区别。从植物学角度看,竹子不开花,与害怕招蜂惹蝶没有联系;但作为诗歌艺术,采用拟人化手法,却可以这么写。同样道理,唐人的“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都属于诗人的拟人与移情之笔。
这里既有对诗的解析,又有从社会学和艺术心理学、创作心理学角度的“说开去”;于是既有對诗的解析,由“诗”入于“思”,又有对读者的“诗”(创作心理学与接受美学的)与“思”(社会学与哲理的)的启迪,从而使诠释成为具有诗意的“思”的散文。
这种散文叙事的新体新意,可谓比比皆是。我在这里“偷懒”,仅顺便举出二例以为证。在总体上,这种新的文化散文的体式精魂,就是把“诗”“思”“史”融会贯通,统为一体,而以简练篇幅,以散文风范、明丽洒脱的文笔,精练简洁地书写出来。它本身也是“诗”与“思”与“史”结合汇融的,因此成为散文园地里的华章新篇。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彭定安,著名学者,江西鄱阳人。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所长、副院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研究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鲁迅学会第三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鲁迅杂文学概论》《突破与超越》《走向鲁迅世界》《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散文集《秋日的私语》等。专著《鲁迅评传》获1983年辽宁社会科学一等奖,《创作心理学》获1992年辽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描绘金河的艺术世界》获1991年辽宁省优秀文学评论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