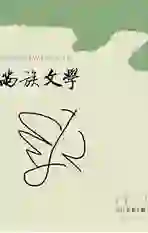逸天闲云
2021-06-29袁敏
袁敏
我有一位画家朋友,不仅画得一手上好的水墨丹青,还能刻一手漂亮的篆体印章。
有一天朋友来了兴致,要给我刻一枚闲章,问我想要刻什么字?我竟没有片刻思索,脱口而出:逸天闲云。
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枚閑章,关键字是“云”。朋友将刻得的印章交予我时,意味深长地说,看来你和云有很深的渊源啊!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定义自己的处女作,而在我的心目中,自己真正的处女作,就是1981年发在《收获》第四期上的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
那部小说长达九万多字,对于一个其时从未写过小说、只零零星星发过几篇小诗歌小散文的我来说,撰写这样长篇幅的小说,显然有些不自量力。现在回想起来,最初我在一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上落笔写下一段段文字时,并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小说,我只是觉得内心有一种强烈的东西在涌动,常常是倒海翻江,甚至让我夜不能寐,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省里的一些文化单位要从工农兵中选拔补充新鲜血液,我因发了一点小诗文,便从杭州织锦厂被抽调到浙江省文联的《东海》杂志社,这次调动,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抵挡不住文学的诱惑,放弃了恢复高考后报考大学的机会,当上了一名小说编辑。
当时我才二十出头,也没有任何编辑经验,但杂志社的编辑不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虽是新人,也立马被要求分管省内四个地区的小说稿件,每天就埋头在字纸堆中,阅读长长短短各种各样好看的不好看的小说。
那时候,编辑部的电话打长途是要登记的,也没有今天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编辑和作者联系全靠写信。因为年轻,又不是科班出身,也没发表过什么正儿八经的作品,自觉底气不足,顶着个编辑头衔,心中其实蛮惶恐的。
我发憷与作者面谈,通电话也担心暴露自己的稚嫩,写信和作者交流的方式,反而是我喜欢的。因为从小练习过一阵书法,柳公权、颜真卿、赵孟頫都练过,所以我的字还算老到。加之我给作者写信,提作品修改意见时,对自己的这份编辑工作存有敬畏之心,特别认真;同时也怕时间长忘了,故而都会先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草稿留底,再字斟句酌地修改,然后抄到编辑部的信笺上,寄给作者。作者回信都称呼我“袁老师”,对我提出的小说修改意见也大多认可,并基本上照改。
其实我给稿子提意见时,只是凭自己的阅读直觉,但久而久之,作者们来信对我的感激和尊重渐渐多起来时,内心便有点小小的膨胀,觉得我既然能头头是道地分析别人的小说,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尝试练练手?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还是蛮敬业的,一心扑在编辑工作上,不敢心有旁骛。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收获》杂志社编辑李小林打来的电话。
小林说,小袁,你可以将你家1976年发生的故事写下来,你都不用编,真实地写下来就可以了,生活本身就是小说。小林的话像一道闪电,点燃了我心中的写作欲望,往事如潮水般汹涌而来,那种倒海翻江、夜不能寐、不吐不快的感觉,大约就是从接到小林电话以后开始的。
我和小林相识于1976年的早春时节。
那时我还是杭州织锦厂的工人,学徒刚刚满师不久。这家工厂原名都锦生丝织厂,是民国著名实业家都锦生亲手创办的一家享誉中外、专门织造风景、人物肖像和各种美图丝织品的老字号工厂,当年周总理陪外宾到访杭州,参观景点,农必“梅家坞”,工必“都锦生”。
“都锦生”坐落在西湖之畔,素有“花园工厂”之称。我高中毕业后分配到这家工厂,招来众多同学羡慕,我自己也有点窃喜。没承想,花园工厂也好,外宾参观也罢,一切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被分到全厂最苦最累最破烂不堪的杠子车间,说是车间,其实就是一个面积大约只有五六十平米的破屋子,坐落在工厂的偏僻一角,十几名大妈女工,几排转动着缫丝的木杠子。我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五十多斤重的杠子抬上抬下,给缫丝分缕编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筋骨像要断了一样。
就在我觉得生活黯淡无光、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省里的文学刊物《浙江文艺》(即《东海》杂志,文革中被改名《浙江文艺》)为反映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地恢复工农业生产的改革面貌,到我们工厂来组稿,厂宣传科要求每个车间上交一篇稿件。我们车间仅有两名高中生,也是所有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了,大妈们自然就将任务交给了我们俩。可那一位高中生说,她从小就怕写文章,不会写,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对我来说,这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还能脱产两天,逃离繁重的劳动,坐到办公室里去写,何乐而不为?
我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散文,题目叫《摄影记》,用自己拍下工厂各种火热的生产场景的图片为轴线,来展现全厂改革后的新面貌。稿子交上去后,任务完成了,我又回到了车间,重新陷入沉重无望的日子。
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厂宣传科通知我去参加《浙江文艺》的笔会,时间半个月,地点在宁波鄞江镇。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啊!当宣传科长将去宁波的火车票交到我手中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
那天赶火车被什么事情耽搁,我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自己赶到火车站,冲进月台时,火车汽笛已经鸣响,我正慌乱地寻找车厢,只看到一扇车窗伸出一个短发脑袋,嘴里大喊:小袁,这里!这里!我急匆匆跳上那节车厢,脚还没站稳,火车就开了。
找到座位坐下时,才发现我旁边就是那个短发脑袋。她笑着埋怨我,你性子可真慢,再晚几秒钟,就赶不上火车了。聊起来我才知道,她叫李小林,是《浙江文艺》唯一的女编辑。这次笔会时间比较长,小林和杂志社头儿说,你们必须给我找一个女作者与我同屋。当时在省里面挂上号的业余作者中还没发现女的,正好我交上去的那篇《摄影记》还入得了编辑们的法眼,情急之下,便将我召来参加笔会了。
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运气”了,这次偶然的写作,让我幸运地遇见了我文学道路上的恩师——李小林,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笔会所在地坐落在四明山东麓,四周青山绿水,翠竹环抱,一顶小小的青石拱桥流淌着岁月的包浆,据说此地红极一时。那个年代的偶像明星达式常扮演男主角的电影《难忘的战斗》,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我和小林住一间屋,每天同进同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去周边的山上踏青,我们会采来大捧的野花插在瓶子里,让春色住进我们的房间;我们也会躺在各自的床上,天南海北地闲聊。那是一段神仙般的快活日子,我摆脱了沉闷压抑的杠子车间,来到这绿意盎然春风拂面的鄞江桥畔,真有一种从笼子里放飞出来的松快感觉!
我和小林聊得最多的,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聊“四人帮”的狼子野心;聊周总理逝世后邓小平地位的岌岌可危;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会向何处去……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给小林讲故事,都是那个年代坊间流传的,记得有《梅花党》《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等,窗外黑魆魆的,听到惊险瘆人处,小林有时会尖叫起来,我就乐不可支。我告诉小林,我在车间干活干不动时,常常用这些故事来吸引大妈们帮我干活,因为早早干完活,还没到下班时间,我就可以给她们讲故事。我会在讲到关键处突然收住,说明天再讲,第二天,那些大妈们为了听故事,又会来帮我干活。小林说,有的故事我也听过,但不如你讲得生动,有些情节和细节好像原来没有,是你自己编的吧?我承认自己经常会给故事添油加醋,现成的故事讲完了,我就开始编故事,没办法,否则大妈们凭什么帮我干活呀?
参加这次笔会的作者都是从全省来稿中的优秀者里选拔出来的,他们都带着初稿来笔会,每天都和编辑们认真讨论修改,只有我一人是临时填补空缺的,没有初稿。小林当然不忘自己的编辑职责,聊天闲玩之外,也会督促我写稿。小林说,你蛮会编故事的,可以试着写写小说,小说的第一要素就是故事。她还说,我听你讲工厂里的人和事都蛮有趣的,你的师傅也很有个性,你可以根据自己在工厂的生活,写一个短篇小说。
那时候的小说创作,“主题先行”盛行,人物“高大全”极为普遍,我虽然没写过小说,起笔时也逃不脱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以我的师傅为原型,不遗余力地拔高这位工人阶级形象,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小林看后也不说什么,搁置一边,弄得我心里很忐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写小说的料。
只要不谈小说,我们还是很开心,形影不离。
有一天,一位作者问我,你怎么和巴金的女儿那么要好?我问,谁是巴金的女儿?这位作者说,你整天和她同进同出,好得跟两姐妹似的,你居然不知道她是巴金的女儿?我大吃一惊,跑回屋去问小林:他们说你是巴金先生的女儿,真的还是假的?小林笑了,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拉着我的手说,走,我们爬山去。
我再看她,和煦的暖阳下,小林一头没有任何修饰的齐耳短发,一件半旧褪了色小碎花中式对襟棉袄,平凡得就像一个邻家姐姐,看不出半点大文豪女儿的样貌和做派。
那一天我们在四明山上逗留了很久,我俩坐在绿荫浓密的翠竹下海侃神聊,我将随身带着的一份抄来的《总理遗言》给小林看,我们都不约而同地为时局担心。
那次笔会回来以后没多久,我家里就出事了。先是我哥哥在上海姨妈家里被抓,后来是父亲、姐姐被以“谈话”的名义从家里带走,紧接着就是抄家,穿着白制服,戴着大盖帽的公安人员连夜赶到杭州织锦厂,将刚刚下中班、还没来得及上床睡觉的我带回家中,看着家里满地狼藉,母亲孤独一人蜷缩在客厅的藤椅上,我感到了巨大的恐慌。
这以后,我和母亲都被软禁了,我们家那栋小楼的四周布满了便衣警察,谁到我们家来,都会被盘问,认为可疑的,就会进一步被传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父亲、姐姐、哥哥在什么地方。隔三岔五,会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来家中问我一些问题,云山雾罩,反反复复,但最后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归落到“总理遗言”。
早年参加革命做过我党地下交通员的母亲,让我把家里的电话线拔了,我知道她是怕连累别人,因为只要有人来电话,事后都会被传讯。我们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
后来有一次,我在四明山笔会上认识的军旅诗人嵇亦工穿着一身军装来我家,也许是他身上的红领章红帽徽起了作用,他并没有受到便衣警察的盘查。小嵇说,小林和那次笔会上的几个业余作者都聚集在萧山诗人陈继光的家里,他们烧了一只鸭子,小林让他来探探情况,可以的话,想让我去萧山吃鸭子,散散心。我很想念小林,也很想念那次笔会上结识的作者朋友,但我还是没去萧山,一来我不能离开母亲,二来我也不想因为“鸭子聚会”,连累小林和那些作者朋友。因为警察传讯我时,曾几次提到我哥哥他们一帮小兄弟们的一次“狗肉聚会”,在公安的眼里,那样的聚会很可疑。后来我才知道,小林因为和我接触密切,也被公安传讯,但她并没有说出我在四明山笔会期间给她看过“总理遗言”这件事。小嵇来的那一天,小林和她的先生祝鸿生其实也来了,但看到我家四周有便衣警察,就沒有进来,而是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望着我家的小楼。
小嵇走后,我流泪了。那时候母亲肝腹水病得很重,我被困在家中和外界几乎隔绝,唯一能让我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就是母亲房间里那几扇硕大的窗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天晴阳光好,我都会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看天上飘忽而过的一朵朵白云,云有时候纹丝不动,有时候却会慢慢游走,形状也会变幻无穷,一会儿像奔腾的马;一会儿像摇曳的树;一会儿像长袖善舞的仙女,一会儿像双手合十的老翁……
天边的云,排解了我内心的寂寞,也消弭了我绵延的恐慌。我能和云说话,云会默默地倾听,天很高远,云很深邃,突如其来的劫难向我重重压下来时,白云像一张绵软的大床将我轻轻托起,让我惊悸的心感到温暖,帮我抵挡住莫名而来的戕害。
粉碎“四人帮”以后,被秘密押送北京、并分别被囚禁了八个月和一年多的父亲、姐姐、哥哥,先后被释放回家,一场冤案最终也获得了平反,我也在软禁了一年多之后,重新回到了杭州织锦厂,这时候再看杠子车间里那些转动的木杠子,竟然没有了从前那份厌弃,那轰隆隆的声音听来竟像是美妙的音乐,劫后重生的快乐,让我觉得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做一个工人的辛苦,和亲人被抓、生死未卜的那种恐慌比起来,根本算不得什么!我的师傅和周围干了几十年杠丝工的大妈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苦不堪言,也从来没有一句对生活的抱怨,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很迅速、很意外,又很令人措手不及。就在我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当一名杠丝工、同时准备复习考大学时,《浙江文艺》到厂里来商调我。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太兴奋,因为我想好了要报考大学,对去杂志社积极性并不太高。等到有人告诉我,这次抽调我去《浙江文艺》,是李小林鼎力推荐时,我心里不由地怦然一动。小林对我在四明山笔会上写的万字小说不置一词,我灰心地以为自己大概没什么文学天分,她怎么会推荐我呢?等到我最后下决心,放弃高考,到《浙江文艺》报到时,发现自己竟然和李小林在同一个办公室。高兴之余,我想,今后可以好好和小林学习如何当好编辑、如何写作了。没想到一年多以后,随着巴老落实政策,小林也将调回上海了。编辑部同仁都喜欢小林,大家虽有万般不舍,但还是都为小林高兴,小林妈妈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仓促离世,巴老身边一直没人照顾,小林自然应该尽早回到巴老身边。
小林回到上海后,我们很久没有联系。等到她给我打来第一个电话时,我才知道,其时她已经是复刊后的《收获》杂志编辑了。电话中,小林约我将自己家中在1976年发生的那段故事写下来。也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电话,唤醒了自己对那段过往生活的记忆。
这样的写作是喷涌而出的,不需要构思,也谈不上任何写作技巧,有的只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生活本身。
九万多字的稿子杀青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小说,但题目却未经思考就自然而然跳了出来:“天上飘来一朵云”。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天上的云,陪伴我走过了那段灰暗幽闭的日子,如果没有和云的对话,没有云的倾听,我不知道自己二十出头的柔弱肩膀,能否担起生活突如其来抛压给我的沉重。
如小林所说,我几乎没有编造,全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我只是忠诚地将它记录下来,然后赋予了它一个在自己脑子里千百次出现过的意境——天上飘来一朵云,作为题目。
稿子写完后,我都没有勇气再看上一遍,就寄给了李小林。说实话,那时候根本不敢奢望自己头一次写的稚嫩文字能在《收获》发表,只不过是想小林能帮我看看,提提意见罢了。没想到,三天以后,小林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和《收获》编辑部的其他同志都看了我的稿子,希望我到上海去修改。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第一次走进《收获》编辑部的情景:阳光穿过那栋美丽而古老的房子窗外的绿荫,投射到编辑部的一间大房子里,桌上、地上堆满了稿件,凌乱却温馨,像一个大家庭。小林向我介绍编辑部的同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老编辑:孔柔和肖岱,孔柔老师慈眉善目,说话总给你一股暖意;而肖岱老师一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白发,让你觉得踏实和安心。小说的修改意见主要是小林和我谈的,孔柔老师有时在一旁插上几句话,他们都说得很温婉,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紧张。
我在上海锦江饭店住了三天,按照小林和孔柔老师提出的意见,对稿子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修改完以后的稿子,清晰地呈现出了小说的样貌,我知道,那里面有编辑的心血和默默无闻的付出。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从上海回到杭州不久,小林陪巴老来杭州休养,住在西湖边的新新饭店。我去拜望巴老和小林,在一个望得见满湖绿水的露台上,巴老对我说,小袁,小林将你的小说给我看了,你是可以写东西的。
一位我从小就景仰的文学泰斗,就这样近距离地坐在我的面前,这位老人恐怕不会想到,他说的这样一句听上去平平常常的话,却影响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
1981年,《天上飘来一朵云》在《收获》第四期上發表,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它让我有幸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小说的人。
【责任编辑】大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