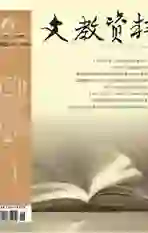游刃于神秘与现实之间
2021-06-28郭瑶
郭瑶
摘 要: 莫言的小说创作立足于乡土,以高密故乡为叙事起点,将蒲松龄鬼神精怪的传统想象与西方现代技巧结合,继承鲁迅以讥讽笔触表达对现实的思考。其近作,更体现出明显的由神秘书写向现实回归的特色,以致敬经典的姿态、“晚熟”的追求,表达激情过后的自我突破。
关键词:莫言 中短篇小说 神秘书写 现实倾向 致敬经典
莫言的小说创作体现出明显的神秘色彩,若将其归入乡土写作,那么他的神秘源于对蒲松龄的模仿与民间鬼怪故事的继承,若将其归入先锋写作,那么他的神秘源于对西方现代技巧的熟练使用。莫言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二者融会贯通纳入小说创作中,因此表现出东方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只是在近期的创作中莫言有意摆脱诺奖光环,表现出致敬经典、回归现实的倾向。
一、奇幻人事的呈现
(一)鬼神精怪世界
莫言小说对鬼神精怪的塑造不是开门见山式的,而是在这些形象出现之前,通过一系列极致环境的描写营造紧张恐怖的气氛,使读者油然地自设阴冷氛围。受蒲松龄影响,莫言中短篇小说塑造的鬼怪世界大致可分为“鬼神”和“精怪”两种类型。
首先,“鬼神”的特征在于与人类似乎有某些相似性,如《奇遇》先是描绘了半月高悬、只闻虫鸣不见人影的暗夜,叙述语言平淡如水,但在这平常无奇的最后由母亲点出赵三大爷已死的事实,读者反观整个故事,才知道烟袋嘴来自鬼的债务偿还,这里的鬼与常人无异,欠债还钱、以物抵债仍是人世规则。《良医》中所谓的“良医”们既像装神弄鬼的传统巫医,又似窥破天机的至圣,所开药方带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色彩。
其次,“精怪”是莫言小说不可或缺甚至是极重要的一类,这些精怪一般而言都是动植物的形象外延,《夜渔》中擅长捕蟹的九叔极可能是一只龟所变,荷花精难解的神秘嘱咐“镰刀斧头枪,葱蒜萝卜姜,得断肠时即断肠,榴莲树上结槟榔”[1](16)。《铁孩》中吃铁作怪的铁精、《翱翔》中长了翅膀逃婚的燕燕及《嗅味族》创造的生活在井底靠嗅味生存的长鼻人的世界,像是饥饿年代的“桃花源”,与武陵人不同的是孩子们不会“为外人道”,桃源世界的创造似乎是在弥补“我”原生家庭的不幸。《木匠与狗》中大黑狗能通人言语,会衔高粱秸丈量主人身长以报仇掘坟,这里的狗已经不是人类的亲密朋友而成为对头冤家。《罪过》中讲述了一个成精老鳖主宰河道命运的故事,并且在河中还有一个鱼鳖虾蟹的王国,它们与人类世界和平相处,带有《柳毅传》与《织成》的神秘色彩。近作笔记小说《一斗阁笔记》模仿古文范式,以言精怪之事。总之,莫言模仿蒲松龄营造奇幻王国,在《学习蒲松龄》中作者通过一个梦见到马贩子祖先和蒲松龄祖师爷,并且以九个响头换来祖师爷一句“回去胡抡吧!”[1](3)的允许,但这更多的是莫言对蒲松龄的致敬。
(二)病患形象的塑造
疾病书写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其中“疧”“疢”“痡”“瘅”等指的是具体的病症,魏晋时期出现了以刘祯、陶渊明为代表的疾病与佛道思想融合的创作,唐代杜甫、白居易有关疾病的创作多是自我经历的诗意表现。现代文学中,鲁迅、郁达夫、曹禺等作家笔下一系列积贫积弱形象的塑造,更侧重对精神疾病的揭示与讽刺。莫言沿袭这一传统,在他的笔下也出现了一批病者形象,《天花乱坠》中满脸麻子的幕后伴唱女子和皮匠,《白狗秋千架》中的哑巴们,《祖母的门牙》中长门牙的婴儿与老人,还有对麻风病人生活与情感的表现等,这些病患似乎都有原型,有的形象甚至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復呈现,这些人因为身体的异样造成心理病态,或自卑、或偏激、或自暴自弃、或歇斯底里,他们是“零余者”,也是“多余人”。这些人如同苏珊·桑塔格所揭示的疾病隐喻一样,因为患病成为道德批判的对象。
除此之外,莫言还擅于塑造的是“痴傻者”群像,如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患恋乳癖的上官金童,《檀香刑》中拿着一根阴毛到处窥探人类本相的赵小甲等。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有许多此类人物,《天才》中质疑地震原理后主动退学的蒋大志,埋首西瓜地终于得出“西瓜即地球”的所谓真理,读者并不知道他辍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又依据何种学说推论地球运动。《罪过》中大福子嫉恨受宠弟弟,痛恨父母偏爱,以致漠视弟弟生命。这一形象和《嗅味族》中的“我”、《枯河》中的小虎及早期的《透明的胡萝卜》中的黑孩,构成了同一类形象,即由缺失亲情温暖所共同造就的“痴傻者”。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儿童纯真特质,被生活中的饥饿与贪婪、冷眼与讥讽消磨殆尽,他们能感受到被群体孤立后的痛苦。
二、繁复驳杂的技巧运用
莫言是继承蒲松龄、鲁迅的传统走来,积极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技巧,并杂糅二者入小说,建构自己小说世界的作者。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既能看到蒲松龄讲故事的传统方式和鲁迅的讥讽笔触,又能看到西方现代技巧,以稳健成熟的笔力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真实却又虚幻的小说世界。
(一)“讲故事的人”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通过聊天闲谈,收集民间奇人异事传闻而来的,莫言虽发挥祖师爷之所长,但更善于讲故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开篇他便为在场的人们讲了一系列小故事[2](4-10+2-4)。从文本创作上来看,《天堂蒜薹之歌》以讲故事的人贯穿全书,《红高粱家族》驻足历史进行讲述。他的中短篇小说常常在叙述者之外安排一个讲故事的人,叙述者退居二线促使讲故事的人讲故事,如《木匠与狗》中管大爷在小说中以“讲故事人”的身份讲述管小六捕鸟、卖鸟、活埋木匠的故事,钻圈作为“木匠与狗”这一故事的转述者讲故事,作者并不参与其中。但有时二者是同一个身份,《枯河》似乎是一个死者在描述如何被打死寻自杀的故事。不得不说,莫言及其故事中的人都是讲说界的行家里手,通过讲故事对过程的虚构、夸张与变形,呈现了许多富有神秘色彩的故乡人事,形成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结构。
既然是讲故事,那么语言的使用就尤为重要。第一,在语词的使用上莫言极尽语言之能事,用各种动物的外貌拼接单峰骆驼的长相,“踩在烂泥里的分瓣的牛蹄子,生动地扭着的细小的蛇尾巴,高扬着弯曲的鸡脖子,淫荡的肥厚的马嘴,布满阴云的狭长的羊脸”[1](138),用“形状如红薯,味道如臭鱼,颜色如蜂蜜”[1](151)形容人的良心。《枯河》中将血管比作四通八达的“老鼠洞”,将心脏比作“耗子”,虽然这一形容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不得不惊艳于其感官放大式的比喻所取得的震撼效果。第二,莫言善于插叙造势,《奇遇》中走夜路时感到后背冷飕飕的,但一转头却空无一物。“木匠与狗”的故事作者有意不和盘托出,而是在讲一段木匠与狗的故事后插入木匠与钦天监的故事,再在讲一段后插入管小六捕鸟遭报应、钻圈老舅爷数来宝的故事,最后才由老钻圈讲出来。《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女》写到侯七下班“侧目西望,猛然看到……”[3](187)便戛然而止,并不着急告诉读者侯七望到何物,而是另起一段交代侯七今天上班的情况。
莫言的小说自带一种冷峻的幽默,一方面这种冷峻源自阴冷的环境描写,作者经常用血红的太阳、蓝色的月光、拖着肠子行走的小狗等描绘场景,在环境描摹中营造恐怖、阴冷、神秘的调子。如《灵药》是鲁迅《药》在五十年代的翻版,但这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如果说鲁迅要揭示的是无知民众变相屠杀革命青年的愚昧的话,那么《灵药》则是放大人的感官,对行刑场面和开膛取胆过程的细致描摹,同样具有安特莱夫式的阴冷效果。另一方面这种幽默是痛苦的笑,《飞艇》中将自己写文章前言不搭后语的特点归咎于年少时被冻的经历,饥饿的讨饭队伍被莫言说成“羊拉屎一样,稀稀拉拉”,穿的是“空心棉袄”,七老妈被封讨饭“状元”,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爱上了寒冷,因为寒冷带来的痛苦远比溶解带来的奇痒好受,饿狼似的人群眷恋烤人肉的香味。
总之,莫言在真实人事的基础上进行神秘虚构,发挥擅讲故事的天赋,同时具有侦探小说质素,在吸引读者阅读的同时增加神秘色彩。
(二)西方现代技巧
莫言小说中有很多关于梦境的描写,但这些描写的目的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梦境解析,而是带有中国民间色彩,《学习蒲松龄》像是祖师爷托梦,《小说九段》更像是莫言对于九次梦境的记录。意识流技巧运用最明显的是《铁孩》和《罪过》,是对《透明的胡萝卜》的延续与承继。《铁孩》中狗剩与铁孩是全身生了红铁锈、专吃铁制品的铁精,狗剩与铁孩的交谈更像是一人分饰两角的意识流动。《罪过》中“我”在观望弟弟溺水过程时不清楚动没动过救他的念头,只是坐在岸边看着青年下水寻人,闻着雨后麦秸霉变的味道,看着毒疮在苍蝇和太阳的骚动下逐渐成熟化脓,在打谷场上毫无痛苦与后悔,仍因父母对小福子的关心而嫉恨,痛恨母亲在小福子死后又怀了孩子,“我”逐渐失去说话的机能,整天只与自己的肠子一起痛恨父母。《三匹马》将刘起套马翻车、刘起媳妇对刘起的愤恨、柱子与一群小孩的厮打、站岗兵张菶长的意识流动放置在一个焦热焦躁的午后,一切情感的爆发都集中在这样的紧张时刻,气氛的营造与人物的心理博弈同时呈现,与曹禺《雷雨》有异曲同工之妙。《枯河》中小虎不小心砸死了书记家的孩子,被书记、父母、哥哥轮番揍打,体会着被甩在空中飞行的奇妙感觉,临死前清晰地感受着骨断与血流,静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这些意识流的小说创作,极易抒发人物的隐秘心理,带给读者窥探欲得以满足的阅读体验。
莫言的小说善于将性与狂欢结合,这种狂欢叙事背后暗含了作者的迷茫与焦虑情绪及对社会与文艺关系的思考。《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女》中机械的生活与工作使侯七自觉糊涂与昏聩,此次的狂欢是在某天结束无聊工作后,上百号人像是被某种神秘力量指引追逐一男一女一马一驴,这是侯七,也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一场反叛。漫长的追逐得到的却是十几个粪蛋子的结果,既使“追逐”變得毫无意义,又消解了“美”本身,荒诞的结局宣告了此次狂欢活动的无意义。《马语》让一匹马讲述自己“瞎”的过往,因军官一句“你这匹瞎马”选择“再也不挣开我的眼睛”[3](168),很有鲁迅“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4]式的思辨色彩。《祖母的门牙》之荒诞,一方面在于将婴儿长门牙与前世仇人报仇的因果说结合,另一方面将长牙的原因归结到饮用特效菌肥以见其荒诞不经。《与大师约会》更是发人深省的,美术展览、摩登少年、喧闹酒吧都是狂欢的硬件,普通的摄影展变成了权色交易的舆论宣传,普通的约会变成了真伪难辨的相互猜忌,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大师是谁?何谓后现代艺术?诸多的疑问加重了此次约会的荒诞与虚无,具有神秘效果。
总之,莫言小说虽魔幻但又忠于现实,通过描绘故乡人事表现社会、人性、艺术之间复杂的关系,表现作者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充满思辨色彩,发人深省。
三、由神秘向现实的退隐
莫言始终是一名关注现实的作家,他的写作态度就如同他在《白狗秋千架》中借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用低调观察着人生,心弦纤细如丝,明察秋毫,并自然地战栗”[1](294)。早期中短篇小说中表现较多的是童年亲见亲历的时代伤痛,如《嗅味族》《粮食》写食物匮乏,《枯河》写三年大旱,《铁孩》写大炼钢铁时的“大跃进”发展。一方面表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如《枣木凳子摩托车》是传统木匠的衰败与现代代表的摩托车之间的对抗,木匠坚持传统手艺,即便在大家都睡席梦思的当下不仅坚持打造枣木凳子,而且是不用钉子和水胶,只用卯榫的传统工艺技法,拒绝电机操作;新出版的小说集《晚熟的人》中塑造了铁匠老韩及其徒弟小韩和老三、擅长“滚地龙拳”的蒋启善、口哨行家三叔与三婶、编筐老人、捕鱼父子等一系列手艺人,在《左镰》小引中直言对打铁行业的尊敬与亲切。《贼指花》中更是直言“中国当代作家们,以及其他行当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都不敢说自己身上没沾染过腐败之油水”[5](78);《等待摩西》塑造了顺应改革开放潮流,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而发家致富的柳卫东形象;《天下太平》虽说延续了以往小说中的精怪神秘色彩,但暗含着河水污染、网络舆论等热点问题;《晚熟的人》中蒋二非法占用土地;《红唇绿嘴》中号称得网络者得天下的覃桂英,可以看出莫言创作的视点既没有放弃以往的五六十年代,又没有在此止步,而是继续向前迈进。
值得一提的是,莫言在小说集《晚熟的人》中仍塑造的“痴傻者”形象,明显与之前塑造的上官金童、黑孩等不同,如果说之前的这类形象带有时代印记和病态因素的话,那么这次塑造的以蒋二为代表的新一批的痴傻者更像是大智若愚的装傻者,是作者所欣赏的品质,这正是莫言所推崇的“晚熟”本质。莫言认为现实中存在很多装傻者,装傻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看作是卧薪尝胆,是力量积蓄。
莫言曾表示愿用所有作品换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短篇的深刻在于揭示了依靠“瞒和骗”求取虚无的满足、逐步走向堕落的国民劣根性,企图通过批判唤醒愚昧的民众,这正是莫言自言努力之所在,因此他在近作《火把与口哨》中塑造了新的祥林嫂——顾双红,这时的三婶不再是令人“怒其不争”的软弱形象,而是明知山有狼、偏向狼山行的勇敢女性,她用杀狼的复仇行动与不幸的命运做坚决斗争。《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首先在主人公的命名上与鲁迅《高老夫子》中塑造的“高尔础”有异曲同工之妙,“高尔础”源于自认为学贯中西的高干亭模仿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名字,同样地,“金希普”源于金学军对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崇拜,“宁赛叶”源于秋生对俄国诗人叶赛宁的模仿。其次在思想上饱含对恶相的讽刺,《高老夫子》是鲁迅对文化界普遍存在的山寨版文人墨客的揭露与讽刺,莫言写了两个文学青年失败的理想与现实,尤其是《表弟宁赛叶》通过复调叙事手法,意在揭露腐败社会造成的个人理想的破灭,对国民性的持续思考,既是向经典的致敬,又是努力摆脱诺奖光环、突破自我的积极实践。
四、结语
如果说蒲松龄的志怪世界来自魏晋小说和民间轶闻,鲁迅的鬼神想象有《山海经》和神话传统的启发的话,那么莫言的鬼怪精灵形象则更多地来自民间,他曾表示“高密民间艺术,有扑灰年画、剪纸、泥塑。这三种玩意儿,对我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124),他的创作手法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说书艺人的“讲故事”方式,另一方面是对现代主义的本土化实验,杂糅二者为读者呈现了丰富多彩的神秘世界。作为首位获得诺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接下来的创作必定受到读者群的高期待,经典化成为他重新出发的创作诉求,神秘的隐退、现实的回归成为新的追求,他要致敬蒲松龄、致敬鲁迅、致敬经典,直击现代文明的不足并公之于众,创作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作品。
参考文献:
[1]莫言.学习蒲松龄[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2]莫言.讲故事的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J].当代作家评论,2013(01).
[3]莫言.与大师约会[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莫言.晚熟的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6]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01.
[7]王西强.论1985年以后莫言中短篇小说的“我向思维”叙事和虚构家族传奇[J].当代文坛,2011(05):77-80.
[8]李昱颖,张学军.论莫言小说中的反讽叙事[J].濟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0(06):73-84+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