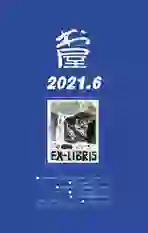陈寅恪晚年史学
2021-06-24徐宇杰
徐宇杰
目前学界基本上将《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看作陈先生的晚期“心史”之作,并认为《论再生缘》的创作,就是其晚年史学的开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其在《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中说道:“此时《论再生缘》初属稿,尚未有成篇,但蒋天枢在广州十日,陈寅恪必已将全文深意告诉了他,所以唐筼诗才有‘今传付之语。”余英时在此处认为陈先生的《论再生缘》在创作之初就是以“心史”为目标创作的,所以陈先生的晚年史学也自然从此开始。此说就《论再生缘》的内容和行文本身来看固然没有问题,这一点陈先生自己在后来也是承认了的。他在1961年答吴宓的七律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并自下注脚云:“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
《论再生缘》创作于1953年9月。是年夏,先生卧病,其助手黄萱为其读弹词《再生缘》。9月后,先生开始创作《论再生缘》,大致到11月份左右已筹备刻印之事,可见当时已经基本完成,但后拖延至1954年2月才正式完成。有关《论再生缘》的创作缘起,陈先生自己曾有如下论说:“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论再生缘》在完稿后,陈先生曾筹备油印,且坚持自付刻写等费用,并说《论再生缘》不是学校教材,是个人著作,并嘱咐行刻写之事的姜凝不要到教材科领取刻写酬金。此外,在1956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高校发出的“专家调查表”的填写中,陈寅恪在“存稿情况”一栏丝毫没有透露《论再生缘》的任何信息。稍微了解陈先生生平的人可知,他对于自身著作的出版一直是十分看重的。比如,1950年因岭南大学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让陈先生十分满意,并直接影响了他的去留。1955年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出版风波,1962年向胡乔木争取《论再生缘》的出版,1963年《金明馆丛稿初编》的出版风波都无不体现了此点。甚至在1966年陈先生已经卧床数载的情况下,仍向竺可桢打听其《金明馆丛稿初编》的出版一事。1962年向胡乔木争取《论再生缘》出版这一事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论再生缘》完稿的1953年前后的政治社会风气明显较1962年宽松许多,若是当时便决意出版,应该并非难事,但当时陈先生却执意不出版,到了数年之后又提起出版一事,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陈先生此一极端反常之举,更可以证明其当时只将《论再生缘》看作聊以自娱消遣的“戏笔”,而并非可公之于天下的“史作”。
明乎此,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校补后序》中所言:“《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就不仅仅只是自嘲与反讽了,恐怕亦是其对它真实的看法所在。
《论再生缘》创作于1953年9月,初稿完成于11月,但却至1954年2月才正式完稿,而且在1953年11月的时候,陈先生已经开始在筹备刻印之事了。按照常理去分析,既然已经开始筹备刻印之事,那么肯定已经没有大的讹误和错漏了,但为何却又突然要再进行修改,并且修改的时间几与创作时间等同,甚或更长,若单纯以订正或者修订去考虑這耽搁的三个月则不免有些奇怪之处。所以,可能的解释是,在这三个月中,因为某些缘故,陈先生对于《论再生缘》进行了很大改动,这一改动,应该与《论再生缘》由“戏笔”转向“史作”有着极大的关系。
目前已经无法看到《论再生缘》的初稿,很难准确得知此次修改到底修改了哪些地方,又加入了怎样的内容,但这并不是完全无法推知的。因为在陈先生晚年的著述当中除开著述的“古典”以外,其实也往往颇为注重所谓的“今典”,如其撰于1951年前后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1954年春,他在酬答朱师辙诗歌的诗题和诗文中公开提及《论再生缘》,其诗题为《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亦赋答绝句五首。近戏撰〈论再生缘〉一文,故诗语牵连及之也》。此一题五首绝句中有两句颇值得注意,即第三首的“玉环已远端生近,暝写南词破寂寥”,以及第四首的“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第三首中的“玉环已远端生近”虽是指代空间距离而言,但是必须考虑到陈先生于1952年才完成《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并于是年2月发表,并且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花大篇幅论述有关杨贵妃的事迹与生平,故此一句“玉环已远”恐亦是实指其已从中古史中脱离出来,并开始发现陈端生的自由精神。第四首的“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更是确定自己接下来的志业,就是“说尽”陈端生《再生缘》所留下的“未了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先生此一题诗实可看作其学问嬗蜕,身世变迁的重要表现。
也就是在同年,《柳如是别传》属稿。就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很可能就是在《论再生缘》完稿后不久。在开篇,陈先生同样高标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并以此为书的宗旨,即:“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尤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换言之,《论再生缘》的创作范式,尤其是再创作后的创作范式已经得到了陈先生自己的认可,并运用到接下来一部作品的创作中去了。
据蒋天枢所编的《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陈先生在1953年以前,几乎每年都创作数篇中古史的论文,但是自1954年《柳如是别传》属稿开始,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较为正式的中古史论文(虽然其1958年撰写了《书〈魏书·萧衍传〉后》,但此文甚短,恐可以读书札记目之)。据1957年陈先生致刘铭恕信中所言:“弟近年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实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捐弃故技”可以说是陈氏史学转向中一个重要标志,早在由早年的“殊族之史”转入“中古以降文化史”时,他就明确表示:“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随队逐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平生所学,实限于禹域之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戏者。”可以说,陈先生之所以有着明确的史学转向,或者说“三变”,就是因为他不断地“捐弃故技”。虽然上引那封给刘恕铭的信写于1957年,但如其自言“近年来”,则肯定是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根据笔者上述所论,则此“近年来”的起始时间就是在1954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