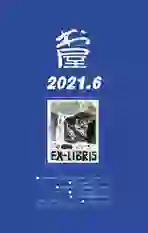任尔风光长寂寞
2021-06-24叶隽
叶隽
在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这批人物中,金井羊(1891—1932)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存在,他字其眉,是江苏宝山人,德国基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归国后在政、学两界都有任职,曾担任政治大学、中国公学、交通大学、光华大学等教席,铁道部参事与政务司司长等。无论是在思想见地还是事功行世方面,他都可算是卓尔不群的人物,可惜年及不惑即逝,实在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对他的生平经历,友人有这样言简意赅的描述:“生而岐嶷,龆龄喜究物理,从同里前辈游,惊为伟器;学于县小学,及上海民立、南洋两中学,欿然不满,课外探讨攻苦至昏厥。君父春波先生,惧苦学伤其生也,乃资令东渡日本,使以游为息。君至日,专攻政治经济,毕业于中央大学。初入学,见讲义简略,不满其志,更沉潜于专门巨著,尝以二月之力,毕英穆勒氏经济学,俯读仰思,欣然神会。当是时德为天下雄,学说称最,君更入上智大学,习德文二年,造诣甚深。毕业返国,各校争招延,君曰:我学未足以为人师,坚谢不就;杜门伏案,厉学不辍,四年如一日。嗣得请于春波先生,赴德入弗兰克福大学,更转基尔大学,得哲学博士学位。”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得见少年金井羊的才华横溢而好学深思,而他的学习成绩也是显而易见的,先留日后留德,符合那代人求知向学之路径,蔡元培、马君武的相关表述当皆为共鸣;由法兰克福转往基尔,则先与王光祈、宗白华等聚会而有发起“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的事业,后则为陈铨之早期校友兼学长;至于治学思路,则与朱偰颇有不谋而合之处,即虽擅长文史,却宁以经世之学如政治、经济为专业。
留德时代,金井羊曾与俞颂华等交往。俞颂华自己也记录下与金井羊等一起去听泰戈尔访德演讲的情形。当时是1921年,他先是6月6日到法兰克福,在金井羊处与宗白华相见。6月12日,俞颂华与金井羊、宗白华、王光祈、张梦九等一起去听泰戈尔演讲,他这样记录道:“台(泰)氏是日所讲的大意是说,欧战之后,人心厌乱,所以各国提议解除武装和互相联合,创造国际联盟,以防止未来的战争,这就是西方帝国主义不能再自由发展的明征了,但是设若根本的精神生活不变,而想望世界和平,则必失败。因为西方以前的社会组织不啻为人类争权攘利,损人利己的工具,所以组织愈扩大,组织力愈强,扰乱世界平和势力亦愈加雄伟。这种基于‘力基于满足浅薄狭隘的物质的欲望的组织不变,世界哪里能够有和平之望。然则世界的和平是无望吗?他说这也不然,只要扩张牺牲、博爱、自治、自由、自主种种宝贵的精神,使精神生活高尚的理想发展,把基于贪得无厌、损人利己本位的组织改变,而基于爱的组织,那时世界就有保持和平的可能了。”如此我们可以大致想见那代留德学人在此期的文化活动,就金井羊而言,他还是颇有兴致积极参与的,当时这批朋友对泰戈尔访德颇有期待与讨论,将其视为东、西文化交通的标志之一,此处不赘。
1924年归国后,金井羊曾在张君劢主持的自治学院任教,所以与张氏关系颇密,这其中与共享的留德背景或也不无关系。金井羊在沪上历任多校,充任教授,社会地位较高,收入亦可,所以能雇佣家教。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钱仲联回忆说:“我到上海后,曾在金井羊教授家中任家庭教师。”另外一件事也值得提及,罗隆基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又为光华大学解聘,其间胡适为之奔走,曾拜托过金井羊,因其与陈布雷交好,可见金氏并非籍籍无名之辈。金井羊还颇通医术,曾帮助庐隐之夫郭梦良治病:“会金井羊先生颇知医理,见君(指郭梦良,笔者注)精神疲苶,舌苔极厚,因惊曰:‘此病势非轻,非请医调治不可。庐隐因恳其代请中医诊治。”后来又迁入上海宝隆医院,请德医诊断,虽不治而亡,但可以见出金井羊的医道及其背后的德国背景。
1932年,当金井羊辞世之际,很多人撰文悼念。钱基博以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名义草拟了《祭陈行救金井羊先生文》:“呜呼行叔,魂兮归来。瀛海涛涌,云马既愦。亦有井羊,霜凋夏绿。容貌堂堂,身长立玉……”这或许多少还带有校方色彩的表述,那么友人之誉则确实表现出其过人之处,相当不俗,譬如“近岁寡交游,然得心知一人焉,金君井羊是已。君粹于学,达于事,论学论政,麆麆有序,合于理而不戾于时;私意中国犹可为者,以君之学行才识,必受大任而有大成就。”期待不可谓不高。而且并非寰澄一人如此说法,胡善恒也称:“人的一生,在有几个道义的朋友,可以做学问物理上的商量,这种情感比任何经济上的欲望,政治的热心,家庭的安慰,尤为深切。近几年来,去世的朋友很有几人,而我心中的伤痛,实以井羊之死为最难堪。”胡善恒与金井羊经历颇似,也是早年留学日本英伦,是拉斯基弟子,归国后历经政、学两界,既为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等教授,也经历仕途,曾任湖南省、广东省财政厅长、行政院会计长等,都是经济官员。更重要的是,“井羊之有许多朋友,个个朋友都以井羊之死为最伤心”,一个人能做到这点,是相当不易的。黄炎培(1878—1965)这副挽联或许更能表现出金井羊的学养气度和人格风襟:
如此世变,如此国难,天奈何夺此清才以去;
敬君学养,敬君器识,吾矢愿依君遗书而行。
这些朋友都非平常人物,而均能以如此高标评价金井羊,虽免不了逝后褒扬的成分,但仍非泛泛虚应之辞,由此可见其绝非池中之物。这样的前贤人物,是值得后世追念的。金井羊与潘光旦是知交,两人曾在政治大学、光华大学等同事,所以潘光旦专门撰文悼念,其中解释说:“先生平日雅不欲以文字沽誉,故著述行世者不多见。”这可以见出金井羊虽为大学教授却著述零落的原因,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作品,譬如以金其眉(King Gee-Mai)之名在基爾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中国的货币制度》,据说还有《集资兴国》、《党政评议》两书,但未能查到。更重要的,当然是潘光旦对金井羊思想的深刻认识:
先生思想大旨:颇能洞察玄学冥想之弊,而以孔门之人本主义为归,故尝曰:“法社会学者孔德氏谓儒家之学为合于理性之宗教,某以为今后苟得有志之士,能含英咀华发挥而光大之,则不难为世界和平立一新基础也。惜国人说而不行,而西哲方吞云吐雾于所谓‘宇宙观,与程、朱误解格物之‘物字,可谓无独有偶;而其真正根本问题,遂未由解决矣。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其信然耶?”
这段话不但言简意赅地揭示了金井羊之基本思想,而且显示了他的博学、敏锐与洞见,一方面能通晓西方新学,譬如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学乃是西方的新兴学科,另一方面则更能打通中、西,即合于钱锺书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通”之理。金井羊不但能阅读孔德更能把握其思想的妙处,即其很有见地的判断——儒学确实在基本路径上通于理性路径,与欧洲启蒙思想的理性定位是相通的;而且儒学虽非宗教,但却未必完全没有宗教的面相,这也是日后韦伯将“儒教与道教”并列的原因。當然,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金井羊的实践品格,即更看重的是如何“起而行”,对西哲之沉于宇宙观讨论、国人之空言不行,都不以为然。但这可能也有其一定之误区,因为哲人的职责本就在于“袖手谈心性”,所谓的“哲学王”更多是一厢情愿而已,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两个不同的运行场域,各有其不同规则,像马克思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后来者秉承哲思而开辟实践路径,则确实应是为人类文明拓新道的不二法门,譬如孙中山强调“知行关系”就是一个例证。
潘光旦还提及了金井羊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先生哲学思想之见于文辞者尤难得,此为先生致侯城先生书中之最后数语,实为先生之绝笔,诚吉光片羽矣。书中于‘西哲二字下并附注曰:‘某以为不通自然科学与史学,而言哲学,是自欺欺人者也,故始终未加深究。其平居接人论学,虚怀若谷,大率类是。”这里涉及对知识整体与学科分割的关系,尤其是知识关联性问题,确属高见。其实凡学皆通,对于作为人类认知高端的哲学来说,尤其需要“博览综观”,如此自然科学考究自然规律、历史学理解人类文明,确实是不可或缺的知识支撑;当然文学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像德语文学这样本就承载着极为重要的哲思功能的文本,更不应被放置在哲学之外考察。但总体来说,虽寥寥数语,已可见金井羊的知学深思,非常人可比也。这一点也得到胡善恒的印证:“他(指金井羊,笔者注)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在现今决谈不到实现何种理想上的乌托邦,所以他说‘欲将现在笨重而复杂的政治机械一肩挑去,实非易事,不细思,乱发言,乌乎可,这是一个意志与理智的问题,决非感情问题。井羊是富于理想的人,而且是情感动荡人,没有一天不是想把国家如何整理起来,但是他发现了在事实上有两个绝大的障碍横亘于前。”其一是“全国人民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其二是“道德的堕落”,且与前者互为因果。此处则表现出金井羊侧重现实、关注起而行的面相,但又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他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的、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场域,确实需要这样的“明白人”去行动!所以,1929年,金井羊选择弃学从政,到铁道部任职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固然是受朋友的拖扯,实在也是他自己认为应当如此。最初他做铁道经济设计的事项,继而任参事,继而兼任债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继而又任财务司长,一年之内,频经迁职,正因为他之做事,是有原则,有理想,而又注意实际。有些朋友说井羊不应当做官,批评者自去批评,但是井羊以为对于国家服务,是国民应尽的职责,还可以从此中获得实际的经验,好却除一般空疏的理想”。从金井羊的基本思路来看,挺身入局也是他起而行的一种选择,所以也是顺理成章;而且他也确实有治事能力,做出了一些颇见功效的“政绩”,但其生病辞世则与其生性职业也恐非全无关系,所谓“先生体质素健,惟平居或勤自修,或为人虑事,或推论时局,精力虚耗亦多”,或也委婉点出其命门所在。如何惜身护体,对于精英人物来说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沈恩孚是当时沪上名流,曾任同济大学校长等职,其两子沈有乾、沈有鼎分别是心理学、哲学学者,外甥潘光旦是社会学家。他悼诗称:“正向淞波吊国殇,又悲志士欲沾裳!童季早识黄江夏,时政能伤贾雒阳。七叶家声貂系贵,五常才调马真良,秋风惆怅罗溪水,珍重楹书话故乡。”以长辈前贤的身份作此评价,不可谓不高不重,“国殇”、“志士”均是钟鼎之词,可见潘光旦对金井羊的学养敬重并非空穴来风,既有自身认知的一面,恐怕也不乏时人包括前辈之共识。1933年5月,担任中央大学兼任教授的俞大维,则捐款创设了“金井羊先生纪念奖学金”,以表达对金井羊的纪念深情,或可为金井羊的品格、友谊与贡献略作注脚。
像金井羊这样的人物,在中德关系史上恐怕未必在少数,他们未以大名显,也未以著述彰,但却绝非没有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很容易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甚至“大历史中的沉默者”,这不是他们的损失,而是后来者自身的遗憾,因为我们忽略了本不该忘却的可能精神资源。若非关注侨易群体而重新审视若干留德群体,进入到法兰克福的“中德文化研究会”学人群,我恐怕也难得深度介入作为个体的金井羊,但打捞这样的“无名”其实是研究者题中应有之意,不仅是为了前贤,也是为了后世与自身。金井羊虽英年早逝,但临终淡定如常,留遗嘱曰:“中国非有人焉能建立一新伦理学,则一切事业悉谈不到。在心方面应取涅槃之乐与无入而不自得之精神,而将一切迷信一切非分之想完全破除;在行方面,则当抱定勤俭忠实四字。”这里我们可见出金井羊的胸襟见识都非凡响,其虽立定于起而行的事业,但绝不忽视坐而思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新理论的学术建构方面,深抱期待,可见其作为一个教育家和学人的气象;而对于伦理学的重视,尤其是“新伦理学”的概念提出,实在是有重要意义。他大概不会不知道留德前辈蔡元培所撰《中国伦理学史》以及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这种伦理学理论建构的思路应有其学脉线索,但将其视为中国未来事业之枢纽,自非明断敏锐之眼光通识不能为,故不可不有以思之。
金井羊因其留德背景,所以自然对德意志有特殊感情,故他与德国的关系也值得记上一笔。“十九年,德国工业协会应我国政府请,遣实业团来华考察,周历粤、苏、浙、鄂各大埠,北行至平、津及于关外。当道使君款礼团员,口讲指画,昕夜编纂中、外文书,备极况瘁。德人极推重君,非君语不信。返国后,立华事研究会,为中德合作基础”。此处可以见出金井羊是很善于实务运作的,在和德方的交往中不仅能长袖善舞、折冲樽俎,而且能获得德方信任如此,真可谓是经济外交的好手。当然,金井羊并非为事务而做事务的职业官僚,他是有着背后的深意的,“君尝谓中国经济落后,非尽量用外资借技术以辟利源,不能图存。德自欧战后,与我订平等条约,尤有利无损。故极注重实业团事,劳瘁不辞”。
俞凤韶早年随张静江赴法经营实业,当过通运公司与通义银行的经理,后又历任民国时代沪上之政经要职,所以是一个有国际眼光的人,他认为:“君(指金井羊,笔者注)学有本原,博而能通,受董尼士及马克韦勃尔影响最深。与人言,渊溢泉涌,绝无拘沫、墨守之习,亦从不作浮光掠影之语。”这里揭示的学术资源值得关注,应为德国学术上的两位社会学大家即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与韦伯(Max Weber),这也可以理解,因金井羊留德之际所学即为经济学,这些学者的著作很可能就是他的学业必修课。但既入德邦,不可能不受到其大哲巨擘之精神影响,譬如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居谓德意志民族的菲斯脱领导思想为勃兴运动之原,乃慨然于国之作者。君爱国至挚,非无心于著述,惜授学从政,不遑有作,天又不假以年,使君为中国之菲斯脱也”,可见金井羊不仅对费希特心有敬重,而且也存效仿之意,这样一种勾连东西方文化,也跨越政治、经济、文化边际的“心理相通”其实是很值得揣摩回味的文明史现象,所谓“十年报国心肝,溘然竟弃人间世。风凄雨苦,萧条四壁,惟余图史。耗矣神州,哀哉吾党,罢闻博议。痛遗书半箧,烧灯检点,空飘坠,人情泪”。真是极为形象地描绘出一代英杰的凄凉悲剧,他们的报国心志,他们的挺身入世,他们的忧思长默,虽然谈不上是金戈铁马、轰轰烈烈,但同样也是可歌可泣、值得缅怀!走笔至此,涌到心头的竟是这样一句:“任尔风光长寂寞!”相对于那些未必深刻却能赢得俗世声名的人物,金井羊的哲思深沉其实意味深长,他的寂寞甚至匿声正说明了我们研究者的浅薄与短见。而像这样的现代留德学人或许未必就在少数,他们就如同藏在沙下的金子值得去深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