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墙上的布包
2021-06-23马晓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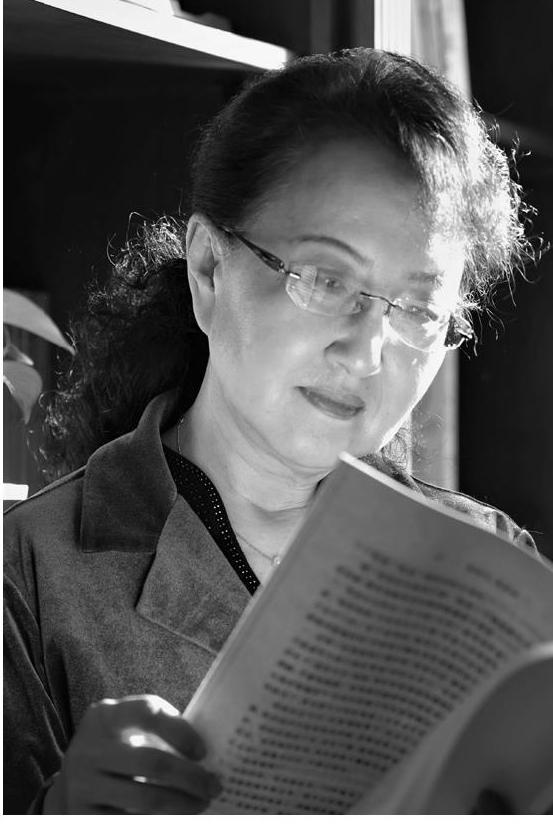
小时候的我一直是个孤独、自卑、羞怯的孩子。至今,我眼前还时常会浮现出儿时的孤独场景——
空荡荡的房间里,五岁的我抱紧自己蜷缩在床上,一声不吭地望着那扇由明到暗的窗户。我染上了传染性肝炎,被关进幼儿园一个单独的房间隔离。身边没有老师,也没有小朋友。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个老师进来告诉我,说我妈妈刚才来看我,因为不能进来,就让老师转交给我一包糖果。说罢,把装着糖果的布包挂在墙中间的一颗钉子上就走了。虽然没见到妈妈,但我还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从未一下子拥有过这么多糖果。我立刻爬起来去拿糖果,但那颗钉子太高,我踮起脚费劲地够着,也只能隔着布包摸到糖块,但就是拿不出来。听着糖纸哗啦哗啦的声响,我很难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哭,只是重新蜷缩到床上,无望地盯着墙上的布包,努力想象那些包裹糖块的漂亮糖纸和那些糖块的甜味。记得直到离开隔离室住进医院,我也没吃到一块糖。不是再没有老师来过,只是每一次,我都没有勇气开口求助。我希望老师会发现并主动问我,但没有。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些糖的下落,但那面空旷的墙,那颗孤零零的钉子,那高悬在墙上的布包,那孤独无助的心境,却深深地留在了我记忆中。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长得不讨喜,所以从小就自卑。我妈怀我时正患肺痨,严重时咯过半盆子血。医生告诫我妈不能怀孕,否则大人孩子都够呛。大概我爸我妈激情上来把医生这话给忘了,或者他俩根本就是想拼死一搏,结果我就趁机钻进了我妈的肚子里。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听医生的劝告把我干掉,反正我足月出生全须全尾地来到这世上了。可想而知,经那样一个病妈妈的身体孕育,我会长成怎样的一副可怜相。我自幼体弱多病,瘦小干枯,脸色蜡黄,头发稀疏,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学校,都没有人会在意我。孤独中,我学会了跟自己说话。有一次,我正自言自语地给自己讲故事的时候,被一个老师注意到了。还没等我为有人注意而感到高兴呢,就听见这老师大惊小怪地对另一个老师说:“你快看,她总是这样自言自语嘟嘟囔囔的,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呀?”那一刻,我听到自己的脑袋里发出咣当一声巨响,连接外面通道的那扇门突然关上了。我捂住耳朵埋下头,拼命想挡住那些嘈杂的声音。但没用,那声音像无数爪子伸向我,死死地卡住了我的脖子。从此,我的声带就哽在喉咙里很难发出声音了。我不再跟自己说话,也更加不愿意说话,对身处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
自卑和恐惧必然结出孤独之果。大概是因为儿时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我,致使我始终惧怕人群,羞于在人前现身、发声,习惯隐没自己,特别喜欢独处。
从事文学创作之后,常被人问及写作的初衷,我只好捋着来路去想。细细想来,极有可能与孤独有关。我发现,写作可能是我找到的另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方式,也是我自言自语习性的延续。也许,对如我这样孤独的人来说,文字是与外部世界相处的最舒适的一种方式,至少我这样认为。但我从来没敢公然说出,因为萨特有一句话压在我头上,他说:“只为自己写作是十分糟糕的,在你把你的感情投射到纸面上时,你只不过在设法使这种感情做无力的延伸而已。”我不喜欢萨特的说法,没有人是不为自己写作的,也没有人是只为自己写作的。从个体生命出发的写作,必然会唤起相近生命体的情感共鸣,这时的感情延伸就是充沛的,而不会是无力的。但萨特的名望太大,总让我不得不怀疑自己,就像再次遇到了一个认为我有毛病的老师那般,令我备感尴尬和无奈。
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究其原因还是内心的自然驱动,与我生命本体中自有的对自由的渴求有关。只不过之前我一直没能体察,没能细想而已。我很庆幸,在被规定被束缚的现实境遇中,我竟然能走到文学这条路上,找到这种与自己内心匹配的方式,通过写作来释放心灵,与这个纷繁的世界相处。我想不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方式能让我的灵魂如此自在,如此自由,如此放纵。
所以,我还是多少有点喜欢存在主义的萨特的。至少,以存在主义的本体论为基础,可以得出人拥有绝对的自由、人的自由即人的存在的结论。其实我更喜欢断章取义地接受萨特的说法,用“意识”具有否定权的自由性来说明个人存在的自由性。显然,我是在滥用萨特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理论,把萨特的学说当作“自在存在”,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与我的意识相关的部分,把其他部分虚无化,实现我的“自为存在”。这样做显然有点对不住萨特,但谁让萨特宣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有选择权呢?
对我来说,选择写作就是选择了一种自由的生存姿态。借由写作,我那蜷曲的灵魂得以一次又一次地从躯壳中逃脱出来,让我精神的躯体得以伸展。就是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灵魂出走,我逐渐摆脱了被规定被支配的思维定式,逐渐认识了自己,接受了自己,与自己和解,与孤独和解。
我还是时常会想起那个挂在墙上的布包。那个装满糖果的布包如文学一样高高地悬挂在那里,诱惑着我,吸引着我。我一直想把布包取下来,尽情品尝里面的糖果。我努力地踮起脚尖,伸长手臂,使劲地够呀够呀,已经摸到了包里的糖块,听到了糖纸哗啦哗啦的响声,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包取下来,没法吃到包里的糖。
好在我已经不再为此焦虑,更不会为此难过了。其实,我很感谢那个高悬在墙上的布包,它的存在给了我虚无的理由,赋予了我想象的自由,任我去自由地想象,自由地追求。
2021年2月18日
于海南清水湾
【小档案】
马晓丽,1954年出生于沈陽市。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
因受社会环境影响,马晓丽几乎未能完成任何阶段的学业。小学五年级逢全国停课,因此未能上完小学,没拿到小学毕业证。复课后直接进入初中二年级,但因初三即参军入伍,又未能上完中学,没拿到中学毕业证。于1969年12月入伍后,再无入学机会。在部队先后做过炊事员、通讯员、护理员、护士、干事等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在职修了函授大学的大专学历。
1987年,马晓丽在《中国青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夜》,获得全国青年短篇小说一等奖,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95年调入原沈阳军区文艺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马晓丽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楚河汉界》,长篇传记《王大珩传》,长篇纪实散文《阅读父亲》(与蔡小东合著),小说集《催眠》,散文集《不堪的朋友》,中篇小说《云端》《手臂上的蓝玫瑰》,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陈志国的今生》等。其中长篇小说《楚河汉界》被改编为长篇电视连续剧《将门风云》;中篇小说《催眠》被改编为同名话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另有作品被译成英文、波兰文介绍到海外。
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曹雪芹长篇小说奖,并多次获全军文艺创作一等奖及辽宁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