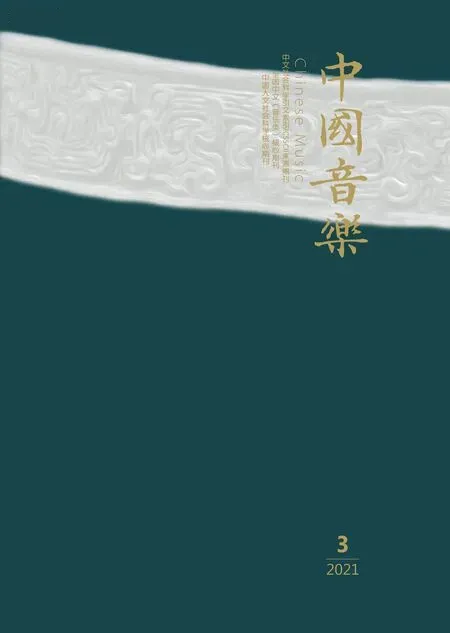宋代少数民族音乐钩沉
2021-06-21曾美月
○ 曾美月
宋代无论宫廷音乐,抑或文人、市民音乐,均较为繁盛,这些音乐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相比而言,宋代少数民族音乐较少受人关注。此外,由于唐代中华盛行西域音乐,人们也常将对外族外域音乐的关注集中于唐代。事实上,宋代少数民族音乐也有丰富表现,部分少数民族音乐活动从宋代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对宋代少数民族音乐进行钩沉,不仅可加深对宋代音乐多样性的认识,也可为部分至今仍活跃的少数民族音乐提供溯源研究。
“少数民族”一词,是近代以来形成并逐渐推广使用的概念。宋朝对汉族以外的其他周边民族,多统称为“蛮夷”“诸蛮”“诸夷”,并依据其所在地区与民族而有不同称谓,如境内的周边民族有“猺”“僚”“蛮”“峒”“夷獠”“黎”“蜑”等,他们大多是西南地区民族。宋朝境外民族有“回鹘”“党项”“吐蕃”“龟兹”等,均属“外国”。①以上“蛮夷”“外国”的称谓均取自《宋史》。而境外北方民族“女真”“契丹”建立的独立政权,更对宋朝政权构成巨大威胁,改变了宋朝疆域与政权状态。
宋代西南周边民族如今已并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而契丹、女真族虽已民族消散,融入其他北方民族,但其所属区域大多属于中国疆域。本文钩沉西南民族及北方契丹、女真族在10至13世纪的音乐状况,因此,沿用现代称谓,而将研究对象统称为“宋代少数民族”。
总体而言,古代周边民族的社会生活处于古代文化主流的关注之外,因此,有关他们的音乐的记录较为零散。但这些零散而珍贵的记录多出自宋代文人的亲眼所见,因此,它们又具备生动活泼的特质。本文依照“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尽力在有机联系的视域内呈现这些史料,以便于今人理解这些少数民族音乐的早期渊源。
一、宋代西南少数民族音乐
本文讨论的西南少数民族,包括广西、贵州、湘西地区的周边民族,如广西瑶族、壮族、湘西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瑶族,及贵州的周边民族。目前能钩沉出的宋代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他们的乐器、音乐活动方式、音乐传承方式等。
(一)乐器
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宋代广西桂林等地的少数民族已使用比较丰富的乐器,包括卢沙、铳鼓、胡卢笙、竹笛、腰鼓、铜鼓等,部分乐器被沿续使用至今。
1.卢沙、铳鼓、胡卢笙、竹笛
宋代广西瑶族的乐器有卢沙、胡卢笙、铳鼓、竹笛等。卢沙外形类似于排箫,由八根竹管编排而成;胡卢笙即今天的“葫芦笙”“瓢笙”。如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
徭人之乐,有卢沙、铳鼓、胡卢笙、竹笛。卢沙之制,状如古箫,编竹为之,纵一横八,以一吹八,伊嚘其声。铳鼓乃长大腰鼓也,长六尺,以燕脂水为腔,熊皮为面,鼓不响鸣,以泥水涂面,即复响矣。胡卢笙攒竹于瓢,吹之呜呜然。笛,韵如常笛,差短。大合乐之时,众声杂作,殊无翕然之声,而多系竹筒以相团乐,跳跃以相之。②[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7“徭乐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相似的记载还可见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铳鼓,猺人乐,状如腰鼓,腔长倍之,上锐下侈,亦以皮鞔植于地,坐拊之。卢沙,猺人乐,状类箫,纵八管,横一管贯之。胡芦笙,两江峒中乐。③[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0页。
卢沙属胡卢笙的一种,按当今学者的研究,“这种纵一横八的卢沙,是目前所知葫芦笙与排笙最早的融合再生物,其笙管穿过笙斗与之构成十字交叉的形制,与当今芦笙基本一致”④杨秀昭:《广西芦笙乐论》,《艺术探索》,2005年,第5期,第6页。。
胡卢笙又叫“瓢笙”,宋代《文献通考》曾对此进行考证。
胡芦笙(瓢笙):唐九部夷乐有胡芦笙,宋朝至道初,西南蕃诸蛮入贡,吹瓢笙,岂胡芦笙邪?⑤[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8·夷部乐》,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1222页。
在《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看来,唐代西南民族音乐已使用胡卢笙,宋代至道年间,西南少数民族曾向宋皇帝进贡,并吹瓢笙,这种瓢笙就是胡卢笙。至道元年(995年)西南民族进贡音乐之事,也可见于《宋史》的记载。
《宋史·卷496·西南诸夷》:至道元年,其王龙汉王尧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上因令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声,良久,数十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曰水曲。⑥《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966页。
上文记录的《水曲》就是西南民族的芦笙舞,其中一人吹胡卢笙,其他数十人围成圆圈、牵手而舞,舞蹈动作以足顿地为节奏。
按以上多种记录,芦笙是少数民族常用乐器,在唐宋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瓢笙、卢沙、胡卢笙多种形制与称谓,它有广泛的群众使用基础,也常被少数民族首领用于朝贡。
按《岭外代答》所记,铳鼓即黄泥鼓,鼓腔体呈红色,以熊皮制革为鼓面,演奏时需在鼓面上抹以泥水才能发声;按《桂海虞衡志》所提“腔长倍之,上锐下侈”的形制,铳鼓即今西南少数民族长腰鼓。此外,广西瑶族的竹笛与汉族竹笛类似,但比汉族竹笛略短。
宋代瑶族大合乐时,乐手与众人围在一起,乐手演奏铳鼓、卢沙、胡卢笙,有时有竹笛,众人身系竹筒,击竹筒为节,彼此跳跃,众声杂作。⑦[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其合乐时,众音竟哄,击竹筒以为节,团圞、跳跃、叫咏以相之。”第100页。
卢沙、铳鼓、胡卢笙至今仍是瑶族的常用乐器。芦笙在西南侗族、苗族、水族中也常被使用。
2.腰鼓
除以上三种乐器外,古代桂林还多用腰鼓。宋代桂林腰鼓用陶瓷做鼓腔,鼓面用羊皮或蛇皮鞔制,声响而富有穿透力。
《岭外代答·卷七·乐器门·腰鼓》:静江腰鼓最有声腔,出于临桂县职由乡,其土特宜,乡人作窑烧腔。鼓面铁圈出于古县,其地产佳铁,铁工善煅,故圈劲而不褊。其皮以大羊之革,南多大羊,故多皮。或用蚺蛇皮鞔之,合乐之际,声响特远,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⑧同注②,第149;150页。
《桂海虞衡志》:花腔腰鼓。出临桂职田乡。其土特宜鼓腔,村人专作窑烧之,细画红花纹以为饰。⑨同注③。
文献中提到的静江即桂林,临桂也属桂林,此地在历史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上文提到的“静江腰鼓”应就是“花腔腰鼓”。“作窑烧腔”即指其鼓腔是烧制而成的陶瓷材质,“细画红花纹”即指鼓腔上的彩绘花纹。按考古工作者推测,今广西永福窑田岭宋窑出土的瓷制腰鼓,就是文献中描述的“花腔腰鼓”。(见图1)

图1 永福窑田岭宋窑出土的青瓷腰鼓⑩图片引自章维亚:《灿若流星——宋代广西的瓷窑及瓷器》,《文物天地》,2015年,第7期,第23页。
3.铜鼓
宋代广西地区多出土古铜鼓,此情况在《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中有详细记录。
《桂海虞衡志·志器》: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其制如坐垫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其声全似鞞鼓。⑪同注③。
《岭外代答·卷7·乐器门·铜鼓》: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据其上,蟾皆类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为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交趾尝私买以归,复埋于山,未知其何义也。按《广州记》云,俚僚铸铜为鼓,唯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不知所铸果在何时。按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或谓铜鼓铸在西京以前。此虽非三代彝器,谓铸当三代时可也。亦有极小铜鼓,方二尺许者,极可爱玩,类为士夫搜求无遗矣。⑫同注②,第149;150页。
宋代西南“蛮人”“骆越”“俚獠”“峒夷”均使用铜鼓。上两则文献详细描述了出土铜鼓的形制,如上所记“其制如坐垫而空其下”“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四角有小蟾蜍”等,与今人见到的广西出土铜鼓相同。铜鼓的纹饰有“太阳纹”“云雷纹”“席纹”“钱纹”等多种,⑬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中国古代铜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岭外代答》所记“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即分别是“钱纹”和“席纹”。
铜鼓是一种较多见的古代少数民族乐器,主要用于村寨集会、重大盛典、战争来临时的村落人群召集等,也是民族首领的权利象征。
《宋史·卷493·西南溪峒诸蛮(上)》: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⑭《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931页。
按《宋史》所记,贵州南部的侗族治疗疾病时,往往击打铜鼓、沙锣两种乐器以祭祀鬼神。
对于爱好古董的宋代士大夫而言,西南周边民族的铜鼓是他们喜爱收藏的佳物,出土的铜鼓常被士大夫“搜求无遗”、用于玩赏。此外,铜鼓也被少数民族用于进贡。
《玉海·卷110·乾德铜鼓》:乾德四年四月辛亥,南蛮进铜鼓,以请内附。七月丁丑,溪州刺史田思迁以铜鼓来贡……淳化元年七月,南丹州刺史洪皓贡铜鼓三。景德元年四月癸酉,象州贡铜鼓,高一尺八寸,阔二尺五寸,旁有四耳衔环,镂人骑花蛤,椎之有声。⑮[宋]王应麟:《玉海》第三册,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本,2003年,第2024页。
溪州是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南丹是广西西北部的多民族聚居区,以壮族为主,也有瑶族;象州是广西中部的壮族聚居区。这些地区曾分别在宋代乾德、淳化、景德年间向朝廷进献铜鼓。淳化年间南丹进献铜鼓之举是当年的大事,此事也可见于《宋史》的记载。⑯《宋史·卷494》“南丹州蛮”:“淳化元年,洪卒,其弟洪浩袭称刺史,遣其子淮通来贡银盌二十,铜鼓三面……上降优诏,赐彩百匹。”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0页。
由此钩沉可知,宋代广西、贵州、湘西几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均使用铜鼓。一方面,这些地区出土的古铜鼓受到宋朝汉族士大夫的珍爱与收藏,另一方面,这些民族也将自己的铜鼓作为贡品进献给宋朝朝廷,同时,铜鼓也是少数民族用于祭祀、禳灾的重要器物。
今天的西南地区如壮族、瑶族、水族、毛南族、彝族、布依族均有使用铜鼓的传统。学者将西南铜鼓民族与东南亚诸国使用铜鼓的民族合称为“铜鼓文化圈”,⑰万辅彬、韦丹芳:《试论铜鼓文化圈》,《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在这些地区当中,尤其以广西出土的铜鼓数量最多。不少铜鼓圆平面的上方饰有蟾蜍,与这些民族对青蛙的崇拜有关。至今广西壮族群众中仍有蛙婆节,它是壮族的传统节日,体现了壮族群众的原始青蛙图腾崇拜。⑱袁炳昌、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0页。此章“壮族音乐史”由范西姆、赵毅撰写。
(二)婚丧礼俗音乐
宋代西南少数民族礼俗音乐见于记载的主要有婚嫁、祭祀、丧葬活动中的音乐活动。具体而言,他们的婚嫁与寻偶音乐活动主要表演为:婚嫁仪式中有送老歌唱,祭祀、农闲时有踏摇、踏歌、芦笙舞中的对歌寻偶。他们的丧葬活动中的音乐主要表现为鼓吹。
1.婚嫁、祭祀、农闲中的音乐与寻偶活动
(1)送老
“送老”是宋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嫁仪式。从字面上来理解,“送老”一词就是指姑娘出嫁、与丈夫共同偕老之意。
《岭外代答·卷4·风土门·送老》:岭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饰庙坐,女伴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道之偕老也。其歌也,静江人倚《苏幕遮》为声,钦人倚《人月圆》,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凡送老皆深夜,乡党男子群往观之,或于稠人中发歌以调女伴,女伴知其谓谁,亦歌以答之,颇窃中其家之隐匿,往往以此致争,亦或以此心许。⑲同注②,第88页。
出嫁前夕,新娘与女伴皆着盛装,众女伴围着新娘为她唱歌,以表达深情、分别之意。由于“送老”时常歌唱至深夜,因此常有邻村的男子结伴前往观看,并挑选女伴群中的女子对歌,双方经此进一步相互了解,则有可能彼此以心相许,不久后结为良缘。因此,“送老”不仅是婚嫁仪式,也是男女青年的择偶活动。桂林(属静江府)的百姓在歌词编撰方面有很强的独创性,很少有蹈袭现象。
以歌唱而“送老”,是宋代西南民族的婚嫁形式。近代以来,湘西、鄂西、岭南、黔东等地的壮族、土家族、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等多种民族普遍存有的“哭嫁歌”或“婚嫁歌”,就是宋代“送老”婚嫁仪式活动的遗存。
上文中提及的“乡党男子……于稠人中发歌以调女伴,女伴知其谓谁,亦歌以答之”的对歌,是前往参加婚礼的其他未婚男女寻找意中人的活动,这种宋代已普遍存在的寻偶方式,也在今天的侗族、仫佬族、苗族、水族、京族等多个西南民族中长期留存。
(2)踏摇
祭祀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信仰仪式。祭祀期间的踏摇,本质上也是少数民族青年寻求配偶的活动。
《岭外代答·卷10·蛮俗门·踏摇》:徭人每岁十月旦,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其庙前会男女之无室家者。男女各群,连袂而舞,谓之踏揺。男女意相得,则男吚嘤奋跃,入女群中负所爱而归,于是夫妇定矣。各自配合,不由父母。其无配者姑俟来年。女三年无夫负去,则父母或杀之,以为世所弃也。⑳同注②,第264页。
宋代瑶族每年十月祭祀本族神灵“都贝大王”,祭祀期间,广西瑶族男女在寺庙前牵手而舞,宋代汉人将其称为“踏摇”。在踏摇过程中,尽管男女分群而舞,但若男女双方彼此有意,男青年便跑入女群中,将所爱之女背负而归,自此结成夫妇。由此可见,踏摇与“送老”婚嫁活动中的对歌有相同性质,都有寻求婚配对象的特点。
在祭祀或农闲时通过对歌或歌舞择偶,是很多少数民族的普遍择偶方式,如苗族、侗族、仫佬族、水族等,宋代广西瑶族的祭祀踏摇择偶歌舞既有一定的代表性,也证明了少数民族择偶歌舞的早期渊源。
(3)芦笙舞与踏歌
西南少数民族在农闲时,众人围成圆圈歌舞、中间有一、二人吹笙前导,此场景曾一度被今人所熟悉,而这种歌舞情景已能见于宋代。
《老学庵笔记·卷4》:辰、沅、靖州蛮有犵狑,有犵獠,有犵榄,有犵,有山猺,俗亦土著……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夜疲则野宿。至三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上元则入城市观灯。呼郡县官曰大官,欲人谓己为足下,否则怒。其歌有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盖《竹枝》之类也。㉑[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83页。
陆游《老学庵笔记》讲述的辰、沅、靖三地分别是古代辰州、沅陵、靖州,此三地今属湖南怀化,是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地。文献中提到的犵狑是仡佬族的一支,犵獠即仡佬族,山猺即瑶族。踏歌与踏摇应是相同类型的活动,这段文献中还提及了芦笙舞。宋代湘西的少数民族时常在农闲时聚而踏歌,有时一二百人围聚,几人吹笙前导,边歌边舞,饥饿时以酒代食,持续三日、五日或七日昼夜。其中的歌词“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具有邀歌的性质,说明这种芦笙舞集体活动也含有对歌寻偶的成分。
芦笙舞是西南民族的文化代表,《宋史》“西南诸夷”记录,西南牂牁郡王带人给北宋太宗赵炅上贡,其中就表演了芦笙舞,而其中有动作“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因此又称为踏歌。㉒《宋史·卷496·西南诸夷》:“至道元年,其王龙汉 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上因令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声,良久,数十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4225页。
《老学庵笔记》记录的宋代湘西少数民族群聚、跟随笙、笛乐歌舞的场景,在今天仍被人所熟悉,我们时常能通过各种媒介看见少数民族围着篝火手牵手踏歌、中间数人吹奏芦笙引领的场景(见图2)。清代云南巍山彝族壁画中的树下踏歌图(见图3),两人吹笙、一人吹笛,群人握手围成圈、歌唱舞蹈,其情景与《老学庵笔记》的描述相同。

图2 当代贵州芦笙舞

图3 云南巍山彝族壁画中的树下踏歌图㉓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史图鉴》,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李廷贵《漫话苗族芦笙舞》描述:“湖南《永绥厅志》所记湘黔交界苗族的芦笙舞也很壮观:‘男外旋,女内旋,皆举手顿足,其身摇动,舞袖相连。而芦笙之音与歌相应。悠扬高下,并堪入耳。’”㉔李廷贵:《漫话苗族芦笙舞》,《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封二。由此可知,宋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录的芦笙舞活动在经历明清代以后,一直延续至今。西南民族的侗族、瑶族、苗族、彝族等,均有跳芦笙舞的传统,“跳月”“跳花”“踩笙堂”等称谓,也与此渊源有关。
2.丧葬活动中的鼓吹
见于记载的宋代广西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与汉族地区有很大不同:死者的邻居聚集死者家中,并鼓吹昼夜,且死者家属的制服上有白巾缀红线。这种丧葬仪式的不悲反喜意味,被汉族文人诗歌评价为“箫鼓不分忧乐事,衣冠难辨吉凶人”。
《岭外代答·卷7·乐器门·白巾鼓乐》:南人死亡,邻里集其家,鼓吹穷昼夜,而制服者反于白巾上缀少红线以表之。㉕同注②,第152;151;148页。
“白巾鼓乐”的丧葬音乐习俗是广西古百越族的传统,至今的广西南丹等地的壮族丧葬活动中,仍有欢乐葬礼的成分。㉖覃丽芳:《中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的传统丧葬礼仪》,《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8页。
3.驱傩
驱傩是一种与信仰有关的节日音乐活动,并有着古老的传统。唐代宫廷每年在除夕之夜驱傩,由教坊大使扮演。少数民族地区的驱傩传统更为普遍,宋代广西的瑶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也有驱傩表演。
《岭外代答·卷7·乐器门·桂林傩》: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㉗同注②,第152;151;148页。
《岭外代答》记录的广西傩戏,包括静江军傩、百姓傩。静江军傩是名闻京师的正规傩队,傩队表演严整,服装道具成熟,面具制作优良,进退言语与队仗等均可观。而百姓傩则在普通百姓中更为普及。
有些驱傩表演有乞讨钱米的性质,如《桂海虞衡志》所记,“岁暮,群操乐入省地州县,扣人门乞钱米酒炙,如傩然”㉘同注⑨,第142页。。这里提到广西瑶族的百姓在年底的时候,众人一同入州县敲门乞米,如同驱傩表演一般。由此可以推测,瑶族的百姓驱傩表演带有乞米交换的商业性质。
今天的西南少数民族仍有表演傩戏的传统,广西毛南族傩戏、壮族师公戏均与《岭外代答》所记的桂林傩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㉙胡仲实:《广西傩戏(师公戏)起源形成与发展问题之我见》,《民族艺术》,1992年,第2期,第99页。毛南族的傩面具至今享有盛名。
(三)音乐传承
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有古老的传统,在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变化较小,不少音乐样式与方式从宋代绵延至今,其中原因在于,他们的音乐有着良好的传承。
《岭外代答·卷7·乐器门·平南乐》: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城郭村落,祭祀婚嫁丧葬,无一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相之,盖日闻鼓笛声也。每岁秋成,众招乐师教习子弟。听其音韵,鄙野无足听。唯浔州平南县系古龚州,有旧教坊乐,甚整。异时有以教坊得官,乱离至平南教土人合乐。至今能传其声。㉚同注②,第152;151;148页。
广西少数民族百姓能乐者极多,音乐也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祭祀、婚嫁、丧葬等重要的仪式活动,乃至日常耕田等行为,都需要使用音乐。广西平南的少数民族有良好的音乐传承机制,每年秋天收割之后的农闲时间,众村寨里的乐师就会教习年轻人学习音乐。这种音乐传承机制也在不少西南少族民族中延续至当代,侗族歌班就是典型案例。
二、宋代的契丹族音乐
契丹族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10世纪,契丹族雄踞宋朝北方并建立辽国,创立了长达200年的辉煌的契丹辽文化。契丹辽与宋朝之间也有各种形式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随着辽政权的衰落,契丹族逐渐走向衰亡,尽管如此,当今学术界一直热衷对契丹族的研究:关于契丹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有契丹族起源于鲜卑族、起源于蒙古族等多种学说;㉛参见郭晓东:《20世纪以来契丹族源研究述评》,《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关于契丹族衰亡后的族群与后裔流向,据DNA提取检测,契丹族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此外,也有契丹族融入蒙古族、融入其他民族等多种说法。㉜参见贾秀梅:《契丹族消亡探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19期;王迟早、石美森、李辉:《分子人类学视野下的达斡尔族族源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因此,钩沉宋代契丹族的音乐活动,可为北方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的音乐文化提供溯源研究,也可为契丹族的后裔流向提供旁证。
总体而言,辽契丹族的民间音乐保留了浓厚的契丹族音乐传统与特色,而作为辽政权,他们的宫廷音乐既保留了契丹族民族信仰和特点,也对汉族音乐有所接受与使用,并表现出本族音乐高于汉族音乐的接受态度。
(一)宫廷礼俗音乐
契丹族建立辽政权以后,契丹族首领的音乐活动便有了一定的宫廷性质,但这些官方音乐活动仍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契丹族的民族习惯与传统。
1.宫廷典礼与祭祀的音乐
对于契丹族首领而言,接受册命是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仪式,而带领族群去圣山祭祖,则是最重大的宗族信仰活动。这两项活动中,都有音乐伴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凡受册,积柴升其上,大会蕃人其下,巳,乃燔柴告天,而汉人不得预。有诨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将尽,歌于帐前,号曰“聒帐”。每谒木叶山,即射柳枝,诨子唱番歌,前导弹胡琴和之,已事而罢。㉝[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61页。
这条文献可见于《辽志》“宫室制度”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天圣九年”两种典籍的记载,其中叙述了契丹族首领受册的仪式过程,即:坛上燃烧柴堆、众人聚集于坛下,通过燃烧柴堆向上天祷告,其后,被称为“诨子”的乐人轮番于拂晓未明时在首领帐篷前唱歌,称为“聒帐”。木叶山是契丹族的发祥地,也是他们的祭祖圣地。每次拜谒木叶山时,乐人“诨子”于队伍前唱本民族歌曲,另有乐人弹胡琴以和。在这两场重要的活动中,乐人在首领帐篷前“聒帐”唱歌,或是祭祀队伍前导的弹胡琴唱歌,都是与信仰相关的音乐活动。
在当今的达斡尔族的萨满斡包祭中,仍保留有契丹族祭祀木叶山的习俗,“契丹的祭山仪与达斡尔的祭斡包相同之处颇多,作为契丹族后裔的达斡尔族,以斡包祭的形式继承了先祖契丹在祭山仪时祭祀天地神祗的做法”㉞王雨竹:《达斡尔族斡包祭的文化研究》,2019年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辽国政治场合一般的音乐活动,则又与以上所述不同。契丹族建立辽国之初,辽太宗耶律德光曾得到晋朝的乐谱、宫悬、乐架等,将之带回辽国都城中京,㉟《辽史·卷54·乐志》:“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36页。故而辽国宫廷音乐体制承袭了中朝礼乐传统。《辽史·卷54·乐志》如此记载辽国国乐:
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故志其略……元会,用大乐;曲破后,用散乐;角抵终之。是夜,皇帝燕饮,用国乐……七月……十四日设宴,应从诸军随各部落动乐。㊱《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35;536页。
文中提到的辽国宫廷在元会日用歌舞,在曲破、散乐之后用角抵,带有草原民族的意味, “国乐”中“各部落动乐”,就是辽国契丹的本族音乐。
《辽史》“诸国乐”提到少数民族音乐的表演:
天祚天庆二年,驾幸混同江,头鱼酒筵,半酣,上命诸酋长次第歌舞为乐。㊲《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35;536页。
这里提到的各部落首领依次歌舞,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中的一种用乐典礼。
2.节日民俗音乐
正旦、中元两日,分别是正月初一日、七月十五日,这两日无论对于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而言,都是重要的节日。
《辽志·岁时杂记·正旦》:正月一曰,国主以糯米饭、白羊髓相和为团,如拳大,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候五更三点,国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在帐外如得双数,当夜动番乐,饮宴;如得只数,更不作乐,便令师巫十二人,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喝叫,于帐内诸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祟”。帐人第七曰方出,乃解禳之法。㊳[宋]叶隆礼:《辽志》,引自[明]陶宗仪纂《说郛》卷86,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十一册。
上文叙述的是契丹族宫室在每年正月初一的民俗音乐活动。当日,国王宫室做糯米饭团若干,每个帐篷内放置49个,凌晨五更时,国王等人在帐篷内朝窗外掷饭团,在窗外若得双数饭团,则是吉兆,当晚宴饮、大兴本族音乐,若得单数,则视为不吉,并令巫师举行“惊鬼祟”的解禳活动。在正月初一凌晨以捡饭团的双、单数来判断吉凶,并举行相应的音乐宴饮庆祝活动,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
契丹族在中元节也有盛大的音乐活动。
《辽志·岁时杂记·中元》:七月十三日夜,国主离行宫,向西三十里卓帐。先于彼处造酒食。至十四曰,一应随从诸军并随部落动番乐,设宴至暮,国主却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动汉乐,大宴。㊴[宋]叶隆礼:《辽志》,引自[明]陶宗仪纂《说郛》卷86,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十一册。
其活动步骤表现为:十三日先行离开行宫,在西边三十里处造酒食;十四日,众随从在帐篷中宴饮并表演本民族音乐;十五日,大型宴饮,并演奏汉族音乐。契丹族中元节的宴乐活动中,本族音乐与汉乐并举,充分说明了契丹族对汉乐的接受程度。
3.对汉乐的接受
辽契丹族一方面保留了本民族的民俗活动,一方面也接受了来自中华音乐的影响,他们不仅在中元日传统汉族节日里轮番演奏本族音乐与汉乐,也在新生儿出生的时候,依照新生儿性别、选择演奏本族音乐或汉乐。
《燕北录》:若生儿时……戎主着红衣服,于前帐内动番乐,与近上契丹臣僚饮酒……如生女时,戎主着皂衣,动汉乐,与近上汉儿臣僚饮酒。㊵[宋]王易:《燕北录》,载车吉心、王育济:《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济南:泰山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如上所记,契丹族首领家有孩子出生时,若出生的孩子是男性,契丹族首领便着红衣、在帐篷前演奏本族音乐、与契丹族臣僚宴饮以示庆贺;若出生的孩子是女儿,首领便穿皂色衣服,在帐篷前演奏汉乐、并与汉族臣僚饮酒。可见在契丹族人看来,本民族音乐的地位是高于汉族音乐的。
辽契丹族对汉族音乐的接受,也表现在他们对汉族礼文化的接受与了解。
《虏庭事实·释奠》:距燕山东北千里,曰中京大定府,本奚霫旧地。其府中亦有宣圣庙,春秋二仲月,行释奠之礼。契丹固哥相公者,因此日就庙中张宴。有胡妇数人,丽服靓装,登于殿上,徘徊瞻顾。中有一人曰:“此鬍者是何神道?”答曰:“者便骂我‘夷狄之有君’者。”众皆发笑而去矣。㊶[宋]文惟简:《虏庭事实》,载《说郛》卷8,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二册。
上文叙述辽国中京大定府宣圣庙释奠礼中的戏剧表演:胡人妇人数人装扮靓丽,其中一人问:“此鬍者是何神道?”另一人回答:“你是骂我‘夷狄之有君’吧?”“夷狄之有君”这句话来自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京大定府是辽国的重要都城,原是古民族奚霫的旧地。在辽国都城建有祭孔庙宇,并由契丹人上演由孔子语录改编的戏剧,说明契丹族对汉族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二)契丹族日常音乐活动
契丹族的官方音乐体现了对本族音乐的继承和对汉族音乐的吸收。而民间日常音乐活动最能体现他们的民族特色。
《画墁录》:北虏待南人礼数皆约毫末,工伎皆自幽涿遣发之帐前,人以为劳。乐列三百余人,节奏讹舛,舞者更无回旋,止于顿挫伸缩手足而已。角抵以倒地为胜,不倒为负。两人相持终日,欲倒不可得。㊷[宋]张舜民:《画墁录》,载朱易安、傅璇琮主编:《全宋笔记第二编(1)》,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
上文提到的“幽、涿”地属幽云十六州,因此,这里所讲的北人应是辽国契丹人。这条文献描绘了北人舞蹈的姿态:舞蹈时并无宛转回旋,而是“顿挫伸缩手足”。
周菁葆《新疆达斡尔族音乐舞蹈》说:“达斡尔族舞蹈中双手左右推掌,步法上用跺步、跳步,道具上用八角鼓,由此变化组合各种动作,形成了其舞蹈的基本特点。”㊸周菁葆:《新疆达斡尔族音乐舞蹈》,《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2页。可知《画墁录》对契丹族舞蹈的描绘与今日的达斡尔族舞蹈特征非常接近。
《宋会要辑稿·16册·蕃夷二·辽下》:渤海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锤”。㊹[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册,第9741页。
《宋会要辑稿》中的这段渤海契丹族的歌舞音乐描绘也可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大中祥符五年”条目。其中记录渤海契丹人有“踏锤”的习俗,即在每年大聚会时,众人由少数擅长歌舞者带领、相互唱和回旋舞蹈。
(三)契丹音乐对中华的影响
契丹音乐对中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宋代最盛行的器乐形式鼓板是由契丹族器乐形式发展而来。
鼓板由鼓、笛、拍板组成,在宋代又名“太平鼓”“打断”。这两者名称见于《能改斋漫录》卷1“禁蕃曲毡笠”:
崇宁大观以来,内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断”。至政和初,有旨立赏钱百五千;若用鼓板改作蕃曲子,并著北服之类,并禁止支赏。其后民间不废鼓板之戏,第改名“太平鼓”。续又有旨:“一应士庶于京城内不得辄戴毡笠子,如有违犯,并依上条。”㊺[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上),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第16页。
这一文献明确阐述“鼓笛拍板名‘打断’”,且“内外街市”盛行。徽宗政和初年,朝廷反对演奏番曲与打断,民间遂将“打断”改名为“太平鼓”而继续使用。
鼓板这一器乐形式由契丹族流传而来,《文献通考·卷148·夷部乐》中记录了它的乐器组合编制、来源及流传情况。
臣观契丹视他戎狄最为强桀……而中国第其蕃歌与舞。其制:小横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和之,其声喽离促迫,舞者假面,为胡人衣服,皆效之,军中多尚此伎。太宗雍熙中,恶其乱华乐也,诏天下禁止焉,可谓甚盛之举矣。然今天下部落,效为此伎者甚众。非特无知之民为之,往往士大夫之家亦喜为之。诚推太宗禁止之制。㊻[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第1293页。
笔者在拙文《宋代的耍令、番曲与鼓板——由此看宋朝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交流》一文中,对宋代鼓板的来源与使用情况有具体阐述。鼓、笛、拍板的组合最初来源于契丹族,北宋雍熙年间、政和初年间,由于两族关系的恶化,这一音乐形式屡次遭遇宋朝廷禁止,但从雍熙直至建中靖国年间,它在中华地区的流行程度仍然成逐渐扩散趋势。崇宁、大观年间,因朝廷禁止使用此乐,百姓则将其改换名称为“打断”而继续使用。政和三年时,朝廷颁布大晟乐,更严格禁赏这种音乐,而都市民间将其改名为“太平鼓”继续使用。㊼曾美月《宋代的耍令、番曲与鼓板——由此看宋朝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交流》,《文化艺术研究》,2010年,第2期,第93页。
鼓板器乐形式后来传入宫廷,《武林旧事》“乾淳教坊乐部”之名单记录中,就有这一器乐组合形式,说明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朝廷对鼓板的态度已由北宋时期的禁止转向接受。宋代《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等,均有对鼓、笛、拍板组合使用的相关记录,说明这种器乐编制曾被广泛使用。
三、宋代的女真族音乐
女真族是古代生活在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少数民族,12世纪,女真族势力兴起、迅速扩张并建立金国,对宋朝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关于女真族的族源,学术界一般认为靺鞨族是女真人的祖先之一,而明清满洲人是女真族的后代,因此,钩沉宋代女真族的音乐,可为满族及其他东北少数民族音乐提供溯源研究。
(一)女真族官方场所音乐
女真族于1115年建立金国,“靖康之难”后,金人将宋朝宫廷的乐器乐工带回本国宫廷,因而,金国宫廷的用乐基本沿袭宋朝宫廷音乐体制,“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㊽《金史》,北京:中华书局,第1999年,第577页。。金建国后的宫廷音乐,包括“雅乐”“鼓吹乐”“郊祀乐歌”等,与中华宫廷礼乐并无太多不同。
在政权官方场合,金国的音乐既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又与女真族的民间音乐呈现出专业程度上的差异性,其中也体现出女真族对汉族音乐的吸收。《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第二十八程”记录咸州州府音乐活动,可以得知金国官方场所的音乐状况。
第二十八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未至州一里许,有幕屋数间,供帐略备,州守出迎,礼仪如制。就坐,乐作,有腰鼓、芦管、笛、琵琶、方响、筝、笙、箜篌、大鼓、拍板,曲调与中朝一同,但腰鼓下手太阔,声遂下,而管笛声高,韵多不合,每拍声后继一小声。舞者六七十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殊不可观也。酒五行,乐作,迎归馆,老幼夹观,填溢道路。次日早……赴州宅,就坐,乐作,酒九行。㊾[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载《全宋笔记第四编(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是作者许亢宗作为使者出使金国的行程记录,咸州即今辽宁开原。这里记录他从兴州到咸州的路上,咸州官方出迎他所用的音乐状况,乐队中所用的乐器包括腰鼓、芦管、笛、琵琶、方响、筝、笙、箜篌、大鼓、拍板等。
宋代汉族器乐合奏形式包括“教坊大乐”“鼓板”“马后乐”“清乐”“细乐”等,㊿曾美月:《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132–138页。而《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第二十八程”条目罗列的金国咸州官邸用乐,不同于宋代中华器乐形式的任何一种编制,从乐器构成来看,基本可以判定此处的音乐兼用了汉乐器与胡乐器。金国咸州州府用乐的曲调与宋朝相同,且也有五行或七行盏制,但作者许亢宗仍认为这些乐工水平不高,如,金国腰鼓乐工“下手太阔”,笛管“韵多不合”,舞蹈“殊不可观”。文中描绘,乐队演奏时在每拍声后“继一小声”,此应是女真族音乐的一种装饰手法。舞蹈时出手袖外、回旋曲折,也应是少数民族舞蹈的一种专有特色、而不同于当时中华汉族舞蹈。
综上可知,金国咸州官邸用乐兼用了本民族与汉族音乐特色,即,沿用了本民族舞蹈特色,吸收了汉族的宴乐体制与曲调。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第三十九程”记录金国国王招待宋朝使者所用的宴乐,可以得知中朝音乐对女真、契丹的巨大影响。
第三十九程:乐如前所叙,但人数多至二百人,云乃旧契丹教坊四部也。每乐作,必以十数人高歌,以齐管也,声出众乐之表,此为异尔……次日,诣虏庭赴花宴,并如仪。酒三行,则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刀牌、砑鼓、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挝簸旗、筑球、角抵、斗鸡、杂剧等,服色鲜明,颇类中朝;又有五六妇人,涂丹粉,艳衣,立于百戏后,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如祠庙所画电母,此为异尔。……次日,又有中使赐酒果,复有贵臣就赐宴,兼伴射于馆内。庭下设垛,乐作,酒三行,伴射贵臣、馆伴使副、国信使副离席就射。[51]同注㊾,第15–17页。
女真族国王招待使者所用的宴乐,规模近二百人。乐队演奏之始,以人声唱歌引领乐器齐奏,作者对此表示“声出众乐之表,此为异尔”,说明作者对歌唱者的赞叹。花宴用百戏,种类包括踏索、上竿、弄丸、角抵、杂剧等,类似中华百戏。此外,女真族国王、贵族宴乐时也有射礼,射箭时行酒三巡、并伴有音乐演奏。
上文中提到的“五六妇人各持两镜”的表演,应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萨满教仪式,“两镜”就是萨满教仪式中使用的“神镜”。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族,如契丹、女真、达斡尔、满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都信仰萨满教,萨满教跳大神中,铜镜是驱邪的法器。[52]景爱:《达斡尔族歌舞的产生和演变》,《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第66页。刘桂腾《达斡尔族萨满音乐》如此描述萨满神镜:“托力,汉译‘神镜’,在达斡尔人那里,托力被认为是雅德根神灵的象征。”[53]刘桂腾:《达斡尔族萨满音乐》,《乐府新声》,2008年,第2期,第104页。
从这场被称为“旧契丹教坊四部”的女真宫廷宴乐来看,其中既有女真本族特色的保留,如乐队演奏前先以歌声引导,萨满教歌舞表演等,又有对中华音乐的吸收,如百戏种类、射礼用乐等。
(二)女真族民间音乐
1.民俗音乐
宋代女真族民间音乐与金国官方音乐不同,由于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小,因而具备更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虏庭事实》“风俗”条目记录:
女真风俗,初甚淳质。其祖宗者,不知人主之为贵,邻人酝酒欲熟,则烹鲜击肥而邀主于其家,无贵贱、老幼团坐而饮,酒酣则宾主迭为歌舞以夸尚。今则稍知礼节,不复如此耳。[54]同注㊶。
这里提到了女真族早期的淳质民风与民俗音乐:邻居家酿酒欲熟时,则烹饪肥美的食物、邀请主人一起去邻居家,众人无论身份贵贱、全都围坐在一起饮酒,醉酒后则众人轮流作歌舞表演。
女真族人有着乐观的天性,即使遇上丧葬事件,也要歌舞为乐。如《虏庭事实》“血泣”记录:
尝见女真贵人初亡之时,其亲戚、部曲、奴婢设牲牢、酒馔以为祭奠,名曰“烧饭”。乃跪膝而哭。又以小刀轻厉额上,血泪淋漓不止,更相拜慰。须臾,则男女杂坐,饮酒舞弄,极其欢笑。此何礼也?[55]同注㊶。
这里记录,身份较高贵的女真族人死亡时,他的亲戚、部下、女婢等先设牲牢释奠、哭丧,并以小刀轻割头额,使自己血泪双流,各自安慰后,则很快转换情绪,男女杂坐、饮酒歌舞欢笑。
以上文献说明女真族在酒熟、丧葬时均用歌舞音乐。这种无惧身份贵贱、无惧男女杂坐而饮酒歌舞的习俗,是完全不同于汉族士人的伦理传统的。不仅如此,辛弃疾《窃愤录》记录女真族欢庆正月旦日的歌舞场景:“二人相见,以手交腋,歌舞笑语。”[56][宋]辛弃疾:《窃愤录》,载《全宋笔记第四编(4)》,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69页。此说明女真族无论欢乐或悲哀时,只要聚集在一起,就会用音乐歌舞助兴。
辽国曾一度统治女真族,为了分化女真族的势力,辽政权将部分女真族纳入辽国的国籍,称为“熟女真”,将部分势力较弱的女真族留在原地,称为“生女真”。《文献通考·卷327·四裔考四》“女真”条目记录:“延禧天庆二年,钓鱼於混同江,凡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会,酒酣,使诸酋歌舞为乐。”[57][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第2571页。这段文献叙述辽国首领天祚皇帝在延禧天庆二年(1112年)巡视生女真,并命令各生女真的酋长为他歌舞助宴。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歌舞音乐在女真族的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无论欢乐、喜庆、死亡、政治聚集、日常相见,都有歌舞相随。
2.女真族歌曲
女真族音乐盛行于宋朝京城。宣和年间,京师盛传的女真族歌曲有《蓬蓬花》《蛮牌序》《六国朝》《四国朝》《异国朝》等。
《独醒杂志·卷五》: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有笛皆寻常差长大,曰“番笛”……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初与女真使命往来所致耳。[58][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46页。
由于双方战争及政治往来,部分女真族使者及投降的人杂居京城,致使女真族音乐盛行于汴京,其中包括部分女真族歌曲、女真族竹笛。
关于《蓬蓬花》歌曲,江万里《宣政杂录》“词谶”记录:
宣和初,收复燕山以归于朝,金民来居京师。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59][宋]江万里:《宣政杂录》,引自[明]陶宗仪纂《说郛》卷26,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五册。
《蓬蓬花》因女真族歌舞音乐的形态特点而得名,“蓬蓬”是击打鼓面的声音,女真族人和着鼓点而歌舞,此曲因节奏明快而流行甚广。由于歌词中有“满城不见主人翁”之句,有些文人将此附会为徽、钦二宗沦为金人阶下囚的不祥谶纬。《大宋宣和遗事·利集》如此形容《蓬蓬花》乐曲:
京师竞唱小词,其尾声云:“蓬蓬蓬,蓬乍乍,乍蓬蓬,是这蓬蓬乍。”此妖声也。[60][宋]佚名:《大宋宣和遗事·利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1937年),第87页。
从歌唱中多次出现“蓬蓬乍”的歌词来看,“蓬乍乍,乍蓬蓬”应是形容鼓声的象声词,这首乐曲的名称及象声词的使用都与歌舞时敲击鼓乐器有关,而当今北方少数民族歌舞中常用乐器鼓、如赫哲族常用单面鼓,应与此有传承关联。
女真族的歌曲《异国朝》等在京师流传很广,并出现了同名舞队。如,《梦粱录》《武林旧事》分别记录舞队有“诸国朝”“四国朝”“六国朝”,从名称来看,这些歌舞内容应是反映诸国朝贺场景。而这些舞队名称的存在也反映了女真族音乐对宋代市井音乐的影响。
结 语
通过对宋代少数民族音乐进行钩沉,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古代渊源逐渐呈现出清晰的样貌。宋代的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包括乐器、民俗音乐、日常音乐活动方式、音乐传承方式等,大多延续至现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一直以相对封闭、自然、稳定的方式传承。
作为与宋代朝廷形成政治对峙局面的两个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与女真族,尽管这两个民族在宋元后期随着政治衰亡而逐渐融入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但他们的音乐对宋代中华音乐产生了较大影响,宋代汉族在官方抵制的主动意识下仍不知不觉吸收了他们的音乐特色与形式,从而使中华汉族音乐更具有丰富性与多样性。而作为辽、金两国民间的原汁原味的契丹族、女真族音乐及其活动方式,则在历史长河中融入了中国其他民族,我们今天在北方少数民族音乐中,仍能感受到这些民族特色与音乐特性。
(一)宋代西南民族音乐在当今的遗存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录的胡卢笙即今天广西瑶族的“葫芦笙”“瓢笙”,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记录的铳鼓即今西南少数民族长腰鼓。卢沙、铳鼓、胡卢笙至今仍是瑶族的常用乐器。芦笙在侗族、苗族、水族中也常被使用。此外,这两种文献中记录的腰鼓是当今广西多有出土的“花腔腰鼓”。宋代文人热衷收藏的铜鼓也在今天的广西及其他西南地区多有出土,这里的壮族、瑶族、水族、毛南族、彝族、布依族均有使用铜鼓的传统。
宋代西南民族的“送老”活动仍遗存于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婚嫁活动中,近代以来,湘西、鄂西、岭南、黔东等地的壮族、土家族、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多种民族普遍存有的“哭嫁歌”或“婚嫁歌”,就是宋代“送老”婚嫁仪式活动的遗存。宋代西南民族的“踏摇”也遗留于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祭祀或农闲时通过对歌或歌舞择偶,是他们的普遍择偶方式,这种方式也在今天的侗族、仫佬族、苗族、水族、京族等多种西南民族中长期留存。宋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录的芦笙舞活动一直延续至今。西南民族的侗族、瑶族、苗族、彝族等,均有跳芦笙舞的传统,“跳月”“跳花”“踩笙堂”等称谓,均与此渊源有关。
今天的西南侗族办歌班以教习音乐的传承方式,也已在宋代广西浔州等地的民族中普遍存在,部分民族的歌班还受到了宋朝教坊乐师的教习。宋代西南少数民族的驱傩活动也遗留至今,广西毛南族傩戏、壮族师公戏等均与《岭外代答》所记的桂林傩有一定的渊源。
(二)宋代北方契丹、女真族音乐在当今的遗存
宋代叶隆礼《辽志》记录了契丹族皇室祭祀木叶山的传统。在当今的达斡尔族的萨满斡包祭中,仍保留有契丹族祭祀木叶山的特点。从张舜民《画墁录》对契丹族舞蹈的描绘来看,与今日的达斡尔族舞蹈特征非常接近。
宋代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记录女真族百戏表演中的“各持两镜”表演,应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萨满教仪式,“两镜”就是萨满教仪式中使用的“神镜”。今天的达斡尔、满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都信仰萨满教,他们的萨满教跳大神中,铜镜是驱邪的法器。当今北方少数民族歌舞中常用乐器鼓,如赫哲族的单面鼓,也与宋代文人描绘的女真族音乐有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