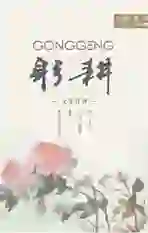麦收记忆
2021-06-20王公叁
王公叁
麦收的序曲是从听到布谷鸟的第一声欢唱开始的。
父亲把从集市上买回的镰刀一把一把磨好,扎成一捆,放在院门的门后。拉麦用的架子车也被检修了一遍,打麦用的扫帚、桑杈、木锨,装麦用的编织袋也都一一就绪了。
母亲则在灶间忙活着蒸馒头,至少要蒸两三锅,全是又长又粗的半圆柱型、腰间还有麦穗状腰扎的杠子馍。母亲说,杠子馍就是麦捆的形状,越多越大,收获的麦捆就越多越大。其实寓意只是一方面,真实的原因是割麦时都在地里抢收,没有闲暇做饭,杠子馍就着蒜汁,就是一顿饭了,省时又能吃饱。俗话说“蚕老一夜,麦熟一晌”,“七分熟,十分收;十分熟,七分收”。不把成熟的麦子及时收回来,让它焦在地里,麦穗一碰就落,这一季子就白忙活了,所谓“焦麦炸豆”就是如此,收麦,就是跟老天爷抢时间。
村头的打麦场早在半月前就被五爷用牛拉着石磙,后面再拖着一大捆用新砍的栎树枝做成的拖扫,一遍一遍地碾轧、清扫,收拾得平平整整、干干净净。
万事俱备,就等着开镰了。
天刚蒙蒙亮,还在睡梦中的我们就被父亲叫醒了,匆匆用凉水洗了把脸,拿上镰刀和草帽,带着几分惺忪,向麦田进发。
为了能够一次性推进,父亲按麦子的行数把任务分了,父亲、母亲、哑爷、大哥、二哥、我一字铺开,我因为最小,割的速度慢,所以就少分了几行。
割麦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弯腰,左手顺着麦垄的方向抓着一大把麦棵的上端,右手在麦棵的下端挥镰,“霍”的一声,一大把麦子就割掉了,转身平铺在身后,如此重复。我的手小力弱,尽管任务少,但总是落在最后,看着他们在前边飞进,急得双手不停,腰都不敢直一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割到头,好停下来休息。
太阳升起来了,空气由凉爽变得炙热起来,额头上的汗水也由一珠珠开始变成一片片,顺着低下的头,流进眼里,蜇得睁不开眼,滴在地上,摔成八瓣。握着镰刀把的手开始磨出了血泡,腰已经酸得直不起来了。抬头看看前边,还是一眼望不到头,只能挥汗如雨,咬着牙坚持。
太阳一丈多高时,一大片麦子被我们全部放倒在了身后,我一屁股坐在地头,喘着粗气,感觉腰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割麦的时候,会有乐趣,比如在麦田里经常能够遇到野鸡的窝。
麦子放倒后,收得越快越好,一方面,割倒的麦子,太阳一晒就焦了,一碰就断,晒的时间越长,丢在地里的越多;另一方面,收麦时的天气往往变化无常,一旦下雨,放倒的麦子就会在穗上出芽,这一季子就白忙活了。
把平铺在地上的麦子收好,就地取材,用两把青麦棵缠着一挽,把麦子拦腰捆成一个个麦捆,麦穗朝上,竖在地里,像一群腰扎皮带的武士。
空气已经有炙热变为滚烫,没有人想去地头的绿荫里休息,都在想着赶紧把这活干完,躲开这太阳的毒晒。我们把麦捆一个个背到车前,母亲把它们在架子车上一层层码好,垛实,前后要匀称,不然拉起来都是很费劲的。左右也要匀称,不然的话,重心向一侧倾斜,路上颠簸,是会翻车的,一旦翻车,一半的麦穗就扔了。
母亲把架子车装得山高,最后用绳子绑牢,她在前边驾着,我们在两旁、后边推,一路颠簸,一路崎岖,小心翼翼地把车拉到了打麦场里卸下、垛好,如此往返。
将近中午的时候,终于把一地麦子全部拉到了打麦场里。人也通身上下黑红黑红的,汗水不知流了多少,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在衣服上留下一道道白色鹽渍,回家后,抱着瓢,对着井拔凉水,一顿狂饮。
就这样,各块地里的麦子,都被我们蚂蚁搬家似的“抢”了回来,在打麦场里,垛成一个顶上起尖的圆柱形的大垛,上边用塑料布罩着,等待着打麦的时机了。
打麦场是几家共用的,所以需要提前协商好哪天谁用。
打麦的天气必须是响晴天,太阳越毒越好,这样能把麦穗晒焦,石磙碾轧的时候麦粒脱得快,脱得彻底。
在头天傍晚收听收音机播出的天气预报后,父亲决定第二天打麦。
我们照例起了一个大早,到场里把垛好的麦捆一捆一捆扛到场中,解开崾子,把麦棵麦穗朝上、均匀地在场中散开,接受阳光的暴晒,为了使麦棵晒得均匀,中间要用桑杈上下翻上几遍,我们称为“翻场”。
吃过午饭,来不及歇晌,爷爷赶上牛,我们拿上桑杈、木锨、扫帚,带上一大壶凉开水,一家人上场了。
午后的太阳正毒。我们坐在场边的绿荫下短暂的歇凉,爷爷熟练地把牛套好,拉上石磙,左手执牛缰绳,右手拿着一根柳条做的鞭子(那是象征性的,爷爷从来舍不得打牛,他说牛通人性,能听懂他的指令),“嘚嘚、咧咧”地吆喝着牛,拉着石磙“吱呀吱呀”在场中一圈一圈地转场。
经过一遍一遍地碾轧,散乱、虚蓬的杆状麦棵变成了倒伏、密实的“皮儿”状麦秸,从“立体图形”变成了“平面图形”,大部分麦粒已经脱离了麦穗,被碾到了麦秸的最下边。
半个小时后,该我们“翻场” 了。爷爷先把牛赶到树荫下,自己再坐下来,擦把汗,喝口水,稍稍休息一会儿。父母亲、哑爷、大哥、二哥、我拿着桑杈,从一边开始,把麦秸上下翻上一遍,以使下层的麦秸也能受到碾轧,麦粒能够脱的更彻底。
经过三次“翻场”,麦粒基本上脱净了。爷爷随手抓起一把麦秸,看一看被轧成“平面图形”的麦穗,上边已经没有什么麦粒了,把牛解了套,拴在场边的树上,饮上水,告诉我们可以“擞场”了。
“擞场” 比较简单,通常是哑爷、大哥、二哥和我干的:用桑杈把地上的麦秸挑起,上下抖擞几下,使夹在麦秸之间的麦粒落下来,达到“颗粒归场”。我们把擞好的麦秸用桑杈挑到场边,由父母亲打垛。
“打垛”是一个技术活,父亲把我们挑过来的麦秸一层一层放好、压实,母亲在旁边清边、整形。我一直不理解麦秸垛为什么都是圆柱形的,可能这样占用空间比较小,或者是稳定性好,抗风。“麦秸垛虽大,压不死老鼠”是农村说一个人外强中干的口头禅,麦秸垛是田鼠的乐园。
父亲踩着脚下的麦秸,随着麦秸垛的升高而不断升高。麦秸挑完了,垛也垛好了,把最上边用麦糠撒上一层罩着,这样可以防止雨水的渗透而造成麦秸腐烂,方便冬季喂牛。
用木锨把留在场上的麦粒合着麦糠拢起来,在场中间拢成一个圆锥形大堆,再用扫帚把周边清扫干净,可以短暂休息了,“扬场”是个技术活,我们干不了。
剩下的事,就是等风了。那时没有机械,“扬场”是全靠老天爷赐风的。
“起风了!”感到身上有一阵凉意,爷爷赶紧招呼父亲、母亲。
爷爷先扬起一锨,试试风向,便指挥父亲和他站在风来的一侧,母亲拿着扫帚站在风去的一侧。爷爷和父亲抡起胳膊,一锨一锨把麦粒迎风扬起,麦粒在麦堆的前方落下,麦糠被风吹向母亲的一侧,母亲戴着草帽,用扫帚不停地清扫,在麦堆的后边堆成一堆。我坐在场边,听着木锨和场地摩擦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看着麦粒如雨滴般落下、麦糠如雪花般飘走,幼小的心里竟感受到了劳动的神奇、美妙和伟大。
好多时候,风只是一阵。风一过,爷爷、父母亲就不得不坐下来休息,等着下一阵风。
如此三番,傍晚的时候,一大堆麦子扬完了。爷爷坐在场边,抽出旱烟,美美地吸上一袋,看着我和哥哥们把扬干净的麦子拢成一个圆锥形堆。我撑口,哥哥们拿锨,把麦装进一个个准备好的编织袋里,尽管新收的麦子有一大股土腥味,尽管总是落得一身微尘,我却总是乐此不疲。
扎上口,装上架子车一车一车地拉回家里。父母用编织袋的数量算计着今年的收成,路上听到别人夸今年收成好时,他们总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嗯,嗯,今年雨水好。我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把麦子全部拉回家,月亮都已经升老高了。
麦收就这样结束,该插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