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乡建
——双螺旋石拱桥设计实践解读
2021-06-20史文剑
史文剑
“乡村建设”作为一项建设活动由来已久,后经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性概念[1]。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就建筑师或艺术家“上山下乡”的乡村建造实践而言,这些“选择性建筑”[2](alternative architecture)正在从孤例的实施拓展为规模化的建造,当今社会针对这些乡建作品的讨论和关注程度也正在从边缘化向主流化转变①。建筑师或艺术家通过不同维度的创作实践,“陪伴式”[3]地参与乡村环境的改造和新建,甚至在乡村经济、产业转型乃至文化复兴等方面做出探索[4]。从网红乡村建筑到高校营造节,目前以竹为主要建造和表现材料,寄以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建设途径的乡建项目越来越多,不能回避,这一方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16年在浙江龙泉举办的“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对竹与在地营造这一设计理念、材料运用的发掘和探索。
双螺旋石拱桥位于浙江省龙泉市的宝西乡溪头村(图1),是首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13座(建成)以竹为载体的单体建筑中最特别的一处②。从2013年8月开始策划设计到2016年9月建成开幕,3年多的时间与110多趟的现场工作,让策展人、设计师葛千涛对本届双年展项目以及双螺旋石拱桥创作的思考和探索显得多面且深刻。从建成效果来看,它的造型灵动活泼,内部空间富有趣味,随时间的发酵,充满艺术化设计效果的双螺旋石拱桥越来越值得细细品读(图2)。
下文从形式的生成与空间的营造两个主要方面,对双螺旋石拱桥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索设计师是如何以一种“艺术介入乡村建设”③的方式回应和践行“场所精神,乡土建设”这一“国际竹建筑双年展”主题思想的。
1 形式的生成:自然与人文双基因的艺术螺旋

图1 双螺旋石拱桥远景

图2 双螺旋石拱桥近景

图3 方案设计透视效果图
双螺旋石拱桥的竹构形体由152扇重竹框栅组成,木框尺寸5m×5m,它们垂直于桥面间隔0.29m等距布置,以3°的等差角度围绕圆心轴同向旋转,在有韵律的转动下,四条边框组合出了四个扭动的面,四个90°的框角节点组成了四条连贯的线,整个建筑外观展现出一种通透的螺旋转动感(图3~4)。在实际空间中,形成了一种面与线相互缠绕却不交叉的螺旋样式,在视觉空间中,在远近高低变化之下,实的框架与虚的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映衬的高低起伏的模糊的轮廓线。这种可以给人以感知的建筑形式,设计师葛千涛表述“桥的造型源于DNA的双螺旋结构图,它寓意了竹建筑双年展的母体,营造法则皆源自宝溪乡的文化基因”④。从具象的直观感受来讲,不难看出双螺旋石拱桥的造型由四条放大的“DNA分子结构”围合拼接而成的,但真正的“营造法则”和葛千涛所言的“文化基因”还需要从场地的自然与人文开始解读。
1.1 自然基因——山与竹之舞
(1)静止的山峦与动态的天际线
宝溪乡溪头村处于群山环抱之间的一小块山涧盆地之上,在村里开阔的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由连绵青山勾勒的天际线。宝溪乡四周的青山与双螺旋石拱桥二者都有一条清晰但又模糊的轮廓线,这条线是由远近高低变换的空间及人眼视觉的双重错位所形成的,是一条通过多个前后错位空间的相互叠加所组成的轮廓线,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印象之中并在潜意识下得到滋养和强化,如同乡愁一样。沿溪水透过双螺旋石拱桥看其背后的山峦,会形成一种借景与叠景的效果,螺旋桥的轮廓曲线与山峦的天际线在远焦与近焦之间相互切换,如同双螺旋石拱桥是拉近的山形,山峦是放大的桥体,建筑的形式与大的自然环境有了对话与共鸣,双螺旋石拱桥的形式并不是对自然山形的机械模仿,二是通过艺术创作,让建筑融为自然精神的一部分(图1~3)。
(2)波动的竹林与静谧的光影
宝溪乡盛产竹子,村落四周的山坡上、双年展场地的四周、溪岸路边随处可见茂密成丛的竹林。“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⑤。在中国人的文化思想中,竹是君子的化身,有很强的精神属性。一棵自然生长的竹子可以长得很高很直,成片的竹林密而有隙,互不羁绊,有风拂过,成群扭动,阳光洒下斑驳光影继而形成风景,这样的大地景观因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不可选择地成为了村庄的生活背景和人文背景。竹是此届建筑双年展的建造媒介,除了在建造中会用到竹的建材,还要思考如何与竹产生更深层次的关系,发掘、提炼、抽象、再现竹的精神属性与人文景观。双螺旋石拱桥一根根竹构框架直接固定在拱形桥体之上,以相互独立存在的形式建造而非在框架格栅之间再次相互拉结固定,这种独立的、干净的形式在体现结构美学的同时,也是对竹精神属性的一种致敬。而那些由旋转框栅所组成的波浪般韵动的视觉效果也恰如风摇竹林一样微妙(图3,5)。

图4 方案设计立面图

图5 双螺旋石拱桥内部空间与光影
1.2 人文基因——乡村意象与场景再现
宝溪村是中国千万个乡村中很普通的一个,但她也有自身独特和真实的一面,这里至今延绵着龙泉青瓷文化的脉络,7座古龙窑安卧于山峦溪水之间(图6);安静的村落内保存着多处上百年形制完整的木构古民居,在当代乡村自发建设充满均质化而缺乏美学的砖混式住宅的冲击与对比下,它们的魅力未减且愈发显得重要和安详,他们是过往生活场景的载体和记忆(图7);在村内可见闲置散落的或大或小、或新或旧的竹编器具,斗笠、竹篮等是日常生产劳作场景的见证;水边有多处水车带着碾杵在转动(图8),杵臼声在陶瓷作坊中传出并消失,随声音一并消失的还有屡屡青烟,如果在日暮十分,将分不清那片是农家的炊烟,那片是龙窑的柴烟,它们都会像溪水一样流远并模糊,但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的是水车、作坊、龙窑已不再仅仅是一处简单的生产场地,而是艺术创作场景的记录者。生活场景、生产场景、艺术创作场景等构成了宝溪的乡村记忆和人文意象。

图6 宝溪龙窑

图7 宝溪古民居

图8 宝溪村头水车与木桥
如果将抽象的建筑形式进行拆解和具象的还原后再解读,便不难在双螺旋石拱桥的形式构造中清晰地找到古民居木构椽条、竹编器具、龙窑、水车、木桥等一系列极具生活、劳作、艺术创作等美学场景要素的影子,例如,0.29m等距布置竹框与民居椽条的间隔相近;竹框的旋转角度与竹编的编织工艺相近;竹框旋转叠加后的圆形如同木桥与水车之间的蒙太奇剪接。而其所构筑的形式也不再是简单的造型美学或对乡村建筑形态、形式的重复,而是对人文场景、乡村意象的再现和延续,一种“轻柔的创新”[5]。
1.3 艺术螺旋——从风格派、构成主义到文化解构与建构的立体构成
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艺术改革运动,结果是从思想方法、表现形式、创作手段、表达媒介上对人类自从古典文明以来发展完善的传统艺术进行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彻底的改革,完全改变了视觉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这个庞大的运动浪潮,我们往往笼统地称之为现代主义艺术,或者现代艺术。其中有一条发展轨迹可以称之为立体主义、构成主义(图9)、荷兰的“风格派”(图10),它们为现代建筑、现代产品和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形式基础[6]。作为画家出身的葛千涛是深谙于此的,在其工作室可以看到具有明显“风格派”特征的绘画艺术作品(图11),在其装置艺术作品“立体清明上河图”(图12)中可以看到将中国传统的绘画进行解构再重构,通过将绘画媒介图版的分段切片化处理,将解构的绘画空间以平行间隙排列的方式建构一个更加立体化的阅读场景。这种通过剥离与拉伸同一平面中多层叠加的、扁平化的二维空间,以达到将平面中的视觉空间转向立体空间的过渡状态,并实现实体化的三维空间的艺术创作手法,似乎正是双螺旋石拱桥形式产生的思想原型。双螺旋石拱桥简单的构筑方式也正契合“风格派”所认为的“最好的艺术形式就是基本几何形象的组合和构图”[7]的思想理念。
建筑创作与艺术创作所不同的是“建筑的根本在于建造,在于建筑师应用材料并将之构筑成整体的建筑物的创作过程和方法”[8]。在双螺旋石拱桥简洁的形式之中,包含了葛千涛多重的艺术创作思考,一是基于艺术风格流派影响下的个人思想与手法的突破性创作,即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转化、平面构成向立体构成转化的艺术创作;二是自然基因与人文基因在建筑形式中得道了环境共生与场景再现式的叠加表达。后者得益于设计师在诸多文化要素深刻认知的基础之上对建筑表现形式的解构与重构。解构是后现代乃至当代艺术家喜欢使用的词汇,它复杂而多义,从葛千涛在第一届上海国际陶瓷生活艺术博览会开幕后宣言式的文章《解构昨天、构筑今天、想象明天》一文中可以读到“文化觉醒与自觉”、“进行时态”、“摒弃文化复古”等一系列前卫、精炼而又犀利的关键词语。乡村建设是思考建构体系的实验场域,是建筑师重新厘清传统与现代构造和材料关系的再出发[5]。在宝溪,设计师同样以一种十分当代的设计手法,将一些充满生活场景的元素进行发掘与提炼,并大胆地抽象概括在十分简约的竹构木框之中,在通过立体构成、形式旋转等一些建造策略之后,将自然与人文等基因重现在建筑形式之中。
从“风格派”到文化解构与建构的这条艺术创作思脉,似乎也展现了从改革传统到文化自觉的螺旋上升过程,这与桥的螺旋形式有某种莫名的暗合。
2 空间的营造:场所与意象的在地实践
关于建筑的空间性,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老子(李耳)的著作《道德经》里说道:“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所以,“有”给人们的“利”,是要以“无”来起作用的[9]。这一点在双螺旋石拱桥的空间性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在石拱桥之上没有双螺旋样式的竹构之前,它的空间性仅在桥面之上有微弱的二维层面的限定,它的功能空间是一种线性的、通过式的、路径式的交通空间。在有了双螺旋样式的竹构三维空间上的限定之后,桥面之上作为交通空间的石拱桥还存在,桥面之上具有感染性的驻足观赏空间、休憩空间得以强调和认定。双螺旋样式的竹构与石拱桥加在一起的功效,远超出了一座造型炫丽、渡河作用的桥本身所产生的意义,正是1+1≥2的结果⑥,超出的部分是其对所处地景空间产生的影响,桥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磁场般的引力,这股引力在传统村落与当代艺术建筑群之间的作用、在竹材料与在地环境之间的作用、在功能空间与历史事件之间的作用等多重磁场叠加之下,所产生的意义也便是“场所精神”⑦。
2.1 从意象到体验的空间营造
海明威曾说过:“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巴黎,那么以后不管你去哪里去,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文化印象与城市意象对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深远的影响由人的体验所得。远观的双螺旋石拱桥轻盈地横架溪上,难以从其外观判断其为何物,有何功能,其所构筑的地景是一处吸引目光的魅力场所。走近桥的两端,呈现的是一处充满好奇引力的漩涡、洞穴,使人产生步入、穿越的急切冲动。当真正步入其中,却又会不自主放缓脚步、驻足停留、四处展望、反观身后,窥视构架间隙外的景观,凝视漩涡两端的村落与青山,一系列动作源自于其内部空间对参与者的感官影响。“景致—自我—行动—景致—自我”[10]这种共鸣式的体验感得益于设计师从在地的自然与人文意象中提炼、解构并建构出十分当代的、艺术化的建筑形式,并在形式之下借鉴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对景、借景、夹景、框景、障景的空间景观的塑造方法,营造丰富有趣味的体验空间。

图9 塔特林(Vladimir Tatlin)构成主义作品《第三国际的纪念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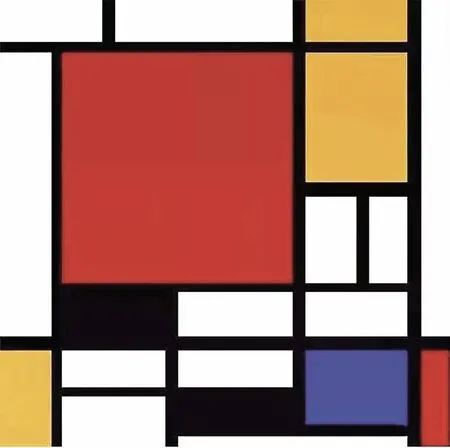
图10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风格派绘画《红黄蓝色》

图11 葛千涛绘画作品《色彩渲染》
桥内的护栏与简洁而富有设计感的凳椅间隔布置,行人可以坐下休息,动态的视线可以变成静态的观赏,让一个原始的交通空间与新增的观赏空间耦合,让从风景处看桥与从桥内看风景的多方位体验变得自然。如果是在阳光明媚的晴天,阳光从富有韵律的间隙中透过并产生斑驳的光影关系,如果是在阴天或风雨天,风雨同样从间隙中穿过,当地的村民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刻从此间经过,天真烂漫的孩童在此处嬉戏玩耍,在由竹构虚实间隔所限定的空间内,可以感知天气与阳光、感受时光与生活,让长居于此的村民乐于接受此景并融入日常生活,让初次身临其镜的游历者与阅读者找回在城市中失去的空间“尺度感、材质感”[5],实现感官和内心与建筑的交互体验与体验感⑧。
2.2 从体验到意象的场所建构
凯文·林奇将城市意象的元素分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等五个关键要素[11]。双螺旋石拱桥所在的宝溪乡溪头村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建筑风貌十分大众化的中国乡村。设计师葛千涛在强调“乡土建设”这一主题概念的同时,另外一个着重突出的概念就是“场所精神”,对具体的宝溪乡,或放大至一个抽象概念的乡村而言,它的场所性抑或在地性的设计与实践自然离不开对其自然与人文等诸多要素的捕捉,在建造之中展现其对地域、场所的理解和建构。双螺旋石拱桥下的小溪是村落的自然边界,溪水划分了村庄的生活区域与生产区域,桥是村内巷道与田林道路之间相互延续的节点,双年展事件在时间发酵之后,其特殊性的建筑区位和建筑形式,从无到有,双螺旋石拱桥无疑已成为宝溪乡的标志性建筑,这一系列意象要素集合在一处是对村子风貌的集中概况和强化,是由历史走向当地的集中展现,且其间设计师通过建筑形式展现了当地自然基因与人文基因双重意象解构与重构的交叠,从体验性空间中可以看到一种在地性文化与生活的延续。

图12 葛千涛艺术作品《立体清明上河图》
随着乡村生产力的迁移和转变,传统乡村的秩序和公共空间在乡村中的作用均被打破。乡村公共空间的败落让乡村文化、乡村精神逐渐失去“ 活性”[12]。双螺旋石拱桥以其独特的形式和空间也在给阅读者提供另一个层面的暗示,即一个源于传统、而又突破传统的新的公共空间和乡村意象。“桥的一端是古村落,另一端则是以“当代建筑”为格局乡村新型社区。这座桥穿梭于历史与未来。时光在流逝,光影在四季,在朝夕间变幻,瞬间,传递出无限与永恒……”⑨。
结语:“场所精神,乡土建设”与“艺术乡建”的探索
如果说“中国·龙泉竹建筑双年展”是一场在地的、不谢幕的建筑艺术展,那么,也可以说是策展人与设计师们一起发动的一场“深思熟虑”且“艺高胆大”的乡建实践。双螺旋石拱桥是这场“有组织、有计划”的乡建实践中的组成部分,通过对自然与人文意象在地的深刻认知,结合风格派、构成主义等艺术流派思想,设计师用极具个人艺术色彩的创作手法,让建筑形式与空间的设计很好地契合并践行了“场所精神,乡土建设”这一“国际竹建筑双年展”的主题思想,营造出了丰富有趣味的体验空间并建构了新的乡村意象。同时,双螺旋石拱桥极具艺术性的创作思路和表现形式也为当下的乡建实践提供了一条“艺术介入乡土建设”的参考途径;竹材料的在地建造不仅唤醒了乡村对低技术与简易材料的美学认知,更为当地传统竹产业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的升级与转变带来思考和契机[13]。
回顾我们的城市化进程,造就了太多的“千城一面”的建筑景象。当今,在逐渐成为建造热点区域并且开始规模化建造的乡村,如何避免沦为“千村一面”的结果、如何避免乡村再次受到入侵式的伤害,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逃避的议题,这不仅关系着乡村物质景观的未来风貌,也牵动着乡村建设中精神文明的学习与教育的发展方向。当代的设计师有责任和义务思考以何种途径的乡建实践来维系、延续、重建、建构自然的与人文的乡村风貌。
资料来源:
图1:http://www. sohu. com/a/225934721_663589;
图2、图4、图11~12:葛千涛工作室提供;
图5:谢震霖摄影;
图6:http://news. yxad. com/news/245558088_165076.html;
图7~8:作者自摄;
图9:https://www.douban.com/note/655107220/?cid=52781035;
图10:http://www. sohu. com/a/280248822_100087519。
注释
① 1964建筑理论家伯纳德·鲁道夫斯基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主题展览,展示世界各地充满地域与民族特色的乡土建筑。(德)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45年以来”的章节中论述,受伯纳德策展的影响,在1982以后,欧洲、美国以及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为突破原有的建筑设计类型而开始探索生土式住宅设计的探索,但这些作为与官方所代表的主流倾向的平衡之物的作品在建筑主体讨论中也只能处于边缘的位置,以一种“选择性建筑”(alternative architecture)的方式被孤例的实施。伴随着中国近20年的城镇化建设,建筑师或艺术家在乡村的实践已经变成热议和核心画图,例如:第16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展览主题就是“我们的乡村”、《时代建筑》近几年连续推出“从乡村到乡土: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建筑师介入的乡村发展多元路径”等有关乡建的主题专栏。
② 从建造缘起来说,它最初并不在竹建筑双年展的策展名单之中,在经历一番富有故事性的波折之后才得以建造并展现,在双年展筹建之初,村民在双螺旋石拱桥之处计划建筑一座仿古廊桥,在参与双年展的设计师们的联名反对之下,决定建造一座与双年展主题契合的桥,并最终由策展人葛千涛完成设计。
③ 笔者从与设计师的访谈交流中得知其“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乡建创作思考和途径。
④ 葛千涛《竹建筑双年展宣传册》中对“双螺旋石拱桥”设计理念的自述。
⑤ 引自[宋]苏轼. 《于潜僧绿筠轩》。
⑥ 倪连生,王琳在《结构主义》一书译者前言中表示:整体并不是各成分的简单总和,它比成分的总和还要多一些,即整体作为整体自己的性质。——(瑞士)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 结构主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2012. 11重印):3。
⑦ (挪)诺伯舒兹认为建筑是“存在空间的具现”,存在空间的立足点即人要“定居”下来,需要在环境中能辨认方向并于环境认同,能体验环境的意义,即人与其环境间的基本关系。[挪]诺伯舒兹著;施植明译. 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7:3。
⑧ 《朱子语类》卷一一九言:“体验是自心里暗自讲量一次”。
⑨ 葛千涛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