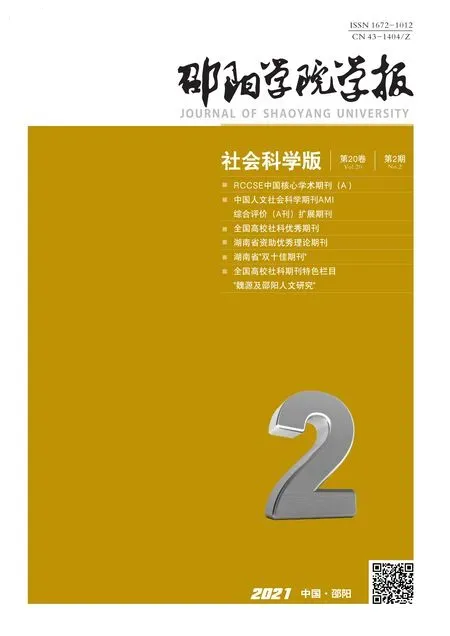扎伊采夫小说《蓝星》的神人思想
2021-05-19张玉伟
张玉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扎伊采夫(Зайцев Б.К.,1881—1972)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新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自1901年开始写作以来,扎伊采夫在文艺思想上经历了印象主义的模糊、泛神论的混沌,最终走向基督教的明晰。在这个过程中,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扮演了重要角色。扎伊采夫后来在《关于自己》(1943)中写道:“在俄罗斯农村,我父亲的领地,短暂的夏夜里,我痴迷地读索洛维约夫的书。往往割草人迎着朝霞去割草,而我才熄灭《神人类讲座》上的灯。索洛维约夫第一个穿透我青年时期的泛神论外衣,推动我走向信仰。”[1]588中篇小说《蓝星》(Голубая звезда,1918)通过描写20世纪初俄罗斯上流社会的生活面貌,刻画了具有神性色彩的多样人物。他们在自身或实现与神的结合,专事精神世界的建构,或沉溺于世俗而脱离神的世界,走向生命的终结。丰富的人物形象、严谨的思维体系共同传达出扎伊采夫继承自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思想,这部小说也被作家本人称为创作之路前半期“最充分、最具表现力的作品”[1]589。索洛维约夫对扎伊采夫的创作影响在俄罗斯文学界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据此对具体小说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本文旨在结合索洛维约夫的神人学说,运用对比分析等方法,考察《蓝星》的多样人物形象体系,探讨扎伊采夫对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思想的艺术性阐释与发展,以期丰富我国对白银时代文化及扎伊采夫创作的认识与研究。
一、索洛维约夫的神人说
白银时代是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和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时代。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ёв В.С.,1853—1900)的哲学论著和美学思想为这时期的文艺发展奠定了基础,尤为受到现代派思潮浸染下的年轻作家和诗人的推崇。俄罗斯宗教意识的复兴与索洛维约夫的名字紧密相连。正如我国学者所言,“索洛维约夫是现代意义上的俄罗斯哲学和神学的奠基人,是整个俄罗斯思想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人物,他结束了俄罗斯没有哲学体系的时代,开创了独特的俄罗斯哲学的时代”[2]译者前言1。立足于西方理性主义的缺陷,结合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面貌,索洛维约夫构建出完整的知识体系,为20世纪初考察世界构造、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范式,开启了俄罗斯哲学史上的新时代。这一体系始于对科学、哲学和传统神学的批判。索洛维约夫认为,来自社会实践和实证科学领域的认识并不完整、并不彻底,导致生活于其中的人并不能获得绝对自由,因而宗教是人的生活的必需。之后,索洛维约夫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天主教和新教,指出前者执迷于教权,后者过分宣扬个性,而真正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人的信仰贯彻到底、实现神与人完满统一的是神人类[2]24。
神人说是索洛维约夫在《神人类讲座》里集中探讨的话题。神与人的结合之所以成为可能,在索洛维约夫看来,是因为同神一样,人本身也有神性,区别只在于,“神性在上帝那里是永恒的现实,而人只能达到它、获得它,在此,神性之于人只是可能性,只是渴望”[2]23。如果人信仰神的存在,那么神的世界就会向人的意识启示,“这是神和人的现实的相互作用,即是神人过程”[2]34。这个过程决定被赶出伊甸园的人能否在精神上得到重生,能否战胜各方面的恶,重新获得神性。
关于神的世界,索洛维约夫指出,构成神自身绝对内容的是来自精神、理性和心灵这三个领域的力量。与它们相应的体现方式是意志、表象和感觉,它们又被分别表现为善、真和美。这三个元素相互包含、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神的绝对原则,同时各自又包含万物,并被包含在神身上。由此,神是统一的有机体,其自身由于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力量,成为“产生的统一和被产生的统一”:前者是普遍的逻各斯,后者是个性的索菲亚,而“基督既是逻各斯又是索菲亚”[2]111。耶稣基督是神与人结合的典范,是索洛维约夫学说里的神人。索菲亚是神的个性存在,不仅使神的绝对内容对外展现出来,还实现神与人的联系。“索菲亚是理想的、完善的,永恒地包含于神的存在物或基督中的人类。”[2]119她既体现神的实质内容,又引导世人获得神性,成为神人类。
神人思想不仅反映索洛维约夫对世界的完整认识,还寄托他对全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好愿景。诚然这一思想不无宗教幻想,但对于揭示白银时代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深受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影响,扎伊采夫也相信精神世界的存在,相信人的神性及其与神结合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篇小说《蓝星》无论在主题思想,还是在人物形象上都具有代表性。在这部小说里,扎伊采夫通过描写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揭示他们是否克服自身的分裂以及与他人、与宇宙世界的分裂,进而表达对人与神关系的艺术性思考。
二、神人形象
扎伊采夫的早期艺术世界观具有鲜明的泛神论倾向,侨居国外之后,其基督教思想得以确立并稳固下来,而在这中间有一个从模糊到明晰的过渡期。中篇小说《蓝星》集中反映了过渡时期扎伊采夫的艺术思想。泛神论的意蕴体现为对星星、对宇宙世界的向往,但人物履行的却是基督的学说,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借由主人公对星星的神圣信仰、对宇宙世界的身心向往,小说得以建立起地上的人与天空中的神的联系。
主人公赫里斯托佛罗夫是一个典型的神人形象,这首先体现在他的名字上。赫里斯托佛罗夫(Христофоров)“准确翻译成俄语的意思是‘背负基督’的人”[3]50。赫里斯托佛罗夫属于基督式的人物,在他身上融合的是上帝的爱和人对上帝的信仰。他的存在拉近了神与人的世界,实现造物主与造物的结合。赫里斯托佛罗夫对人对物充满怜悯与关爱,是贯穿小说的灵魂,其余主要人物都受到他的关照。他们围绕在赫里斯托佛罗夫身边,以是否获得神性而鲜明地区分开来。
赫里斯托佛罗夫的神性还体现在他与星空的关系上。赫里斯托佛罗夫喜欢观察星星,像熟人一样与星星保持“友好的”关系,认为那颗蓝色的织女星是他的“庇护者”[4]229,278。对赫里斯托佛罗夫而言,这颗星星意味着“美、真、神灵”,而且“它是位女性,向我传递爱之光”[4]278。在这颗星星上,在它“淡蓝色的、迷人的和神秘的光里”,赫里斯托佛罗夫能发现“自己心灵的一部分”[4]231。此外,赫里斯托佛罗夫的眼睛也是蓝色的。因而,他能够洞悉这颗星星的本质:“这是蓝色的处女星。它使世界充实,使世界渗透绿植茎秆的呼吸、空气原子的呼吸。它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看得到,却摸不着。在它内心融合的是大地上所有类型的爱,所有的迷人和忧伤,所有短暂的、飞逝的——还有永恒的。在它神性的面庞里,总有希望,也总有无望。”[4]316赫里斯托佛罗夫在这颗星星上感受到真善美的统一,体会到最普遍的爱。
星星来自自然界,但超越了有限的自然,在自身中包含万物,统一于神的世界。赫里斯托佛罗夫将基督的真理内化于心,因此他与星星相互包含,表征神的存在实质。赫里斯托佛罗夫借由星星的闪光向周围的人传播真理,实现神的世界与自然世界的连接,属于神人形象。
由于深受索洛维约夫的影响,扎伊采夫也相信“女性的原质是宇宙的原质,是创造的基础:人只有通过永恒女性才能参与宇宙生活”[5]35。永恒女性在上帝那里表现为索菲亚,在现实生活里化身为神圣女性形象。她们构成万物统一的绝对内容,单独每一个都在自身中包含万物,同时相互间又和谐统一。具体在小说《蓝星》里,这表现为蓝星、神人形象和神圣女性形象在精神上的紧密联系。赫里斯托佛罗夫领悟到蓝星的智慧,并以这颗星星的光照启示周边的人。其中马舒拉和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深受赫里斯托佛罗夫的影响,成为自身与神结合的神圣女性形象。
马舒拉过着文化人的体面生活:书籍、音乐、画廊……后来加入“白鸽”协会。这个协会“尽由姑娘组成。大家聚在一起读书,报告,座谈,以精神上的自我发展为导向,专事宗教,寻找生活的意义,讨论诗歌,讨论艺术,举办音乐晚会”[4]249。马舒拉犹如一股清泉,冲淡上流社会的污浊。赫里斯托佛罗夫不仅在马舒拉身上看到星星的闪光,还把她视为宇宙星空的一部分,是一切美好与和谐的象征:“在您身上现在就有夜的反光,……所有芬芳、迷人的反光……可能,您本身就是星星,或者夜……”[4]230这种与宇宙、与星空的亲近促使赫里斯托佛罗夫向马舒拉敞开心扉,向她讲述自己对星星的思考。而马舒拉在这颗星星的照耀下,在赫里斯托佛罗夫的感染下,顿悟他们之间的爱情在此世的荒谬,意识到自己要永葆爱情呵护美的使命,作出为爱牺牲的决定。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出身贵族,早年被迫嫁人,步入了以物质为准绳的上流社会。不幸的婚姻和被安排的命运使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变得麻木,上流社会的恶风恶习侵染了她。但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并没有失去本真,她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主动承担起拯救他人的责任,躬行基督式博爱的善举。在她身上,赫里斯托佛罗夫看到“神秘的痛苦”[4]247。而在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眼里,赫里斯托佛罗夫是“纯洁的和真正的”人,是能够带来真理启示的人[4]267。赫里斯托佛罗夫的出现,对她而言犹如一面镜子[4]242,照出了整个上流社会的丑恶。
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与马舒拉一样,追求真理,渴望精神上的联系,在这方面赫里斯托佛罗夫是她们的“精神向导”[6]58。赫里斯托佛罗夫向她们灌输来自宇宙、来自星星的顿悟,而她们则以各自的方式传播这束灵光,并通过自身实现大地上的人与天空、与宇宙的交流,履行神圣女性的使命。马舒拉在赫里斯托佛罗夫的引导下,领悟到蓝星的意义,在列季赞诺夫对拉本斯卡娅的描述中看到这颗星星的闪光,并向列季赞诺夫解释蓝星。赫里斯托佛罗夫关于“神圣贫穷”的学说更坚定了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无条件救助尼科季莫夫的信念。
基督的真理通过宇宙世界(星星)启发人的个性,产生象征万物统一的神人形象赫里斯托佛罗夫。被神化的人自觉履行传递宇宙智慧的使命,深受俄罗斯文化熏陶的马舒拉和备受上流社会折磨的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赫里斯托佛罗夫的引导下,克服物质的诱惑,成为传递真善美的神圣女性。
三、“理性的人”——尼科季莫夫
索洛维约夫在分析构成神的三个独特主体时,结合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划分出三类人。第一类由爱对方到塑造对方的表象,以此确定爱的价值,属于“精神的人”;第二类首先思考对方的实质,产生“关于自己的一定的普遍的理论表象”,之后再依据这个表象确定自己的态度,属于“理性的人”;第三类是其态度取决于对方在自己身上点燃的激情,属于“心灵的人”[2]105。在神身上,这三个主体表达的是同一个内容,区别在于表达的样式[2]106。而在个体存在者、在普通人身上,这三个成分之间出现不平衡,进而产生脱离神的世界的人。
赫里斯托佛罗夫满载世界灵魂的爱,在大地上找到织女星的神圣化身马舒拉,并通过这份爱向马舒拉传播基督的真理,是“精神的人”的代表。如果赫里斯托佛罗夫代表的是“光明的形象”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尼科季莫夫是“黑暗的”形象代表[7]208。这首先体现在尼科季莫夫黑色发暗的眼睛上。马舒拉同样有黑色的眼睛,但不像尼科季莫夫的那般发暗,从马舒拉黑色的眼睛里发出的是明朗的光。尼科季莫夫整体上给人的印象并不轻松。正如小说里写的那样,赫里斯托佛罗夫感觉他是一个“沉重的”人[4]285,列季赞诺夫直言他是“黑暗的人”[4]292。按照赫里斯托佛罗夫的“神圣贫穷”说,“追逐财富的意志就是追逐沉重的意志”[4]268,尼科季莫夫正是一个因过度追逐财富而变得异常沉重的人。他醉心于纸牌游戏,生活里一片混乱,与秩序井然的上流社会格格不入。
可实际上,尼科季莫夫同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一样,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早就看透了生活本身的空虚:“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构成社会的一个阶层,未必某个时候会与满足自我的人合拍。我们一直都是被驱逐的,向来都如此。难道随着时间人们会稍微变聪明,会明白只有高尚的姿态还不够吗?”[4]265换言之,“高尚的姿态”、优雅的作风并不能完全规范社会生活,不能彻底消除人自身的恶,也不能使人达到真正的完美。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明知道尼科季莫夫嗜赌如命,却主动接济他,帮他还债。假面舞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化身成威尼斯交际花,向尼科季莫夫坦言,愿意为他承受一切苦难。之后她还提出带尼科季莫夫离开莫斯科,离开这个到处鄙视他的环境。可见,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心想要拯救尼科季莫夫,是照亮他前程的织女星。
然而,尼科季莫夫拒绝了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爱。在他看来,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是出于怜悯才到处帮助他。尼科季莫夫之所以不接受这份爱,正如前所述,他那黑色发暗的双眼早已折射出这个人物内心的黑暗。就其实质而言,这源自尼科季莫夫对社会现实的决绝立场。他强烈排斥上流社会,对现实生活早已丧失希望,来自这样的社会和现实的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自然不能引起他的好感,他也不会怜惜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尽管她愿意为他承受一切苦难。这是尼科季莫夫从自己的理性认识出发确立的价值体系,他将此付诸行动。尼科季莫夫本可以在神的有机统一里成为“理性的人”,可他内心没有对善的渴望,也没有对美的崇高追求,而是一味沉浸在物质的诱惑中,沉迷于纸牌游戏,肆意挥霍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救济,甚至在假面舞会上侮辱拉本斯卡娅。尼科季莫夫坠入恶的深渊,成为自身灵魂与肉体分裂的人,对外表现为目空一切的破坏者。
因此,尼科季莫夫是脱离神的世界的“理性的人”,与“精神的人”赫里斯托佛罗夫形成强烈反差。“尼科季莫夫和赫里斯托佛罗夫——善与恶两极的代表——相互补充:一个人的残酷被另一个人的温柔与安慰的能力所遮盖。”[8]90显然,尼科季莫夫的恶为生活注入了不和谐,加速了上流社会的灭亡。而赫里斯托佛罗夫的善借助星星的闪光,努力抚平生活里的不和谐,给人带去温暖与关爱。赫里斯托佛罗夫和尼科季莫夫,一正一反,一明一暗,相互映衬,共同传达出扎伊采夫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即贵族阶层道德腐化,精神堕落,内在世界变空虚,现实社会亟需变革。
四、“心灵的人”——列季赞诺夫
小说题目中的“蓝”起到了统领全篇的作用。它不仅修饰了赫里斯托佛罗夫经常仰望的织女星的闪光,还是赫里斯托佛罗夫眼睛的颜色,表明了他与宇宙世界的亲近,相应地也暗示其他人物与宇宙世界的疏远。尼科季莫夫的双眼发黑发暗,他拒绝接受来自宇宙世界的光照,最后不得善终。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列季赞诺夫,他的眼睛是青色的(синие),与赫里斯托佛罗夫蓝色的眼睛相近。但这微妙的色差,却暗示了两人迥然不同的性格与命运。
按照索洛维约夫对神的三个主体的划分,列季赞诺夫属于“心灵的人”。他感受到舞蹈演员拉本斯卡娅的美丽与迷人,被她深深吸引,狂热追求她。此外,列季赞诺夫具有超然的力量。他经常遁入幻觉,聆听魂灵的声音,与魂灵交往,以寻求此世问题的解答。小说里有三次描写列季赞诺夫的这种状态:第一次是他迫切感到上流社会需要保护精神文化,第二次是与尼科季莫夫决斗前,第三次是在他决斗受伤之后。最后一次的时候,马舒拉向列季赞诺夫解释了蓝星的意义,他深受启发。在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体系里,除了论证充分的理性思辨以外,还有神秘主义成分,即“诉诸于直觉、顿悟、超验和非理性的所谓神秘主义”[9]32。列季赞诺夫的这些幻觉表明,他虽没有达到赫里斯托佛罗夫对世界那般明晰的认识,但与魂灵的交往促使他走近神的世界,而不是一味生活在现实的混沌与黑暗中。
尽管如此,列季赞诺夫同尼科季莫夫一样,终结于死亡。列季赞诺夫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心灵的人”。他那青色的眼睛一方面肯定他与蓝星的接近,另一方面暗示这终究不是蓝色的闪光,因而他没能完全接收来自宇宙世界的启示,没有获得真正的神性。“列季赞诺夫眼睛里的青色是赫里斯托佛罗夫蓝色的危险的、虚假的反映符号。列季赞诺夫青色的眼睛……只看到他眼前的东西:事物的表面。”[3]62的确,列季赞诺夫是个天真烂漫的人物,可他一味爱恋的对象无情地玩弄了他,并弃他而去。
对于列季赞诺夫的个人悲剧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理解。内在主观方面,列季赞诺夫青色的眼睛看到的并非真正的美,而只是拉本斯卡娅外在虚假的美。列季赞诺夫天真地认为,“韵律和神圣的轻盈构成她的实质的基础”,在她身上“异常纯洁地表现出女性的原质。淡蓝色飘飘然的实质,充满了轻盈和光”[4]307-308。可事实上,拉本斯卡娅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她既没有给列季赞诺夫带来心灵上的光明,也没有照亮他的前程,更没有像马舒拉那样给人清澈的安宁。假面舞会上,列季赞诺夫疯狂地寻找她,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感受不到拉本斯卡娅的存在,对她的狂热追求导致列季赞诺夫丧失理智,精神上变得盲目无所适从。之后他与尼科季莫夫决斗受伤,最终在得知自己被欺骗后抱悔而终。
外在客观方面,对于列季赞诺夫的悲剧,拉本斯卡娅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在扎伊采夫笔下,她同马舒拉一样都是女性气质的化身,但拉本斯卡娅已是另一种代表——轻盈。赫里斯托佛罗夫感觉,“终生不安,受难,受折磨——不属于她。她纯洁,轻盈,优雅,像一块为春天、为天空造就的云彩那样度过一生”[4]296。拉本斯卡娅本应成为和谐与美好的化身,可充斥她内心的是物质名誉。当列季赞诺夫为她决斗受重伤时,她虽去探望,但仍旧接受新崇拜者的照料,并打算与其一起奔赴欧洲。“她身上没有爱,没有与某个人的精神联系”,因此,拉本斯卡娅“不能给人永恒的生活,只能给予死亡”[5]38。可见,列季赞诺夫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这样的女性,其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
无论列季赞诺夫认为自己的追求多么美好,拉本斯卡娅虚假的反光在他身上激起的仍是世俗意义上的情欲,还没有上升到精神的高度。诚然,拉本斯卡娅曾经给予列季赞诺夫的心灵以快乐,可这种快乐并没有使他的存在变坚实。相反,在对拉本斯卡娅的狂热追求中,列季赞诺夫感到漂浮不定。他完全被爱情吞噬,沦为拉本斯卡娅轻浮、飘渺性情的俘虏,进而脱离神的世界。
五、结语
小说《蓝星》里复杂的人物形象体系表达了扎伊采夫对和谐宇宙世界的理想追求,对神圣女性形象的宣扬,其在一定地程度上发展了索洛维约夫的神人说,艺术性地展示了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的结合。蓝星来自自然界,但超越有限的自然,在自身中包含万物,承载世界的灵魂。“背负基督”的赫里斯托佛罗夫借助这颗星星的庇护与指引,在此世找到了带有蓝星闪光的马舒拉。马舒拉从赫里斯托佛罗夫那里体会到蓝星的宇宙意义,并将这束神圣的光传递给列季赞诺夫,从而界定后者对拉本斯卡娅狂热追求的实质。虽然织女星的蓝光照耀整个大地,但仍有这束光射不穿的地方,这便是尼科季莫夫黑暗的心灵。即便如此,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依旧用自己微弱的光向尼科季莫夫送去温暖与关爱。尼科季莫夫和列季赞诺夫深陷生活的泥淖,与神脱离,他们的生活最终化作悲剧。马舒拉和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深刻领悟经赫里斯托佛罗夫传播的宇宙智慧,自觉承担传递蓝星光照的使命,通过自身与神的结合使生活充满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