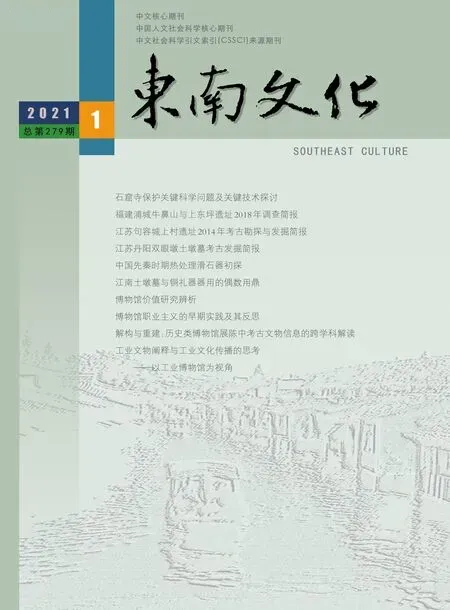博物馆展览中考古文物的阐释模式
2021-05-11魏敏
魏 敏
(成都博物馆 四川成都 610000)
内容提要:博物馆展览从器物描述、文物解读到主题阐释的发展和转变,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成果。而阐释理念的发展并不是“淘汰”或“取代”,描述、解读和主题阐释并不相互排斥。在具体的策展实践中,根据展览主题和展品类型,综合应用阐释手段,合理处理各个阐释层次之间的主次关系,以更有效地传递知识、信息,才是展览成功的关键所在。同时,博物馆应更加注重描述性阐释在信息传递中的重要作用,利用适当的陈列手段突出信息传播的重点,根据目标观众对展览信息的偏好确定阐释层次的侧重点。
一、阐释理念的深层发展与观众认知模式的矛盾
作为文化遗产大国,我国的考古文物构成了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的主体。而博物馆围绕历史文物所进行的“阐释”则与相关的学科发展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嬗变中。
1.从器物描述到主题阐释
最基本、最常见的文物阐释是基于考古类型学对器物本体的描述,即“描述性阐释”。从考古学诞生起至20世纪60年代,类型学(typology)一直是考古研究最主要的分析手段,旨在通过对器物的形态特征、装饰风格的分类描述建立年代序列、构建文化谱系和研究文化关系,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博物馆阐释的基础。基于考古类型学的分类展示并不是对展品的简单罗列,而是力求通过完善的分类体系来揭示藏品本质属性,但这种分类体系往往使博物馆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器物类别作为经验性的归组,并不能涵盖器物的所有属性。例如,一件精美的、纹饰丰富的史前陶器至少具备了历史和艺术的双重属性,而类型学的分组方式侧重于建立文化序列,并无法提供艺术史上的阐释。另一方面,基于考古类型学的器物描述往往有一定的范式,如“侈口”“鼓腹”“圈足外撇”“是××文化的典型器物”等艰深、晦涩的考古学术语频频出现在博物馆的展品说明中,很难激发普通观众的观展热情。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器物本身的描述性阐释所能够提供的信息相当有限,使其难以在更加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被认知。虽然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cultural-historiacal ar⁃chaeology)将复原历史文化作为目标,但囿于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无法从根本上达到“透物见人”的目的。
20世纪60年代,以路易斯·宾福德(Lewis R.Binford)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认为,考古学应该抛弃历史学的描述性方法,而进行规律性的探索,并将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定义为三个范畴,即复原文化历史、复原人类的生活方式、重建文化过程[1],而现有的考古学分类和比较根本无法达到考古学的预期目标。于是,民族学、生物学、环境科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被用于考古学研究,增强了考古学家提炼、分析和复原信息的能力,也直接促使了博物馆阐释理念的纵深发展。从器物层面来说,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使得考古学家能够对文物进行全方位的立体研究,策展人有足够的学术支持在纵横的时空坐标中对器物功能、艺术风格、社会意义等进行综合性的“解读性阐释”。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来,新考古学强调“系统论”,认为文化是适应外界环境的系统,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转,传统的类型学分组未必能够反映社会系统的运作和演进方式。而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则进一步指出,人的思想和能动性对文化的塑造和环境同样重要[2],鼓励多元阐释,强调相关性(context)研究的意义,即处于不同背景中的器物具有不同的意义。以此为基础,博物馆展陈理念开始由实物主导向信息主导转变。在信息主导型陈列(information-oriented exhibition)中,展品本身不再是展览唯一的焦点,而已经转变为信息传递的重要实证。策展人根据展览主题来组织展品,“并以考古学为核心,对博物馆展陈中的考古文物、资料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系统阐释,使文物能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相联系,赋予其情节性和故事性”[3],即所谓“主题性阐释”。这也是目前博物馆学界较为推崇的阐释方式。
2.基于观众研究的阐释悖论
博物馆展览从器物描述到主题阐释的发展和转变,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成果。根据新颖的展览主题来合理构建展览框架、组织展品,按照“设计”好的思路对观众进行历史叙事或引发观众思考,是当代策展人津津乐道的工作。然而,观众是否会按照馆方设计好的方式层层深入地理解展览所要传达的信息和主题?那些传播主题鲜明、学术研究基础扎实,并在信息解读的过程中充分应用考古学阐释方法的展览,能否真的给观众带来最佳的观展体验?
博物馆观众研究的数据表明,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总是从具体的细节开始的,如“这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用来干什么”“它值多少钱”;而很少有人关注器物背后的抽象信息,如“器物在历史过程中的质量变化”“为什么这幅作品会成为抽象艺术的里程碑”“这些器物有什么象征意义”等关于展品的解读性内容并非观众关注的焦点所在[4]。换句话说,“描述性阐释”比“解读性阐释”更符合观众的认知模式。而在“主题性阐释”的层面,策展人强调以器物组合的形式来传递展览信息,存在于展览信息链条中的个体特征被弱化。或许新颖的展览主题在展览宣传上更吸引眼球,但在实际的博物馆展厅环境中,参观过程的不连续性是博物馆观众的普遍行为。这首先出于人体的本能反应:在陌生的环境中,人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熟悉适应,寻找适合自己的参观方式。同时,受参观时间和体力所限,人们无法在有限的参观时间里观赏所有的展品,因此大部分观众无法按照策展人预设的逻辑和线路观展。此外,人们的认知过程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面对陌生事物,人们通常会依据一定的线索从记忆中寻找所需要的信息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如果新信息能够与观众的认识结构相沟通,那么就十分容易被观众吸收,反之则被观众排斥[5]。在参观过程中,观众倾向于为陌生的展品寻找“参照系”,用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理解新的事物。因此,即便在参观时间相当充裕的情况下,人们也倾向于选择一些自身感兴趣的内容仔细阅读,而略过一些相对枯燥的内容。尽管策展人根据既定的展览主题给出了完整的故事线,但大部分观众所获取到的展览信息仍然是碎片化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博物馆所推崇的阐释理念与观众需求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博物馆作为公众服务机构,应与一般的娱乐性场所相区别,利用文物藏品进行普及性教育、为社会公众提供持续的文化补给是博物馆的根本使命,有意识地将学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所能接受的知识和信息是博物馆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虽然博物馆体验的最后效果与参观个体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性格特征、同行人员等密切相关,但博物馆创造出的特定环境、陈列语言的合理应用亦会对观众的博物馆参观体验施加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阐释理念的发展并不是“淘汰”或“取代”,描述、解读和主题阐释并非相互排斥。根据观众行为模式和理解能力,如何在展览中综合应用阐释手段,合理处理各个阐释层次之间的主次关系,从而更有效地传递知识和信息,才是展览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案例分析:展览中几种常见的分层阐释模式
实际上,博物馆阐释与观众认知行为之间的矛盾已引起博物馆的注意,博物馆尝试根据展览主题和类型而采用不同的阐释模式,对信息层次作出必要的取舍,创造更好的观众体验。
1.主题性阐释下的文物解读
根据一定的展览主题、以打破原生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来传递展览信息的主题性阐释,仍然是目前博物馆展览最常见的阐释模式。尤其是对于地方历史文化陈列而言,主题性阐释具有明显的优势。荣获“第十六届(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以下简称“‘湖南人’展”)、“陕西古代文明陈列”均采用主题性阐释的模式:“湖南人”展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示湖南的历史与文化,层层递进,以打破时空关系的主题来组织展品,力求达到“见人见物见精神”的目的;“陕西古代文明陈列”则以陕西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为主线,重点突出周、秦、汉、唐各时期的文明成果。这种主题传播的模式将历史的情节性、故事性与具体的文物联系在一起,能够迅速、有效地引导观众理解展览内容。除地方历史文化陈列外,近年来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特展,如“平天下——秦的统一”(以下简称“‘平天下’展”)、“大海道——‘南海I号’沉船与南宋海贸”也采取了主题性阐释的策展模式。尤其是“平天下”展,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家书——“云梦秦简”中的“黑夫木牍”开始,以“黑夫”和“惊”两个普通百姓的视角回看2200年前的世界,展现秦国由西方的弱小部族成长为统一帝国的漫漫征程,并试图让观众思考和体会为什么是秦人最后统一六国、秦人凭借什么力量完成统一、为什么布衣黔首会追随统治者并参与统一战争以及“大一统”政体的创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的解读使得整个展览体现出强烈的叙事色彩,可谓主题性阐释的典范之一。
然而,虽然主题性阐释本身仍然以文物解读为基础,并且力图将精品文物作为重要的信息传递结点并合理地安排在展览的重要位置,以发挥调动观众观展情绪和控制展览节奏的作用,但在具体的文物解读上,往往因为需要与展览主题高度契合,而不得不放弃许多重要的信息。例如,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以下简称“‘花重锦官城’展”)中对镇馆之宝——“秦汉石犀”的阐释,就是基于《华阳国志·蜀志》中李冰“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的记载,佐证都江堰修建的重要意义。而观众访谈的结果却显示,石犀的来历、被发现的经过、何以成为镇水神兽乃至其原型是否为曾经生活在成都平原的犀牛等都是观众希望了解的信息[6]。换句话说,在信息解读上对展览主题的高度迎合使得镇馆之宝的精彩故事难以被观众了解。这实际上也是主题性阐释的通病。因此如何在归纳展览各个层级主题的同时兼顾文物阐释的层次性与多角度,是值得在实践中探讨的问题。
2.文物阐释与宏观叙事
近年来,国内外的策展团队也在力求打破主题性阐释的一般模式,试图将信息传播的重心从主题转向文物本身,即通过对文物的深度阐释来推动展览故事线的发展。由英国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策划,在全球巡展的“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即是通过深度的文物解读进行历史叙事的典型案例。策展人以全球化的宏大视野选取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100件(套)文物来讲述人类200万年的历史,并涵盖了世界所有地区的文明。展览将文物按照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分为“开端(公元前2 000 000—前2500年)”“最初的城市(公元前3000—前700年)”“权力与哲学(公元前700—前100年)”“仪式与信仰(公元1—800年)”“贸易与侵略(公元300—1100年)”“变革与调整(公元900—1550年)”“邂逅与连接(1500—1800年)”“我们创造的世界(1800年至今)”八个部分,每个部分虽然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十件左右的展品,但对每件文物都进行了详细描述和深度阐释,既有出土地、时代、流传等基本信息,也对展品的形态、纹饰、用途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最后延伸至揭示展品所体现的社会面貌等。类似的案例也见于由浙江省博物馆策划的“越地宝藏——一百件文物讲述浙江故事”、湖南省博物馆策划的“根·魂——中华文明物语”(以下简称“‘根·魂’展”)等。尤其是“根·魂”展,仅选取了来自全国23家单位的30件精品文物来讲述中华文明史,因此在文物解读上比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更加细致深入,每件文物的阐释都分为“基本信息”“背景资料”“文物图解”“内容拓展”,从各方面层层深入,力求将每一件展品都置于立体的历史时空中多方位阐释。例如,展览对甘肃省博物馆藏“魏晋驿使图画像砖”的解读首先从文物的基本描述入手;接着对展品的出土地——嘉峪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及该地区出土的类似文物概括等进行了解读;进而以文物图解的方式对画像砖的画面内容进行了阐释;最后的“内容拓展”部分则将画面所表现的“驿使”的内容延伸至关于中国历代通讯方式与保密措施的演进、交通工具的演变等方面的介绍,在时空坐标中对展品重新定位(图一)。

图一// “根·魂”展对“魏晋驿使图画像砖”的文物图解(图片来源:《根·魂——中华文明物语》,第60页[7]。)
虽然通过对文物的深度阐释来推动展览故事线的发展彰显了“以物述史”的独特魅力,但问题也显而易见:展览的文物与文物之间、文物与所谓的展览主题之间的联系过于抽象,如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的“最初的城市(公元前3000—前700年)”所选取的“美索不达米亚‘大洪水’记录板”和“印度文明印章”,在出土地、文物形态特征、功能用途上均无直接关联,普通观众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并理解展览所要表达的“不同地域的早期城市发展面貌”这一主题。观众在观展过程中或许可以“窥一斑”,但的确很难“知全豹”。同时,由于展览对文物的阐释模式相对统一,缺乏表达形式的转换,难免使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产生审美疲劳。
在展览策划中,有没有可能将展览的主题性阐释与个体文物的深度解读相结合?
3.主题与文物并重的阐释模式
成都博物馆2020年组织策划的原创性展览“映世菩提”特展,是典型的以佛教造像为题材的文物专题展。从展陈内容和展品组织看,策展团队打破了该类题材的展览以造像艺术为解读中心的阐释模式,力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讲述南朝造像艺术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对南北朝各重要时段、各区域造像艺术的关联性阐释展现南朝造像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策展团队注意到,南北朝时期兵戈扰攘、政权更迭频繁的社会因素是造像艺术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展览框架的构建以历史发展的大事件为主要分割点,分为“丝路佛影”“齐梁之变”“和韵共生”三个部分,是典型的主题性阐释的展览框架模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策展团队放弃了对造像本身艺术性和宗教含义的解读和阐释。相反,“佛教艺术的中国化”是贯穿展览始终的主线。在具体的内容呈现上,策展组在每个造像组合中都选取1~2件造像作为中心展品,综合性地重点阐释其艺术特征、宗教含义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等内容,以点带面,既避免了以文物组合传递信息相对笼统的短板,亦帮助观众有重点地深入理解造像艺术。例如,展览第一部分“丝路佛影”将四川博物院藏“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作为中心展品,该造像碑是现存时代最早的、有明确南朝纪年的佛教造像碑之一,可视为南朝造像碑的代表作。对这组造像碑的解读集中于两个关键点,讲述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一是通过造像碑出土地点阐释南朝益州(今成都地区)与西凉佛造像的联系,以及“丝绸之路河南道”的文化通道地位。此造像碑出土于四川西北部的阿坝州茂县,处于“河南道”岷江支道的必经之路。从造像碑题记可知,造像主持人为西凉比丘玄嵩,而造像上的主尊弥勒佛和无量寿佛则是当时凉州地区流行的信仰题材,实证了四川南朝早期造像与西凉的关系密切,高度契合本部分的阐释主题。二是通过南齐永明元年(483年)造像与益州同期造像的服饰形态的比较,展现四川地区南朝早期的造像特征以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此造像与此前印度、西域一带佛像的衣饰和台座均有所不同,是典型的“褒衣博带”式佛衣,其样式应来源于东晋南朝士大夫流行的褒衣博带装。这种中国式佛衣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影响深远。在空间布局上,“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处于该单元展示区域的中心位置,与之有文化关联的展品,如“北凉高善穆石塔造像”、成都出土的同为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南齐永明八年释法海造弥勒成佛背屏像”和“南齐建武二年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背屏像”等则环绕四周,既突出重点,又能够使观众在文物的关联性阐释中理解展览主题。
类似的策展模式也见于山东省博物馆组织策划的“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以下简称“‘衣冠大成’展”)。展览共选取山东博物馆和孔子博物馆藏32件明代传世服装作为核心展品,既深入解读服饰的色彩、面料、纹样和款式,也详细介绍织绣工艺和裁缝技术。但文物解读并不仅仅围绕服饰本身,而是与古代书画、青铜器、金银器等文物相结合,展现明代服饰礼仪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更难能可贵的是,展陈还辟出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文创专区,策展团队与著名服装设计师合作,仿制了此次展陈中的三件明代服装;同时将传统的服饰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制作符合当代审美的服装。将古代与现代、传统与时尚完美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一次跨越七百多年的服饰美学对话。
总之,“映世菩提”特展和“衣冠大成”展将具体文物与宏大的时空背景相联系,通过文物组合重构叙事性历史,同时结合对重点文物深入的综合性阐释推动展览故事线的发展,兼顾了主题阐释和文物解读。但这种阐释模式能否被观众接受?针对类似的文物专题展,还有没有更加有效的策展方式?这些都需要未来更多的策展实践和观众研究数据来提供答案。
三、如何在展览中构建有效的阐释模式
无论是以器物组合传递信息的“主题性阐释”,还是以文物解读推动展览故事线的“解读性阐释”,或是文物与主题并重的阐释模式,都与具体的展览主题、展品选择和表达形式密切相关。从目前国内博物馆的展览情况来看,“主题性阐释”可能更适合时间跨度较长、文物相对丰富的常设展,而“解读性阐释”则更能凸显以精品文物为主的特展的展品内涵。虽然文物和主题并重是一种更为理想的阐释模式,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可能会受到展览场地、展品组织及形式设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在展览中建立有效的分层阐释模式,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可初步考虑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重视描述性的阐释
如前所述,观众对陌生事物的认知是从具体细节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描述性阐释”是博物馆展览语言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需要注意的是,观众所期望的展品“细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基于考古类型学的器物描述,而是在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器物所进行的深入浅出的形象介绍。例如,“映世菩提”特展在对南齐永明元年主尊弥勒佛的褒衣博带式佛衣进行介绍时,并没有对佛衣样式进行传统的考古学描述,而是将其与南朝士大夫的服饰相联系,配以1960年出土于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拓片,形象生动地说明这种佛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再如,四川乐山华夏自然蜜蜂博物馆在介绍不同类型的蜜蜂标本时,大量使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大家好,我们是蜂群中的隐居者,来自泥蜂科的沙蜂,因为身材好,也有人称我们为‘细腰蜂’。我们喜欢居住在海岸边的巢穴里,几乎不与人类来往,过着与世无争的独居生活。”以亲切生动的语言代替了呆板的科普性描述,为观众营造出轻松惬意的观展体验。
2.合理利用陈列手段
虽然我们对文物阐释层次划分,首先是基于学科研究和对展览主题的综合把控,但在实际展陈空间中,内容表达必然与一定的形式设计相联系。除文字表述之外,陈列手段的合理运用也是突出信息传播重点的关键环节。“根·魂”展对文物的描述性阐释实际上通过“文物图解”完成,以“图示”代替语言表述来剖析文物的细节信息,不仅更加生动、直观,而且能够有效地缓解观众的观展疲劳。而“映世菩提”特展对南朝“飞天”形象的解读借助了科技手段。序厅的圆弧形空间展示了成都博物馆藏一级文物“王州子造释迦像”,该造像的顶部有“飞天托塔”的图像。“飞天”(亦称“天人”)属古印度佛教天龙八部护法神,为诸天侍。早期的飞天形象带有明显的异域特征,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的神仙思想、道教、玄学等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人形象。中国式天人较早出现在南朝墓葬中,着典型的南朝常服,是益州南梁背屏式造像上常见的纹饰,并影响至北朝。在进行飞天形象的解读时,策展团队与设计人员反复沟通,以南朝墓葬中的“天莲花化生天人图”为原型制作创意动画,投屏于半圆弧形的背景墙上,与文物相呼应,从而调动观众的情绪。“衣冠大成”展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不同服装在不同场合的穿着情况,将明代于慎行的《宦迹图》以多媒体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收到良好的效果。
3.注重阐释的层次性与观众分层
值得注意的是,展览侧重于哪种阐释层次应与博物馆观众分层密切相关。不同类型的目标观众在博物馆展览语境中如何欣赏和理解考古文物?面对同一件考古文物,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理解知识的方式有何不同?根据不同观众群体行为模式的常规推断,针对儿童或青少年的展览应更加侧重对展品的描述性阐释,普通成年观众可能更易接受主题性阐释的模式,而博物馆资深爱好者、相关的专业人员则可能更偏爱解读性的阐释方式。但在实际的观众调查中,观众群体对展览内容的需求比馆方设想的更加复杂多样。以成都博物馆为例,2018年“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是典型的主题性展览,而针对此展览的观众调查表明,普通成年观众(18~65岁)对展览内容的需求分散于“相关历史背景”“区域文明的交流”“青铜器纹饰、工艺演变”“器物功能用途”“铭文解读”等,并未特别集中关注某一类信息;而2020年举办的“光影浮空——欧洲绘画500年”展虽为典型的艺术品展览,但大量绘画艺术资深爱好者却对欧洲绘画发展的时代背景、画家生平等提出了信息需求。
当然,目前的统计数据可能受到主观、客观条件的影响,未必能够完全反映不同观众群体的信息需求。博物馆需要结合具体的策展实践,进行大量的观众调查和数据分析,才能建立起适应公众需求的阐释机制,从而使考古文物最大化地发挥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