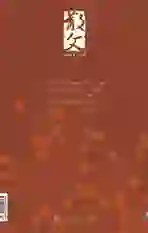城市十公里
2021-05-07卢鑫
卢鑫
一
大雨终于到来, 仿佛内心形容不清白的东西也落到实处。窗外路上,有人与雨正面交锋。地面的潮湿味飘进屋。雨水的轰响和汽车的雷鸣剧烈。想起小时候在老屋,我们与暴雨抗争,从房子这边跑到那边。炸雷仿佛能把屋劈碎。我们用三米长的门闩棒关门。那个堂屋门有点变形, 很不容易合拢。奶奶在瓦屋用锅碗瓢盆接漏。不知风雨什么时候会停。等太阳把热气带回,我们发现, 猪圈楼边的那棵橘子树已被风雨拦腰斩断了。
不过,现在窗外的雨并未示弱。暑热像一只蚊子在雨中左躲右闪。
小女孩正在屋内耍玩具。以前小学五年级时, 爷爷一副麻将牌都能被我当成积木,配合几颗玻璃弹珠,独自从吃完午饭玩到天黑……还有小学六年级, 一个人在小河边玩沙玩水直到傍晚……
也一个人背书包走过很多里山路,看过无数种云、无数颗星,微观过无数种小事物。
二
在成都的暑假时光, 每分钟都会有孩子望向窗外。她会看见对面小区窗棚上有一只橘色小猫正在吃半截火腿肠; 那截火腿肠是在电梯口那间屋里做饭的老婆婆丢给它的, 她当时正高声与修理厨房下水道的工人讲价:“你这是砍人嗦!”修理工收拾完油渍遍染的工具箱,毫不退让,展示二维码收款就转身离开,与外卖员擦身而过;外卖小哥边等电梯边接电话, 听电话那头询问到货时间,电梯来了,他帮助一位遛狗的妇人摁到五楼; 妇人刚刚给她的狗套上狗链, 她与这只雪色大狗在附近公园畅游三小时; 雪色大狗当时四处寻找适合拉便便的草坪,不巧被保安训斥此处不能践踏;保安大爷左手有残疾, 整只手掌据说抗美援朝时被炸毁, 他如今沉默寡言, 但喜欢吼人,不像年轻时那么风趣;这种风趣代表二十世纪的四川,那时麻雀成群,常常撞击成都某扇玻璃窗而死; 跌落的麻雀成为小孩们好奇的起点,他们拿它喂兔子,小兔只对路边太阳照耀下的蒲公英感兴趣; 蒲公英被风吹散,汽车驰骋每个街区;街边店铺柜台斑斓,却一片慵懒,孩子们路过,走上楼来,靠窗而坐,有人依然望向窗外。
三
从家里到地铁的路上, 很多老人摆摊卖小东西。这似乎和其他城市不同。午后,老人们干坐、打盹。人群往来。而优地B区门口, 总有一个老奶奶逡巡, 肩背红色背包,戴耳机大声唱歌。她陶醉在她的世界。还有个瘫痪的老奶奶坐在轮椅上, 身边两只刚孵出不久的小黄鸡叽叽喳喳嬉戏,老人仿佛对它俩说话,像对两个迷你小孙子。
步行途中, 一对母女驾电瓶车飞驰而过。母亲的思想教育课声如雷霆。女儿嘴巴也嚼,大概正读中学。母亲显然处于上风:“本来你就不爱收拾啊! ”
附近路边有块窄地,以前全是葱兰。只要头天晚上下点雨, 第二天早晨就会开一大片。最近变成荒土。另有几株三角梅、紫花地丁。
膳食菩萨招牌已卸,玻璃门紧锁,里面空空如也。某晚回家路上,太饿,进去点两碗三两牛肉粉。旁边刘家面,换成5G体验馆, 去年暑假每天清晨路过都会吃一碗肥肠粉。何必只关注小餐馆? 路边摊位增多,好多人下班都选择卖些小东西赚外快。
“码头故事”是一家火锅店。三年前冬天我们去吃过一次。次年开春,屋里面拆卸一空。如今招牌还在, 一直没有新商家入驻。百世快递包裹分类运输中心,同年也搬离,我曾把签了名的《不鼓自鸣》一本本提去那里,寄送到南北四方,如今成为一家生鲜超市。
红灯刚亮,一只小猫咪来到车道间,爬上一辆货车的车轮,那位司机也发现,开门下车寻找,猫已消失不见。
这一段路,一家冷锅鱼前,有一条胖老狗,形同一个残喘的老人,总被拴在门前树下,昏昏欲睡。今天难得看到它睥睨一切。
四
坐地铁经常如此,发现时已坐过站。立马下一站跑到对面往回坐,结果一抬头,又发现坐过站。又跑到下一站往回坐,结果一抬头,又发现坐过站……于是,在两列往返列车间跑来跑去, 坐过来又坐过去———在这样的死循环中了此一生吗?
五
清晨雨后,风雷余响。看到路过小区阳台上的白色花,想到昨晚雷声大作,雨点喧哗,想到一首歌。
骑车去坐地铁, 听这首《花都在耻笑我》。“死去的友谊,死去的爱情,死去的人,死去的事,还有,就是那些死去了的想象,有很多时节也居然常常不知顾忌地扰乱我的生活。尤其是最后一件,想象,无限制的想象,如像纠缠人的一群蜂子!为什么我会为这些东西所包围呢? 因为我这个人的生活,是应照流行的嘲笑,可呼之为理想主义者的! ”(沈从文《若墨医生》)昨晚,从文先生来入梦。生活总是如此转山转水转场。时光倏忽而逝。我们都像电影《美丽人生》中从花园空镜头里蹦出来的小孩,喊:“早安,公主。”
我说“我们”,是因为提前讲述了这件事。昨晚走在佳灵路,小老虎说肚子刺痛两三秒,很有可能是小天使正在抓脐带。
七月的暑热令人窒息。可成都却连续下了十多天雨。星星使出浑身解数散发光亮。你可以打开心眼,看到雨幕之上那更远处的星光,反射在四川盆地。
直到搬離幸福时光, 才理解为什么那位门卫总是板着脸。当你没带门禁,当你双手都举重物, 当你好声好气叫叔叔帮忙开一下门时,他都是一脸冷漠,装没听见。
他手上有残疾, 右手全废, 右手手指头、右手手掌都没了。搬家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件事。
想起爱笑兄弟创作的小品《功夫餐厅》,讲了一个故事——
这家餐厅的员工都拥有特殊武艺。有右手会冲击波的,有会无影手的,有会草上飞的,有会狮吼功的。他们来自不同环境,却凑在一起。餐厅不久将被收购,这些员工何去何从?编剧在后小半部分揭晓答案,以会冲击波的肖旭的视角,公布他的日记:右手会冲击波的他只是左手残疾, 会无影手的哥们儿是因为腿发生故障, 会草上飞的只是坐在轮椅上, 会狮吼功的老板也只是平常说话声音大而已。
他们都是普通人,却发挥自己的优势,以世间所得,滋养天赋,让天赋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这一天正以理想的速度逝去。坐在书桌前,又翻到伍尔夫女士令人心碎的文字。“她本该平静地写作, 现在却在愤怒中写作;她本该明智地写作,现在却在冲动中写作。她本该写她笔下的人物,现在却在写她自己。她在和自己的命运搏斗。这样一个女人, 除了精神抑郁、内心苦闷和早早地去世,结果还能怎样呢?”写作如此平静、如此明智、如此悲悯的伍尔夫女士,你是那么想留下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亮光, 可为何会像文森特一样,过着吊诡的人生?
“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曾把这句诗改成“时人见我恒稚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是自我解嘲吗? 翠红说,“适应不良”也是个成问题的判断。有些适应不良是病态,比如不能共情,难以建立、维持人际关系,然而,社会也从来都是由不能完全接受它,从而想要改变它的人推动。无原则地接受、适应社会的注定是庸人,而在变态社会(比如纳粹德国)适应良好的,毫无疑问的只能是病态。究竟什么是成熟呢?我们该如何做父亲?
时人见我个性形成,自我发现,精神结果、丰收。教育的目的难道不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凸显出来吗?关于爱的教育,其实同样如此。
这真是一个吊诡的夜晚。
充电台灯电量逐渐虚弱, 仿若古时行将燃尽的松明。那些书和稿纸,那些画册,投射的影子组合重装, 困倦的夜魔将你恍惚间套进影子之城,仿佛脱出了躯壳,飘浮在轻盈的空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