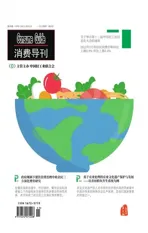卡勒德·胡赛尼的创伤叙事
——以《追风筝的人》为例
2021-05-06赵芳兰郭佳
赵芳兰 郭佳
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创伤叙事,即“对创伤时间、创伤影响、创伤症状、创伤感受、创伤发生机制等的叙述”[1],可分为医学性和文学性创伤叙事两种。“文学性创伤叙事的目的至少是双重的。”[2]其创伤主题旨在“祭奠人类历史上创伤事件中的受害者,记录人类发展中的艰难、遗憾和痛楚”[2];其叙事技巧旨在“以创伤为创作媒介以便创作出更深入人心的作品”[2]。
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小说《追风筝的人》讲述了阿富汗普通个体遭受的家庭创伤与性别创伤,通过朴素的文笔将真实的阿富汗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小说中的创伤书写就是这种双重目的的体现,也是本文探讨的核心内容。
二、创伤主题
作为胡赛尼的代表作之一,《追风筝的人》表现了家庭创伤、性别创伤等多重创伤主题。其中,家庭创伤主要体现在主人公阿米尔身上,而性别创伤则集中体现在其中的女性形象身上。
(一)家庭创伤——母爱缺席与父爱错位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小说主人公阿米尔,由于童年时期母爱的缺席与父爱的错位,遭受了严重的家庭创伤,是“用一生治愈童年的”的典型人物。
研究证明,单亲家庭子女在情感方面会产生“孤独感和抛弃感”、“自闭自卑心理和自尊心扭曲、逆反、仇视心态”、“自责感和不安全感”以及“猜忌心理和不信任感”等。而在性格和行为方面,“单亲儿童具有高精神质、偏内向、情绪不稳定、心理发育不成熟的个性特点……有研究显示,随父亲生活的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差,易退缩、明显偏执、人际关系紧张。有的单亲儿童会出现性格不完善和性别角色移位。”[3]而幼年丧母的阿米尔有着明显的上述特征,比如他除了哈桑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童年玩伴,“总是埋在书堆里,要不就在家里晃晃悠悠,好像梦游一般。”[4]除此以外,他经常会因为母亲的去世而自责,总觉得父亲恨自己,“毕竟,是我杀了他深爱着的妻子,他美丽的公主,不是吗?”[4]性格方面,借父亲的话来说,阿米尔“身上缺了某些东西”,“我看到他们推搡他,拿走他的玩具,在这儿推他一下,在那儿打他一下。你知道,他从不反击,从不。他只是……低下头,然后……”,[4]这些都形象地反映出阿米尔童年时期易畏缩、“不能保护自己”[4]的性格特点。而父亲对哈桑的关心爱护的这种父爱错位,让阿米尔开始对哈桑有了仇视心态,在父亲请人医治哈桑的兔唇时,阿米尔心生妒忌,觉得“太不公平了……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4]甚至之后阿米尔陷害逼走哈桑,都有这种仇视心态的驱动,这些都是阿米尔在母爱缺席与父爱错位的家庭创伤中所产生的情感以及性格问题的表现。
(二)性别创伤——“她者”与“女从”
“肖沃尔特将那些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她们声音的女性称为‘other women’,国内将其翻译为‘她者妇女’‘女她’或者‘她者’。”而将被“推到政治伦理等级的下层,从而沦为男性‘附庸’‘仆从’”的“从属”“边缘”女性称为“女从”,“处于‘女从’地位的女性无社会主流文化话语权,她们的话语权利、女性意识与她们的身份一起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她们是社会主流文化的缺席者与受虐者。”[5]这些“她者”和“女从”形象是典型的性别创伤受害者。阿米尔的母亲索菲亚·阿卡拉米便是其中之一。故事中,这位女性角色自始至终是一个缺位的状态,我们每次见到她,都是通过阿米尔的描述,而阿米尔对母亲的了解,都是从他人口中的得到的,这种辗转反复、间接呈现女性角色的描述方式,充分体现了女性个体价值的渺小与微弱,是典型的“她者”。其次,在提到这个角色时,“父母”、“妈妈”、“妻子”等字眼出现得较为频繁,而她自己本来的姓名“索菲亚·阿卡拉米”却只提到了两次,这让她几乎成了一个男性的附属品。对于阿米尔父亲而言,妻子是他的“公主”,能娶到她让“爸爸十分高兴”,[4]然而高兴的原因却是索菲亚“受过良好教育,……祖上是皇亲贵胄。”[4]这种简单粗暴地用外在物质因素定义女性价值、用女性的优势用来“装裱”男性形象、为男性服务的态度,是对女性个体价值的忽视与蹂躏。索拉雅的母亲雅米拉是另一个性别创伤的承受者。雅米拉是阿富汗将军的夫人,“在喀布尔时,一度以美妙的歌喉闻名。……可是,尽管将军非常喜欢听音乐……他认为演唱的事情最好还是留给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去做。他们结婚的时候,将军的条款之一就是,她永远不能在公开场合唱歌。”[4]就这样,强硬专制的将军,无情地扼杀了雅米拉喜欢唱歌的爱好,剥夺了她本应该拥有的权利。除此以外,她在自己的将军丈夫面前地位低下,“她细数身上病痛的时候,……将军对此充耳不闻。”[4]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身份地位完全低于男性,卑微、低眉顺眼、没有话语权、毫无存在感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她们的社会职责便是承担所有的家务,服务男人,忘却自己的烦恼,想方设法取悦男人。”[5]这种男权社会下,女性理所应当的自我牺牲,使女性完全沦为了“典型的社会主流文化的缺席者与受虐者”[5]。
三、叙事技巧
《追风筝的人》同样以其结构复杂、匠心独具的情节设置著称于世。而将这些复杂内容架构得惟妙惟肖、使得整部作品熠熠生辉的,便是其巧妙的创伤叙事技巧,其中包括时空倒错与固定式内视角。
(一)时空倒错
热奈特称:“时间倒错叙事毎时每刻全部存在于叙述者的头脑中,自从他在精神恍惚中领会其涵义的那天起,便不停地同时抓住一切线索,同时感知一切地点和一切时刻……主人公一刹那间重新织出由他的一生变成的,并将成为其作品之经纬的纵横交错的‘回忆网’”[6]。《追风筝的人》其实就是阿米尔的创伤经历纵横交错的回忆之网。本书由阿米尔重返阿富汗,踏上再次成为好人的路开头,然后引起了下文的大篇幅回忆。热奈特将叙事时序做了分类,“用预叙指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用倒叙指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述,留下时间倒错这个笼统的术语指两个时间顺序之间一切不协调的形式。”[6]本书中不断交错重叠的时空倒错就是由大量“倒叙”并配以少量的“预叙”构成。
倒叙的运用撑起了全书的叙事框架。最为典型的是小说开篇。“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4]一句引起阿米尔的回忆,倒叙就此展开。作为一本杰出的创伤小说,这种大篇幅的倒叙恰恰证明了“创伤故事是对一种迟来体验的叙事”[7]这一本质。在经过时间积淀之后,叙述者阿米尔对于整个创伤故事的理解更加深刻,这让他的娓娓道来更易深入人心,而主人公阿米尔对于种种创伤的体验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有了新的认识。因此,无论是叙述者阿米尔对自己所受伤害的描述,还是对哈桑、阿里所受伤害的描述,都在这错乱的双重时间中更富有感染力,更引人入胜。每当有愧于哈桑的阿米尔想起自己曾经的“卑劣”行为,时间——叙事所在的时间、叙事中所讲述的回忆所在的时间——便以明显的“之”字形交错重叠,往复运动。大篇幅倒叙中,两种时间的分离让读者以阿米尔的视角进入叙述者的创伤记忆之中,与阿米尔感同身受。
此外,小说中预叙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叙事方式,而且为读者铺设了暗示故事发展的线索。如,拉辛汗和父亲对阿米尔的性格进行评价,拉辛汗称阿米尔软弱但并不卑劣,而阿米尔暗想道:“至于那卑劣的性格,拉辛汗错了”[4]。此处阿米尔对自己的评价,其实是对后文中他间接及直接伤害哈桑的“卑劣行为”的铺垫。后文中,阿米尔目睹哈桑遭强暴却转身离开;之后,又诬陷哈桑以逼迫其离开,都印证了此处阿米尔自己所想的“卑劣”二字。
(二)固定式内视角
叙述视角,即“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8]。关于叙述视角和聚焦模式,申丹进行了以下分类:
(1)零聚焦或无限制型视角(即传统的全知叙述);
(2)内视角(它仍然包含热奈特提及的三个分类,但固定式内视角不仅包括像亨利-詹姆斯的《专使》那样的第三人称“固定性人物有限视角”,而且也包括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中心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
(3)第一人称外视角(即固定式内视角涉及的两种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眼光);
(4)第三人称外视角(同热奈特的“外聚焦”)。[9]
根据以上分类,我们可以发现,《追风筝的人》主要采用的是与第一人称有关的固定式内视角,主要为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和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只有在涉及到哈桑和拉辛汗所写的信件时,才将角度暂时移向了哈桑和拉辛汗。这种固定式内视角的使用更利于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首先,固定式内视角能够让文中自由地出现独白,为主人公充分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提供了可能,“在展现人物内心创伤方面更能起到渲染读者情绪的作用”[10]。而另一方面,固定式内视角的使用具有限定性功能。“‘内聚焦又是一种具有严格视野限制的视角类型。’叙述者观察的角度仅限于自身,表达内心所思所想与目之所及,而关于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动,只能揣度猜测。一个人的视角总是有限,远不如全知视角居高临下俯瞰全局,因此小说中自然会出现视线死角,形成‘空白’,若空白和案件正好相关,那悬念也自然而然形成。”[11]而作为故事中的唯一叙事人,阿米尔从自身视角出发所观察到的事情,具有很大的限制性。比如他无法知晓哈桑是否想念他的母亲,亦无法知晓父亲为何那么喜欢哈桑。这种“视线死角”所形成的“空白”,让父亲的秘密和哈桑的真实身份被隐瞒了几十年,也让他犯下了赶走亲兄弟的大错;同时也为读者设置了悬念,给与了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对之后的故事情节充满期待。
四、结论
胡赛尼用时空倒错与固定式内视角等高超的叙事技巧,构建起《追风筝的人》独具匠心的心理空间,编制出纵横交错的回忆之网,为读者展示了阿富汗裔美国人的创伤记忆。其中,家庭创伤扭曲了以阿米尔和哈桑为代表的阿富汗儿童的人格,令他们的童年记忆不堪回首;而严重的性别歧视所造成的性别创伤则成为一代又一代阿富汗妇女难以治愈的集体创痛。而胡赛尼的创伤叙事则是通往疗愈与救赎的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