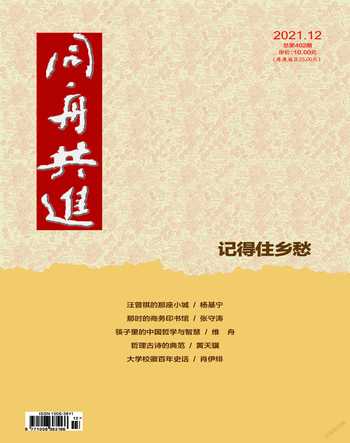筷子里的中国哲学与智慧
2021-05-03维舟
维舟
筷子,毫无疑问是中国餐饮乃至中国文化最广为人知的象征之一。
学会使用筷子,往往隐含着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接受”。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因为无法使用筷子而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之后他为了增进两国关系,特地让助手给他准备了一套专门练习拿筷子的道具。
最早看到中国人用筷子吃饭的西方人,对此是极感好奇的。最早描述此事的是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1515年他来到东方,惊奇地发现“在马六甲所见到的那些中国人……他们用两根小木条吃饭,左手捧着陶碗或瓷碗,碗凑在嘴边,用两根小木条将饭拨进口里”。1682年,中国天主教徒沈福宗随传教士柏应理到欧洲,许多从未见过中国人的欧洲人对他充满好奇,被欧洲各国王室成员竞相邀请。两年后,他到访法国时,路易十四被他深深吸引,在见面的次日又邀请他共同进餐,只为看他如何使用筷子。
到19世纪,西风东渐,西式礼仪被许多亚洲国家的中上阶层所效仿——但这种效仿是有选择性的,如同日本、波斯抗拒了西式的椅子,中国则拒绝了刀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3到1845年间,五口通商不久,英国谢菲尔德的一家著名洋行运来大批刀叉,宣称要把这些餐具卖给中国人。英国人库克说:“中国人向来不用刀叉,而是用筷子的,对这些东西当然看也不要看。结果这批刀叉的售价还抵不上运费,而香港店铺里许多年后还陈设着这些刀叉,排成像武器库里的刀枪剑戟一样。”如今的东亚,仍有着自己的餐具文化形态。
餐具并不仅仅只是餐具而已,在人们眼里,那往往是文明的象征。
相比起中国源远流长的筷子,西式刀叉的兴起甚晚。古罗马人不用餐叉,欧洲人长久以来的主食是燕麦粥(普通人)或面包(上层社会的配餐),都可以用勺子或手来吃。11世纪时,欧洲当时最富有的城邦威尼斯的执政元首迎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她用“有两个齿的金属的长柄叉”把食物送到嘴里,这是欧洲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餐叉,但时人的反应却几乎将之视为丑闻:“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是一种极度的讲究,以至于元首夫人受到了教会的严厉斥责。教会把天怒降到她的头上。不久,她染上了一种令人作呕的疾病,圣·博纳旺蒂尔立刻宣布,‘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文明的进程》第一卷)
此后,餐叉逐渐被意大利城邦的上层社会所接受,但对于西欧的很多地方而言,这仍是稀罕物。1520年参加威尼斯公爵的宴会后,法国丝绸商人雅克·勒赛格在日记中惊奇地写道:“当贵族们想吃肉时,他们就用银叉叉取。”当时的西欧还远比意大利落后,1533年,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嫁给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时,使用餐叉仍被法国人视为一种做作的行为,如果食物没叉好而掉落,会遭到旁人的讪笑。在当时,“从国王、王后一直到农夫和农夫的妻子都是用手来进餐的……最讲究的人只有三个手指进餐。这便是上流社会区别于下层社会的高雅标志之一”。(《文明的进程》第一卷)因此,当法王亨利三世又从威尼斯把用餐叉的習惯带到法国时,并将叉子由原先的两齿、三齿,改成了至今固定不变的四齿,为了这种“矫揉造作”的就餐方式,他的宫廷侍从没少受别人的嘲笑:“上帝给了我们双手,用来进食,而亨利三世的宫廷上下,竟然如此娘娘腔和如此丑陋,居然用叉子吃饭。”当时的大作家蒙田也说:“我很少使用勺子和叉子……吃得忙乱,我几次咬到了自己的手指头。”
如果说西方在近代文明的进程中强调用餐“不能直接用手”,那么在东亚,这一点早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事实上,在近代西式餐具普及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文化圈的东亚地区是不用手进餐的。《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从17世纪时起,在欧洲,人们开始用小刀、叉子和汤匙进餐。在此之前,世界上除了中国文化圈以外的地区,一般都是用手吃饭。”
佛教徒在印度原本习惯了坐在地上用手抓饭吃,但戒律中关于“踞食”“手食”的条文,在传入中国社会后渐渐被改掉,时至唐代,僧人用筷子进食已成“佛教本土化”之一大特征。
当然,在文明诞生的初期,全人类都是用手进食的。现代汉语中将第二根手指称作“食指”,可知这是古时伸到食物或汤水中尝味用的手指。《左传·宣公四年》中记载,郑灵公得楚人献“鼋”(甲鱼),与大夫们共食,却不给子公吃,子公大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此即“染指”一词的出典。

中国人早在汉唐时代,就已将用手进食看作是不雅、不体面的行为了。最早记载日本人的古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就提到当时的倭人用手进食——直至7世纪,日本人才开始使用筷子。“共饭不泽手”一语见《礼记·曲礼上》,孔颖达疏:“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既与人共饭,手宜洁净,不得临食始捼莎手乃食,恐为人秽也。”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共餐时不可弄脏手,以免影响他人,否则那是相当无礼的。
《史记》载,义军灭秦后,项羽在荥阳围攻刘邦,张良紧急入见,刘邦正在就餐,张良遂说要借他的筷子来比划当前策略(“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至西汉,筷子开始用来从碗中夹取小口饭食放到嘴里;到东汉,人们已普遍使用筷子,王充在《论衡·四讳篇》也引用《礼记》之语“毋抟饭,毋流歠”(不可用手抓饭,不可大口不停喝汤),认为这是“礼义之禁”,可见在当时这已是深入人心的社会准则,并逐渐发展出许多相关的文化禁忌——如不能将筷子插在碗里米饭上,因为只有祭祀死者时才这样等。
如今我们习惯说的“筷子”一词,可能晚至明代才出现,这原是江南一带的吴语词汇,后因避讳而改。明代苏州府太仓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吴中民间多行船,讳言“住”,觉不吉利,连带着“箸”也改为“快儿”,或称“快子”;由于筷子多为竹制,后又改成“筷”字。现在英语对筷子的称呼“chopstick”,源于广东话表“快”之意的“速”(旧拼chok),并变化为“chop”,再加上表示“小木棍”意思的“stick”,最后组成了这个词。但很多方言中仍沿用筷子的古称“箸”——例如福建方言。台湾人陈明忠回忆,他是在1951年后接触到外省人的国语之后,才首次听到“筷子”一词。在接受了筷子的汉字文化圈中,“筷子”一词的称呼大都来自“箸”,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筷子还被亚洲东部的其他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如老挝、泰国、菲律宾,甚至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作为一个外来词,“箸”还经过突厥语进入了波斯语,被称作“chūgī”。
到明清时代,中国已全民普及使用筷子,长挑近夹无不如意,以至于明末时利玛窦来华,看到中国人进食时不用刀叉而用筷子,能以两根光滑的小木棍将任何食物灵巧地送进嘴里,不由得大感惊讶。1934年,丰子恺时著文说“以前听人说:中国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虽是戏谑,但放在17世纪的世界背景下,确实除了东亚之外,没有一地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如果说餐具的使用满足了社会文化礼仪的需要,那么,为何中国人不是像西方那样发展出刀叉,而是发明并使用筷子?
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与中国人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有关。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饮食习惯偏向于吃熟食,除水果之外,菜肴大都要熟透,饮水也惯于煮开,尤其是泡茶,极少直接饮用生水。这的确是更进步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生食带进肠道的微生物比熟食多得多,更易致病,在现代消毒法问世前,仅喝开水就让中国人活得更健康。
熟食意味着离不开火。人类学家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中说:“原始的熟食的方法有二种:一是烘烧,二是烹煮。最先发生的方法自然是烘烧,把肉类放在火内烧,或埋在热灰内烘的方法,是很普通的……用水烹煮食物的方法是较迟的发明,南美火地人和非洲布须曼人据说不久以前还不晓得这法。但这法的发明却还在陶器之前,最早的烹煮器大都是兽皮、树皮或木制的。”西方的主食面包、中东人的馕,都是由前一种烘焙法制成,仍可直接用手吃,甚至烤肉也未必需要餐盘,只是偶尔需要刀叉的辅助;但在中国饮食传统中,最传统的烹饪法是蒸、煮、焖、炖,如果想“趁热吃”,不借助餐具,势必会显狼狈。
更重要的是,煮食需要大量的水(当然还有容器,中国史前文明有发达的陶器文化),煮食的过程中往往也需要小木棍来搅拌。惯用陶器、多竹木、水源丰富、喜食谷物而非水果肉类或乳制品,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饮食中注重烹煮的基本条件,缺乏这样条件的地区也较难接受筷子,因为无此必要。
欧洲的饮食传统偏重肉类及乳制品,肉可以大块烤,但在烹饪时,筷子无法处理这么厚重的食材,必须用刀割(所谓“割烹”)。可能也正因如此,东亚的料理往往致力于极细微的味道,因为筷子更适于处理小块而非大块的食材。附带一说,由于烹煮时大量用水,中国人讲究喝汤,西餐虽然有炖菜,但汤往往是浓汤——英语里的“soup”(汤),从词源上看,最初的本义是“肉汁”,但汉语的“汤”,本义却是“大水”或“热水”——浓汤不利于搅拌混合,清汤就不一样了。
目前所知最早的筷子是春秋晚期的铜筷,但其出土地点在当时文化并不发达的皖南贵池,按常理推断,中原应该早有筷子,只是竹木筷易于腐烂而难以久存。根据战国末年韩非子的记载,在商朝末期纣王已开始使用“象箸”;学者宫崎正胜认为,筷子的起源是为了“怕弄脏献给神明的祭品”,而长筷可以“用来夹取祭品”。这固然也可备一说,但根据现在一些学者的推测,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可能已在使用小的棍儿、细枝和骨头作为“梜”,把事先加热好的石头丢进烹煮器里煮水,筷子的最初名称“箸”“筯”“櫡”也与“煮”同源,也就是说,最早的筷子极有可能是烹饪器具,而不是进食时的餐具。
但烹饪与进食毕竟是两件不同的事。筷子在进食时的最初功能可能是为了夹菜,所谓“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礼记?曲礼上》)可以想见,一般没什么菜肴的庶民,吃东西也是用不到筷子的——事实上,先秦时平民的主食是“粟稷”——一种煮熟后成糊状的羹,这是极不便于用筷子来吃的(《礼记》中说“饭黍毋以箸”),而要用手或“匕”(即匙或勺)。
即使是有粘性的白米,用筷子取食也颇不容易——稻米在商代是贵族食物,到秦汉时虽渐渐普及,但多是无粘性的籼米,筷子很难夹,还是得用匙吃。《三国志》记载,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当时还寄人篱下的刘备正在吃饭,闻之一惊,“失匕箸”。唐代似已兼用匙筷来吃饭羹,盛唐时薛令之有诗:“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自悼》)不过,直至宋代,吃主食时仍普遍用羹匙,宋人朱弁在《曲洧旧闻》中云:“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到了明朝,筷子开始成为餐食的日常用具,英国汉学家魏根深推测:“这可能是因为,统治精英来自南方,习惯了吃粳米饭,而米饭粒比较黏,很容易用筷子夹。今天北方吃的仍然是不黏的籼稻米饭,人们把饭贴到嘴边用筷子把饭扒拉到嘴里。”
事实上,受中国影响颇深的朝鲜,在这点上一直谨守中国传统。中国古礼是以箸夹菜,以匙吃饭,自新罗时代筷子传入朝鲜半岛后,韩国的用餐礼节至今如此。直至清代,朝鲜学者洪大容出使清廷,还和人探讨“为何中国吃饭用筷,朝鲜用勺”的问题。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也是箸匙齐用,《枕草子》中有“听见筷子和匙子混杂作响”的句子,可见他们不仅使用这两种源出中国的餐具,而且贵族们用的是金属制的高档物品。
筷子之所以能取代“匙匕”在中国社会扎根,原因之一可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無论是刀叉还是匙匕,“就只能各自分食,不可能像中餐一样会食了”,而筷子却由于可以众人在一盘菜中取食,“故亦可发展合桌会食的型态”。
在筷子尚未普及的汉代之前,中国人的饮食方式是分食制。据《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与食客们一起吃晚饭,因为光线不好,一位食客误以为他吃得比自己好,因而发怒;孟尝君拿着自己的饭食给他看,表明一律均等,此人惭愧之下,自刎谢罪。这在同桌合食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据《陈书》记载,徐孝克在任国子监祭酒时,陈高宗经常宴请群臣,但在宴席上徐几乎不吃东西,到席散,在他面前的食品却少了。高宗私下询问中书舍人管斌,管斌回答不了,便留意观察此事。结果发现徐孝克拿珍果塞在宽腰带内,管斌当时不解他的用意,后来查访,才知是拿回去送给母亲——这显然也是分食制时代的情形。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由分食制改为同桌合食,是与唐末五代高脚桌椅家具的兴起有关。毫无疑问,筷子恰好能适应这种家族团聚、大桌同食的社会变迁,同时也推动了友善和睦的社会日常生活。不过,日本在近代之前既未接受高脚家具,也未采纳分食制,却仍然用筷子彻底取代了匙匕,可能还是因为只用一件餐具对人们而言更方便。
东方的筷子多以竹木而非金属制成,这一点本身也耐人寻味。中国古代有银筷、铜筷,但那都是极少数人所用,而不像西方的刀叉餐具普遍为金属制造。首要原因可能还在于筷子原为烹饪工具,而中国菜最初又以蒸煮为主,要在烹饪过程中不断加以搅拌、调和,竹木筷的导热性不像金属刀叉那样强,不至于烫手。此外,中国传统生活智慧向来强调“物尽其用”,注重尽量利用有限的材料,美国学者苏珊·韩利注意到,东亚人特别节俭而能巧妙利用资源,因而不仅设计倾向简洁——如做的茶杯一般不带把手,而且省材料,“筷子造起来很容易,也不需要用到贵重的材料”。
可以说,筷子包含了一种聚合式的功能设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的产物:刀叉明显注重特定的功能,是分析性的;筷子却是综合性、多功能的——除了夹菜扒饭,还可以当做夹子、搅动器、搅拌器、粗滤器、重排器等来使用,也就是说,它既是餐具,也是厨具。而这样一种承担诸多功能的工具,使用轻便,却又具有如此简洁的形式,无怪乎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曾赞叹:“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发明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高妙绝伦地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都能做,且不怕高热,不怕寒冻,真是高明极了。”作为一种餐具兼厨具,它意味着发明者在思维上不注重去研发各种细分功能的工具,而是强调用一种通用、简易的万能工具来应对所有问题,因而对使用者的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种类而言,抛开材质差异不谈,筷子的功能分化并不大,进食时所使用的筷子通常就是一般的筷子以及为客人分菜用的公筷。作为厨房烹饪用具的筷子,基本上围绕着它的核心样式来分类,如捞面用的长筷、日本人为适应本国烹调海鲜而发明的真鱼筷及烹调植物性食材的菜筷,现在又有了孩子使用的练习筷等,实不像西式厨具有那么门类众多的功能分化,形式差异也颇为细微。不过,筷子仍有相当灵活的适应性:在中国由于偏好从大盘里分菜,故筷子多较长而两头同样粗细,但日本料理由于多鱼贝类,筷子的前端就通常较为尖利,以便用筷子来切断、剔骨。
与西式餐具不同,筷子极为廉价易得。在17世纪,餐叉仍是西方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多以金银制成,平民家中极少能拥有:在法国的阿尔萨斯地区,直至18世纪,宫廷内外使用四齿餐叉的人才多了起来,同时仅有1/10的家庭才拥有一把餐叉。餐刀一般被认为是客人们带来的,系在腰带上,至于汤匙,最初只是用以舀汤的贝壳,后来为避免弄湿手指才加了木柄。无论是餐叉还是16世纪以后逐渐普及的台布、餐巾、玻璃瓶,在欧洲,这些餐桌上的器具大多与财产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最普通的是木制的、陶土或上釉陶土的,有钱人用陶器、锡器、铜器甚至于金银器。自18世纪初叶起,英语中开始出现用“含着银匙出生”来比喻生在富贵人家,便是当时这种社会形态的写照。
而在中国,帝王贵族使用象箸玉杯一向被视为是值得谴责之事,社会上层与底层人民可能使用同样材质的竹木筷,因而筷子并未像餐叉那样成为区别社会阶层和财富的标志。在《红楼梦》第四十回,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时,王熙凤等为取笑她,“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她,结果刘姥姥使不惯,说:“这叉爬子比俺那里铁锨还沉,哪里犟的过他。”最后换了一副和别人一样的“乌木三镶银箸”,刘姥姥仍感“到底不及俺们那个伏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刘姥姥并没有像16世纪那些从未见过餐叉的法国人那样有文化自卑感,仅仅是觉得这些富贵人家使用的筷子沉甸甸的不好用罢了。因为筷子可以用低廉易得的材料制作,確保大家都用得起也好用;而西方的刀叉,则必须是金属的,木头制的没法用,因而在金属和制作工艺大工业化之前,成为明显的阶层象征。

中国早在秦汉帝国成形后,就在“编户齐民”的制度下形成了相对齐等的平民化社会结构,以至于帝王贵族也要适应这种社会变化,先秦那种所谓“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需要大量青铜器,它们都是坚固的耐用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早期西方的金属刀叉也是如此)。但在秦汉之后,昂贵的青铜食器几乎消失,越来越普及的是价廉物美、干净、质轻、历久弥新又不会生锈的瓷器。尤其在汉代,朝廷一直强调以节省为礼,限制奢靡傲慢,加上筷子取材简易,门槛低,因而对中国人来说,“文明”不像西方那样是一种上层礼仪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过程,而更多是一种普遍的教养。筷子也是应对这种普遍的文明生活需求的最佳物品——价格低廉、人人都用得起、功能用途广泛,又能满足基本生活。
可以说,一双筷子,折射出的正是中国文明和历史发展的侧面。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