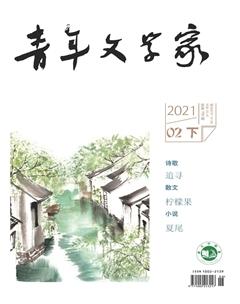从精神分析角度看新感觉派的暴力书写
2021-04-28张榆甜
摘 要:“暴力”是人类文学史上历久弥新的母题,而“暴力”也是新感觉派小说中呈现的一个重要特质,本文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作为探究新感觉派小说中的“暴力书写”的切入点,从压抑的力比多、潜意识及白日梦两个层面解读新感觉派小说“暴力书写”的特色与意义,揭示其体现的人性关怀。
关键词:新感觉派;暴力;精神分析
作者简介:张榆甜(1997.11-),女,汉族,四川省南充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文艺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6-0-02
当代人本主义文论认为,人类的精神文化世界丰富而复杂,远远超过传统的科学理性所能认识的范畴,“在人类精神活动中,还存在一个远大于科学理性范围的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心灵活动领域”[1],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构建了精神分析学说,以探析人类的情感与欲望。弗洛伊德将人类心灵分为三个层面,即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并提出了三重人格结构理论,他认为,完整的人格结构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构成,其分别对应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晚年时期,弗洛伊德认为“本我”中存在两种状态,即“生本能”和“死本能”,“生存本能”可以理解为性本能即力比多(Libido),它追求自我满足,罔顾社会与他人;“死亡本能”是一种回归无机状态的倾向,通常表现为破坏和毁灭的冲动。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暴力,就是审视人类的原始强力及欲望突破本我的“现实原则”,释放死亡本能的摧毁冲动的过程。
作为20世纪我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影响颇深,自觉在文学创作中发掘人的意识,并且从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对暴力进行再认识。从精神分析角度看新感觉派的暴力书写,将研究视域超脱于语言符号,从精神和暴力着眼,找到了文本中“人”的位置,并进而对“人”作为主体的精神境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1、压抑的力比多
施蛰存的小说《石秀》是对水浒故事的解构,作者试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回答了《水浒传》没有回答的问题——石秀为什么非杀潘巧云不可,从精神层面探讨了暴力发生的动因。
石秀跟杨雄结识后,对杨雄的妻子产生了爱慕与欲念,他虽为这种想法感到羞愧,但欲望却不可遏制。在之后的相处中,石秀只能被动地注视着潘巧云的勾引,他对潘巧云有着疯狂的迷恋,却又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兄弟杨雄,在性本能的冲动与道德的规束中进退不得,“超我”压抑着“本我”的欲望,使石秀在不得排遣的情欲涌流中痛苦万分。他的“力比多”无法通过正常的性行为得到宣泄。弗洛伊德認为,“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神经病。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2]随着潘巧云的陷害,石秀的压抑终于到达临界点,他设计使潘巧云被杨雄虐杀。文末对虐杀潘巧云的暴力场景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刻画,在施蛰存笔下,石秀已不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性欲被压抑的变态施虐狂,整个人物内部充满了阴暗与猥亵心理。石秀作为虐杀的策划人,目光一直陶醉地放置在这场凶案之上,他“多情地看着”,觉得“每剜一刀,便是一阵爽快”,当潘巧云被开膛破肚乃至肢解,“石秀重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对潘巧云的占有欲,通过旁观她的死亡而达成,因为在欣赏潘巧云被虐杀的场景时,石秀的性本能终于以这种变态的形式得到了宣泄,而石秀自己的死亡本能也在摧毁他人肉身的奇异快感中得到满足。最后,施蛰存意犹未尽地写乌鸦啄食潘巧云的内脏,石秀看着,心中不禁想道:“这一定是很美味的呢。”更是深化了这种令人战栗的满足。
与施蛰存对暴力令人心惊的刻画相比,刘呐鸥在小说《杀人未遂》中的身体暴力书写则要温和得多。小说中,“我”的朋友“罗君”被公司的女职员所吸引,作者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空间内只有罗君和“那位女性”,以此更清晰地展现罗君的知觉和欲望。罗君对女职员的性欲是茂盛的,而女职员却永远只是一副“机械般无情热”的态度,罗君追求“女职员”,认为她是“恐怖的白日梦”,“无意识”和“本能”是在对待这白日梦时驱使他的全部动力。而面对女职员的拒绝,“白日梦”濒临崩溃,撕裂了罗君压抑的力比多的闸门,恶的洪流便倾涌而出,罗君终于“双手绑住她雪白的喉咙,用力绞……”对女职员施暴,但终未遂,在警铃响起时,他仍出神地欣赏着女子被凌虐的身体。小说最后,“我”去探望罗君,“他似不觉得他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并且“极度兴奋”,这是因为罗君的性欲已然通过向性欲对象施暴的形式得到满足,“兴奋”就是这种变态的满足的确证。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提出了“无意识”、“非理性”与“意识”和“理性”的对立。虽然其“泛性论”的观点受到不少非议,但弗洛伊德理论仍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早在古希腊,人就被认为是理性的生物,而弗洛伊德却试图说明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动物,受“无意识”的驱使,对人类自尊进行了第三次打击,[3]将人类从自设的神坛拉下,重新审视自己。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在人类“理性”的表象之下,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非理性”冲动,原始的暴力和厮杀本能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典型表现。而新感觉派小说的暴力书写,以敏感的笔触切入人类精神的症体,揭开了传统人本主义语境下人类“理性”的面纱,展现出人类意识深处的“非理性”,从而还原了一个更加立体、真实的“人”。
2、潜意识与白日梦
新感觉派的作家敏锐地察觉到了现代都市机械文明的发展给人类生存境况带来的显著改变,他们怀着“一种对于现代都市的复杂审美感情”[4],一方面崇尚着快节奏的都市文明,如穆时英在小说《上海狐步舞》中运用同样快节奏的蒙太奇手法表现了出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同行姿态,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这种机械的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不吝表达个体在都市生活中遭遇的精神困境。自我意识与社会的凝视、挤压,将个体完全置于充斥着精神暴力的空间之下,个体的孤独、焦虑甚至病态被放大呈现在作家的书写中。
施蛰存的小说《春阳》通过写一位妇女的无意识行为、白日梦幻想,反映了妇女潜意识里根本的孤独与欲望。十多年前,婵阿姨的未婚夫突然病死,作为一个健康美丽的女子,婵阿姨没有选择另嫁他人,毅然抱着牌位成了亲——为了独占夫家三千亩地的财产。但这样的选择带给婵阿姨的并不是坐拥巨额财富的快乐:族中人虎视眈眈等着瓜分她的财产,虽然她潜意识里渴望开始新的婚姻生活,可是看着自己枯萎的容颜,就想起族人讥讽的笑,她便失掉了这勇气。此为婵阿姨面临的第一个精神困境,即潜意识的渴望被压抑。这样的压抑并非婵阿姨自发的形成,而是受到外界规训后产生,族人的眼光其实代表着恪守落后封建家族制度的每一个普通人的眼光,这眼光限制着婵阿姨的自由、打击着她的意志,使她成为了被禁锢在家族中的僵尸。小说中写到,婵阿姨在一个春日里来到上海,在春阳和煦的背景下,她心里某些渴望也蠢蠢欲动,在看到来来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么年轻,那么美丽,有那么小玲玲的”,她感到自己穿得“累坠”,便在无意识之中就“把那绒线围巾除下来”,这里反映了婵阿姨渴望融入年轻的男女,同他们共享春光的隐秘心理。可是,作为昆山的妇女,她与这工业文明下的上海城里的人毕竟格格不入,上海的春天分不到她的身上。她产生了一系列白日梦臆想,看着旁边美满的一家人,她“沉醉地耽视着”,想象着“假如我来抚养”别人家的孩子,传菜的侍者很快打断她的梦幻,她又难堪、又感到害怕,便陷入第二重精神困境。然后,“一只文雅的手”将她暂时带离这种精神困境,她兴致勃勃地开始幻想与这名男子展开交往,她走在街上,便“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这种欲望支配着她,但就在她试图与银行行员示好时,白日梦却被扼杀在行员一句冷漠的“太太”里,而这行员很快却管另一名华服的女子叫做“密司”,婵阿姨彻底幻灭了,匆匆离开。这就是婵阿姨所受到的第三重精神暴力,来自于自身的身份认知——即被上海年轻男女所轻视、排斥的“昆山的太太”。文本对婵阿姨的叙述集中于她的精神与意识的流动,把婵阿姨受到的几次精神暴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族中,她是受讥讽的寡妇,到城里,她是无法融入的“太太”,她既不能在一个老旧的封建家庭里获得满足,也不能在外部更广阔的都市世界里有容身之处,这是一个处处龃龉的女子,她的情欲、孤独、焦虑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病态使她不断碰壁、经历着来自外部世界对她精神的摧毁,而又是这种摧毁,更增加了她的情欲之火、孤独和焦虑,反映出现实世界无法调和的矛盾。
除《春阳》外,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用欢场切片点染出颓靡的表象之下,虚弱失意的灵魂们成为无意识驱动下空洞的肉体符号,作为无理性的一份子,被世界的无理性无情抛掷在都市的精神荒原上;《上海狐步舞》里呈现的林肯路上的枪杀、豪华别墅里的淫乱、建筑工地上的惨剧……小说人物也都被抛弃在无德无爱的、反理性的世界上,他们只遵循“快乐原则”,世界在此分裂出二元对立的性质:快乐虚幻的白日梦世界与冷漠封闭的现实世界,主体无论选择哪个世界都逃脱不了精神世界被暴力摧伤的命运。
通过展现现代工业文明侵蚀下个人精神所受到暴力的压抑或打击,新感觉派的小说强烈地撞击了封建社会禁欲主义的牢笼,将传统的理性驱逐出文本世界。通过描绘个体生命的暴力体验,表现出个体精神秩序的失落和崩溃、消解了人性的崇高、叩问了现代机械社会对个体生命的挤压,深入地揭示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形态由撕裂走向整合与重建时个体所遭受的深层创伤,新感觉派小说家正是以一种极端的书写方式完成了小说叙事人道主义的关怀使命。
注释: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高觉敷译,商務印书馆1984年版,第246页。
[3]一般认为,如果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人类自尊的第一次打击,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是对人类自尊的第二次打击,那么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学说就是对人类自尊的第三次打击。
[4]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1]黎保荣:《暴力与启蒙》[D].暨南大学,2009.
[2]杨程.《论新感觉派的身体审美》[D].华中师范大学,2015.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