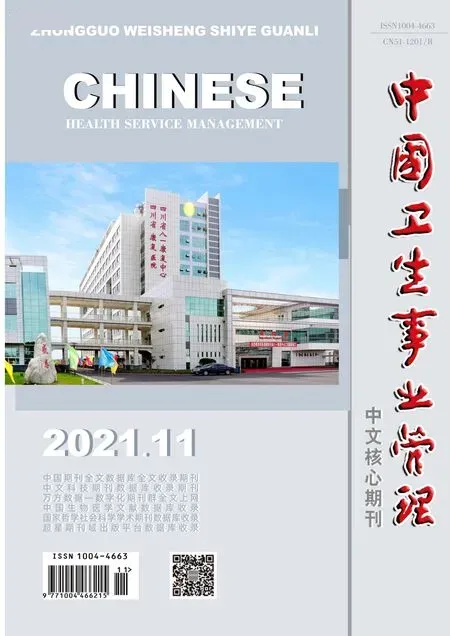基于医史文献视角研究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的价值与实践*
2021-04-18刘辰昊刘毅
刘辰昊,刘毅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7)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现在已波及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世界70多亿人口,对全球经济、社会、人类健康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中医药防治疫病历史悠久,在未来中国特色传染病应对体制中要强化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1]。在积极探索中医药治疗成效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中医药应对体系的一些问题和短板。以史为鉴,可以明事理,可以创未来,从医史文献视角梳理先秦至近现代不同历史朝代的疫病发生情况,阐释中医药防治疫病的发展脉络,旨在加快创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医药应对体系,确保中医药“利剑”在手,全面提升中医药疫病防控能力和水平,彰显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的重要价值与生动实践[2]。
1 疫病的概念、分类
中国疫病流行与防治斗争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步,从甲骨文最早的疫病(传染病)记载 “疒役(疫)”到五疫、伤寒、戾气、温病、温疫、瘟疫,从天花、鼠疫、霍乱到SARS、禽流感、“甲流”,再到现今“新冠肺炎”的发病与流行,有关疫病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日渐丰富。
《说文解字》曰“疫,民皆疾也。”《时病论》曰“盖疫者役也…大概众人之病相似者,皆可以疫名之。”可见古代疫病主要是指众多人同时患病。在古代,疫病的含义除了传染病,还可能包含一些季节多发病、地方病、营养缺乏病等[3]。《肘后备急方》:“伤寒、时气、温疫三名同一种耳。”早在《黄帝内经》时期,就已经提出“五疫”的概念。如《素问·刺法论》[4]: “帝曰: 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本病论》运用五行运气将五疫分为“木疫”“火疫”“土疫”“金疫”“水疫”,分别代表致病邪气的性质特征,这也是最早的疫病分类[5]。医家论及五疫者多为温疫,其中吴鞠通对五疫有较为客观而准确的解释,《温病条辨》: “盖风火暑三者为阳邪,与秽浊异气相参,则为温疠,湿燥寒三者为阴邪,与秽浊异气相参,则为寒疠”[6]。从五疫分类法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疫疠的认识仍是源于五邪的基础理论,即疫是自然界的邪气,但致病较甚,呈一定程度的暴发流行,不同疫病有不同的规律特征,这与其后医家认为疫非风、非寒、非暑、非燥,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疠气的认知明显不同[5]。疫病概念中谈论最多的是“温疫”,顾名思义是感受温邪而导致的疫病。最初的“温”与“瘟”是混用,渐渐“瘟”与“疫”同,用“瘟疫”作总称,指代所有疫病。温疫可以理解为温病与瘟疫的交集。《伤寒杂病论》是第一部系统论治疫病的专著,后世医家不断实践《伤寒论》,在明清时期形成了温病理论与方法[7]。至元明清温病盛行时,瘟疫也较多,很多医家亦将“温”,“瘟”相混,范行准认为,“瘟”字原作“温”[8],清代医家刘奎认为二字在概念上有着明确区分,将疫分“湿疫”“寒疫”“杂疫”三类。由此可知,疫有几种基本的分类,从最早的五行五疫分类法演化为运气病因分类的风疫、寒疫、燥疫、湿疫、温疫,从疫的流行程度分大疫、小疫,从致病轻重分时疫、疫毒,从邪气上看可以有邪-疫-疫毒关联性与可转化性[5]。
综上,中医认为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具有传染性的一类疾病,瘟疫的病因是疫毒,与“非时暴寒“”非节之气”密切相关,是受到“时行乖戾之气”,也就是带有致病因素不正常的邪气。这与现代医学认识的疫病,即发生在人、动物或植物身上,一般由寄生虫、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引起,并具有可传染性的疾病的统称的认识有所不同。
2 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一脉相承
中国有悠久的防治疫病史,史料记载疫病在不同朝代发生的次数是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4次,清朝115次,我们的防疫思想源于古、用于今,防疫文化、理论与实践一脉相承[7]。
2.1 先秦时期的防疫
殷商甲骨文有关疫病的记载如 “甲子卜,殻贞:疒役(疫),不延?” (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乙编》),是我国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之一,卜问疫病是否蔓延、卜问疫病是否有治及如何治,如呼令举办袐祭禳祝治疫病、用大枣作为药物治疗疟病。郭沫若《甲骨文合集》记载“疾,亡入”。《诗经·豳风》中“洒埽穹窒”“穹窒熏鼠”对预防疫病流行有积极意义。《周礼·天官冢宰》分食医、疾医、兽医和疡医,其中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商周时期已对流行性、传染性疾病已有描述记载,阐释了流行病与季节的关系,并出现治疗方法的记载,如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
春秋战国时期对疫病记载多见于《左传》《论语》《庄子》等,该时期的医药卫生知识有很大进步,其标志就是集医学最高智慧的经典医著《黄帝内经》基本成书,包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观即重视内因,强调正气足是防疫的关键因素,也重视外因避其毒气,“上工治未病”的预防观,运气学说对流行病的推算与预防,对痢疾、霍乱、疟的认识有助于指导后世疫病的防治[3]。
2.2 秦汉三国时期的防疫
有关“疫”或“大疫”的记载多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伤寒论》《三国志》等史书和医书。秦汉时期设置了医官制度,政府在传染病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如设置“疠迁所”是对麻风病患者的强制收容场所,在汉代首次设置专门收容机构,如《汉书》“诸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是防疫史上很重要的记载。
对于疫病,政府和民间均采取了一定的举措,如皇帝下罪己诏修政、节俭费用、祁禳驱疫、疫灾救济、佩戴香囊、焚烧香药、饮椒柏酒、屠苏酒等,政府和官员对百姓给予一定的医药和物资方面的救济,如设立收容病坊、发放救济款、安置贫民、改善生活[9][10]。中医药防治疫病在该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存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部分内容涉及到传染病,如“痎”指疟疾,也开出了方药。《伤寒杂病论》著作产生与瘟疫有着密切关系,创立了六经辨证体系,开创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体系是后世医家的基本思维法则,广泛应用于伤寒、杂病、疫病的防治实践[3]。
2.3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防疫
据记载该时期疫病发生达40多次,疫情出现频率与社会治乱密切相关。继承前朝疫病防控措施,官府最早创办医学教育。中医药防疫有很大的进步,其标志就是《肘后备急方》,葛洪对疫病病因提出了“戾气”致病观点,提出“以毒攻毒”如以狂犬脑组织敷贴伤口预防狂犬病发作的免疫学思想,认为传染病是可防可治的,并提出了一系列防治方药如“治伤寒时气温病方” “瘴气疫疠温毒方” “辟天行疫疠方”等,用药途径有内服、外敷、鼻吸、佩戴、熏烧、悬挂等,对复方防疫的贡献甚大。我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受到《肘后备急方》的灵感启发,从青蒿中提取出了青蒿素,为疟疾这一疫病防治作出了卓越贡献,彰显了中医药原创性重大突破[3]。
2.4 隋唐五代时期的防疫
该时期疫病发生20余次。隋唐医事制度更为完善,中医药对疫病防治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明确提出“乖戾之气”学说,认为传染性疾病都是由“乖戾之气”引起,时令不正之气候导致“病无长少,率相似者”的时气病(疫病),具体论述了不同季节气候反常所致的不同疫病、9种寄生虫的形态与传染途径、体质与染病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养生预防思想,提及的导引法、与防疫有关的饮食卫生等有价值的防疫原则对疫病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千金方》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都有独到见解,认为疫病是天地自然存在的客观现象,对疫病既可摄生以防之,也可 “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患病之后还可 “汤食竞进”来救疗;对于疫病的防治,孙思邈强调早期治疗,可内服屠苏酒、辟温方,外涂雄黄散,粉身散,针灸治疗,熏烧太乙流金散,重视养生思想如食疗养生、导引养生、房室养生以及各种生活卫生与心理卫生等[3]。
2.5 宋金元时期的防疫
这一时期发生的疫情共有90余次,朝廷的医政制度出现了飞跃,设置不同职能的医政机构,兴办医学教育,创办官营药局,多次征集和编撰医方、本草。此时期政界、医药学界名家名师名医辈出,如陈无择、苏轼、韩祗和、庞安时、朱肱、许叔微、王履以及金元四大家及其弟子等,促使疫病防治理论与实践取得新进展[3]。
2.6 明朝时期的防疫
明朝时期发生疫情共34次,部分疫情很严重,如永乐六年江西、福建疫情死亡者超7.84万人,福建建宁、邵武、延平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发大疫,死亡达17.46万人;《温疫论》对疫病有更深入的认识,是中医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突破,明确指出“温疫”不等于“瘟疫”,伤寒、温病与温疫是有区别的;提出温疫病因之“杂气论”,认为温疫是由一种具体的病邪物质所致;提出“邪伏膜原”的病机理论与透达膜原的治法,如三消汤、达原饮等方剂;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辨析各种杂气之来源和差异,事实上,吴又可已经接触到了微生物学的边缘,比“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早200年,部分认识甚至接近“病原细菌学奠基人”科赫的水平,他认为每种杂气必有相对应的特效杀灭药,如果当时有条件进行微观研究,则中医防治疫病的方法将更为前沿和全面[3]。
2.7 清朝时期的防疫
据史书与方志记载,这一时期发生的疫情多达115次,尤其天花、真性霍乱流行,实际上,1820年正处于第一次世界霍乱大流行时期,据研究,霍乱从东南海路传入中国迅速蔓延,形成全国流行,伍连德整理真性霍乱流行情况(由印度、缅甸、泰国传入中国,随后又蔓延至俄国),这也是全球疫情的一次较为详尽的记载。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对温病学派形成作出重要贡献,一方面明确了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另一方面确立了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此外还有清代医家在疫病诊治方面有新认识,如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戴天章《广瘟疫论》、刘奎《松峰说疫》、杨璿《伤寒温疫条辨》、余霖《疫疹一得》等。对传染病专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理论与临床防治研究,如真性霍乱(吊脚痧)、烂喉痧、白喉、瘴气、疟疾、麻风、梅毒、肺痨、麻疹、水痘、大头瘟、虾蟆瘟、羊毛瘟、天花等,尤其是天花防治方面,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一项重大突破。
清末时期霍乱、天花和鼠疫三种烈性传染病在晚清时期都曾严重流行,在防治方面,西医尚无好办法,中医积极投身防疫发挥积极作用,如采用升麻鳖甲汤等;鼠疫流行促成了鼠疫杆菌的被发现,如北里柴三郎与耶尔森采用科技手段发现了鼠疫杆菌。清政府于1911年4月在沈阳隆重召开了“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是近代医学史上由中国政府主办的首次国际疫病学术会议,此次防疫国际会议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3]。
2.8 民国时期的防疫
民国时期各个城市有主管防疫事务的卫生行政机构, 1916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传染病防治法规《传染病预防条例》,同时也重视生物制品的研制与生产,民国时期的卫生行政虽然以西医为主体、逐步推行西医防疫之法,但中医仍在疫病防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中医研究的特点是参用西医理论明确诊断,治法上则继续发挥中医辨证论治之所长。中医兴起了学校教育,中医学校大都兼授部分西医课程,西医以病原体为依据所建立的传染病学体系对中医有较大补充[3]。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对卫生防疫工作十分重视,如1932年通过了《卫生决议案》体现了以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是一篇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1948年陕甘宁边区的疫病流行,边区政府积极配合组织当地民间中医下乡防疫治病,迅速配制有效的单方,无偿发给患病群众,取得了切实成果[3]。
2.9 新中国成立后的防疫
1949年10月在察哈尔省发生的鼠疫,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新中国防疫第一战,确立了“卫生以预防为主,预防以防疫为主”的工作方针。经过1949-1952年的努力,各种烈性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设立中医司、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进大医院、改善中医进修工作、整理出版中医古籍等一系列发展中医的措施,中医治疫显示实力。195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乙型脑炎流行,中医的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有记载称1954年的34例、1955年的20例乙脑病人,中医药的治愈率分别为100%和90%。随后,卫生部派遣由中西医共同组成的调查组进入石家庄市调查中医治疗乙脑的情况,调查报告肯定了中医的卓越疗效,称其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无出其右。1956年7月-8月初,北京也发现了少数流行乙型脑炎,刚开始采用石家庄的中医治疗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进入8月以后,效果却不理想。这时,以蒲辅周为主要成员的专家组指出不同的气候环境会产生不同的发病因素,不同的禀赋体质也会有不同的症状感受,故不能只在验方和效方上着眼。在运用中医的辩证论治思维更改治疗方法后,北京乙脑的中医治疗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3]。同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筹备成立了中医学院,中医有了正规的高等教育,新中国的中医工作才基本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3]。随后中央和地方都十分重视血吸虫病、流脑、疟疾等疫病的防治,尤其是青蒿素的研究成功是抗疟药研究史上继喹啉类药物之后又一突破。1968年“赤脚医生”这一名称正式出现,其来源是贫下中农的子女,对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改善卫生环境、预防疾病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北省长阳县首先创办合作医疗,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开辟了药园,种植常用药物,减少了村民吃药的费用开支。
2.9.1 SARS与中医药防治
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8月,中国内地共有24个省(区、市)先后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累计报告非典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治愈率93%; WHO专家组通过考察认为广东防治疫病工作卓有成效,对SARS治疗的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中西医结合治疗很有特色[3]。广州中医按照中医理论,将SARS全过程分为早期、中期、极期(高峰期)、恢复期,分别拟定治疗方案,前期注重清热化湿,后期注重益气养阴扶助正气,总结中医辨证分为9个证型,行之有效的基本处方10个,这套方案被纳入卫生部公布的《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试行)》当中以指导SARS疫情的防治工作,肯定了中医药在SARS防治当中发挥的作用。广东省中医院总结时认为,用中医药早期干预治疗可以有效阻断病程发展,明显减轻症状,缩短发热时间和住院时间,促进炎症吸收,减少后遗症、并发症及西药的毒副作用[3]。吴仪副总理强调中医是抗击SARS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中西医结合共同防治SARS[3]。WHO代表马克索尔特肯定了中医药用于治疗疾病的功效,并认为今后中医药一定能更广泛地被用于治疗疾病[3]。WHO公布各地SARS的死亡率,中国大陆6.6%,香港17.1%,台湾27.1%,广州5.1%,其中广州死亡率为全球最低,原因为广州中医第一时间介入SARS防治。根据标准化死亡比显示,中医药治疗对降低SARS的死亡率发挥了作用[3]。
2.9.2 COVID-19与中医药防治
对于COVID-19疫情防控,除了不聚会、少外出、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措施外,中医药在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表示: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中医药能够有效缓解新冠肺炎症状,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11]。张伯礼表示,中医药早介入、早使用,能有效阻断轻症转为重症,促进病人康复[12]。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是有效的,中医药在防治新发传染病方面是有优势的。中医药在抗击SARS、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战中,充分发挥了这个“伟大宝库”的不可替代作用,从而让世人重新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
3 中医药在疫病防控能力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3.1 中医药临床证据和中医药疗效的科学评价体系不足
中医药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本次新冠疫情当中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疗效,但鉴于文化的差异性,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未得到国际医学工作者的广泛接受和认同。中医药的传统研究形式主要通过人体试验和反复的直接观察、经验总结,但由于其疗效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不统一,而由此归纳、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难免有片面性、局限性。故完善传统中医药疗效的科学评价体系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关键,也可为进一步提升中医药在疫病防控中的能力和地位打下基础[13]。
3.2 中医药第一时间防治疫病的机制亟待完善
中医药尚未完全融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中西医并重、共同防治的体制机制仍未有效形成。各级医疗单位中,尚未建立自上而下的中西医防治传染病诊疗体系,中医参与度不够,相关应急处理体系和行动机制尚未充分建立。缺乏稳定应对突发疫情的中医药专家库及团队,尚未完全建立与现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相对接的中医药分级应急响应机制[14]。
3.3 优势资源整合不足,信息化体系建设不够
在中医防治疫病方面,虽然历史上有著名的温病大家如吴鞠通、吴又可、叶天士、薛雪等,也有《瘟疫论》《温病条辨》《温热论》《湿热条辨》等中医经典著作。但在应对突发疫病时,还未充分发挥现有中医药资源优势以及国医大师、名老中医带头作用,未能及时制定有效的中医药疫病防治诊疗方案并进行早期干预[14]。中医药健康大数据建设和“互联网 +”发展进程相对缓慢,尚未构建覆盖基层社区的中医药疫病防治临床救治信息化体系,优质中医药资源无法完全覆盖到基层社区。未能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对现有医疗健康数据进行有效挖掘,并对潜在疫情进行提前预警[2]。
3.4 中医药防治疫病基础保障体系建设亟待加快
截至 2019 年底,中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 65809 个,中医类医院数 5232 个,分别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全国医院数6.53%、15.23%,与西医类别相比,差距甚大[15]。现有中医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多数中医院未建立重症医学科、传染病科,未设置隔离病区病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应对能力略显不足。目前中医药行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不均衡,在中医理论、疾病机理等中医重点研究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还需提升,仍未建立中医疫病防治国家级科研支撑平台[14]。
3.5 中医药疫病防治人才培养不足
截至 2019 年底,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 62.5 万人,分别占全国执业(助理)医师数的16.16%,与西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量相差甚大[15]。中医药人才在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当中的人数相对西医更少,导致了在疫病防治过程中,中医药治疗方案的覆盖面相对不足。各大医院的防治措施仍然以西医为主,中医药的接受度和使用频率尚显不足。且当前的西医临床医师和公共卫生执业医师接受的中医培训教育不足,运用中医药防治疫病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够。
4 全面提升中医药疫病防治能力和水平的思考与建议
4.1 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
在针对短板、弱项时,将各项政策措施落细落实:强化中医药管理体系建设;强化中医药古籍的抢救性、再生性保护和系统规范整理;强化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中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临床研究基地、国家中医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深化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建设;加快构建完善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中药特色审评审批体系,如国家药监局通过特别审批程序应急批准清肺排毒颗粒、化湿败毒颗粒、宣肺败毒颗粒上市。建立完善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生产、仓储流通、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健全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规划建设一批国家中医应急救援和传染病防治基地,统筹建设一批中医传染病医疗中心[13];加强疫病防治人才培养和储备,推进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设立中医疫病防治人才培养专项和中医药疫病防治人才库[15]。
4.2 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加强中医疫病防治的体制和能力建设,在充分认识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丰厚历史积淀和亮点基础上,长远布局我国疫情防控战略:一是要强化政策保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西医并重的突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科学、完整、中西医并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和规章制度;二是要加强中医临床诊疗技术创新,加快开发中医药临床诊疗技术装备,实现中医药标准化、规模化供给,进一步提高中医药重大疫情救治能力;三是要重视抗疫临床实践中中医药理论方面的总结,加强中医药抗疫人才队伍建设和防治能力建设。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应是人类防治疫病以及许多疾病的最佳方案[16]。
4.3 提升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能力
提升国家、省、市、县各级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网络,建立由国家和地方应急管理部门统一指挥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将中医药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程参与到系统的各个子环节[17]。在国家层面建立中西医协同响应和干预平台。在应急指挥系统中,需有中医药背景的专家人员参与决策指挥,在制订突发卫生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将中医医疗机构与西医医疗机构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明晰在应急处置过程中,中西医需要全程同步参与[17]。充分发挥中医医院及中医药高等院校的中医优势,加强其和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协调,交流,联动[18]。
4.4 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提升中医药参与疫病防治认可度
中医药文化传承上千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19]。但在中国当前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中,西医药仍占据主导地位,这源于对公众开展的中医药普及教育不够。当前社会大众对疾病医疗的认识大多建立在西医的认知上,而对中医药防治疾病和其健康保健知识认知不够。这也降低了社会公众、政府部门对中医药参与疫病防治的认可度[18]。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使用率达到 90%以上[15]。
中医药今天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传承不足、创新乏力等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自立、自信、自强,进一步科学、客观地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的规律,探究其内在科学内涵,持续优化防治方案,让中医药能够更好地造福人类,惠及苍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疗效是检验医学医术的根本标准,应该拿这一把尺子去衡量中医药的科学性[2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们要更加增强中医药自信,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注入中医药力量[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