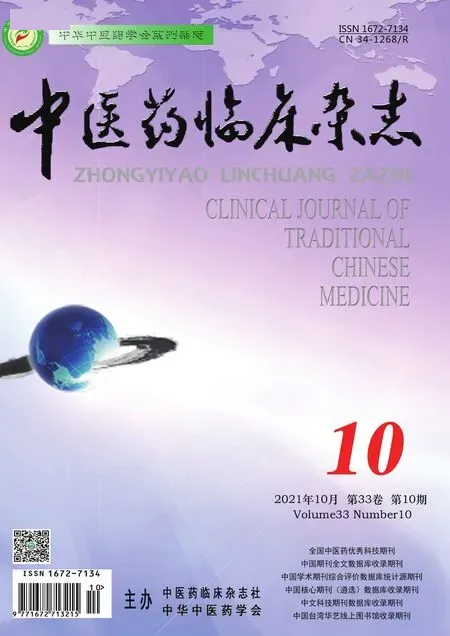杨文明创肝豆扶木汤治疗肝豆状核变性肝纤维化经验*
2021-04-17唐露露杨文明
唐露露,杨文明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合肥 230031
肝豆状核变性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慢性铜代谢障碍性疾病,致病基因ATP7B位于13q14.3,ATP7B基因突变导致铜蓝蛋白合成障碍及铜在胆汁中排泄障碍,过量的铜在肝脏、基底节、角膜、肾脏等器官病理性沉积而发病[1]。本病全世界患病率为1/100000~1/30000,是少数可以治疗的神经遗传病之一[2,3]。如果能在发病早期或症状前期被确诊并得到及时治疗,大多数预后良好,反之病情逐渐加重甚至危及生命。本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但无论是肝型、脑型还是其他类型,肝纤维化几乎是每一个患者肝脏的主要病理改变,是进展至肝硬化的必经阶段[4,5]。临床上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肝硬化及其并发症,金属螯合剂在驱铜治疗中往往由于副作用较重而被迫停药。中医药治疗本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能通过多途径、多层次、多靶点的方式延缓病程[6]。杨文明教授是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中医临床优才指导老师,博士生导师,江淮名医,安徽省名中医,现任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长期从事中医脑病的诊疗,临床经验丰富,尤其对肝豆状核变性的研究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现总结杨文明教授临床治疗肝豆状核变性之经验供临床参考。
肝肾阴虚为本,痰瘀互结为标
中医学尚无肝豆状核变性一词,亦无肝纤维化的记载,但根据其临床表现,WD可归属于 “肝风”、“颤病”“积聚”“水肿”“痉病”“狂病”等病范畴,肝纤维化可归属于“黄疸”“胁痛”“积聚”“肝积”等病范畴。历代医家对WD病因病机的认识各有不同。杨任民[7]认为先天不足,肾精亏虚,导致精不化血,血失濡养,筋脉不利,生风动火;铜毒蕴久,酿生湿热,熏蒸肝胆,发为该病。鲍远程[8]认为本病病位在肝肾,涉及脑髓、心、脾,致病特点多为本虚标实,以气血亏虚、肝肾不足为本,病理因素包括痰瘀、邪热等。《内经》载:“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基于此理论,于鸿钧[9]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为肝肾阴虚于下,阴不制阳,水不涵木,阳亢在上 ,导致火生风动。本病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患者禀受于父母遗传物质,即先天之精异常,是引起本病的根本原因。肾藏先天之精,化生肾气以促进生长发育和生殖,为人体生命之本原,故称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充足,肾气充沛,机体发育正常。《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云:“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灵枢·海论》指出“脑为髓之海”。本病患者之疾禀受于父母,肾精匮乏,肾气亏虚,禀赋不足,加之后天饮食不节、七情失调、劳累过度等均会诱发或加重本病。本病位起于肾,《素问·金贵真言论》有“肾开窍于二阴”之说,先天不足,导致开合失司,肾主二便失常,铜毒外泄无出路,蓄积在体内而发病。又肝主藏血而肾主藏精,肝主疏泄而肾主封藏,故肝肾之间关系有“肝肾同源”或“乙癸同源”之称,肾病常累及于肝,肝肾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资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先天不足,肾精素亏,水不涵木,则肝亦失濡养。肝肾阴虚,症见腰膝酸软,口燥咽干,眩晕耳鸣,男子遗精,女子月经量少,面色晦暗,形体消瘦,五心烦热,鼻衄齿衄,舌红少苔,脉细数无力。又肝肾阴虚,阴不敛阳,虚风内动。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临证指南医案·中风》亦云:“凡肾液虚耗,肝风鸱张,身肢麻木,内风暗袭”,“肝体阴而用阳”。症见肢体震颤、手舞足蹈、肢体拘挛、步履蹒跚。
本病初期以本虚为主,随着病情进展,往往可因虚致实,形成了本病“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致病特点。肝肾阴虚,阴不敛阳,虚风内动,或肝失濡养,调达不畅,气机郁结。《张氏医通·积聚》言:“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故正气虚弱是WD肝纤维化的内在基础。铜毒郁久,酿生湿热,湿热既是病理产物,又可以反过来作为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进一步影响脏腑机能活动,影响气血津液的代谢。湿为重浊有质之邪,易阻遏气机,气不行血,瘀血内生,气不行津,聚而为痰。邪热炽盛,炼液成痰,热入血脉,煎熬成瘀。痰来自津,是体内津液代谢障碍的病理产物,瘀本乎血,是血液停聚的病理产物。血与津液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资生,相互转化,故有“津血同源”之说。如《灵枢·邪客》提出“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亦有《灵枢·决气》云:“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痰瘀既可单独为病,也可交结为患,痰饮一旦形成,又可以进一步阻滞气机,加重瘀血。血瘀日久必兼气滞,津化失常,聚为痰饮。二者相互影响,或因瘀致痰,或因痰致瘀,最终导致痰瘀互结。如《血证论》中记载“须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血迹既久,已能化为痰水”。《灵枢·百病始生》中亦云:“胃肠之络伤,则血瘀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搏结,则合并凝聚不得散,而积不得散。”痰瘀互结,阻滞肝络,症见胁肋刺痛、或见癥块、痛处不移、面色晦暗、舌质紫暗等瘀血证候,又有腹大如鼓、肢体浮肿、咳唾痰涎等痰浊征象。《素问·评热病论》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痰瘀积久,正气日渐虚弱,机体抗邪无力,疾病向恶化、危重、甚至向死亡转归,即邪胜正衰。肝硬化是WD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患者晚期常出现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继发感染、腹水等并发症。若正气衰竭,邪气独盛,阴阳离决,则机体生命活动亦告终止。综上,肝豆状核变性肝纤维化的病理性质总属本虚标实,疾病初期,以本虚为主,本虚主要表现为肝肾阴虚,后期以标实为主,标实表现为铜毒湿热、痰瘀互结,肝气郁结,而痰瘀又是本病的关键,贯穿疾病之始终,故痰瘀互结为标实之关键[10-12]。
补益肝肾扶正,豁痰化瘀祛邪
杨教授基于WD肝纤维化的肝肾亏虚,痰瘀互结病机,提出补益肝肾、豁痰化瘀是治疗本病的基本治法[13],并创制了中药复方制剂肝豆扶木汤,广泛用于临床,疗效显著[14]。本病的病理性质为本虚标实,肝肾阴虚为本,痰瘀互结为标。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提到“气血冲合,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内经》有“邪之所在,皆为不足”之说,故导师强调治疗本病要做到标本兼顾。本病的发生以肝肾阴虚为基础,阴不敛阳,虚风内动或肝失条达,气机不畅。滋补肝肾,则精血得充,正气渐盛,肾气充沛,则能激发脏腑经络官窍的生理活动,推动精气血津液的运行,而不使痰聚血瘀。调达气机,则肝郁得疏,柔肝敛阴,则阴阳平衡互制,内风得熄。豁痰祛瘀,既能去除标实亦有利正气恢复。即所谓扶正祛邪,扶正邪自去,祛邪正自安。肝豆扶木汤由何首乌、枸杞、土茯苓、白芍、三七、郁金及柴胡等组成。方中何首乌、枸杞补益肝肾、扶正固本;三七、郁金、土茯苓活血化瘀、解毒除湿;白芍、柴胡柔肝敛阴、调达肝气,诸药合用,共奏补益肝肾、豁痰化瘀之功效[15-17]。此外,杨教授在临床中结合每个患者的不同情况灵活加减:若中焦湿热重者加苍术、白术、厚朴、半夏、陈皮以化湿行气;若气滞血瘀重者加川楝子、延胡索、赤芍以行气活血;阴损及阳,脾肾阳虚者可合济生肾气丸加减;痰瘀互结,肝硬化甚者加姜黄、莪术以活血散结。
典型病案
某女,16岁,于2016年7月11日初诊,以“发现肝功能异常1年余”为主诉就诊。患者1年前开始出现形体变胖,体检时发现肝功能异常。父母为非近亲婚配,家族无类似病史。症见:胁肋隐痛,痛有定处,形体肥胖,纳呆,泛恶流涎,舌质紫黯,苔滑腻,脉弦滑。辅助检查:角膜K-F环(+)。肝功能:ALT 116U/L,AST 69U/L,肝纤四项:HA 265.48ng/ml,铜蓝蛋白0.081g/L,铜氧化酶 0.023活力单位/L,尿五元素:铜1322.07ug/24h,血清铜:10.250umol/L,肝胆胰脾超声提示脂肪肝。中医诊断:肝风,证属肝肾阴虚,痰瘀互结。予以中西医结合一体化治疗,中医补益肝肾,豁痰祛瘀。处方:(1)肝豆扶木汤加减。方药:制何首乌 6g,枸杞 30g,三七 10g,土茯苓 15g,白芍 20g,郁金20g,柴胡12g。14付水煎,1日1剂,分3次口服。嘱患者避免高铜饮食;(2)二巯基丙磺酸钠0.5g静滴 一日一次。二诊,患者述胁肋隐痛减轻,食少,夜寐差。原方加鸡内金 10 g,二芽各 15g,酸枣仁15g,远志10g,茯神10g。继服14剂后,诸症缓解。复查结果:肝功能:ALT 58U/L,AST 34U/L,肝纤四项:HA 58.62ng/mL。
体 会
患者先天禀赋不足,肾精素亏,水不涵木,延及肝脏,肝肾阴虚,铜毒内聚,发为该病。阴不敛阳,虚风内动。肝失濡养,条达不畅。铜毒郁久,湿热内蕴,湿邪为患,易阻滞气机,气滞血瘀,气滞津停,又邪热炽盛,炼液为痰,热入血脉,煎熬成瘀。痰饮一旦形成,又可以进一步阻碍气血运行,加重瘀血。瘀血必兼气滞,津化失常,聚为痰饮,故痰瘀之间形成痰凝血瘀,血瘀津阻的恶性循环,痰瘀互结,病势缠绵,胶着难解。瘀血内积,气血运行受阻,不通则痛,故见胁肋刺痛、痛处固定;痰浊内生,泛于肌肤,故见形体肥胖;痰浊中阻,胃失和降,故见纳呆流涎;舌质紫黯,苔滑腻,脉弦滑为痰瘀互结之象。遂投以肝豆扶木汤加减运用。何首乌、枸杞补益肝肾,扶正固本;三七、郁金、土茯苓活血化瘀、除湿解毒;白芍、柴胡柔肝敛阴,调达肝气;鸡内金、二芽健脾消食;酸枣仁、远志、茯神宁心安神,益智祛痰。诸药合用,标本兼顾,使肝肾得补,痰瘀得祛,诸症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