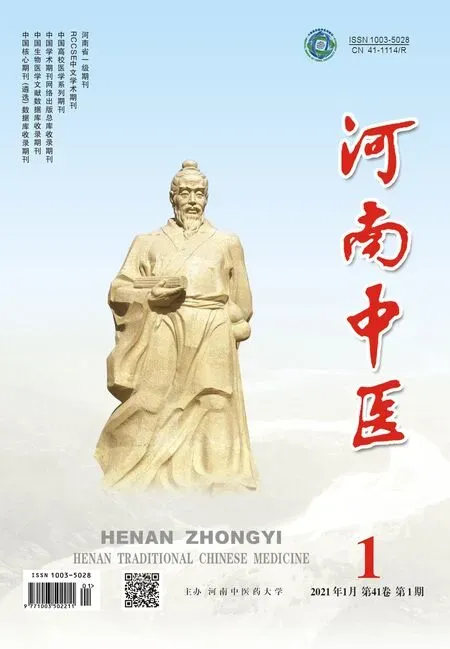肠道微生态与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病机制的相关性*
2021-04-17安洁周琴薛毅芳
安洁,周琴,薛毅芳
昆山市中医医院,江苏昆山 215300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是一种发病多因性、临床异质性、不可治愈性、进展性发展的内分泌紊乱综合征,在育龄期妇女中PCOS的总体发病率为5%~10%[1],而在我国汉族育龄期女性中的发病率为5.6%[2]。在无排卵性不孕症患者中的发病率高达30%~60%[3]。PCOS除了会造成生殖激素紊乱,还具有影响较大的远期并发症,且病因尚不十分明确,是女性生殖障碍疾病研究的重点及难点。
近年来,肠道菌群与多种内分泌疾病发病相关性研究不断深入,证实了肠道菌群失调参与介导PCOS小鼠的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肥胖、高雄激素血症等过程[4-6],有数据表明约41.7%的PCOS的患者常见有胃肠功能紊乱先于月经失调,其中一项临床病例对照研究也发现,PCOS患者(包括肥胖、非肥胖)的肠道菌群失调率高于正常人群[7]。历代医家有云:“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百病皆生于气”“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万物之生杀,莫不以阴阳为本始也”等等,溯源PCOS的中医病证、病因病机,无不与脾胃气机升降失调、脏腑阴阳气血失衡密切相关,治疗上也赖于健运脾胃,燮理阴阳,而肠道微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医学的“中土思想”,以及“整体观、系统观、平衡观、恒动观”,二者理论内涵一致[8]。本文将从中西医方面对其进行分述。
1 病因病机
PCOS病因复杂、高度异质,中医认为其根本病机为本虚标实,脾肾亏虚,致脏腑功能失常、气血失调,化生痰浊、血瘀等,引起生殖功能障碍。近年来,肠道微生态在中医证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脾虚证、肾阳虚衰证、湿热证、脾虚湿盛证等[9]。其中与肠道菌群密切相关的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征的中医病机证候与PCOS的病机本质不谋而合[10]。研究者根据中医理论,通过益气健脾、化痰祛湿、补肾疏肝等理法,运用中药复方或单体,改善患者的肠道菌群,修复受损的肠黏膜,调节胰岛素的敏感性,促进代谢。可见二者共调共荣,共损共衰,现就其共性阐释如下。
1.1 阴阳失衡,同为发病根本阴阳学说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之一,不仅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亦是万物生长壮老已之根源。诚如“生之本,本于阴阳”“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人身病损,必先阴阳致偏”“人有阴阳,即为血气……人生所赖,唯斯而已”“阴阳交则物生,阴阳格则物死”,理论种种,古圣先贤,百病千方,无不遵循“四时-五脏-阴阳-气血”以调治之。月经病,亦如此。月经,常候也,调候其一身之阴阳愆伏,知其安危,故每月一至,太过或不及,皆为不调。如阳太过则经水先期而至,阴不及则经水后期而来,亦有乍多乍少,断绝不行者,崩漏不止也,此皆由阴阳盛衰所致。PCOS临床多态表现之根是肾阴阳失衡,累及他脏,变生多症[11]。夏桂成[12]临症常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治疗PCOS常于静中求动,降中求升,以燮理阴阳为关键。肠道微生态之稳态是涵盖物质、能量、基因间的动态平衡,也体现了阴阳消长、互根转化理论。一般情况下与宿主、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保持“互利共生”的相对平衡状态。若平衡被打破,肠道中有益菌、有害菌之间制约、消长失衡,则出现肠道菌群结构或数量、种类异常,致使微生态失衡,代谢性疾病产生。研究证实,阴阳失衡患者与正常人的肠道菌群存在显著的差异[13]。由此可见,二者阴阳内涵是一致的,所以从肠道阴阳失衡角度来研究PCOS,也可以更好地认识疾病[14]。
1.2 “脑-肠”理论贯穿其中现代研究发现,与食欲、食物摄入量、能量平衡、糖脂代谢和体质量相关的“脑-肠轴”(其以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为核心)对PCOS的发病、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15]。被称为“成人的第二大脑”的肠道菌群是“脑-肠轴”信息交流的主要介导者[16]。中医虽无“脑-肠轴”这一概念,但在众多中医理论及临床实践中不难发现,此概念深含于各方面,绝非单纯的器官层面认识,文献研究发现,医家多从“气机升降、脏腑和养、经络相通”角度来阐释中医理论对“脑-肠”关系的认识。
其一,气机升降相因。生命活动的本真,源于气的“始-散-布-终”,并通过“升-出-冲-降-入”的形式完成“生-长-化-收-藏”之气化圆通的结果。诚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云:“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流通有序,循环有常,则“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以灌溉四肢百骸、充养脑髓。升降失衡,则气、血、精、津液无以化,湿停为痰,血阻为瘀,久致脏腑痰浊瘀毒形成,壅塞冲任,血海不能按时满溢,而致月经失调、肥胖、不孕。“气病”日久而致“形病”,如PCOS临症多见肥胖、痤疮、多毛等。有学者提出,气机郁滞是PCOS最基本的病理变化。女性常处于“血常不足,气常有余”的生理状态,故妇人气机枢转的正常与否更为重要。旺建伟等[17]研究证实,情志因素(大脑)-肝郁-脾虚-肝旺乘脾理论与“脑-肠轴”(神经-内分泌-免疫体系)学说有相重叠之处。甚则有学者提出“脑-肠轴”学说,其失衡的实质是气机紊乱[18]。故而气机调畅,升降相因,乃是调病根本。
其二,脏腑和养。此理论基础源于脏腑之间经络相通、五行相联、功能相关。五脏平和,则百骸皆润泽而经候如常[19]。
从“心胃相关”出发,本(脾)胃赖于心阳宣发温煦、心气气化以运化水谷,化生精微物质,心为君主之官,又赖于精微之涵养,以主“五脏六腑”。且“胃足阳明脉,正别上至脾,入腹里,属胃,散而之脾,上通于心”,又“胃与心,母子也”,若阳明发病,则心脾二脏无所禀受,神机、枢机失常;反之,心脾病者,胃肠受累。故“月经之本,所重在冲脉,所重在胃气,所重在心脾生化之源耳”[20]。周惠芳教授遵于此理,辨治PCOS首从健脾胃、宁心神出发,疗效显著。
从“脾肾相关”而言[21],该理论溯源于《黄帝内经》,经后世医家发展论述至今,二者在生理上相互滋生,病理上互相影响,但何以与“脑-肠”相关?唐宗海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全体总论》中曰:“肾系贯脊,通于脊髓,肾精足,则入脊化髓,上循入脑而为脑髓,是髓者精气之所会也。”可见“肾通于脑”,经络功能相通,又“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荣养之源根于脾胃,脾胃乃“后天之本”,运化精微以充养脑髓。如恣食肥甘厚味,损伤脾胃,则湿邪内生,内蕴肠腑,气滞血瘀,久则脂膜血络受损,而至肠病;或肾阳虚,脾阳失于温煦,脾肾两虚,水失运化,湿聚成痰,而成“痰泻”,多数研究证实,PCOS患者肠道菌群紊乱,易见肠道病症。痰湿上扰,阻滞清窍,神机失用,精神失常,国内外研究也证实,PCOS较正常人群更容易患精神障碍[22],但该研究有其局限性。
从“膏脂”论。膏脂转输体现脏腑功能,若如常,则病邪难生。“膏,脂也。”膏脂来源有二。其一,多食肥甘厚味之品;其二,水谷精微转化而来[23]。“三焦气化”为膏脂主要运动形式,布散精微至周身脏腑。若脏腑功能失调,膏脂过剩,即“脂凝、脂结”,不归正化,久成痰瘀阻络之势;溢余经脉之外,则积于皮下,积于脏腑,导致肥胖、不孕、代谢综合征等疾病的产生[24]。诚如《素问·通评虚实论》说:“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或曰“肥人多痰,乃气虚也,虚则气不运行,故痰生之”“妇人有身体肥胖,痰涎甚多,不能受孕”。数据表明,PCOS肥胖患者比例为20%~60%,其中,肥胖型PCOS患者高胰岛素血症的发生率高达75%。而肠道微生物的“内稳态”不仅是脏腑协调的重要体现,又是脂质代谢的重要前提。贾连群等[25]通过全转录组技术对造模小鼠(脾虚痰浊型)的肝脏进行基因表达谱分析,初步发现造模小鼠的肠道微生物是通过驱动TMA/FMO3/TMAO信号通路影响膏脂的转输。有研究表明,肠道微生态失衡是膏脂转输障碍的关键环节,可能是通过肠道多种信号分子,影响机体胆汁酸、肝脏脂质的代谢来影响雌激素代谢、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的产生和肠道细菌的过度增生,尤其凸显于对胆固醇逆向转运途径进行调控,这些均被证实参与PCOS的发病过程[26-28]。所以可以通过调肠道,转输膏脂,来治疗PCOS。
其三,经络相通。“脑-肠”间存在广泛的经络联系,经络具有运行气血、联系脏腑、沟通内外的作用。从循行看,“大肠手阳明之脉……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抵胃,属小肠;其支者……至目内眦,斜络于颧”“胃气上注于肺……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又“人头者,诸阳之会也”;从络属脏腑功能看,“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可见二者存在坚实的生理联系。若经络病,神机失常,变生多病,故而有医者通过针灸来调“脑-肠”,治疗代谢性疾病及脑病,现代研究也证实“脑-肠”轴发挥作用的基础包括神经内分泌信号传导、免疫传导等方面。
从中医学理论出发,并无“肠道菌群”这一说法,但肠道微生态的生理功能却敏锐地反映在周身脏腑、气血津液、精气神等诸多方面,尤其是脾胃功能[29]。五脏之病,俱能生痰,但脾胃枢机失常乃为核心。因脾胃地处五脏六腑之中枢,内寓升降浮沉、寒热燥湿之功,人体之精髓、气血、津液、营卫皆由其化生而来,濡养灌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脾胃枢机顺畅,可下滋肾水、上济心火,以维持脏腑功能正常运行。转运失常则至痰浊瘀,“壅滞中焦,伤及肠腑”“闭阻胞宫”等[30],这与PCOS的根本病机也是一致的,故而临床上许多医家提出,治疗PCOS以健运脾胃为要,杜绝病理产物。脾气升则肾肝之气升,胃气降则心肺之气降,故而中土旺,气机升降得疏,水精四布,五精并行,微生态自然内稳[31]。现代“组学”类技术(如宏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等)也已经有力佐证,中医药可通过多信号通路、多环节、多脏器靶点与肠道微生态相互作用,治疗代谢性疾病。通过中医药调节肠道微生态角度来治疗PCOS可能是个新靶点[32]。
2 现代作用机制
早在2012年,Tremellen等[33]提出PCOS发病机制的“DOGMA”(dysbiosis of gut microbiota)假说,可总结为:①长期暴露于高糖高脂或低膳食纤维饮食、肥胖型的PCOS患者群,均存在肠道菌群紊乱状态,肠道上皮细胞间连接遭到破坏,肠壁黏膜通透性增加,形成所谓的“泄漏肠道”。②肠道细菌胞壁上的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进一步渗入血液,产生慢性炎症反应,诱导IR产生。③IR促进高雄激素血症,干扰卵泡发育,致PCOS患者不孕。随后多项研究也证实了其假说的成立,发现PCOS患者肠道微生态及通透性确有改变,且肠道菌群紊乱与相关临床症状密切相关。
2.1 高雄激素血症高雄激素血症作为PCOS的重要临床表现之一,也是疾病诊疗的核心点,其导致卵巢基质增生、卵巢包膜增厚,加速了卵泡的闭锁,抑制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合成,进而促使外周血转化增高,导致女性多毛、痤疮、排卵障碍等。已有动物实验发现,肠道菌群的改变会影响动物血液中睾酮(testosterore,T)的含量。Poutahidis等[34]发现,喂食过罗伊氏乳杆菌小鼠血液中的T水平确有升高。Kelley等[35]对来曲唑诱导的PCOS高雄激素血症小鼠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小鼠大肠中细菌的种类及数量确有减少,且小鼠的体质量、脂肪量及血糖水平较对照组升高,说明高雄激素血症导致了肠道菌群的改变。Guo等[36]对PCOS造模大鼠灌喂了健康大鼠的粪便提取物后发现,大鼠的雄激素水平显著降低。说明在PCOS中,二者均参与疾病的发生发展,但二者间的关系、机理有待深入研究证实。
2.2 胰岛素抵抗通过对PCOS患者血清和卵泡液组分的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可通过LPS、支链氨基酸、短链脂肪酸(引起肥胖的关键因素)和胆汁酸等介导炎症反应,从而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
肠道菌群能够破坏肠黏膜的屏障作用,使LPS渗入血液[37]。LPS又通过血中的脂多糖结合蛋白结合运输,与免疫细胞表面CD14(一种白细胞分化抗原,可介导LPS性细胞反应)结合,并被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s 4,参与LPS信号传导的重要受体)识别,进一步作用于脂肪细胞及巨噬细胞,从而产生多种炎症因子(例如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等)介导炎症反应的发生,来诱导胰岛素受体底物-1的丝氨酸磷酸化,发挥干扰正常酪氨酸的磷酸化的作用,减弱胰岛素信号的转导,致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引起胰岛素抵抗[38]。Cani等研究发现通过添加益生元,增加双歧杆菌的总含量,能够促进结肠细胞对胰高血糖素样肽-1的分泌,促进胰岛素分泌释放,改善IR等代谢异常[39]。Zheng等[40]通过几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人体摄取越多的支链氨基酸(人肠道内的一种普氏菌参与支链氨基酸的合成),罹患糖尿病的概率就越高,分析机制可能是因为缬氨酸的分解代谢产物3-羟基异丁酸盐,刺激了肌肉组织对脂肪酸的摄取途径,从而引起了脂肪堆积和IR,但还需进一步研究。
胆汁酸作为重要的细胞信号转导因子之一,可激活多个信号通路来调节生物学过程,其中包括脂类、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和介导炎症反应等。徐运杰等[41]研究发现,胆汁酸降脂机制有:①乳化脂肪,扩大与脂肪酶的接触面积;②调控胰脂肪酶和脂蛋白酯酶的活性,提高其对脂肪的水解代谢;③在肠道内转运脂肪,来促进脂肪的吸收。Li等[42]研究发现,胆汁酸可以通过肠神经内分泌细胞,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高血糖素样肽-1的分泌,调节机体能量代谢。
胆汁盐作为胆固醇分泌的辅助分子,经研究证实,其可以促进肠中营养物质的吸收,进而刺激胰腺分泌足量的胰岛素,并抑制小肠中细菌的增生,促进小肠对脂类的吸收,降低IR的发生[43]。
上述成分在雌激素代谢、胰岛素抵抗和小肠细菌过度增生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均参与PCOS发生发展。
2.3 肥胖肥胖与PCOS并非一类疾病,且不是PCOS的致病原因,但肥胖却是PCOS的常见表现。据统计,PCOS中肥胖患者比例高达20% ~60%,肥胖是公认发生胰岛素抵抗最常见的危险因素之一[44]。肠道菌群的改变参与肥胖、代谢异常等发病机制。Cani等发现,肠道菌群产生的LPS会改变肠道通透性,引起机体慢性炎症反应,最终导致肥胖的发生。Bkhed等[45]发现,B6自交系无菌小鼠肠道植入正常菌群后,小鼠的脂肪量增加了57%,但进食量反而减少27%。NMRI用自交系小鼠做了同样的实验,发现有菌小鼠的总脂肪含量增加了90%,进食量却减少了31%。这两项研究证实,肠腔内肠道微生物可以促进单糖的吸收,诱导肝脏脂肪的重新合成,导致脂肪堆积。佐证了肠道菌群可以影响肠道中能量的获取、贮存,并促进脂肪累积。研究者从肥胖者中采集肠道菌群并移植到无菌小鼠,发现小鼠身体脂肪含量会明显增加,并出现IR。LPS被证实是形成IR的主要原因之一。Cani等[46]给无菌小鼠连续皮下注射4周LPS后,小鼠出现慢性低度炎症,并导致肥胖和IR。可见肠道菌群失调,肠壁通透性增加,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减少,引发的内毒素血症加重慢性低度炎症,并参与肥胖的发病过程。肠道菌群可能是通过影响能量代谢、慢性炎症反应、免疫系统调节、肠道激素等多种途径参与疾病的发生、发展。但目前具体机制尚未完全明了,如肠道菌群结构、代谢机理等诸多方面,所以有待更深入、更精确的研究[47]。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对免疫机制、微小RNA、微生态、脂肪代谢组学等层面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相关性的深入研究,对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因及发病机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仍不十分明了。目前,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治疗仍集中在针对特定症状,还无法达到患者内环境稳态、子代健康的理想结果。肠道菌群作为内环境因素,可与宿主相互作用,多项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因素参与PCOS的病理生理过程的发生和发展,但究竟谁是机理的引导者,尚未知晓。由于PCOS疾病的特殊性、终身性,治疗上并非短期可以速效,中医药在治疗PCOS中体现出了显著的优势。目前,关于中医药干预治疗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肠道微生态影响的临床研究报道较少,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