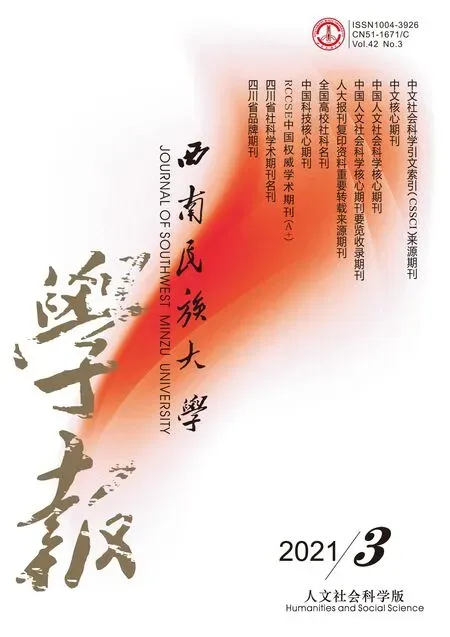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的跨文化和多维度研究
2021-04-17谈凤霞
谈凤霞
[提要]西方华裔儿童文学是长期被中国学界忽略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一文学群落具有独特的创作宗旨、生态样貌和传播价值,大多聚焦于儿童对族裔文化的认知及成长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其文化书写中往往包含跨界性的文化场域和融合性的审美经验,鼓励儿童构建想象中的东西方“文化共同体”。对于这一具有鲜明跨国族意识的儿童文学群落的研究,需要运用民族志文化研究、身份理论、差异理论等深入辨析这一群落内部跨文化身份书写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此外,还需要对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及其相关的亲缘文学进行多维度的比较,考察其在文化书写经验方面的相因性与异质性。对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华裔儿童文学的研究,可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如何拓展话语空间提供借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西方华裔儿童文学是长期被中国学界忽略的一个文学群落,这一文学是移居或出生于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北美和澳洲)的华裔用居住国的语言或汉语写作的儿童文学,时间跨度上包括不同代际的华裔作家的作品。据笔者查到的现有资料来看,西方华裔儿童文学最早发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清末留美学生李恩富(Yan Fhou Lee)的童年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IWasABoyinChina,1887)是华人在西方出版的第一部与童年相关的英文作品。在20世纪上半叶的北美,蒋彝(Chiang Yee)的《中国童年》(AChineseChildhood,1940),施妹妹(Sze Mai-mai)的《哭喊的回响:始于中国的故事》(EcoofACry:AStoryWhichBeganinChina,1945)等数量不多的童年成长故事在英美出版,但这些并不是专门针对儿童读者的儿童文学。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美国平权运动和亚裔文学的兴起,华裔儿童文学的创作开始显山露水,插画家杨志成(Ed Young)等的图画书、叶祥添(Laurence Yep)等的儿童小说开始陆续出版。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去往西方国家的华人移民和留学生大量增加,且出生于西方的年轻一代的华裔作家也开始风生水起,华裔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日益壮大,并在西方主流儿童文学圈乃至国际儿童文学界逐渐赢得一席之地。①
就创作宗旨而言,华裔儿童文学大多聚焦于文化传递和华裔儿童成长中的身份问题,力图为处于西方社会边缘的华裔儿童发声,使华裔儿童读者从中“看见自己”,并对其文化身份的认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其对于自身族裔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培养其跨越双重文化的自适感和自足感。这对于华裔儿童的主体性建构、华裔社会文化圈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同时,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往往包含跨界性的文化场域和融合性的审美经验,能吸引异域文化的儿童读者领略中国文化风情,催发其包容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品味,促进国族间的文化和艺术的共赏,对于鼓励儿童读者构建想象中的东西方“文化共同体”具有推动作用。研究西方华裔儿童文学,既包含对其文本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价值的衡量,也包含对其显在或隐含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功能的考察。对于这一具有鲜明跨国族意识的儿童文学群落的研究,尤为需要跨文化的深入辨析和多维度的广泛考察。
一、跨文化身份认同书写的复杂性与差异性辨析
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属于华裔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学者对西方华裔文学的研究兴起于1980年代,之后这一研究蓬勃发展,至今已有七十多部研究专著,但主要聚焦于成人文学,而对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的关注非常缺乏。事实上,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的创作版图有其独特的意义,对此分支的研究的缺席,会影响我们对于整个华裔文学群落生态的确切把握。研究族裔儿童文学的美国学者凯瑟琳·凯普修·史密斯(Katharine Capshaw Smith)指出:“如果没有儿童文学发出的声音,我们就不能讲述美国族裔写作的故事。”[1](P.3)她强调族裔儿童文学之于整个族裔文学的重要性,因为儿童文学能呈现族裔问题的“特殊轮廓”。多萝丝·德·迈纽(Dolores de Manuel)和罗西欧·G·戴维斯(Rocío G. Davis)在谈到美国亚裔儿童文学的意义时也强调亚裔儿童文学相对于整个亚裔文学的作用:“美国亚裔儿童文学并非是族裔文学这一大问题的微型版,而是必须被解读为亚裔作家试图为美国文化语境中的亚裔儿童建立其位置所付出的多层面且微妙的努力,他们创造性地参与其边缘的定位。”[2](P.v-xv)戴维斯进一步分析:“亚裔美国儿童文学强调与历史、国家和民族关系、跨文化关系相关的社会意义或价值,强调每个群体如何占用或影响他们所在的地方和他们构成的社区。对于当今美国亚裔儿童,历史、遗产、文化或学校的同伴社区、自我形成的可能或需要变得非常重要,这是赋予儿童读者权力和建构主体性的动力。”[3](P.185)这些观点都突出了族裔儿童文学之于族裔文学、文化和儿童接受主体的独特价值。
研究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的关键词涉及族裔、社群、文化、身份、错位、认同、离散、边缘、夹缝、家园、传统、现代、殖民、后殖民、东方、跨界、寻根、主体、成长、冲突、困惑、协商等。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由中国文化基因与西方文化相碰撞、对话和交织而成的,对于文化立场的考察与华裔成人文学研究相会通。杨匡汉和庄伟杰在对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进行诗性考辨时提出:“无论从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还是从话语方式与精神姿态等加以透视,抑或是从狭义的语种和广义的文化予以观照,都有必要把其放置于文学甚至文化理论思潮之中,不断挖掘和发现其中潜藏的独特价值。”[4](P.190)对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特质的研究也需要置身于诸多的理论领域,包括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等范畴,主要涉及民族志文化研究、东方主义、读者接受理论、差异理论等,其中差异理论尤为重要。解构主义之父德里达(J. Derrida)认为意义产生于差异,而集空间差异和时间延宕于一体的“延异”是事物的真正本源,是差异产生之源,是意义和身份产生或确立的最终本源与根据。差异理论强调在多元文化中,对不同族群的语言、生活方式、身份认同等的差异都须予以认可,“必须承认异质文化的存在,更需要张扬异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交融和认同。关注同与异两个方面的内容,既要关注其可比的共同性,更应关注其因不同文化语境而形成的差异性,考察其在多元文化背景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特性。”[4](P.194)西方华裔儿童文学虽然主要目标读者是儿童群体(包括华裔儿童和非华裔儿童),但作者同样在文本中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植入异质性的中西文化元素,自觉地在故事或图像中表现文化差异及其碰撞,我们可将差异理论内化为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研究中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无论是考察宏观现象还是解读微观个案,都要深入辨析其涉及的文化异质性、交叉性、矛盾性或共生性等问题,并寻根探源,深入考察形成差异的文化原因和对待差异的解决方式,揭示西方华裔儿童文学跨文化表现的特色及其价值。
从文化空间而言,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由于其文化跨界的性质,成为了既不同于原民族、也不同于居住国的“第三文化空间”的文学产物。文化身份认同是处于“第三文化空间”中的族裔文学的一个核心,在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对跨界的文化场域和审美经验的表现中,如何处置双重文化身份之间的差异、如何选择或融汇,是华裔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选择同化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直接决定其作品的思想立意和艺术取向。多萝丝·德·迈纽和罗西欧·G·戴维斯辩证地指出身处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面对主流文化的尴尬:他们要保持对本族祖先遗产的忠诚和继承,同时又可能被主流文化劝诫或引诱同化;要成为完全的西方人,但最终发现由于其族裔基因,西方主流阶层可能不会完全接纳他们。少数族裔正是在西方遭遇的压力和被激发的梦想之间相互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族裔儿童文学。[2](P.XV)凯瑟琳·凯普修·史密斯将少数族裔儿童文学概括为“作家构造历史和协调不同读者需求的一种复杂性存在”,她认为少数族裔的儿童文学“给儿童读者提供了一种途径去重建他们和种族与国家身份的关系,给儿童讲故事成为社会和政治革命的一个渠道。”[1](P.3-8)身处西方白人文化语境中的华裔儿童文学也不例外,许多华裔作家都在儿童文学中注入与文化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蕴含了对于西方主流既定秩序的挑战。例如,加拿大华裔儿童文学的开创者余兆昌(Paul Yee)致力于反映中国人形象,“可以让北美华裔从中看见自己,认识到与主流文化不同也是有价值的,可以让他们从新的不同角度认识自己和彼此。”[5]他曾在加拿大主流媒体的采访中谈到创作儿童文学的宗旨:“我写作是为了让更多人更直接地了解历史,写作中确实带有教育的目的。我想灌输一些东西,成年人可能会排斥,但是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他们应该意识到中国人为加拿大所做的贡献,因为下一代将会改变这个国家的社会肌理。”[6](P.63)由他撰写、陈志昌(Harvey Chan)绘画的《梦魂列车》(GhostTrain,1996)等反映早期赴美华工修建铁路的血泪史,对自身族裔历史和文化的发掘隐含了对于抹杀华裔移民贡献的西方文化霸权的抗议。
另一些出生于西方的华裔作家则从自身童年被白人文化边缘化的遭遇出发,以儿童文学来构想融通族裔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新的文化空间。美国华裔林佩思(Grace Lin)的图画书和儿童小说大多以西方为故事背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元素,讲述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儿童对文化身份的认知。她在美国PBS News Hour新闻访谈节目中,谈到文化身份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有机性”的主张:不能把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当作宝贝去紧紧粘附,而是要把文化当作一颗种子,它需要养育和尊重,也需要在时间和环境中适应、改变、再造、创新。她认为文化遗产是构成族裔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把文化遗产当作不能更改的部分,则文化遗产会缩小,所以她主张文化要具有弹性,只有不断得到养育,文化才能生长。她的图画书《丑蔬菜》(TheUglyVegetable,1999)讲述华裔小女孩对妈妈在花园里种菜而美国白人邻居种花进行对比,孩子在对两种园艺文化的观察中发现各自的长短,对自身族裔文化由隔膜、疑惑到接受。故事的高潮是邻居们拿鲜花来交换中国蔬菜汤,华裔妈妈热情招待并慷慨传授中国食谱。一锅美味的蔬菜汤打破了民族界限,彰显了华裔文化的魅力。结局则进一步锦上添花:华人妈妈开始在菜园旁种鲜花,而西方邻居则在鲜花旁种蔬菜,这一中西文化各取所长的结合意味着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引、渗透和改造,传递了不同文化并存共生的乐观希望。
澳洲华裔学者庄伟杰体察到华裔写作中关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文化认同以民族性为基本单位,但在全球化或现代性拓展的语境中含义非常复杂,除了‘民族性’指称的种族、族群和民族—国家等范畴,它还可指涉地方社群、宗教、性别、代际等亚文化群体的认同。在叙事文本中,各种文化身份的符号是互相交织的,需要加以历史的、个别的解读。”[7](P.128)这一主张提醒我们注意,西方华裔作家所处的不同“亚文化群体”会给他们在作品中的文化认同带来不同的立场、取舍等差异性。即便是同在一国的华裔作家,如叶祥添和杨谨纶同为出生于美国的华裔,但由于两人所处的不同代际和文化境遇,在表现美国华裔少年身份认同的故事——如叶祥添的《猫头鹰之子》(Child of the Owl,1977)、杨谨纶(Grne Luen Yang)的《美生中国人》(AmericanBornChinese,2008)等作品中,对于文化身份的冲突能否解决也有各自的考量。同样是书写北美的华埠或唐人街,美国的叶祥添的童年自传《失落的花园》(TheLostGarden,1991)和加拿大的崔维新(Wayson Choy)的自传《纸影:唐人街童年》 (PaperShadow:ChinatownChildhood,1999),由于旧金山和温哥华的华人移民状况和作者个人家庭环境的不同,对文化根系的判别和接受也有不同的倾向。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者帕特里夏·褚(Patricia Chu)认为,亚裔美国人的主体性应被视为“两个相互构成的族群之间的辩证法——亚洲的和美国的”[8](P. 6),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反映华裔成年作者对华裔儿童进行跨文化身份建构的设想,并不因为儿童角色年龄较小而将两个族群文化简单整合,而是对其内外的冲突性和协商性给予充分的关注。研究西方华裔儿童文学,需要重视其跨越的两种文化角色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辨析这一文学群落中不同代际和个体在文化身份构建中的联系与区别,不能忽略其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多维度亲缘文学的相因性和异质性比较
“西方华裔儿童文学”这一群落的名称本身包含了多个要素——“西方”“华裔”“儿童文学”,这些限定性或本质性的关键词决定了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一文学群落内部不同国别华裔儿童文学的异同,也需要注意这一文学群落与不同维度上的“亲缘”文学之异同,比如:同处于“西方”的其他亚裔儿童文学、其他族裔儿童文学、主流儿童文学,同属于“华裔”的成人文学,同表现中华文化视野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等。这些亲缘关系有远有近,虽不一定要作分门别类、面面俱到的细致比较,但是为了能更为精确地发现和概括华裔儿童文学性征,最好能将这些相关的亲缘文学纳入视野,哪怕只是隐性的参照。
首先,自然是关注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内部的国别之间的异同。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存在某些共通之处,给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带来某些共同性。但是,由于西方各国的华裔移民历史、对华人移民的政策、社会文化思潮(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华裔社群生存状况以及华裔文学发生发展等方面存在具体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裔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同步、质量并不均衡,其创作思想和题材方面也会有不同方向的选择和不同角度的表现。大体而言,北美地区华裔儿童文学作家和创作数量最大,尤其是美国华裔儿童文学已形成多个代际,自成气候。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华裔儿童文学创作虽然不似北美地区那样蔚然成风,但其华裔儿童文学也充分利用原民族和移居国的文化来进行特色性移植和创造。因此,对于不同国别的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的研究需要放到具体的地理、历史、文化场域中进行细化,在“这一类”中见出“这一个”。此外,还要区分身在西方的华裔作家用西语和中文写作的文化倾向之不同。根据作品所采用的语言和目标读者来区分,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包括两类:一种是长期定居或出生于西方国家的华人作者用居住国语言(主要是英语、法语、德语等)写成,作品在西方国家出版,目标读者为西方儿童(尤其是华裔儿童);另一种是成年后移民至西方国家的华人作者,如程玮、朱奎、张怀存、郁蓉、邹凡凡、梅思繁等更擅长用母语写作,中文作品在中国出版,目标读者是中国儿童。尽管多位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也有意识地进行跨文化叙事,但是与西方土生华裔作家相比较,他们在选择文化对象、文化冲突及其处理策略方面也呈现出各自的侧重。
其次,华裔儿童文学隶属于更大范畴的“亚裔儿童文学”,因此要注意华裔与其他亚裔儿童文学的关系。以美国族裔儿童文学为例,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泛亚运动崛起,亚裔文学开始在美国文坛赢得瞩目,亚裔儿童文学也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与非裔、拉美裔、犹太裔儿童文学并列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亚裔崛起的过程中,无论是亚裔的无心之为,还是美国主流社会与其他族裔的有意为之,亚裔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安置在一起的。”[9](P.3)华裔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它所在的亚裔儿童文学群落息息相关。在亚裔儿童文学中,华裔儿童文学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位居前列,多位华裔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以立足于族裔文化的独到的创作成就跻身于美国主流儿童文学文坛,日裔、韩裔、印裔、菲律宾裔、越南裔等亚裔族群的儿童文学也有一些成就斐然的作家作品。我们需要以比较的方式考察不同亚裔族群的儿童文学生存、发展与传播的轨迹,发现华裔儿童文学在亚裔儿童文学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的互动性或整合性,从政治文化层面去考察华裔儿童文学与其他亚裔儿童文学在对抗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话语霸权中发挥的作用。若再进一步延伸,则可将华裔儿童文学中的身份和地位问题与其他少数族裔儿童文学对此问题的书写相联系,从其他族裔对文化身份的书写经验来识别华裔书写的特质以及可拓展的路向。此外,还可将处于边缘位置的华裔儿童文学与西方国家主流儿童文学相对照,考察西方主流儿童文学对华裔创作存在怎样的影响,华裔书写对主流采取的是迎合、趋附、妥协还是独立、融汇、反叛等立场,又如何确立其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另一个细节性考察点是西方主流儿童文学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由于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中常有偏见与刻板印象,这也渗透进儿童文学,导致了传播中的误导。这个问题在接受西方文化哺育的土生华裔作家的一些创作中也有存在,由于其对中国本土的疏离和中华文化的隔膜,关于中国文化的表现也有失当之处。考辨这一文化真实性问题,可以对文本中偏误的华人文化形象进行“拨乱反正”。
再者,研究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必须要注意其与华裔成人文学之关系。大体上,华裔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华裔成人文学这一环境气候密切相关,有些华裔成人文学作家本身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比如谭恩美(Amy Tan)等,其文化倾向和价值观会贯穿儿童文学。华裔儿童文学与华裔成人文学有一些相通的命题——如对民族文化的开采、再现、重造,对处于中西文化夹缝中的移民身份认同问题的捕捉和表现等,同时二者也存在差异——如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过滤、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程度、对于移民处境的探索维度及解决矛盾的方式与尺度等。比如,二者在对待族裔文化的态度方面,华裔作家在成人文学中主要表现为“眷恋式”或“审视式”,而在儿童文学中则主要表现为“好奇式”和“融通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反映了作家对隐含读者年龄层次的考量。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立足于儿童维度,带来对华裔文化的别有洞天的观察和阐释,在题材、主题、空间、形象、风格等各方面展示了创新的活力。它们聚焦于儿童生活或视角,为华裔文化景观和个体生存状态作了符合儿童认知能力和审美取向的补充,有的还对华裔文化困境提供了带有温和色彩和理想主义性质的解决之道。以华裔角色对于中华食物的态度为例,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7)等华裔成人文学中的子女一代对中式烹饪表现出反感和批判的态度,以此象征代际冲突;但是,林佩思的《丑蔬菜》等儿童文学中的儿童主人公则对传统烹饪更多充满新奇和赞赏。前者的文化冲突具有偏执性和不可调和性,而后者则具有平易性与和解性,因为华裔成人作家常在儿童文学中赋予年幼一代融合双重文化身份的平衡型设想。在与华裔成人文学的比照中,也可以发现华裔儿童文学所没有抵达的文化层面,由此揭示新的发力点。
另一种易被忽略的姻亲关系是西方华裔儿童文学与中国本土儿童文学,二者都表现华人儿童形象和故事,但由于产生作品的文化土壤不同,其共有的中国视野必然会存在异质性。饶芃子指出海外华裔文学因为“背后隐含的不同文化之间交织过程的种种纠葛,具有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形态”[10](P.1-2),西方华裔儿童文学与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区别也是如此。华裔作家在中华传统文化向外位移和流散域外之后,往往糅合西方现代社会文化思想,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和重建,从而在经验呈现、思维方式、文学形态、审美面貌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质地。华裔儿童双重文化身份及需要协调的处境、母族与异国相交织的生存经验虽然具有异域特色,但在剥离这一特殊的空间文化表象之后,也会发现其蕴含的普遍性:华裔儿童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主体成长以较为突出的文化碰撞的背景,映现了儿童在成长中都可能面临的困境。比如,会经历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与冲击,经历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和抗争,经历主体认知的寻找和蜕变等。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兼具文化经验和审美经验的熟悉感与陌生感,以“第三空间”文学来丰富国族儿童文学的文化景观和成长情境。
上面提及多种与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相关的亲缘文学,旨在将华裔儿童文学考察放入多纽带的显性或隐性的参照系,以求通过多层面、多方位的观照,发现其相因性与异质性,达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之效果。
结语
研究多元文化儿童文学的西方学者玛丽亚·玖斯·波特欧(Maria Jose Botelho)和玛莎·卡巴寇·鲁德曼(Masha Kabakow Rudman)对这类文学的功能给出了“镜子、窗户、门”的隐喻:“镜子、窗户、门的隐喻渗透在多元文化儿童文学的学术对话中,通过文学来确认和获得进入自己文化和其他文化的途径。这些都是强有力的隐喻,因为它们假定文学能够真实地照见或反映一个人的生活;透过窗户去看别人的世界;打开门,让人们出入自己的日常生活。镜子邀请自我反省和认同,窗户许可观照别人的生活,门则邀请彼此互动。”[11](P. xiii)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对文化差异性的映照、认知和融合,为不同国族的儿童进行多元文化的阅读与沟通包容,打造了“镜子、窗户和门”,也展示了可能的“道路”。
当今世界的儿童文学正在经历全球化发展的浪潮,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的跨文化和越界性创作反映异质文化如何相处相生,涉及如何帮助儿童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时代性命题。华裔儿童文学作家在多元文化并置的语境中,通过对不同文化宇宙的探索与协调寻找可自洽的精神家园,从而走向文化和艺术的自信。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华裔儿童文学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或可看作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境遇的一种折射。作为东方国家的儿童文学,如何突破西方社会主流文化的覆盖,如何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形象,如何扩展和彰显文化身份,如何融汇基于族裔又超越族裔的主题,如何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共生,如何赢得跨越国族的儿童读者的接受……这些是西方华裔儿童文学所经历的挑战,也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要拓展话语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所面临的挑战。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在文化经验、身份经验、美学经验方面的跨界性探索,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性发展提供了一个窗口。相应地,跨文化和多维度的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研究,具有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独特意义。
注释:
①美国的杨志成、叶祥添、杨谨伦、林佩思等先后获得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加拿大作家余兆昌、插画家陈志昌等获加拿大总督儿童文学奖、温哥华文学奖等,澳大利亚插画家陈志勇(Shaun Tan)获林格伦儿童文学纪念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