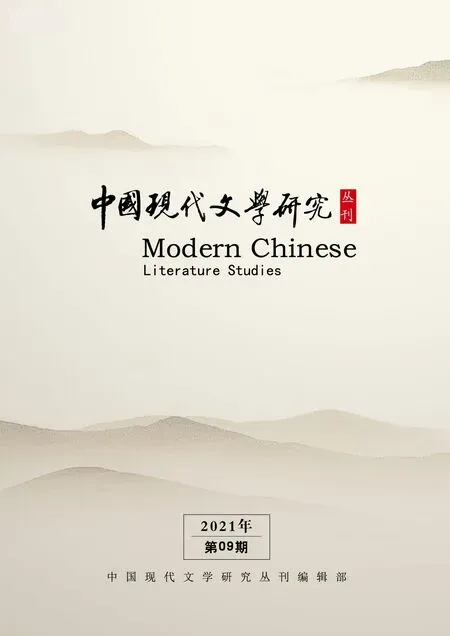近年非虚构女性乡土文学辨析※——以《妇女闲聊录》《中国在梁庄》《生死十日谈》为例
2021-04-17刘婧婧
刘婧婧
内容提要:非虚构女性乡土文学是近年女性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一翼,出现了以《妇女闲聊录》等为代表同时极具争议性的诸多优秀作品。这部分女性文学在写作内容上主要面向当下乡土社会的生存困境与凋敝现实,在写作技巧上打破了传统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界限,在写作情感上趋向日常生活与女性情感诉求。非虚构女性文学创作是近年来乡土社会走向萎缩困顿的真实写照,是女性作家由个人化叙事转向社会化叙事的重要体现,是21世纪女性文学寻求艺术创新与精神高度的成功实践。
新世纪以来,非虚构文学创作日益繁盛,备受关注,愈来愈多的作家开始尝试以去文学化、非想象性的文学表达来关注现实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特别是乡土底层的生存现状。其中女性作家的非虚构创作实绩尤为瞩目。近年的非虚构女性文学是指女性作家以田野调查、实地访问等介入现实的素材采集方式,以将被采访者的口头叙述记录下来的口述实录体为主要文学表达体式,再加以文本叙述人文学的选择、加工、描述而形成的文学性文本创作。近年的非虚构文学创作以口述实录这样的方式使文学呈现出“非虚构”的一面,使其不同于报告文学、回忆录、史传文学等传统的非虚构文学样式,同时由于加入了叙述人的个体论说及其种种情绪感受的表达而呈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也就是说,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界限,一方面,口述实录的部分表现为文本叙事对象——“他(她)说”的极度真实的还原;另一方面,叙事人的叙事动机、行程轨迹、对人物事件的评说辨析与抒情感叹等,又表达出强烈的主观思维与主体情感的介入。这两种叙事内容交错叠至在叙事文本之中,以口述实录的客体叙事来阐述“真实”,以叙事人的主观评判来辅助“真实”,呈现出一种令阅读者“置身其中”的强烈真实感。
当我们观察这些女性作家的口述实录体非虚构文学作品,比如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以及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等时,就会发现她们的叙事对象与叙事内容都更倾向于表达中国当下乡土世界的种种,同时又裹挟着这个世纪资本时代的残酷与清醒,以速写的模式向沉浸在都市梦境里的现代人无情展露出华美衣袍之下趋于幻灭的乡土的“伤疤”。女性作家的非虚构文学与乡土世界的秘密链接是因为什么呢?首先是创作主体的“乡土”身份。这几位女作家都不是农村妇女,真正的农村妇女也不具有自动自我言说的能力,但是她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就是女性作家由乡土身份所带来的与乡土叙事的“同构性”。只有当作家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有天然的亲近的渴望和热情时才能成就她的这部分乡土写作实践。再者,就作品的叙述主体与叙述内容而言,女作家更倾向于对乡村伦理情感、人际关系、日常生活以及命运生死等天地伦常内容的关注与讲述。
《妇女闲聊录》:都市女性的非虚构
在《妇女闲聊录》1的末页,作家林白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战争》与《妇女闲聊录》是有一致性的,前者是我和内心的另外一个自我的对话,是垂直的,后者是我和外界的对话,是横向的。”林白的这句话鲜明地昭示出她自身文学创作的延续性以及199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与21世纪非虚构女性文学叙事的独特关系,或者说,女性非虚构写作的出现是孕育在女性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之中的。这部作品无论是写作文体上的突破(由浪漫自由的散文化写作到琐碎平实的口述实录体的表达),还是叙述视野与叙述主体的转变(由城市女性到乡野村妇),都展现了一种女性文学写作的可能的发展前景。
小说的叙述人是一位来自湖北农村的39岁妇女木珍,小学文化,在北京打工,是在社会底层求生存的卑微的女性。作家林白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离乡村并不遥远,她说自己本就是“边民”,“跟北京相比,北流是荒蛮之地。这种边民的身份就是我生命的底色”2。所以,从多米(《一个人的战争》)到木珍,对林白来讲只是豁然开朗之后的必然结果。当作家向内看,她看到她自己,一个自恋自怜的都市女性;当她向外看,她目光所及之处,她经验范围之内,乡村女性就在那里,等着与她的目光相逢,与她的人生对接。这里的不同在于所述女性主体的身份与阶级不同,这里的相同在于她们都是女性个体,都是蓬勃生长的植物一般自由的生命。1990年代林白的创作被称为“私人化写作”或曰“个人化写作”,这里的“私人”“个人”是相对于1980年代的群体性概念来讲的,是由宏大叙事向个体叙事转变过程中女性得以伸展自我与言说自我的文学实践,个体之中自然包含着“女性个体”的因子,女性个人化写作也因之登上文学表达的舞台。但这种女性个体在当时的创作语境中只集中在知识分子女性自我的身上,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到《妇女闲聊录》,这种“个人化”的概念被延展开来,“她只是把此前的私人生活的‘个人化’悄悄地转换成了民间立场上的‘个人化’,这也是她尊重原生态的王榨生活的原因”3。这部小说作家林白没有出场,她只是将木珍的话语记录整理下来,也没有作任何个人的主观判断与评价。作家祛除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及其主观色彩的判断,让乡村自说自话,让乡村女性自己表达自己。木珍眼中的王榨的世界,在启蒙者与知识者的眼中充满了肮脏、贫穷、愚昧、道德低下、情感混乱等各种负面问题,是让人痛心疾首的没落的乡村景象。但叙述人木珍的讲述眉飞色舞、有滋有味,充满了生活的希望和过日子的情趣,木珍坦然自足地面对着她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
不过林白的叙事依然相当诡谲。乡村女人木珍的讲述,与任何另一个乡村个体对于农村的叙述都会有所差异,每个人所能看到的乡村世界都只能是乡村的一面。林白的叙事显示出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与性别选择,小说中对于男女关系的描写格外密集与浓稠。在女性都市小说中,人们看到都市男女情欲的敞开与关系的混乱;与此相反,古老的乡村,则以相对封闭、落后、凝固的面貌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中;然而木珍的叙述呈现了乡土与都市同样的甚至更加欲望化的男女情爱景观。如果城市的男女关系更多是一种爱情游戏,意味着隐秘的情感猜忌与情感背叛,那么乡村由于年轻人不停外出打工所带来的情感缺失而引起的混乱多角男女关系,则是令人震惊的透明化与公开化。木珍在讲到她身边人甚至是她自己丈夫的情人时,并没有特别的愤怒和嫉妒。基于普遍的人性与男女恋爱心理,木珍的表现是不合常理的,因此这部作品被质疑木珍讲述故事内容的客观性,或者说质疑林白在挑选采访内容时的客观性。但笔者更愿意相信,当下的农村男女情感关系正如木珍所说,在人口流动相对较少、家族亲朋相对集中、传统文化与对女性的道德约束依然残存的乡村,木珍哪怕心中有怨,却也只能泰然处之。当下的乡村确是一个矛盾的、多元的、奇异的存在。木珍的叙述因为不得不带有的个人的某种主观性,也显示出口述实录体乡土小说的限度与存在的问题。
“下笔之前曾经犹豫,是否写成传统的笔记体小说,如《世说新语》那样的。但总觉得,文人笔记小说对词语的提炼,对生活的筛选,对人物的玩味和修整,跟我所要表达的东西有很大不同。”4尽管林白最后选择了口述实录体的方式,但行文依然带有《世说新语》类笔记小说的面影:简约的叙述,叙述内容大量留白,少评论与主观臆断,单个叙事片段中有清晰的人物关系与完整的情节链条。这样的描写透露出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在无言与空白中,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让阅读者去体味感受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生死,显示出尊重生命的自由意识,以及对人世变幻,命运无常的哀痛与慨叹。
尽管在《妇女闲聊录》中不再具有反抗性别秩序的独特意义,林白还是将这种个人的显在叙事方式延续下来:放弃现代小说长篇结构的基本法则,没有中心人物,没有主要矛盾,没有纵横交错的复杂人物关系与逻辑严密的前后事件进展与发展,总之,它并不呈现为现代小说所惯有的独特的网状叙事结构,它的内部结构是松散的、零碎的,是林白个人感性叙事风格在乡土小说写作中的一种外化形式。小说共有218段,每一段都可以单独呈现,与任何另一段做顺序的结构的调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些段是独立的,而每一段的内部又呈现出某种自足的简短的叙事特点,在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叙事中体现出乡土生活的鲜活、跳跃、有趣。将这些片段整合在一起,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这个意义并不仅仅如有论者所言,是文体的革新,它更是对当下乡村生活与生存本质的深刻揭示:后现代的、破碎的、零散的乡村;没有英雄人物、没有整体建构的、看不到未来在哪里的进行式的乡村。至此,女性小说的碎片化叙事不再指向单纯的性别反抗,也指向庸俗琐屑的日常生活本身;不仅指向个人自我的内心情绪与感受,也指向外部世界的零落与苍茫。
《中国在梁庄》:女性学者的非虚构
《妇女闲聊录》是典型的单一女性版本的原生态的口述实录,《中国在梁庄》却是乡村的众生杂语并渲染了作家的主观情感;林白以此实现了自我的写作风格与写作旨趣的转变,梁鸿则实现了一位女学者由“书斋”到“田野”的个人文学经验与生存空间的开拓。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梁鸿作为叙述人深入文本内部,既描绘了她所看到的当下中国古老农村的凋敝荒凉的景象,也对被采访的人物与事件进行了丰富点评与深入分析。前一部分的内容对比《妇女闲聊录》对乡村描述的景观所具有的文学性与审美性,梁鸿的整理记录显得更加客观纯粹,也更加偏向社会田野调查。后一部分的叙述情感汁液饱满、主体乡愁浓郁、思想表达也端正平和,它如同口述实录的校订与释义,成为整部作品中的独特存在。“很明显,‘梁庄系列’是一种跨界写作。它非报告文学,非社会学调查,亦非作为一种类型的‘非虚构’小说。它可视为作家写的乡村社会调查;或者一个学者的返乡心路记述。”5这种跨文体写作补充与丰富了当下非虚构女性文学的写作类别与表现形态,是一次成功的跨界文学实践。
带着“故乡的女儿”忧郁的乡愁、带着人文学者理性的思考、带着为当代乡村立传的“宏愿”,作家讲述了“我”的家乡梁庄及梁庄人的生存现状。“中国在梁庄”意味着在当下的中国一个小小的村庄实际上蕴含并折射着一个时代的农村景象与农民境况。在“我”看来这样一种生存现状并不乐观。面对荒凉凋敝的乡村,作者的整个行文风格冷静理智,不过内心的叹息哀婉之情已溢于笔端。
“‘在场’不仅是作家创作的一种态度,更带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即他们往往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他们是带着明确的主观意愿介入社会现实生活,去对某一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的。作家们开始主动去参与行动计划,之后成为行走的个体,亲自介入,有的还会对事件发展产生影响。”6作为从小小的乡村走出去的乡村的女儿,作者的“归来”“在场”及其“影响”就转变为一种“乡愁”。一个游子对故乡的依恋之情,因为曾经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乡村世界已面目全非而转化为所谓的“乡愁”。“乡愁”是很多批评者在面对梁鸿的这部作品时所使用的关键词,批评家张莉坦言:“乡愁于《中国在梁庄》是一把双刃剑,没有乡愁,就没有这部作品的诞生,也没有这部作品的广受欢迎。事实上,许多读者在这样的乡愁中感受到某种亲切。但是,这种乡愁也遮蔽了其他一些东西。”7从鲁迅的《故乡》开始,“乡愁”就必然成为现代化之后现代人返归自我的一种情感吁求,乡村既是我的物质的乡村,也是我的精神的家园。乡村是自我的折射,更是一个他者,作家梁鸿的“乡愁”自始至终地存在着,哪怕作为学者的她那样执着、锐利、笃定,面对破败的乡村景象与落寞的村民生活形态可以刀削斧辟、抽丝剥茧探得生活的真相,这也不能丝毫减弱并泯灭她日渐浓重的“乡愁”。可能梁鸿并未想把乡愁作为讲述的方法,作为学者的她可以有更多“高、精、尖”的方法,但无形之中,乡愁左右了她,使其主体叙述与人物自述都带有了某种柔美的黯淡的气息,这削弱了她学者的中性特质,女性色彩得到渲染,使其更似一个情感丰富的“乡村的女儿”。
令她忧伤也令她愤怒的不只是割裂大地的公路、黑暗可怕的河流,更有梁庄无数因为现代社会发展而被抛弃的人们,这是无数孤独而痛苦的灵魂,对他们灵魂与血脉的触摸让作家找到了“乡愁”的根本所在,或者说凭着一个女性对于熟悉的乡村的怜悯与体恤,她看到了那些让她忧愁的活生生的个体。杀死并强奸了82岁老太的高中生王家少年,“我”以女性的温柔也以学者的人文视角,看到了“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生活的寂寞”对少年潜在的致命的伤害。“我”也质疑自己漠视了82岁老太的行将就木的生命,是对不同生命评价的价值偏颇。“我”审视我自己,“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最后“我”在监狱里见到了还未被判决的王家少年,但是我什么也没有问,我觉得自己的问题苍白无力。有论者认为这是知识者启蒙者面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无力包括交流的困难与障碍,在笔者看来,“我”的苍白无力蕴含了一种无言的悲伤,是对这些在孤独与无爱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命运的痛惜与叹息。毫无疑问,在面对衰败的乡村时,由于“乡愁”的驱使,作家选择了更多的“老弱病残”作为她叙述的主要人物。对于这些乡村边缘人物的描述,使作家看到了乡村在现代化变迁中的“爱”与“痛”,对这些柔弱生命的关怀,也让作品呈现出某种隐在的性别叙事的母性情怀。从纯朴的乡村对话到理性的问题分析再到动人的情感抒发,作家在作品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小说从“乡愁”开始也到“乡愁”结束,氤氲在整个梁庄上空的忧郁的乡愁一直挥散不去,构成了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叙事肌理。
《生死十日谈》:乡土女性的非虚构
与林白、梁鸿等女性作家的自我转型或自我突破不同,孙惠芬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孙惠芬成长于辽南农村的广袤土地之上,后因写作离开辽南农村并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不过作家没有因为离开乡土而放弃乡土书写,在其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朴实、真诚、自然都来自乡土的养育。歇马山庄、翁古城、青堆子湾等都成为她小说中的经典地标与象征,翁月月、买子、申吉宽、刘立功、翁秀珠等也都成为她塑造的当代乡村经典农民形象。因而,无论从个人身份还是书写主题来讲,孙惠芬都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作家。作为农民作家,在关注当下乡村的种种情状时孙惠芬不会带有“惊喜的发现”或者“痛心的乡愁”等审美的距离或批判的眼光,孙惠芬面对乡村书写乡村就是在不停地面对自我书写自我,这里会有更加浓郁的情感投射以及更加贴合的情感认同。正因此,我们很难将孙惠芬与“非虚构写作”联系在一起,毕竟作家在面对更加陌生的或者强烈的需要被描述的对象与事物时才更愿意采用非虚构的方式,更何况非虚构作品要求具有更加客观理性的文学表达方式,这与孙惠芬一贯的写作风格也迥然不同。《生死十日谈》对于孙惠芬的个人创作来讲,是艺术表达上的创新与探索,对于农村自杀死亡现状的调查这一主题也表明当下社会对于农村以及农村人生存困境的聚焦,迫切的社会责任感与农村代言人的使命意识使作家更愿意采用这样一种淡化文学修辞的表达方式。
《生死十日谈》以作家在辽南农村十天的社会实地调查作为基本叙述背景,聚焦农村的自杀死亡事件,对死亡者家属、亲人以及邻居等进行深入采访与交流,还原自杀事件本来面目,探究自杀个体行为的心理缘由与生存曲折,以期引发更多社会关注与人类思考。《生死十日谈》的非虚构写作方式相较于林白的单一主体叙事,更接近于梁鸿的写作模式,将“我”的采访过程与人物的自我表述都铺陈于文本之中,构造一种独特的对话模式,营造一种访谈的氛围。不过与梁鸿的写作不同,孙惠芬的问与答、“我”与“他”之间并没有非常明显与清晰的界限,《中国在梁庄》中,他者言说都是以不同字体单独显现出来的,以期区别于“我”的阐述。孙惠芬的写作方式,模糊了创作主体的尖锐视角,主体“我”与客体“他”在文本中获得了更好的融合与交流,人物的自我表达都以加引号的话语方式自然呈现,在故事的讲述之外虽然也充满了主体“我”的种种慨叹与惋惜,但并不存在跳脱的说教与刻意的解读。这样一种叙事方式的呈现使得《生死十日谈》的文本整体风格统一,作为非虚构文学的文体探索意味更加浓厚。
不过与浑然天成、温文敦厚的叙事风格不同,《生死十日谈》的文本主题较为尖锐夸张:聚焦农村自杀死亡事件。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中的死亡事件更多被赋予文化以及象征意义不同,非虚构小说中的死亡事件更多指向对于当下农村政治权力遮蔽、经济境况不佳、价值观念转变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结构失衡等问题的揭露。孙惠芬作为一位熟稔农村生活的女性作家,显示出她对于当下农村愈演愈烈的各类死亡事件的独特叙事角度与解读方式:放弃对各种抽象的农村实体与所谓的事件因素的想象以及可能的对号入座,而是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还原死亡者的个体生存环境、亲属的各种亲疏关系以及其中错综复杂的家庭纠葛。也就是说作家更愿意从家庭伦常的角度来考量农村死亡事件的种种是是非非,将宏大的严肃的农村死亡主题的调查化解为一个个生动的人生故事,并依靠文学的想象去填补去追寻人物可能经历的百般人生滋味,所以孙惠芬的非虚构文学写作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拟想以及隐在的虚构情节,加之作家行云流水般的叙事与朴实真诚的诉说,这些都显得合情合理、熨帖人心,引导阅读者对于农村自杀死亡者有更多的理解、亲近与同情、怜悯。或者说,只有如此,“在写作中,事物的细节、幽暗面、矛盾处才有可能变得可见,乃至刺目,进而催人深思与行动”。那么,“如何为看不见的、难以名状甚至转瞬即逝的不公正状况赋形?如何捕捉、理解和呈现那千丝万缕的(无)意识状态呢?”8
在孙惠芬笔下,由于道德约束或金钱绑架,由于自我的个人需求与大的家庭责任的冲突,更由于根本无法改善的贫穷与无法获得良好疏通的情感淤积,带来种种的人生悲剧。农村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小人物们,怀揣着自己小小的人生希望与梦想,却被残酷的现实挤压而扭曲变形,在一次次的隐忍负重,一次次的委曲求全之后,便是无法继续前行的绝望、后撤、放弃、离开。微小如尘土的生命实则拥有过丰富而灿烂的心灵世界,只是如烟花般转瞬即逝了,只空留遗憾和叹息。作家无意于写一本女性的悲歌,女性人物却从她的文本中鲜明地跳脱出来让人惊叹,或许无形之中,“女性”仍然是作家打开通往乡村苦难与伦常诉说的一把钥匙,经由她们,无数的人生画卷才得以展开,得以获得人们的关注与聚焦。
《生死十日谈》的整体叙事风格,没有《中国在梁庄》的凌厉尖锐,也没有《妇女闲聊录》的肆意洒脱,它更趋平实质朴。由于叙事人的主体意识与情感表达较为温婉细腻,对农村自杀事件的剖析也是娓娓道来,这些都使作品的呈现更倾向日常生活的摹写与伦理道德的思考。不足之处在于作家对待事件与人物的观察距离过近,情感认同过于强烈,导致其主体精神走向并不明晰,在这里看不到显著的批判,也看不到积极的救赎,只有面对农村人苦难生存现状的无尽的哀伤与愁绪。在非虚构女性文学创作中,在葆有女性的文学审美与生命认知的同时,如何提升自我的精神高度与确立自我的精神追求,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注释:
1 林白:《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2 林白:《生命热情何在——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3 徐则臣:《小说、世界和女作家林白——评〈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
4 林白:《低于大地——关于〈妇女闲聊录〉》,《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5 叶君:《非虚构以及“看与被看”——论“梁庄系列”的叙述策略》,《文艺评论》2015年第5期。
6 彭恬静:《“非虚构”的兴起与当代散文的新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
7 张莉:《非虚构写作与想象乡土中国的方法——以〈妇女闲聊录〉、〈中国在梁庄〉为例》,《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8 李静:《那刺目的清醒——“新女性写作”的当代价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