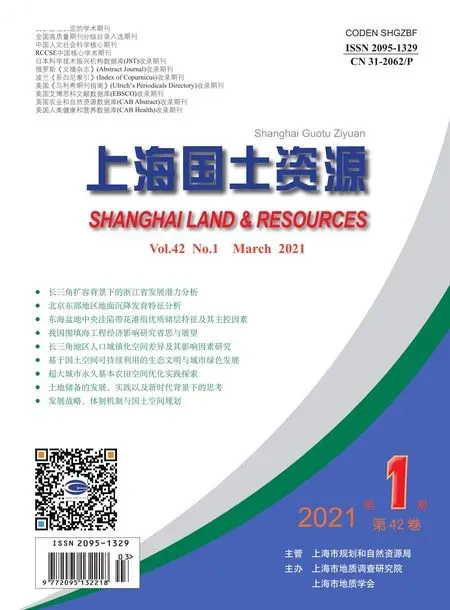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视角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研究
2021-04-16张小东韩昊英
张小东,韩昊英,陈 宇
(1. 塔里木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新疆·阿拉尔 843300;2. 浙江大学城乡规划理论与技术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58;3. 新疆南疆人居环境研究所,新疆·阿拉尔 843300)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在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中央2019年18号文件要求,在2025年之前国家要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的、完善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系统,并建立完整的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制度。可见,国土用途管制体系的构建是制度建立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在国土空间规划的限制条件和用途限定前提下,对全域的土地、水域和林草等资源进行开发建设、用途变更和保护利用等环节进行监管,其主要依据为国土空间规划,主要手段为具体的管控方式。由于目前国土空间尚未有效建立和实施统一的用途管制体系,一些地方因缺少对林地、山地、海域等空间进行有效的管控手段,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耕地减少、生产空间紧张等城市问题出现[2],严重影响了国土空间可持续利用。为了能高效的监管国土空间保护和开发,必须改变被割裂的单一空间用途管制手段,探索构建出全域、全类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1 国内外实践探索研究
1.1 国外实践探索
空间规划最早起源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早在20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Hettner就提出把区域当做一个整体系统来看待,通过地理区划将全国划分为多个相互关联的区域,对区域间进行整体的空间管制[3]。二战后,后工业时代到来,世界各国开始进行空间规划体系变革,空间规划变革也逐渐引起了国际规划界的重视[4]。于1960年代开始,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空间用途管制探索。
日本作为亚洲较早开展空间规划的发达国家,早在1919年和1950年就分别制定了《城市规划法》和《国土综合开发法》[5],规定了全国、都府县、地方和特定区域的综合开发计划。随着区域协调发展的形成和土地用途管制的细化,日本于1968年对1919年的《城市规划法》进行修订,以解决战后日本城市无序蔓延的现象[6],实行的是“三区”管控手段,即“市街化区域、调整区域和限建区”三个管控区,“三区”只要审批通过,将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7]。在城市规划法修订过程,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出了城市化控制地区和城市化促进地区细化管控制度,即“划线制度”,深入细化了土地利用分区管控,并引入容积率作为控制指标[8]。伴随着划线制度推行,各级间政府的博弈导致划线制度淡化了“优先开发”和“严格保护”两项控制内容,弱化了对小面积地块的管制[9],反而促进了小规模开发及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高密度化,部分地区的城市问题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日本控制城市蔓延失败。随后,日本于1974年颁布了《国土利用计划法》,进一步细化各层级政府的土地管控细则,革新“划线制度”控制城市快速扩张。随着日本进入快速老龄化的国家行列,日本于2005年颁布的《国土形成计划法》[10]明确了国家和地方的分工合作和责权范围,要求国家和地方需要编制土地形成、利用及整备的全过程计划,再次细化了空间管控划线体系。并提出由“粗狂增量”发展模式转向“存量提质”发展模式,以应对少子、过度老年化社会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也制定了《海岸法》《景观法》等相关法规,以保障森林地区、自然公园地区、海岸带控制线、景观规划区域等土地用途管制措施落实到各层级规划,也规避了政府之间的博弈弱化“划线制度”落实的问题,保障规划层级、规划内容之间的衔接和过渡。
此外,荷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始于1960年,以战略性、实用性和管制性著称[11],其战略性和控制性主要体现在“绿心”控制,实用性体现在分层级规划理论和相应的分区、分类、控制线等技术手段[12]。新加坡于1971年开始编制覆盖全域的“三区一线”的概念规划用于空间管制分区,通过划定建设用地区、开敞区、发展预留区和交通廊道来管控、引导城镇空间发展[13];巴西实行“五区”空间管控手段,划定疏散发展地区、控制膨胀地区、积极发展地区、待开发区和生态保护区对区域进行全覆盖空间管制[14]。纵观发达国家的空间管制理念,国外空间规划管控具有较强的整体性、战略性和协调性,以保障城镇可持续发展[15]。主要以“区划”为主,控制线为辅,地方具有较强的自治空间,在不违反上一级区划的前提下,每个地方可根据自己的空间管控需求制定空间用途管控线细则。
1.2 国内实践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空间规划的雏形是为了完成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所确定的发展目标而编制的经济区划和重点项目建设的空间规划[16]。1978年改革开放实施之后,国家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变[17],空间规划的管制体系作为粗犷的土地定价技术应运而生。主要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初步探索阶段(1986年以前):早在1920年左右,中国相继开展了上海都市计划、南京首都计划等一系列规划活动[18],在这一时期,城市主要发展建筑空间,城市规划关注的对象也只局限于建筑空间,无法从总体上满足城乡融合发展的需求,城市规划与城乡建设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之间仍出现了脱节现象[19]。初步探索期,空间管控手段主要以区划为主。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从单一自然要素视角出发对区域进行分区划定,如黄秉维的植被区划、李承三的地形区划等[20]。随着城镇高密度发展,单一的区划无法满足城镇精细化管理诉求,用地红线从区划管控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形成了控制线体系。
持续发展阶段(1986~2000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集体土地“分田到户”解放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促使中国“世界工厂”的形成,这个发展过程导致土地的需求剧增,大量耕地被吞噬侵占,突破了原总规的管控指标,国家也意识到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尤其是耕地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国家于1986年颁布了《土地管理法》,编制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防止城镇空间过渡扩张,保护耕地[21],划定了相应的耕地保护红线。城市空间扩张加速,分区规划和用地分类管控手段的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持续发展期,为了解决用地指标管控、土地分类、耕地红线划定等核心问题,出现了耕地保护红线、用地红线等控制线,控制线体系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混乱调整阶段(2000~2013年):城镇快速扩张,城镇空间越来越紧张。从2001年开始,国土资源部开始了城镇空间规划,空间规划逐渐成为政府开展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引起了其他只注重发展规划、不注重空间规划的行政部门开始编制自己领域的空间规划,从而引起了规划管理部门对空间规划归属的争夺,各部门竞相为管辖内容制定属于自己的分区、分类和控制线(表1)。主要表现在建设部、发改委和国土部三个部门都在开展相似的空间规划[22],导致土地利用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等主要规划之间的土地用途管控逻辑关系开始变得复杂混乱,空间用途管制进入混乱时期,主要体现各部门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分区、分类和控制线标准。在划定过程缺乏部门之间的沟通,各自按照自己的管理方式进行划定,最终导致了划定内容、划定范围、管控要求等内容完全不一致。

表1 各部委空间分区管制Table 1 Space zoning control of different ministries
变革转型阶段(2013~2019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为了满足地方管理需要,住建系统对“城市五线”内容进行了扩充,例如,青岛市提出了“城市七线”管控体系,以保障全域空间规划正常运行[23]。不论是住建的用途管制系统,还是其它规划的管制系统,仍暴露出了横向管控目标差异大、纵向管控规模各说各话、管控标准不统一等问题[24]。而空间规划作为社会利益分配工具、公平权益载体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被重视[25]。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建设[26],在201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划定“三生空间”边界,完善国土资源监管体系,统一行使对全域国土空间资源监督管理的职责[27]。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各地需要完成永久基本农田等三条基本管控线的划定工作,会议还强调为了保障国家顶层设计落实到位,需要建立完整的用途管制传导系统[28],强化空间规划管控[29]。国内规划系统开始对新空间规划管控系统进行了实践探索,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相继开展了“三区三线”的划定试点工作,都提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区、线”管控体系。
综上,国内外空间管制手段主要可归纳为四类:分区管制、用途分类管制、控制线管制、指标管制[30]。规划分区和政策指标管制更侧重人的主观认识视角,将人的、抽象的、政治的认知结果落实到土地管理中,其规划成果的管制力度弹性更大;而规划用途分类和控制线管控的对象是客观认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人对自然资源本质的、具体的、物质的认知[31],其规划成果变更的弹性空间较小,更侧重刚性管理实施。而各管控措施往往属于不同的行政部门、不同的规划体系、不同的政策体系,进而在管控实施过程中,导致不同行政部门、不同规划体系和不同政策体系之间的博弈。最终博弈的结果导致空间用途管制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出现。因此,如何构建一套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统一空间用途管制成为了亟待探索研究的问题。
2 浙江国土空间规划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2.1 全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基于对国内外空间管制手段进行梳理研究,本研究结合分区、指标、地类、控制线四种管控措施,构建了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体系(图1),形成了弹性管控与刚性管制协调推进的空间用途管制框架,其中,弹性管控手段主要包括指标和区划管制,指标和区划作为顶层政策设计的载体,具有较强的政策引导作用,政府可以划定相应的主体功能区和分解指标来实现政策制度的落实;并对地类和控制线的划定、管控提供政策法规依据,进一步保障了上级政策意图执行到位,故地类与控制线更侧重政策意图执行,可以作为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刚性管控手段。

图1 浙江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Fig.1 The land and space use control system of Zhejiang province
全省按照“空间不重叠、边界可确定、管控有依据”的基本管控原则,并结合国家“三区三线”的划定成果,将分区管制分为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定、市级一级规划分区、县级二级规划分区三个层级,并与相应的市县级用地分类相衔接,以保障区划规划得到进一步传导和执行。其中,将市县域空间分为“生态保护区”“城镇发展区”“农业与农村发展区”和“海洋保护与利用区”四类一级规划分区;“生态保护红线区”(禁止建设区)、“生态保护控制区(限制建设区)”、“一般生态保护区(限制建设区)”等13个二级用途分区;结合13个二级分区,制定了基本农田、一般农田、特色种植园地、生态林地、住宅用地等24个一级地类,86个二级地类,113个三级地类。逐级细化用地用途,直到用地用途出现唯一为止。最终形成了分区管制与地类管制的融合衔接,也表征着政策制度到实施落地的过程。为了进一步落实强制用途管控,建立了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控制线体系,全省构建了“3+6+5”的控制线体系[32],由“国家基础三线+省级特色三线、市级特色三线+传承五线”组成。其中:国家基础三线为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省级特色三线由防止城市蔓延的都市区绿线、优化区域设施建设的区域基础设施走廊控制线、对特定区域进行特定意图保护的文化景观线组成;市级特色三线由保障工业用地合理布局的产业区块控制线、盘活存量的低效用地控制线和控制增量的近期增量建设用地控制线组成;道路红线、城市黄线、城市紫线、城市蓝线、城市绿线组成了传承五线。总之,构建了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控制线体系。控制线体系与用地分区分类在用途管制过程形成了弹性和刚性管控互补局面,进一步为全省的空间用途管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管控手段。
2.2 全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传导体系
(1)边界坐标传导
随着全域精细化管控要求越来越高,浙江省提出全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需要划定详细管控的边界,并统一坐标系,以明确用地分区、土地分类、控制线的边界坐标。在向下的管控传导过程中,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需要严格执行上一级政府划定的边界坐标,逐级向下传导管控边界,且需要保持坐标不变。各级政府在加入新管控边界的时候需要避让上一级政府核定的管控边界,尽量避免新划定的边界线与已有管控边界出现覆盖、交叉重叠等现象,导致管控内容重叠、事权不清等问题出现。最终形成“至上向下”的强制性管控传导模式。
(2)名录分解传导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空间管制措施在制定过程中,编制人员发现并不是所有空间用途管制措施都能在国家、省域或者市(县)域层面进行边界划定,国家、省域、市域等层面的规划图纸比例较大,较小面积的图斑在图纸上只能看到一个点。需要国家、省域等层面通过指标清单的方式进行管控传导。例如,文化景观线除了需要划定跨行政区域的特色风貌区外,也包含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景观区域,图斑相对来说较小,不宜在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图纸中表达,需要附相应的特色景观控制区域名录,名录需要明确特色景观区的面积大小、地理位置、保护类型等要素,以便向市县级规划进行指标传导。其余无法图示化划定的用途管控边界也可以参考相同方式,制定名录分解相应的指标,并给下一级的划定工作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该弹性空间也为满足各地发展述求的“自下而上”申请留有余地,形成下级校对划定,上级根据指标目录审核的“自下而上”的弹性划定模式。
(3)政策制度传导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划定、实施、监督都需要配套相应的政策制度,政策制度作为“刚性”与“弹性”管控传导模式“上下联动”的纽带,需遵循“节约优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自然恢复”管控政策导向,推动国土空间由规模驱动向存量挖潜、流量增效、质量提高转变。在空间管控政策设计时需要注意强化空间管制政策的协同作用,促使中央、省、市、县、乡镇、村等部门在土地用途管控范围划定、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协同发力,捋顺与其他区域政策的优先次序;并抓住与空间用途管制政策相关的关键政策,如财政、投资、产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政策,并制定绩效考核、生态补偿制度,以建立较完善的国土空间管理制度体系,来保障城镇化地区优化发展,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发挥市场能动作用。
(4)管控方式传导体系
结合名录分解、边界坐标、政策制度三种空间管制传导方法,对空间管制手段在“五级”规划体系内的管控传导方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表3)。明确了各层级政府在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需要编制相应空间管控传导成果。从各级政府需要编制的空间管制传导成果来看,国家和省级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宏观政策导向、明确城镇发展方向、划定省域主体功能区和部分重要控制线;市级政府作为土地分区分类、控制线划定和管控传导的关键层级,其主要任务是根据上级政府要求落实、划实各条空间管制范围,以指导县级行政部门继续深入空间管控。乡镇、村级政府作为管控传导的最后一级,也是管控体系实施落地的主战场,乡镇、村级政府应该严格划定相应边界和执行其管控规则,以保障国土空间规划正在落实到位,完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表3 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的管控传导方式Table 3 The control transmission mode of space use control system
3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措施编制的逻辑关系
基于上述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的构建与传导逻辑,结合当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分级需求,从国土空间规划分层级编制视角出发,文章制定了浙江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措施的划定和分解逻辑(图2),并对省、市、县和乡镇级的空间管控措施进行图示化。

图2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措施的实践划定逻辑关系Fig.2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practice delimitation of land and space use control measures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划定各市级单位的主体功能区、分解国家指标、划定省级控制线,省级需要深入细化国家级主体功能区划,落实国家级分区,划定“基础三线”,因地制宜划定“特色三线”,落实省级“刚性”管控内容,无法图示化的功能区和控制线可以用名录逐级分解指标的方式表达。省级政府落实上级政府政策制度的同时,需要制定相应政策制度指导、审核、监督下级政府编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划。
市级承上启下,对省级空间用途管制措施进行衔接的基础上,需要细化规划分区至一级规划分区、分解省级给定的指标名录、加入市级控制线,划定城镇、农业、生态、历史文化等基本功能区范围,并与控制线管控范围协调划定,保持“只增不减”的传导原则,在省级传导要求下落实划定的“基础三线”和“省级三线”;划定一级地类,衔接上一级规划分区的主要管控对象。不能划定的也可以采用点结合名录的方式向下传导,市级政府落实上级政府政策制度的同时,需要制定相应政策制度指导、审核、监督下级政府编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划。
县级做法与市级类似,在市级用途管制的基础进一步深化落实,保持“只增不减”的传导原则,对用途管制区和控制线精准落地。最终在乡镇层面落实到图纸上,所有空间用途管制措施在乡镇层级需要落实到具体管控边界和坐标。若部分空间管控要素或指标无法落地,可以按照相反的分解逻辑去校对每个层级的规划成果。形成自下到上的校对体系和从上往下的分解逻辑协调配合的规划模式。在落实顶层设计的同时,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述求。创造性的把土规“一步到位”的强制性传导模式和城规“过于寻求技术理性”的弹性管控模式结合在一起,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土地管制提供可行性依据。也保障了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空间管控的传导机制兼具“刚性”与“弹性”。提高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效率和可操作空间。
综上,分区、地类、控制线、指标四个土地用途管制措施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其中,指标一直处于分解状态,直到乡镇级;控制线呈现出一直增加的状态,且顶层控制线逐级传导到乡镇级不改变,再次体现出控制线的“刚性管控”特性;而分区管制在市县层面逐渐向市县层面的用地分类转化,呈现出政策意图的“区域管控”向土地用途的“要素管控”转变特征。
4 结论与讨论
国内各个规划体系都拥有自成体系的空间用途管制手段,随着规划管理职能部门的整合,相应的用途管制体系也需要整合,文章将原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区域规划等规划系统的土地用途管制手段进行整合,扬长避短,构建了新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得到如下结论:
(1)通过梳理总结国内外用途管制措施发展历程,提出了由指标控制、分区管制、地类管制和控制线管控组成的全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2)总结出边界坐标传导、名录分解传导、政策制度传导三种传导方式,提出了“自上而下”的刚性管控传导模式、“自下而上”的弹性划定校准模式和政策制度作为“上下联动”纽带的三类管控传导模式,形成反馈机制完善的闭环控制系统,构建了全省空间用途管制措施在国家、省、市、县、乡镇村五级规划中的管控传导理论框架;
(3)结合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述求,明确了全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措施之间的编制逻辑关系,以保障本研究提出的管制体系的实操性,以期为全省规划编制提供系统性的参考依据。
为进一步保障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的可操作性,建议将其纳入到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指南中,以保障其权威地位和严肃性,并指导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当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庞杂,本研究主要从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视角出发提出全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框架构想,以满足当下规划编制、审批、实施和项目审批的现实需求。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边界坐标传导和名录分解传导已经有较多实践探索,而针对政策制度传导方式的研究还尚不足,这也将是文章接下来需要研究的地方。
感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组成员以及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课题组的李艳教授、彭亦松博士、朱斯斯博士等提供宝贵修改建议!